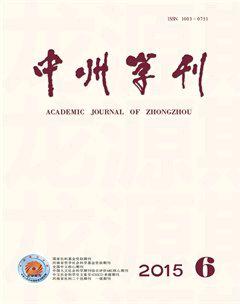知情同意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介入:问题与出路*
2015-07-22陈化
陈 化
知情同意①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从《纽伦堡法典》到《赫尔辛基宣言》,交织着人们对系列医学丑闻的拷问与反思,伴随自主权理念被广泛接受,知情同意获得了在生命伦理学领域的合法性,并成为开展临床实践与医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发轫于西方社会的知情同意,进入我国视野已有三十余载。然而基于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差异,制度建设赖以存在的土壤培育不足,知情同意在国内的实践呈现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尽管在形式上按照相关程序履行告知义务,手术要求签字等,但是与“尊重个体权利”的价值诉求相去甚远。不管是轰动一时的“李丽云”悲剧,抑或是引发学界热议的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均暴露了知情同意在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的尴尬。它们蕴含的深刻意蕴表明,知情同意在中国土壤里并未完全落地生根,目前达成的普遍共识更多滞留于形式,对其理论基础等实质内容有不同的解读与阐发。为此,有必要全面考察与系统梳理知情同意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廓清人们的认识迷雾,从而为破解其“中国式”困境提供参考意见。
一、知情同意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介入
改革开放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知情同意作为重要的医学人文理念受到我国学者关注,并逐渐升温。西方医疗卫生制度的引入与社会对患者信任的不足,推动了知情同意制度的萌芽与被认可。
纵观知情同意在中国临床实践中的演变,经历了从“简单同意”到“知情同意”的过程。在“简单同意”模式下,治疗常限于“或有或无”两种选择,患者知情权阙如。换言之,起初的知情同意是拒绝将患者权利纳入考察视野的,而是作为一项促进医疗目标达成的措施。1982年,卫生部颁布的《医院工作制度》规定:实施手术前必须有病员家属或单位签字同意。这种规制基于保护医生与医院的价值诉求,而非出于对患者权利的尊重。1986年,卫生部、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告》规定:任何个人未经院方许可,不得私自翻阅、索要、涂改、毁损病历及其他医疗文件。1988年,卫生部发布的《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规定:病人所在单位、病人、家属、事故当事人及其家属不予调阅病历。囿于时代特征、社会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当时对于知情同意制度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对于患者自主权存有戒心,并未赋予其独立的权威性,但它已经具有知情同意制度的雏形。当然,它残留了医疗父权主义模式太多的痕迹,对于患者权利并不重视。
伴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医患纠纷日趋增多,传统的医疗父权主义模式难以为继,患者知情权的合法身份逐步得到承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执业医师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医生的告知义务。在当时社会语境下,患者知情权以消极权利的形态出现,即并不是像美国《病人权利法案》一样以成文的形式明确规定病人知情同意权,而是通过规定医师的告知义务而确保患者知情权的实现。然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叠加着知情同意实践的社会准备的匮乏,导致社会对知情同意概念完整性认知不足。在21世纪前,我国涉及知情同意的司法判例极少,即使患者以知情同意权被侵犯为由起诉,法院亦判令医方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判决依据并非侵权,而是借助《民法通则》的规定,认为医生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切除脏器,侵犯了病人对自己“物”的权利,故应承担民事责任。②
由于患者权利意识的日益强化,涉及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案件迅速增加,社会对医患关系、患者权利的认知趋向理性。同时,全球性的生命伦理文献如《赫尔辛基宣言》,多次修缮知情同意的规定,细化其实施程序与要求。国家与社会需要对知情同意权利做出积极回应,政府颁布诸多法律文件对知情同意权进行规范,使其从消极权利升华为积极权利。《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病例书写基本规范(试行)》分别规定了患方对“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的知情权与接受“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的同意权。《侵权责任法》承认了患者个体作为权利主体的优先性,并补充了“医疗风险”与“替代医疗方案”的信息揭示要求。如果不告知替代疗法,导致患者身体受损也需承担责任。《精神卫生法》的实施对精神障碍者的知情同意权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制,对保障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指导。这些文件与规范的颁布,标志着简单同意历史的终结,呼唤着知情同意新时代的开启。尽管与本真意义上的知情同意存在差距,但也应该看到,知情同意在我国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
综上所述,知情同意在我国从引入到规制的进程整合了国际生命伦理的文献基本精神与我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是,由于原初意义上的知情同意内生于西方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而我国在文化土壤、社会环境、伦理理念等方面均与西方存在差异,这决定了知情同意在中国的实践必然呈现出特殊性。
二、知情同意在中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知情同意在中国的演绎与流变,时间短暂但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告知与同意为主要内容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知情同意制度。然而,在中国医疗领域,知情同意实践深深烙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痕,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之间的鸿沟造成了知情同意理论诉求与中国实践的价值断裂。
1.主体间性凸显为信息告知的“权威主义”
主体间性是主体存在结构中的“他性”,一种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范畴内的主体间相互联系并具有平等地位,同时保持各自的特性与彼此差异的张力,彰显了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交往、沟通、对话与理解。知情同意颠覆并解构传统医疗模式中医生的单一主体性,凸显了患者在医疗实践中的自主性。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医生与患者均以主体性身份参与医疗关系,医患间的统一性构成了知情同意的主体间性。从信息告知到理性决策整个过程,均彰显了医患双方平等的主体性。但是在中国当下的医疗实践中,医患关系呈现为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特征——权威主义。医患关系的权威主义范式表明,它既非传统中的家长主义模式,亦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模式。
在漫长的医学历史长河中,医患关系表现为医疗家长主义模式。医务人员以提升患者福祉或保护患者免受伤害为专业伦理之首要考量,甚至违背患者意愿而干预其选择。这种模式的可辩护性基于:第一,医务人员承载的专业性知识,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第二,行善是医学伦理的古老传统,医务人员应当尽可能地维系患者的健康福祉而避免不利于患者健康的选择。家长主义模式下,医生处于绝对权威地位,而患者只能服从,医患世界是“沉默的”,但是医生必须履行治病救人的社会责任。知情同意的横空出世瓦解了医务人员在医疗领域中的绝对权威,抛弃了医患不平等的理念,树立并接受了民主平等的价值观。易言之,在知情同意模式下,医患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并彼此信任。
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家长式医疗观念并未完全抛弃,新的价值体系正在建构,而权威主义正是道德真空阶段医患关系呈现的一种范式。一方面,“医疗父权主义”思维对于医务人员的影响较深,部分医务人员缺乏对患者权利的尊重。医患信任资源不足,部分医务人员在功利主义的推动下,以治疗或研究为目的,忽视病人的知情同意权,甚至不惜采取欺骗、诱骗、隐瞒等不道德方式。从患者维度来看,患者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不少患者依然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未能真正意识到权利的内在价值,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知情同意的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对于患者自主权的绝对保护并未得到法律认可”③。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公民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但是国民并未全面接受权利教育,权利意识与自主观念淡薄,国民并未真正成为“公民”。这种境遇下,医患双方对于医务人员权威还具有依赖性,距离民主平等的医患关系模式亦有距离。医患关系的特殊性导致知情同意实践出现由传统的“沉默”向现代的“沟通交流”模式过渡。
2.决策主体表现为知情同意的家庭主义范式
发端于西方个体文化的知情同意,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践表现为家庭主义范式。家庭作为知情的主体,做出临床决策,并由家属代表在知情同意书签字授权。家庭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参与知情同意的全过程,并承担知情同意过程中的绝大部分义务,从而遮蔽了病人作为知情同意主体的角色。医生首先要告知家属相关病情,病人的整个临床决策事务全部由他的家庭来承担。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医患关系并非医生与孤立的病人的直接关系,更多情况下是指医生与作为整体的患者家庭之间的关系。由这种家庭主导的关系模式所形成的医患关系称之为医生-家属-病人关系,医生与家属之间的关系构成一种比较简单的信任关系。
在告知环节,信息参与方有医生、家属与病人构成,但是告知对象是家属,而非病人。是否告知病人以及告知哪些信息,家属具有决定性权威。在告知的优先次序上,相对于医生对病人的告知以及家属对病人的告知,医生对家属的告知具有逻辑与时间上的优先性。即使家属对病人的告知和医生对病人的告知可能同时进行,甚至医生对病人的告知在先,但是医生的告知是在同家属协商之后才进行的,并且医生的告知需征求家属意见,并征得家属同意。医生对病人是否告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告知,这都是同家属协商并由家属决定的。家属则是需要完全告知、充分告知,对病人只是部分选择性告知。对于说真话问题,中国的临床实践一直是这样的:第一,在医生提供信息的基础上,由家属判断真相是否有利于病人;第二,家属有最终权威来决定是否告诉病人真相。④如果癌症患者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医生往往是首先将结果告诉给患者最亲近的一位家属,由家属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告知患者。如果家属决定不告诉患者真相,医生必须服从这个决定而隐瞒真相。在中国的临床实践中,医生甚至有配合家属对患者说谎的义务。
在同意方面,决策与授权作为知情同意的最后环节由家属做出。信息告知是同意的逻辑前提,决策与授权是知情的必然结果。同意并非患者对于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简单地给予“是”与“否”的表态,而是患者综合自己实际情况后对各项方案的优劣进行判断并抉择。在西方,一个完全行为能力的病人具有医疗决定的最终权威,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但在中国,病人的临床决策由家庭做出,或者说家庭才是医疗选择的最终决策者。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脆弱的患者,维护患者的最佳利益,因为亲子之爱是超越任何契约关系的。一个人的伤残与病痛不仅是个体的事情,更是整个家庭的问题。照顾病人是家庭事务的内容,也是家属的应当责任,而接受信息告知与决策是为病人分担责任的方式。若让病人自己签字接受手术是奇怪的,也是不人道的。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如果患者拒绝治疗,而家属成员与患者意见不一致时,即使患者是行为能力人,医生也往往会尊重家属的意见。当多个家属参与决策时,家属代表最后在同意书上签字。家属代表由全体家庭成员同意并推选,通常能代表整个家庭的利益,其授权代表整个家庭。在做重大的临床决策时,所有的重要家庭成员都要聚集起来召开家庭会议,这说明决定与授权是由整个家庭做出的,家庭代表只是起到一个在同意书上签字的作用。
3.程序性流变为实践操作的形式主义
知情同意是对患者自主权、人格与自由的尊重。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形式与质料是知情同意原则的两个向度。⑤保持形式与质料的内在统一是贯彻知情同意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中国语境中,基于根深蒂固的医患所属的上级关系,知情同意的实践走向了形式主义与律法主义,片面追求程序上的合法性,甚至遗忘了医疗行为的终极价值。一方面,由于知情同意外生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对于知情同意的认知与接纳并不全面。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快速发展、多元结构的社会特点,在传统价值向现代价值转向过程中出现了利益冲突与道德真空,医患关系紧张,信任缺失。知情同意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告知的程序性与同意的形式主义。
在告知层面,告知的形式主义简化为履行程序的完成。形式在知情同意的实践层面体现为一种程序性,在这种意义上,它(允许原则)是形式的:它为俗世的多元化的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通过互相同意来产生道德权威的程序。⑥不管在临床实践还是医学研究中,纯形式层面的告知并不缺乏,但是告知的语词、方式流变为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甚至是缺乏情感色彩的文字。病人(受试者)或因身体/知识的因素,或因陌生环境的因素,在复杂、过多的信息面前,失去了常有的判断力,而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基于对专业人员权威的敬畏,患者与受试者即使存有困惑亦不敢问,其典型性表现是将告知等同于“知情同意书”。为规避因疏忽带来的诉讼责任,医务人员尽可能告知病人所有信息,将重点放在“知情”层面。这造成了医务人员或研究者将决策责任转嫁到病人与受试者身上,弱化了医务人员与受试者保护病人与受试者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告知的不是尊重病人的知情权,也不是“以病人为中心”,而是“防御性医疗”。
在同意层面,为追求程序的合法性而放弃了医生的告知义务,忽视了患者对信息的实质理解。同意本身是一个决策过程,但是在中国,同意已经简化为患者或家属的“是”与“否”的表态与签字。知情同意已经异化为医患之间相互提防、保护自我的一种工具,甚至为了追求知情同意的程序性而抛弃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道德承诺。形式主义抽离知情同意行善的质料规定与价值内容,既没有真正地尊重个体的自主,也违背了医务人员忠实于患者健康的社会承诺。形式主义真实揭示了知情同意实践的空洞性,虽然知情同意的外表还在,但褪去其华丽的外衣,只剩下一个空虚的框架而已。
三、建构中国知情同意制度的出路
伴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日益加速,城乡个体逐步从原来作为其行动框架的家庭结构中抽离而出,国民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我国实施知情同意的政策环境正日趋成型,不管是在医疗实践中还是在研究领域,个体知情同意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当失去家庭与医生的庇护之后,个体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困扰,社会风险不断向独立的社会个体沉淀,社会结构转型、人际信任资源不足为我国建构与完善知情同意制度提出了巨大的难题与挑战。关键在于,如何将社会转型形成的压力转化为推动知情同意制度建设的动力。
1.开启现代公民伦理教育,推动权利启蒙与责任教育
理想社会的达成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与良善的公民,知情同意的制度建设亦是如此。如果说完善的知情同意制度是现代和谐医患关系建构的基础,那么具有正确权利观与责任观的现代公民就是其良好实践的根本保证。知情同意的深层道德基础是个体权利保障。权利既是催生知情同意的重要条件,也是实施知情同意的基础,权利话语缺席必然造成知情同意实践的空洞。
由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过度张扬人的情感性,强调血缘关系与人情世俗,而公共权利话语却空场,个体自治资源枯竭。在由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我国缺少韦伯式的新教伦理的文化积累与精神准备,缺少可以直接孕生哺养出现代性社会精神与人格类型的精神资源。⑦在公民教育层面陷入误区,将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割裂开来,要么片面追逐公民义务,要么过于强调公民权利。我国的公民观念中无视或回避了公民权利,忽视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的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⑧我国语境下阐释的知情同意,是一种强调重视医患对话形式的、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原则,当中并不存在对患者自主权的尊重。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在全国范围对全民进行系统的权利启蒙教育,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与能力。通过对患者的权利教育,让社会民众熟知知情权与同意权的内在要素、基本要求与程序,让整个社会包括医务人员以及研究者学会尊重他者权利。
责任教育是推动知情同意实践的另一个维度。知情同意作为一种制度能否健康、稳定地实行,取决于社会对知情同意权利及其责任的认知、履行。一种治理机制是否健康和稳定,取决于公民如何看待他们的权利和责任,又怎样行驶这些权利,履行这些责任。⑨然而,在现实语境中,部分主体责任意识不足,出现问题推卸、逃避责任,缺乏一种对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担当。实际上,只有在关系中,权利话语才具有可能价值;当医患关系被瓦解,患者身份的认同便失去了所依附的载体。社群主义者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其能力,而且活在社会文化之中是个人发展理性、成为一个道德主体以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存在者的必要条件。⑩单向度地张扬个体权利而忽视责任履行,必然导致个体权利与个体义务的分离、个体权利与他者权利的断裂。只坚持个体权利的优先性教育,会产生一种误导,即“个体在本体论、认识论乃至道德上都具有优先的权利,个体的地位至高无上”[11]。责任的缺位背离了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公民要求也相去甚远。因此,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加强医患的责任教育,要求双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敢于承担自身行为的后果与责任,敢于承担对和谐医患共同体的道德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其道德价值。
2.加强信任的制度建设,形成知情同意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在当下中国社会语境中,医患信任危机对知情同意实践影响最大。信任既是医患关系形成的基础,也是自主个体“安全感”的防护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时空的虚化”与“社会脱域”(吉登斯语)机制的形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人群交往提供了便利工具。人际交往更多地面对陌生人,医患关系已经演变为“道德异乡人”。如果说传统社会中,医患间的熟人信任模式凭借与行为者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那么,现代医患信任易遭到医疗系统中的“官僚主义”的侵蚀而不太稳定,甚至导致个体美德亦被湮没于医疗科层系统之中。由于现代系统的信任比人际信任抽象,容易降低心理上的“安全感”,为医患之间的良性互动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导致知情同意的可靠性大为降低。因此,医患信任机制的形成有助于推动医患双方良性互动。
由于信任模式由传统的熟人模式向现代的“异乡人”模式的转变,由人际交往向社会与医疗体系的“普遍主义信任”(韦伯语)的转变,制度性承诺是现代社会培植医生与患者之间信任的根本。福山曾揭示信任的基础是“群体共有的伦理规范”[12],按照福山的逻辑,社会成员相互信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存有在共识基础之上所共享且有实效的伦理规范,以及社会成员对这种伦理规范的自觉诚服。当下中国,普遍信任危机充分表明,社会有效、共享的伦理规范的缺失。传统信任基于对方人格,那么现代信任必须奠基于制度性承诺。一方面,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权威表现无力感,只能期望通过制度实现对复杂社会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制度性承诺是社会系统承诺的实质与核心,对抽象系统的信任实质上是对制度承诺的信任。当然,构建普遍社会信任的制度并不意味着抛弃健康人格的形成,毕竟医疗系统中个体的人格素质是制度实施的基础。
3.建构独立的第三方干预模式,破解知情同意实践难题
如同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等伦理难题一样,知情同意也正在成为生命伦理学中的另一个难题。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知情同意都面临一定的困难。要破解知情同意难题,构建合理的干预模式是其必要路径。这种模式应当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从医院层面看,要发挥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功能。伦理审查制度已经成为解决医学实践难题的重要举措,如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等,知情同意亦可以借鉴。在日本,医疗机构所有的知情同意书,必须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执行中遇到问题,也有伦理委员会出台改善措施。[13]第二,从社会层面看,要引入社会治理模式,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社会治理已经成为社会变革进程中解决社会难题的重要进路。在生命伦理学实践中,当知情同意出现问题时,医患双方或研究者/受试者双方各执一词,纠缠不清。独立的、与医患双方利益无涉的第三方有助于解决医患信任不足情况下知情同意的实施。第三方承担的职能涉及建立专家信息库,制定知情同意的程序与方法;形成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组建非专业人员监督组协助专家监督组进行监督,此方式采纳陪审制度中的旁听、判断及非裁决性给予意见功能[14],从而发挥其对于知情同意实践的监督功能。第三,从政府层面看,要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司法审查是指法官运用司法权力审查公共团体的行为或者决定的合法性。其关注点不是决定本身的合法性,而是达成决定的程序的合法性。司法审查制度使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争议做出裁决,公众基于对司法及其程序性的信赖可以接受其结果。欧美部分国家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处理知情同意难题。在美国,有一名17岁的孩子,因抢救其生命需要为其输血,其父母因为宗教信仰拒绝输血,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并依据最佳利益原则裁定医院有权为患者输血。[15]在医疗紧急情况下,知情同意该如何实施,司法审查制度的介入可以为医疗决策提供合法性辩护,避免将医务人员推到医疗风险面前。
四、结语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东西方文化相互激荡、碰撞与对话,我们既需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又需要挖掘并学习他者先进的社会理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原则,做到兼收并蓄。在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建构中,在遭遇诸多生命伦理难题时,必须立足我国社会实践,结合中国文化土壤。若只是对西方概念与制度的简单移植,罔顾我国文化传统与现实境遇,必然遭遇“消化不良”的困境。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既需要与世界上保持经济合作与制度引进,又需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构建自己的理论视域。家庭主义与“仁爱”伦理是我国道德传统的核心,因此,如何在知情同意制度的建设中发挥家庭的作用与履行医生行善的义务,依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实地看,在生命伦理学领域,我们需要树立社会转型思维,培养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知情同意作为生命伦理学的研究热点,在我国社会现实中遭遇困境,寻求有效路径已经成为我国现实的迫切要求。
注释
①知情同意最初源于英文“Informed consent”,其字面文义是基于说明的同意。日本学者将其翻译为“医师的告知、患者的同意”,我国学者通常将其译为“知情同意”。②参见李本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医生的道德法律义务》,《健康报》2002年5月23日。③乔乐天:《论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中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8期。④参见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45页。⑤参见陈化:《形式与质料:知情同意的两个响度》,《湘潭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⑥参见[美]H.T.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基础》,范瑞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⑦参见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⑧参见常淑芳、扈中平:《权利与责任:公民教育的两个维度》,《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⑨参见[英]基恩·福克斯:《政治社会学》,陈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页。⑩参见Charles Taylor.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90.[11]Adrian Oldfoeld.Citizenship and Community:Civic Republicanism and the Modern World.Gershon Shafir.The Citizenship Debates:A Reader.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p.67.[12][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34页。[13]参见陈秀丽、陈伟、袁江帆:《医疗知情同意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医院》2011年第3期。[14]参见李雪阳:《困境与策略——辨析医疗领域中的“知情同意”》,《哲学动态》2012年第8期。[15]参见Kurt M.Hartman,Bryan A.Liang.Exception to Informed-Consent in Emergency Medicine.Hospital Physician,March 1999,pp.5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