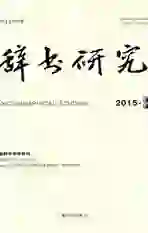新词语研究和新词语词典编纂六十年
2015-07-20周荐
摘 要 新词语搜集、整理等工作,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迄今已持续进行了六十余年,成果之丰硕自不待言。新词语不论从词条本身反映对象的广泛性上看,还是从对其进行搜集整理的时间性上以及研制手段的先进性上看,六十年间都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路。检讨得失,总结经验,对于把握未来新词语研究的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新词语 词条的多元化 编年本词典 研制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百废待兴,但语言文字工作仍备受重视: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1950年6月25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1952年6月11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的《中国语文》杂志社成立……新中国建立后,新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样样都是新概念,各个都需词语表述。因此,解放之初,人们几乎每日每时都会接触到新词新语,新词语的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较早推出的一部工具书即是《新订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1952)。
从1952年至今,六十余年过去了,有关新词语的工作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粗略估算,仅专门的新词语工具书即出版有一二百部之多。再看五十余年间历次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更可明了:对新词语的搜集、整理等工作,中国科学院(1977年5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可以说一刻也未停歇,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亦是如此。1960年《现汉》试印本出版,其后的每个版本,都或多或少地将一些新词语收录进去,反映出该词典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如2002年的《现汉》增补本,有1200余个新词语被增收其中,如“按揭、宽带、蓝牙、双赢、疯牛病、实名制、转基因、纳米技术、三个代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邓小平理论、可持续发展、CEO、WTO”等,令人耳目一新。2012年的《现汉》第六版,更有3000多个新词语被增收其中,如“宅、北漂、给力、捷运、雷人、山寨、团购、微博、限行、摇号、潜规则、情人节、云计算、pm2.5”等,格外引人瞩目。六十年来新词语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工具书的收条上,更表现在对新词语所进行的研究上。检视六十年来新词语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将对未来新词语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深有裨益。
一、词条收录由对政治条目的过分关注向各类词语的全方位收录发展
《新订新名词辞典》收条目5500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性的条目,例如“第三国际、减租减息、法越三八协定、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等,甚至有不少是政治性的“事件”,例如“意尔斯事件、柯佛海峡事件、波兰九一事件、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事件”。这不奇怪,一个新的政权建立起来,各族各界群众对这个政权还不甚了解,对建立这个政权的政党的政治主张和与其政治主张息息相关的一些事件也还不十分熟悉,因此新政权利用工具书将其政治主张在群众中加以宣传,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一个时代较多出现过分政治化的词语,只能说那个特殊时代社会发展还不够平衡和健全。一部新词语工具书,对那一时代产生出来的词语只能忠实地加以记录。从所收词语本身来看,政治性的词条词目往往过长,词感也不强,与我们通常所见的普通词语相比,相去甚远。像《新订新名词辞典》这样较多收录政治性条目的工具书,在那个比较特殊的年代,当然并非仅此一例,《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一书,所收的近400个新词也有不少是政治性的。这样的情况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巅峰状态,从周荐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韩国大邱:中文出版社1997)所收条目看,那一时代所造出的新词语更无一不是政治性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中国政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生活愈趋丰富,反映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新词语逐渐常态化,这些词语也很快成为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词语,逐渐成为了新词语研究和新词语词典关注的主流。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政治性词语的数量逐渐递减,到21世纪初编纂的编年本《2006汉语新词语》时,纯粹政治性的词语几乎难觅踪迹了。应该说,新词语词条所反映的对象由类别单一向全方位发展这样的现象,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是新词语产生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也为新词语研究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新词语词典的编纂由以若干年为一时段向年度性逐渐过渡
新词语的搜集和整理,最初常见的是以若干年为一时段进行的,新词语工具书的编纂,最初一般也是以若干年为一个单位进行的,而这个若干年的时间长度,短则至少二三十年,长则可达四五十年。例如,闵家骥等的《汉语新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林伦伦等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花城出版社2000),所收词条的时间跨度,有的长达二十余年;李行健等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亢世勇等的《新词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收条时间更长,有的跨度甚至达到四十年。近年出版的沈孟璎《新中国60年新词新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2),收条时限超过半个世纪。宋子然等正在编纂的《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收条时限更长达一个世纪。或许正是因为新词语词典编纂时段长短可以不拘,并无硬性的要求,所以不少人都曾编纂新词语词典,八仙过海,乐此不疲。仅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新词语词典,较为著名的就有闵家骥等的《汉语新词新义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宋子然主编的《汉语新词新语年编(1995—1996)》(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王均熙的《汉语新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诸丞亮等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新语新义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李达仁等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周洪波主编的《精选汉语新词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1世纪的头几年又有不少新词语词典问世,举其要者即有:林伦伦等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花城出版社2000),姚汉铭的《新词新语词典》(未来出版社2000),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的《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曲伟等主编的《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沈孟璎的《新词新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王均熙的《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邹嘉彦等的《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这还不包括编年本新词语词典。我们注意到,上述词典中不乏学者们的精心结撰之作,融入了学者们对新词语研究的成果;但也毋庸讳言,个别的较为粗疏,更使人难以容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出版的现象。有的作者编纂的新词语工具书,出版不久旋即拿来改编一下再度出版。至于不同的作者编纂的新词语工具书所收词条的重复现象,更是常见,陶炼(2002)《编年本〈汉语新词语〉系列词典部分词目的著录年代》一文对此有评述,此处不赘,读者可自参阅。倘无利益驱动,如此重复劳动,反复进入市场,智者谁为?这样的做法对作者的精力和社会财力来说都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于书包一再减负却减不下来的学生及其家长来说,花钱买回来的东西却有着相当大的重复率,问题不容小觑。
若干年一时段的新词语工具书,反映出来的自然只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概貌,这种反映也并不及时。能够比较及时地反映新词语面貌的是按年度来编纂的新词语工具书。编纂编年本新词语词典,这在俄罗斯、美国等国家是早已开展了的工作,而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吕叔湘先生(1984)《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的号召下,才开始关注——先是1986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了“新词新语新用法”编写组,在《语文建设》杂志连载“新词新语新用法”的一些样条,又在《世界汉语教学》杂志连载“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的若干词条,主观意图是突出语言应用,做些辨析、比较、预测;之后是于根元、刘一玲先后主编的编年本《汉语新词语》陆续出版[1],算是正式填补了我国此项工作的空白。可惜的是,由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主导的这一工作,在当时只进行了四年旋告中断,十数年之后才由国家语委立项,由周荐、侯敏、杨尔弘等继续做下去[2]。编年本的新词语搜集、整理和出版,受人力、经费等各种因素制约较大,因此有可能出现一年一度的编年本和若干年一时段的时段本折中的类型,例如宋子然等主编的《汉语新词新语年编》,虽称“年编”,但是有的并非以年度为单位,已出版的五卷中,1995—1996年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001—2002年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是以年度为单位的,而1997—2000年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2003—2005年卷(巴蜀书社2006)、2006—2008年卷(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09)却又是跨年度的;王均熙编著的《汉语新词词典(2005—2010)》(学林出版社2011)主要收录2005—2009年之间产生的汉语新词新义,也是将四五年的材料裒辑在一起的。
三、新词语研究手段的更新——电脑、网络、网站、评选和监测
早期的新词语搜集和整理工作,跟语言研究的其他门类一样,是靠查阅报刊、抄写例句、记录卡片来进行的。我国新词语的研究,真正利用电脑和互联网,还是最近十来年的事。《2006汉语新词语》采取的方法是先手工查找再机器筛选;自《2007汉语新词语》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两个科研团队,一个侧重手工查找,一个侧重机器识别,之后再汇总进行机器筛选。两个团队的工作,殊途应该同归,筛选出的词语本应有较大的重合率,但实际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说明新词语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还存在着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随着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纸版的工具书似乎已有落伍之势,因为即使是年度新词语词典也仍需一个编纂出版周期,这个周期至少也要一年以上;而电子版的工具书则可实现词条的随时增添,内容的随时更新,这是纸版工具书无法比拟的。当然纸版和电子版工具书各有利弊。目前看来电子版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防伪,如何防止盗版现象的发生。
新词语的研究,借助网络技术,更是当今社会必备的技术条件之一。这一点台湾和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例如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专门所建立的“语文网站”(http:∥140.111.1.192),持续不断地推出“新词语料汇编”; 香港教育学院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也开始公布“LIVAC泛华地区中文新词榜”,入围的新词除涵盖政治、经济方面外,民生、文体等方面的新词,尤其引人注目。这样的工作,无论对新词语的研究还是传播而言,无疑都颇有助益。
进入21世纪后,新词语的研究气氛愈加活跃,研究手段也愈加出新。其中,利用网络优势,调动社会资源,对新词语的产生过程、传播途径、意义作用、社会功能等进行监测,并请社会大众对词条加以评选,是一条崭新的研究路径。2007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平面、有声、网络三个媒体分中心首次合作发布了“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流行语与新词语存在着相当的重合度,这一点我们已做过研究[3]。对流行语进行搜集整理,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做新词语的搜集整理工作。2007年的十大流行语是“十七大、嫦娥一号、民生、香港回归十周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廉租房、奥运火炬手、基民、中日关系、全球气候变化”,2008年十大流行语是“北京奥运、金融危机、志愿者、汶川大地震、神七、三聚氰胺、改革开放30周年、降息、扩大内需、粮食安全”,2009年的十大流行语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落实科学发展观、甲流、奥巴马、气候变化、全运会、G20峰会、灾后恢复重建、打黑、新医改方案”,2010年的十大流行语是“地震、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高铁、低碳、微博、货币战、嫦娥二号、‘十二五规划、给力”,2011年的十大流行语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十二五开局、文化强国、食品安全、交会对接、日本大地震、欧债危机、利比亚局势、乔布斯、德班气候大会”,所反映的均为各年度当年的社会热点现象和问题。2006年起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开始对新词语进行监测,2007年起每年出版汉语新词语编年本。2011年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从新词语中选取使用率最高的十条新词语作为“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发布,并成为“汉语盘点”活动的一部分。2011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是“伤不起、起云剂、虎妈、政务微博、北京精神、走转改、微电影、加名税、淘宝体、云电视”,它们是当年度的新词语,所反映的也正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现象。“十大流行语”也好,“十大新词语”也罢,虽都只是模范型的词语样本,但这样的筛选和发布对于使新词语进一步赢得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和关注,至少在目前来看是颇有成效的。
四、未来研究走向的预期
新词语的搜集和整理,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这是不言而喻的。从新词语研究所需的观察面上看,潮语、网络语言等已经有人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以往学者们对新词语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大陆这个主流社区,未来似乎还可腾出精力来更多地关注一下非主流社区,例如相对于大陆社区来说稍显狭小的港澳台社区,因为不少新词语恰恰是先在港澳台产生出来,而后才为内地引进的。港澳社区的新词语有港澳学者做过研究,产出了成果,如邓景滨199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港澳新词语研究》,以一个港澳人的视角,依据多年来搜集的3400多个港澳新词语,从来源、结构、词形、词义、影响及规范诸方面探讨了港澳新词语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助于人们对港澳新词的整体认识。澳门社区也有单独进行新词语研究的必要,《澳门特有词语辞典》的编纂和研究已在澳门启动。台湾社区的新词语研究,有台湾学者做过,如许斐绚1999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当代国语新词探微》。比较而言,从事台湾新词语研究更多的是大陆学者,例如苏新春《台湾新词语及其研究特点》(《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董欣胜、林天送《台湾国语新词语一勺》(《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将两岸四地不同社区的新词语拿来进行对比研究,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另一个热点,成果如:原新梅《台湾的字母词语及其与大陆的差异》(《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5卷第6期),邓瑷敏《新时期中国两岸三地新词语发展现象浅析》(《语言新观察》2008年第6期),俞允海《大陆和港台新词语语差研究》(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语文教学论坛”2011—07—12),赵聪《大陆和台湾新词语差异的认知考察》(《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如上所说,大陆的新词语研究也在蓬勃发展,例如汤志祥的《汉语新词语和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刘晓梅2003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邵宜《近年的新词语研究》(《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刘长征《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的新词语监测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鲁文莉《网络语言新词语研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王显志、王一川《浑沌学视阈下的新词语研究》(《科技视界》2012年第29期)。大陆之外,其他社区的学者也在关注大陆的新词语问题,例如台湾金慧兰2007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新词研究》,香港李谷城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新词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某种意义上说,异地的学者对新词语进行研究,他们对新词语的敏感度,是本地学者无法比拟的。学者们将不同地区的新词语拿来进行对照研究,也有助于使研究在比照中得到深化。未来新词语的研究,可考虑更多地采取两岸四地学者联手协同攻关的方式。
新词语研究除了要继续关注传统媒体(从信息来源上看:官方媒体、大众媒体;从传播方式上看:立体媒体、平面媒体)之外,一些自媒体,也要给予关注。这是因为,比起传统媒体来,自媒体更是年轻一代喜欢发表议论,经常发表意见的处所。关注自媒体,对于我们了解青年一代的新词语创造、使用、传播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以更开放的思维面对新词语,恐怕是未来需要我们着力考虑的问题。从新词语查找、筛选,工具书编纂的手段上看,走电子化、网络化的道路当是方向。而由国家层面组建研究队伍,则意味着有了经费的投入和保障,可避免小作坊式的经营和分散多头经营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也有利于打造过硬的产品——品牌辞书。“中国梦”,要经我们全体辞书人之手具化为中国的“辞书强国”梦。而“辞书强国”梦的实现,要从大家自身做起,现刻做起,一点一滴做起。新词语工具书虽只是辞书中不起眼的一个小门类,但它的研制,未尝不可作为我们“辞书强国”这座大厦的一撮砂、一粒石子。
附 注
[1]这就是于根元主编的《1991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和《1992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刘一玲主编的《1993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和《1994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2]这就是周荐主编的《2006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7),侯敏、周荐主编的《2007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8),《2008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9),《2009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0),《2010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1),以及侯敏、杨尔弘主编的《2011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2)。
[3]参看夏中华《中国当代流行语全览》(学林出版社2007)周荐“序”。
参考文献
1.江蓝生.《现代汉语词典》与吕叔湘先生的辞书学思想.辞书研究,2004(6).
2.李宇明.关于辞书现代化的思考.语文研究,2006(3).
3.陶炼.编年本《汉语新词语》系列词典部分词目的著录年代.辞书研究,2002(4).
4.王铁琨.中国辞书的“强国梦”还有多远.中华读书报,2006—10—18.
5.张志毅.我国离“辞书强国”究竟有多远.人民网,2010—10—14.
6.周荐.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中国语文,1999(4).
7.周荐.新词语的认定及其为词典收录等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7(3).
8.周荐,杨世铁.汉语辞书研究三十年回顾.辞书研究,2009(5).
9.周荐,杨世铁.汉语辞书研究的热点展望.辞书研究,2010(3).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澳门 999078)
(责任编辑 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