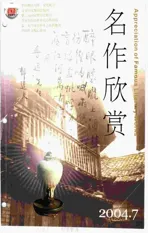值得一读的散文五十九篇(三)
2015-07-15北京祝勇
北京 祝勇
值得一读的散文五十九篇(三)
北京 祝勇
著名作家祝勇在本文中推荐了新文学发生以来的五十九篇散文,并对每篇文章进行了简要的评析,这些评析体现出其个人性的精神旨趣和阅读视角。文章按作者出生时间依次列出,最早为出生于1881年的鲁迅,最晚为出生于1982年的马小淘,跨度为一百年。因此,本文亦可视为一份独特的中国现当代散文史样本。
散文 精神旨趣 文学百年
4 0.鲍尔吉·原野(1958—):《最想依傍的八位高邻》
此篇在形式上并非原创,在鲍尔吉·原野之前,苏东坡写过《赏心乐事十六则》,金圣叹写过《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梁实秋写过《不亦快哉十一则》,林语堂写过《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但鲍尔吉·原野写《最想依傍的八位高邻》不算抄袭,否则我们还得去追究前面几位圣贤的版权责任,实在费事。鲍尔吉·原野此文,格式是别人的(或者说是公用的),内容却是自己的,用别人的瓶装自己的酒,用别人的文字养自己的眼,不失为节省资源、提高效用。依此类推,我的这篇文字,就叫“值得一读的散文五十九篇”。
4 1.宁肯(1959—):《藏歌》
我最初是从《大家》“新散文”栏目中读到《藏歌》的,后来又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聆听西藏》里读到。当时还不知宁肯何许人也,那实际上也是宁肯从事写作之初。曾经援藏的宁肯,通过《藏歌》,找到了写作的最佳入口。这篇散文,也的确把他的文学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西藏在当代散文中已是一个熟题,有马丽华、巴荒、唯色等许多作家以散文的方式聆听过西藏,但宁肯有自己的方式。他充分调动了语言的活力,使他笔下的所有词语都有极强的动感,如风吹过时,所有的词语都活跃起来,彼此交织和连动,成为一个层层推进的有机体。在他的笔下,寂静是可以聆听的,河流则变成竖琴。他的语言,有一种极强的魔力,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与那片神魔之地交谈。
4 2.苇岸(1960—1999):《美丽的嘉荫》
苇岸笔下的嘉荫,从一开始就感染我们。它“纯粹、明澈、悠远,事物以初始的原色朗朗呈现”。苇岸是土地原教旨主义者,他用自己的笔,维护着土地原有的秩序和美。苇岸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他眷恋的土地早已面目全非,田野大幅度缩水,到处是小工厂、城乡结合部、垃圾场、废料仓库、粗糙低劣的农民房……总之,乡村已经变成不伦不类的事物,假如被苇岸看到,不知该作何感想。
但苇岸的纯情依然令人感动。在他眼里,土地是人类的最大共和国,是所有人的故乡。他说:“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陆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
4 3.张锐锋(1960—):《船头》
张锐锋喜欢写圣哲,中国的孔子、庄子,以色列的本·耶胡达,他都写过。自己的散文,也有了些许圣哲的意蕴。从成语、唐诗,乃至算术题中,他都能发现朴素而深刻的真理,这种能力,文坛上并不多见。比如这篇《船头》,开篇就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问题:“一条河流为什么不找一条最简单的捷径入海?”我们无从回答,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想过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说,张锐锋写散文,总有一只“第三只眼”躲在后面,他的思维,总比别人多一个维度。
这个问题,张锐锋自己当然是能够回答出来的,所以开篇那惊世骇俗的一问,不过是他卖的一个关子而已。他的回答是:“河流之所以选择了弯曲,乃是因为这样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展开自己优雅的长度,把自己的力量放置于最大限度的面积上。作为附带的意义,人类的生存在最大的面积上得到恩惠,也许这里有着至高者的慈悲用意。”①
这当然是文学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散文要遵从文学的逻辑,在这逻辑面前,所有的逻辑都算不上逻辑。
4 4.庞培(1962—):《乌篷船》
这是庞培《乡村肖像》中的一篇,很短,在庞培的作品中不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篇,但它如乌篷船一般灵巧,储存着江南水乡文化的巨量信息。庞培是典型的江南人,几乎每天到长江里游泳,他对江南比对自己还要熟悉。他的思维、气质、语言,全部是江南的。所以,任何一个有关江南的题落到他手中——比如乌篷船,他都会把江南的美表达得淋漓尽致。
4 5.刘亮程(1962—):《先父》
这是一篇回忆先父的散文——回忆那个几乎没有留给他任何记忆的父亲。因此,他的回忆,几乎成了一个虚空。由于父亲早逝,那些残留在作者童年岁月里的零星记忆,最多只能算是记忆的微量元素,而无法构成记忆本身。本文也因此成为一篇特殊的悼词。它充满矛盾:一方面,作者的生命是父亲给的;另一方面,那个给了他生命的男人又几乎不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生命的系统中。然而,作为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又往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即使血缘传承在中国人的道德伦理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无论家谱还是牌位,对于生者来说也只是一些抽象的符号而不是亲切可感的生命。它们从理论上对一个人的来路给以界定和通知,但站在这人世的一角,一个人依旧会感到身前身后两茫茫。于是有了那跨越千古的悲慨: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
4 6.徐累(1963—):《褶折》
徐累是画家,但他的散文令人惊艳。他的文字与绘画交相辉映。在这篇散文里,褶折成为物质,成为审美的对象,这完全与画家的思维有关,一个舞文弄墨的作家很难注意到褶折的审美性。与褶折相连的,不仅仅是衣裳,还有涅瓦河的波浪、彼得堡宫殿或博物馆里的水波型帘幕、荒木经惟的摄影、巴特农神庙女神雕像身上性感的衣纹、达·芬奇的草稿……从几缕褶折出发,徐累挖掘出艺术史中一个博大然而又隐秘的事实:“褶折不仅是观念,而且还是伟大的操作,它使世界为之昏迷。”
4 7.张远山(1963—):《告别五千年》
一文写尽五千年,张远山写得机巧聪明,又力道十足。聪明在于他把朝代与身体部位对应,从历史中搜寻出一条自头脑到膝盖的不断下行的路线;力道在于这虽然称不上“规律”,而仅仅是一种比喻,但不失为一个视角,让人遐思。
4 8.彭程(1963—):《在母语中生存》
彭程外国文学读得多,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那些离开母语环境的写作者,比如张爱玲,比如布罗茨基,然后从反面证明了母语对一个书写者的价值。所谓母语,就是母亲的语言,它像母亲一样只有一个,而并非很多语言中的一种。它携带着温度、记忆、感情、价值,属于身体内部的一种遗传细胞。这一切,后天习得的语言是没有的。假如不考虑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数人通过外语阅读很黄很暴力的文学,都没有什么生理反应。彭程发现了一条文学的规律——语言遵循的是母系氏族的法则,以母为遵。一个写作者,只有在母语里,才能找到自己的故乡。
4 9.凸凹(1963—):《游思无轨》
这又是一篇思辨性的散文,写于20世纪末。它关乎人类的处境、命运这类宏观话题。但凸凹没有写成长篇大论,而是将人类的荒谬、两难、无助落实到细处。这需要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我以为处理大题有三种境界:举重若轻、举重若重、举轻若重。第一最佳,第二尚可,第三最差,本文属于第一种情况。篇末神明与鸟的寓言,让人久久不忘。
5 0.李书磊(1964—):《河边的爱情》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很多人幼时就会读的诗句,李书磊却从中发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密码——为什么那些古老的爱情大都发生在河边,爱的歌咏也大多与河流或河水有关?这无疑是有趣的发现,而李书磊的破译过程更加有趣。他仿佛是文化的血液鉴定师,通过他的化验,鉴定、鉴别并鉴赏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李书磊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重读古典》,是这些鉴定报告的集成,它们并不枯燥,而仿佛思维游戏,想人之未想,丝丝入扣,非常好看,《河边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篇。可惜这样的文字现在见不到了,连李书磊都多年不写了。
5 1.李敬泽(1964—):《小春秋》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人的选择。他们已经选择过了,不再有选择的机会了。但我们还有。每个人看过去的事,心里都在想当下的事;看别人,都在想自己。所以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
这样的交流固然困难重重。写历史,最怕隔。语言、思想、文路,处处相隔,对不上话,那文章就越看越拧巴,十三不靠。像李敬泽借用了《三岔口》的规则说:“雪亮的刀锋贴着对方的头顶划过,他们对面凝视,就是不能穿过那虚拟的黑暗看到对方……他们绝不能看到对方,就像人和历史之间横亘着词语构成的明亮的黑暗。”②
但这些风险,还是可以化解的,否则历史就成了一个纯粹的时间现象,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历史还“在”,就证明了历史与我们的粘连关系。李敬泽用散文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历史的因果、人物的短长,尽奔赴他的笔端。我看到李敬泽对历史信手拈来的功夫。但他志不在史,在以史为媒,借用历史的长度透视自己。他在文字中独步,看孟夫子一身正气,看盗跖一脸杀气,看宋襄公一脸天真气,等着在河里狗刨的敌军爬上岸来把他打个狗血淋头,落荒而逃……历史的“镜像”浩大,照鉴的全是今人的事实。
李敬泽像一架续航能力极强的侦察机,跨越自春秋时代至今的巨大飞行距离,机载雷达可以轻易锁定历史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游刃有余,袖底藏风,空气阻力几乎为零。
这组散文,曾是李敬泽在《南方周末》等处写的专栏,原题“经典中国”,出书时改名“小春秋”,据作者说,“因为大部分是有关《春秋》的”。在《春秋》之外,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不带书名号的春秋。
5 2.格致(1964—):《利刃的语言》
在这篇文章之前,格致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把本文当作格致的“处女作”,不知是否准确。很多年前的一天,友人拿来一组格致的散文,我立刻被它们惊住了,由衷相信“写作高手在文坛之外”这句忠告。那组散文就这样发表在我主编的《布老虎散文》上,《利刃的语言》是其中之一。
一个家庭妇女,到楼下的西瓜摊买西瓜,交了钱,把西瓜拿回家——这能构成一篇散文吗?
但格致就写这样的题材,貌似家常,却危机四伏。文中那柄锋利的刀刃,象征着生命中无处不在的凶险。格致揭露了我们生存的本质——我们被危机罩住了,但它含而不露、引而不发,却时常没有预告地不期而至,把我们置于死地。这是那个卖瓜人手里的利刃告诉格致的,格致的语言,也因此闪着利刃的寒光。
5 3.蒋蓝(1965—):《指缝里的白烟》
蒋蓝的散文,有点像足球队里的前锋,总是冲在最前面,机锋锐利、刀刀见血。个人生活入他文字者甚少,本文便是为数不多的一篇。这同样是一篇祭悼文,这样的文字,本文已提到多篇。或许只有面对亲人的亡故,情感力量才最强大,所有平日里忽略的亲情,都在此时奔涌而出,一一反刍。
但与其他祭悼文不同,本文没有过多地回忆逝者的经历,或者与逝者相处的日月,而是细细地描绘丧事的全过程,冷静、细致、静穆,像一个不轻易流泪的汉子,把强烈的情感隐藏在后面,只通过个别的细节流露出来,诸如那条通往殡仪馆的路,刚好是父亲曾经锻炼身体的路;又如父亲遗像背后,还留着作者儿时的笔迹,仿佛已逝的时光,隔着一层纸,仍与父亲共处。这些细节犹如指缝间的白烟,丝丝缕缕地溢出,弱如轻风,却成为文字最有力的推动力量。
他书写丧葬、火化、拣骨灰的过程,一丝不苟、一丝不乱。整个过程静谧无声,却比仰天长哭更有力度。蒋蓝还是没改他的残酷文风,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宣告死亡的残酷。至于对生死的思考,死者已经不能、或者说不用去思考了,那是生者的事。
5 4.周晓枫(1969—):《种粒》
周晓枫的《种粒》,写于十多年前,今日重看,光泽依旧。那是语言的光泽。周晓枫是不可救药的语言至上主义者,她的语词,珠玑闪亮,意象纷繁,似乎不愿意把任何一个汉字浪费掉。本文第一句,就给人下马威:“最小的水系在果实里流动,我把这个光亮的苹果举起来,就听了声音,非常小的声音,类似于安静。”
“最小的水系”,是指苹果里的汁液,但她不说汁液,而说水系。倘说汁液就俗了。周晓枫把她的语言意志贯穿到全篇,甚至贯穿到她的全部写作中,她的执拗,在文坛上也并不多见。她写过魔术师,或者,她的理想,就是成为语言的魔术师。
种粒是至为微小的事物,但周晓枫把它写得很大——甚至有水系流动其中。“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世界上就没有无关紧要的事物,关键是你怎样看它。
5 5.冯唐(1971—):《致石涛书》
冯唐的文学身手,在散文中展露无遗。或许,他个性中的自由刚好吻合了散文的属性。写散文,最怕拘谨,端着写,自己把自己当大师、当知识分子、当圣人——与此类散文相比,冯唐显然走到了另一个极致。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散文的这一属性,自由、放任、游刃有余,但绝非胡言乱语,对事、物、人,都别具洞见。
这篇《致石涛书》,先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后来更名为“大画”,收入散文集《三十六大》。这是一篇与清代画家石涛探讨艺术的文字,却不同于任何一篇艺术散文,行文不是紧紧密密、步步为营,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没有一大堆的术语,却充满了真实的大白话,只不过那些大白话,句句直指艺术的实质。比如他说:“耗尽自己所有的歪邪,孤注一掷,倾生命一击,成与不成,你都是佛。”
他引用的那段石涛的文字,我也喜欢。那段话是:“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也。”这不是抄,是眼光。
5 6.东君(1974—):《刀在黑暗中有其丰饶的光》
2001年,东君在第5期《人民文学》“新散文”栏目里发表了一组以藏地为题材的散文,总名为“幻象”,本文只是其中的一篇。那一年,东君只有三十二岁,但他在这组散文中展现了令人羡慕的成熟。比如这篇《刀在黑暗中有其丰饶的光》,把他对一个民族的认识凝聚在一把刀上——它代表着历史、工艺、性格、生活,甚至,爱。这首先需要一种别致的眼光,把再普通不过的刀,从藏族汉子的身体上拣选出来;其次,他的语言,也具有刀的力度,比如他说:“对于这里佩刀的汉子来说,刀是他们的钢铁兄弟。拿走刀,就会使一具身体失去亮度,使天气坏掉,使他们的目光变得黯淡。”作者还注意到,让女人铸刀,会使刀变得柔和、唯美,使刀的暴力含量减少。这是藏族人深藏于刀中的哲学性,也是这篇散文的深度所在。
5 7.塞壬(1974—):《下落不明的生活》
假如有人指责“70后”作家写作的“新散文”越来越遁入虚幻的空门,与现实人生的粘连越来越少,那么我就劝他去读一读塞壬的散文。在中国繁华的南方,塞壬,这位湖北姑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打工妹——即使今天,她的散文在文学界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也丝毫无助于她生存处境的改变。这使她的散文少了小女人的矫情,多了沉实的痛感。那痛感如影随形,落实在每一个细节上,甚至落实在她的地址上,因为很多年中,她是一个没有地址的人,即使有了,那地址也是“弯弯曲曲”,犹如一段无法公开的隐秘。比如,她的地址曾是:广州天河棠下西边大街西五巷之三靠北四楼。有点像联络图,一个陌生人要想准确地找到她居住的地方,确实需要不凡的摸地形的能力。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像塞壬这样的年轻人,拥有一份“下落不明的生活”,一切都是干净的,包括信用卡和爱情。但他(她)们还得生活。既然生活,就要为自己找寻生活的理由和乐趣。我们应该向他(她)们致敬,更应该向塞壬的散文致敬。
5 8.李修文(1975—):《荆州:劫难与花朵》
这篇散文,明显带荆楚文化的意味,有古意,又有“70后”的旁逸斜出,胆大心细。他写自己生活的城市,却从劫难入手,回望那一场场“鲜血的洗刷”,借此凸显荆州的个性。文字密实,史实厚实,而这一切都不是外在的,而是化于他的血肉骨髓。这样的写法,李修文独有。
5 9.马小淘(1982—):《余幼好此奇服兮》
这是马小淘《衣说》里的一篇。马小淘用散文写的“中国服饰史”,从屈原讲到尹雪艳、梅艳芳、夜总会陪酒女郎。这当然不是一般的“服饰史”,而是任性的、个人化的、别致的“服饰史”。
服饰是符号,服饰背后透露着内心深处的某种有意识或无意识。从穿戴的蛛丝马迹,可以破译一个人的内心。
这很像陈丹青,透过面孔七窍看灵魂。
写屈原的《余幼好此奇服兮》,我最喜欢“水是他最后一件衣服”那一句。她把屈原的魂写出来了。
①张锐锋:《船头》,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②李敬泽:《小春秋》,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作 者: 祝勇,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非虚构作品《纸天堂》《辛亥年》,论著《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
编 辑:孙明亮 mzsul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