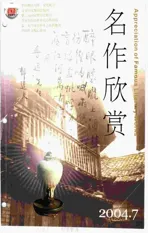文化研究:“文革”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
2015-07-15北京魏建亮
北京 魏建亮
文化研究:“文革”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
北京 魏建亮
“文革”文学的真正意义或研究价值就在于它的反向警示性,应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加强研究。可从三个方面展开:宏观层面,可运用田野调查、民族志或访谈的方法建立翔实完备的“文革”文学史料库;中观层面,可集中研究某一或某类“文革”文本的生产、传播和影响;微观层面,应深入到“文革”文学的文本内部,对它的主题、意象、人物、语言、叙事、结构等文学性因素展开具体分析。
“文革”文学 反向警示性 文化研究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文革”文学的研究经历了“断裂论”到“延续论”的变化,且在“延续论”领域成果丰硕——不仅“前溯”阐明了“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与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甚至“五四”文学在创作群体、作品风格、精神指向等维度的因依赓续,而且“后瞰”辨析了它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之间的家族相似,还有人对“文革”后三十年来小说中绵延不断的“文革叙事”进行了分析和阐释——这表明饱受诟病的“文革”文学的确不是“空白”,而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面对独特的“这一环”,对其进行“延续性”研究很有必要,一来可证明“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是个整体性命题,这对我们从宏观上审视百年来的文学遗产,总结经验教训大有裨益;二来可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但不得不说,目前的这些研究对认识“文革”文学还远远不够,因为“文革”文学含有的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因子,所以,若仅满足、停留于上述角度的介入,无疑会对彰显它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造成遗漏和遮蔽。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对其进行文化研究可能是一种方法论的丰富。
之所以有此主张,主要是由“文革”文学的特点决定的。众所周知,作为政治化和社会化的特殊“文学”样式,“文革”文学与其他时段的文学有很大不同,不怎么具备“文学性”和“审美性”,而且还反人性、反文化,属于“非常态”文学。但是,不具备文学性和审美性并不代表“文革”文学就没有价值,它身上还携有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意义: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神、文学文化体制、大众趣味、精英追求、理想主义、浪漫精神,以及“黯淡”的审美等诸种因素奇妙地凝聚在一起,并产生了新的排列、组合与交织,使其成为迥异于历史上大多数文学形态的单义又复杂的“复合性”存在,如“文革”文学的主要代表样板戏。它是在特殊的文化体制和相关政客的指使下,按照“三突出”的政治原则和创作标准集体加工而成的典型“艺术”作品。按以往的理解,这些作品仅仅是为了迎合、图解“四人帮”政治而生,毫无价值可言。但实际上,样板戏不仅由于它的“大众趣味”满足了当时民众,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的精神需要,从而局部性地实现了对他们的文化艺术启蒙①,而且它们也大都是精英知识分子们“精雕细琢”的集体成果,其叙述、语词、谋篇布局及舞台演出等,都堪称经过了“千锤百炼”。不仅如此,作品中还氤氲着浓厚的浪漫精神和崇高的理想主义,体现着“文革”时期特有的思想文化内涵,因而它们还是时代精神的“显示器”和活体标本。当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毫无创作个性、脸谱化的政治性“遵命文学”近乎病态,所谓的审美只不过是僵硬的行政律令的衍生品,因此,若动用常态的文学眼光对这样的文本进行文学性的审美分析就会出现南辕北辙、“钢”“刃”错位的尴尬,从而离真正的“文革”文学越来越远。但是,若将之视为雷蒙·威廉斯意义上的“活文化”并运用文化分析的方法进行细致考察,就能在呈现文本特定的思想史意义时,将时代精神也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也许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会随时发现这些文本的“实然”意义极其残酷,是反人类文明、反人性的,但这些恰恰从反向的角度表征了从常态的生活世界中遁匿已久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应然”面貌,从而给我们以警醒:这正是“文革”文学的意义,也是它们的真正价值所在。诚而言之,“文革”文学的真正意义或研究价值就在于它们的反向警示性。诸如探讨它的审美性,它与此前或此后文学的接续性等等都没有抓住“文革”文学的要害,因为根本而言,“文革”文学作为“文学”必然有一定的审美性,作为“历史”的产物也必然会与其他时段的文学有内部勾连,但大面积的“反文化,反人性”的文化性却是它独有的。
那么,怎样对“文革”文学进行文化研究呢?依笔者浅见,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宏观入手,运用田野调查、民族志或访谈的方法尽力搜集、钩沉和抢救散落在乡野民间及海外的“文革”文学资料,并运用一定的分类标准,将之建设成翔实完备的“文革”文学史料库。杨健、北岛、李陀、易光等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七十年代》),但这仅仅是“文革”文学之冰山一角,还有大量的“文革”文学资料埋在地下,处于沉默状态。今天看来,这项工作已显得异常紧迫:一是“文革”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年事已高或正在离去,若不及时对他们进行补救式的回访并将获取的材料公示于众,“显明”的“文革”和“文革”文学将成为一个越来越模糊的事件,产生“闹剧式”的影响。比如网易博客2014年4月7日进行了一次“愿不愿意回到‘文革’时的中国”的调查,结果显示40%的人愿意!②往大处说,这是有关方面虢夺“文革”记忆,“去历史化”的恶果;往小处说,则是学界没有对“文革”文学进行恰当还原和研究的后遗症。二是“文革”文学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已被毁弃殆尽,只剩下些零零星星的存在,但这些零星存在的“文革”文学的容量也极其庞大,若不及时捕捉,也有完全散佚的可能。它们主要存在于三个地方:一是海外,二是偏僻的乡村(尤其是“文革”时的“革命”老区),三是当时的私人日记。对于海外的资料,可通过学缘关系尽可能获得;处于偏僻“革命”老区的材料,则需要我们下苦功夫去进行田野调查,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应把注意力放在当时的一些“文化人”身上;对于私人日记,可通过个人亲自下乡或向旧书摊主购得。笔者在翻阅购得的一些“文革”日记时发现,人们不仅记录了那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还写下了个人的学习、恋爱及文学写作情况,由于是私人的,最能披露人们的真实想法。笔者在王宝胜(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西贾公社牛角川大队社员)写于1972年的日记中读到了如下文字:“脖颈处的那一抹红/是爱恋的色彩/素芳/比之红太阳/你更为娇艳。”很明显,这首“小诗”极不成熟,但它却写了当时被视为禁忌的爱情,并在呢喃般的絮语中大胆表达了对恋人的浓烈感情,而且还是在与“红太阳”的比较中彰显了“她”的魅力。这与红卫兵诗歌的激情夸张不同,与白洋淀诗歌的深沉理智也不同,填补了“文革”诗歌题材的一个空缺。这些“文学”无疑是“文革”文学的亮点,但它在数量上到底有多少、质量究竟如何还未知,需要做进一步的发掘。
其次,从中观入手,集中研究某一或某类“文革”文本的生产、传播和影响,显示凝聚在它(们)身上的各种社会性力量和关系以及它(们)所表征的时代的思想文化状况。比如对样板戏的研究,我们需要考察的不是某一样板戏或电影的故事内容、艺术特色究竟如何,而是它在何时、由哪些人、经过了哪些改编才变成当时的样子的。比方说,为什么要在1965年而不是1970年或1971年改定《沙家浜》这部戏,同样是“根正苗红”的一批作家,为什么选择汪曾祺、萧甲、杨毓敏而不是其他知识分子参与到改编中,具体而言,《沙家浜》又经过了怎样详细的修改?在修改中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实上面的行政指示的,落实中是否还有改动?改好了以后,先在哪里演出,为什么选择在那里演出,选择哪些演员演出?这些演员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演员有何不同,后来又经过了怎样的演出变化?演出的接受效果在“文革”前后又有何发展变化等诸如此类的生产性和传播性问题。只有将这些琐碎的非文学性问题搞清楚,才能真正明白缠绕在《沙家浜》周围的各种博弈性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这些力量是如何参与到创作中的以及由此体现的时代的思想文化状况的递嬗演变。在这一方面,英国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王尧的《“文革文学”研究》、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等著作是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样板”。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红岩〉是怎样炼成的》③一书,该书运用文化研究的“接合”方法,以田野调查得到翔实的一手资料,对《红岩》在不同时段的生产和消费,以及生产和消费中各种思想和力量的博弈进行了系统性的还原和论述。通过这些论述,该书不仅让读者知晓了《红岩》的前世今生和公众接受的效果历史,而且通过它还领略了时代变迁中的思想激变。
再次,从微观入手,深入到“文革”文学的文本内部,对它的主题、意象、人物、语言、叙事、结构等文学性因素展开具体分析。但这种分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化把握,而是将它们置于“文革”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运用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理论知识,跨学科地考察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化体制、社会权力、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互构,从而立体地呈现它们的复杂生成以及文本形式自身的社会化和政治性意味,换句话说,就是将它们从自足自立的文本审美学阵营拉入到知识社会学阵营中,在社会性的链条上对其进行细致演绎。譬如,研究《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这一形象时,我们需要分析的不是他的形象如何丰满,如何成为人物长廊中的又一个典型,他与此前和此后文学中相关形象的承续、勾连等文学史意义,而是他是如何在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传播方式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纠缠和共同牵制下,一步步从真实人物→小说中的人物→话剧中的人物过渡到样板戏和电影中的人物的,并且还成为“正气,匪气,或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④的融合,从而成为“文革”历史的思想镜像和活体标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他在社会历史中的生成演变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价值。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对《黑暗的心》的文化政治学分析,陶东风近两年来对知青小说和“文革”题材小说的系列形式文化学解读在这一方面颇具示范意义,尤其是陶东风的研究,为“文革”文学微观性文化研究的开展立了标杆。
上述研究方式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必会激起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它脱离了文学研究之“文学”根基,是在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为中国文学“做手术”,并不能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的发展做出实质性推进。但如上所述,“文革”文学的文化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霸王硬上弓”地对其进行审美分析反而是一种错位。与其如此,何不换个思路试试?况且,理论的产生和应用有它的普适性,使用西方理论不见得一定就是在“简单套用”。
①高默波:《起程——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见北岛、李陀:《七十年代》(下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②网易博客:《谁该为“文革”道歉》,2014年12月22日,http://blog.163.com/hot/400/?Touping.
③钱振文:《〈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赵勇:《正气,匪气,或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杨子荣形象塑造简史》,《文艺争鸣》2014年第7期。
作 者:魏建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编 辑:孙明亮 mzsul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