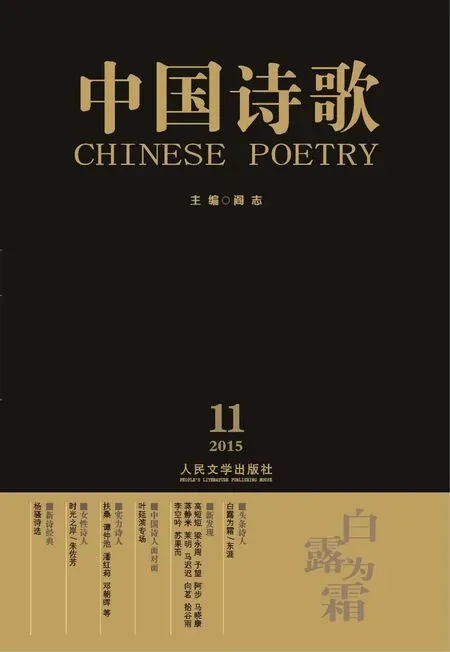野地独酌〔组诗〕
2015-07-07马晓康
马晓康
野地独酌〔组诗〕
马晓康
MA XIAO KANG

1992年生,祖籍山东东平,留澳七年。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山东诗人》等。出版诗集《纸片人》、译著《当代世界诗人诗选》(英汉双语版)等。有作品入选《2014中国诗歌排行榜》、《新世纪好诗选》、《华语诗歌年鉴》、《山东诗典》等选本。获首届“岷州杯”全国诗歌、散文大奖赛优秀诗歌奖,被评为2014年度《时代文学》十大新锐诗人。
我想擦一擦父母头上的雪
二十三年了我才注意到
躲藏在父母鬓角里的冬天
这是违反季节常识的现象
它忘了随着自然去轮回泯灭
为了寻找放逐它的方法
我只好
把记忆倒带回七年前——
法定年龄不足十五岁的那段时间
他们的音容没有改变
只是不经意时没有躲开——
雪花洒满的人间
父亲的冬天在牢房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迈不出的墙
不到三米的房间里除了鹅毛只有铁窗
母亲的冬天在旅馆
史书和病体只能用来电话记录
她最牵挂的两个男人一个看不见一个够不着
我不知道自己算什么
败家子砌砖工皮条客还是杀人犯
哦对了也许还是个大学生
我时常羡慕别人的棉衣
却不知道他们的肉体拼命榨取着谁的温度
世界更冷了
还好我不愧对良心
万能的主请再赐给我一点儿力量一点儿就好
让我咬断这一身镣铐
再次举起双手……
擦一擦……
父母头上的雪……
行山记
山借我一双眼睛我便学会了俯视
当我想起该仰望些什么时
却已失明
是呀,我只是人
一个墨点便可替代的无数个人
随着山呼吸每一口气都化为沸水
不得不扶着镂空的老树
把强心剂注入心脏
青草轻佻地告诉我在尽头
有只老铁笼在吱呀作响
白鸟白鸟飞
再也看不到
不张之世
把左手的错推给右手
让大脑也变成帮凶
欲望们轮流执笔
睁开一千双眼也无动于衷
这城实在太耀眼
我只能先熄灯
怕有人认出自己
只能把人群丢在垃圾桶
一万个人骂我不争气
所以我想写点儿东西
看看文字之下藏了什么脏东西
主啊!我早已知晓
杯子里的水掺了黄连还是蜂蜜
迟到或早退都没有关系
泛黄老纸上有最纯的文字
我没有生病更不需要怜悯
窗帘轻轻地合起
让每一个缝隙都痛不欲生
它何时变成魔鬼的奴隶
我和躺着的我换了换位置
影子也可以竖着活在阳光里
房子没有根
却比树木活得更长
自我被埋在地底
把身体切成蜘蛛网
从塔尖到狗尾草
能捕捉到何等的慌张
去潍坊
1
这个清晨没有酒只好饮一场雨来解渴
也让那些盘中米粒可数的人借雨水煮一顿饱饭
咖啡也煮好了街上的蘑菇们沸腾起来
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白糖被黑色替代
路边的求助者同时收获了我的善良和憎恶
搜刮着为数不多的温暖好让冰川纪提前到来
我并不贪婪只是游走在天平两端
白色凤凰展开了翅膀告诉我乌云已被驱散
2
马现光先生的腿断了
于是乎接上了一截诗歌
——风自蛮荒之地
——吹断夸父之杖
喝酒的时候他拄起了拐
伤痛好像被捅得很远
3
在八十年代的老楼里喝二十一世纪的酒
谁又知道这里曾是整个市的头颅
坐在年轻人群里惟一的老人在耍酒疯
不走谁都不能走妈了个逼的
都给我留下喝酒干喽都干喽
父亲说呵
在八十年代的楼里居然又喝到了八十年代的味道
野地独酌
野地其实也不算是野地
只是长过三千五百万荒草
天不管地不管就都枯死了
今晚有人哭了我看到了这座城——
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睡得那么坦然
就好像七十七年前的三次空战也只是——
一行字……那么简单
躲进草丛里我一个人偷偷喝酒
买醉的蚊子必须来吸我的血和我——
感受这三千五百万份孤独
星星那么多那么远那么好骗
用水或酒就能把它们诓到碗里
可我还是一个人呐一个人一个不完整的人
来武汉好像没有真的醉过头脑清醒得很
只是听雷平阳老师讲腾冲的时候酒劲上来
忍不住哭了
我想起某个破落的村子有一个抗日纪念碑
上面刻着战争中牺牲者的名字1998年被定性违规
还有一家找了五十年才得以正名的烈属
相关部门只给了一个证至今没有任何补助
我什么也做不了可我真的很害怕
在我看不到的将来是不是和他们一样——
安分地存在于三千五百万后的某个零数
大工业时代,请原谅我抬高了心跳
我们都是植物人把根向深处扎
扎向地心也扎穿你的身体
种下一片灰色森林将天空顶了又顶
模仿齿轮的呼吸转动一生直到分崩离析
不需要表情每一根链条都不会多余
曾经躺在身边的白马飞走了
只有从缝隙中掉落的一具具发了霉的尸体
来不及流出的眼泪汇成一望无际的黑色阴影
对不起在我没被锈蚀以前
请让我听一听天上的声音
整修路段,一株玉米傲立中央
玉米地被劈开了一道口子
左面是临时路段,尘土飞扬
右面是新柏油路,道路保养
一株玉米长在夹缝中,几棵小草是它的随从
尘土里的车辆喇叭不断
每个人都想插队,恨不得飞过去
一株玉米在阅兵
那些死去的玉米是否还活在它的心里
至少还有草陪着
可惜它们的根太短
路边大片的玉米们,它们看不到啊!
任凭乌黑的柏油路炫耀战果
山太慢,来不及喊疼
山头被整个削去
露出它沧桑的脊梁
儿时的记忆也随着被削去
方便面里的水浒传
石头缝里的蝎子
甚至是路灯下的蚱蜢
山太慢,来不及喊疼
这一刀竟割了你十年
何以面对这沧海桑田
只剩下几户老人
守着最后的一点皮肉
山太慢,来不及喊疼
这一哭竟用了十年时间
绿油油的毛发被啃食光了
是一些金属的爬虫
年轻人给它们带的路
到他们初生的山头
山太慢,来不及喊疼
这一怒不知要用多少年。
纸片人
风会不会吹倒他们?
或是一摔就会骨折
也许只需一个不牢固的相框
医生们给出的判断
是过度减肥
是心理扭曲
拒绝进食,拒绝交流
如果纸片人身上可以记录文字
那么
那些厚厚脂肪掩盖的下面
是不是写满了肮脏
点不亮的灯
如果把所有的灯光都熄灭
是不是就能看到漆黑的夜
伸伸手,摸不到任何温暖
就算看着路
尽头也没有取暖的火炉
黑夜是我们的本性,它凝聚在瞳孔
灯光穿不过瞳孔
就像阳光刺不穿深夜
那深处,是一盏我点不亮的灯
醉酒威海卫
在鸡蛋与石头之间我更向往背后那只手
看前面海螺女微笑着一动不动
和被人刻过名字被海水打湿过的脚掌
一样这便是我的立场
刘公刘母不在无人指明方向
落难的皇室不在只有刘公岛上沙哑的炮台
人们赤膊嬉戏早已忘却北洋沉没的炮响
真大真宽岸尽头只有空空
刘步蟾用尽了悲愤也无法染红
借着海腥味下酒饮自己一身锈迹
期待一个更庞大的肉体装下一层层伤痕
落幕时分谁先吞掉了月亮吞掉诗人的故乡
吞吐着百年前的硝烟还戏弄着一个又一个烟圈
我拗不过你但请不要吞掉我的孤独
你若实在想要就拿走吧孤独本是生生不息的植物
细听阿华收到鲜花时的感动以及佚名者的关注
断了枝的桃树会长出新芽荷叶败落也会重新开花
面朝大海我们披头散发做人还是海妖
无所谓头顶上的海藻本就是命运的赐福
前方有漂流瓶上岸是来自九十年代的祝福
写信的人呀是不是也读海子
脚下的土地灯红酒绿海上却寻不到船只一艘
倒在路边的麻雀
我能看到的每一只脚
都让我听到了地面的涟漪声
大地是不是快要沉下去了
可为什么我身体还没有变湿
我清楚地知道我爱太阳
却永远也飞不上去这个夏天
好热天空离我那么近只差——
一个站起来的距离
我吃过无数只虫子如今
幼虫们纷纷破壳而出
它们围着我一旦我闭眼
便将我分而食之
“不要碰它”
一个声音喝止了孩子的手
谢谢你
是的
请不要碰我我只是翅膀断了
请不要碰我我只是流血了
请不要碰我我只是……
我还能飞请不要碰我
那么多粮食和草籽在等我去吃
那么多猎枪和网在等我去原谅
请不要碰我
我是造物主的麻雀
我必须飞
重生
嫩枝的芽尖饱饮昨日勇士的鲜血
残破的旗帜焚在风中呐喊声遁入远去的河流
每一朵鲜花都是来不及回复的信封
同乡的过路者请把这份思念带回家中
蝴蝶起舞草丛和青苔掩住所有铁器的口
树荫依旧会冒出让战火与黑烟封印在灰色相片
人间的欲望冲撞黄昏便开始燃烧
黑夜里有人替我们承受苦难
光明来后蔚蓝空中飘着遗落的白袍
那是为世人赎罪而死的耶稣
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去做神的羊羔
你知道人性不可战胜的软弱不是吗
不请再等等你还需要一个——
一个愿意撇弃一切换取赦免的囚徒
沙漠
也许再过十年我还是学不会世故
享受最多阳光的土地总是最枯涩
一切交给上天进行一次不思索的苦行
有路便走路有水便游水
石子会被碾碎沼泽也会凝聚成形
放弃了草原更放弃森林
这些都不是荣耀
草原上每日都有新生影子忙着相互侵蚀
还来不及关注枯草秋风就到了
只留下一颗传宗接代的种子
巨树要圆滑一些活得久了擅长低头和俯视
高耸挺拔笼罩住所有小树
只有白云能看到巨树偷偷弯着的腰
万般景象敌不过秋风敌不过——
干裂的沙子上仙人掌带刺的一巴掌
空中意象
双脚背叛了脚下的泥土
我只好飞到空中
是谁把渔网撒在了这里
将它勒成一座座坟头
我试着读取墓碑上的名字
却找不到半块石头
这场困兽游戏关乎我云和风
还有下面不会说话的绿色哑巴
就算说了又怎样
我也是同样的又聋又哑
云有许多种但一定会遮眼
白云真美分赃了所有阳光
乌云很丑却给我们雨水的给养
我不再为太阳赞美它也一样发热
我不再为月亮哭泣它也一样哀伤
原来
所有我能看到的都被风掌握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