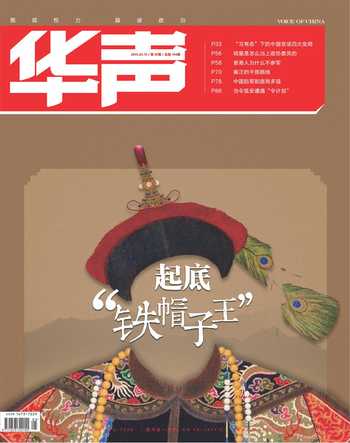历史上那些“任性”的改革者
2015-07-06刘绪义
刘绪义
“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正是改革家所必须具有的智慧。
据信,历史上大凡倡言改革者都是有些脾气的,而且大多数还有着一种牛脾气,用一个时尚的词,就是任性。改革需要“脾气”推动,但细究起来,这种靠任性、强力意志推行起来的改革,往往容易使改革走向另一面。历史上,依靠“脾气”进行的改革最终都是以悲剧收场,改革者个人的命运也惨不忍睹。
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孤傲任性甚至有些偏执的性格不无关系。尽管他看到了黎民百姓的苦难,儒家的道义传统又使他多了一份担当意识,因此,一开始就抱着“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为,人言不足畏”的信念,拒绝一切在他看来有违他改革意旨的人于千里之外,不与水合作,强力推行他的改革。王安石的脾气天下人皆知,他有个外号叫“拗相公”,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西他偏说东,你说东他偏说西。他生平第一个职务就创下了历史之最:淮南签判,做了25年。这是一个什么职务呢,宋代各州幕职,协助长官处理政务及文书案牍,相当于一个办公室主任,从八品。这个职务倒并不丢人,苏东坡也做过,问题是谁能像他做那么长?后来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欧阳修、韩琦等人赏识他,多次说服皇帝召他进京,当钦差来递圣旨时,他竟然躲了起来,钦差没办法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當钦差走后,他又抓起圣旨一路狂追把圣旨送还,从中可见他的“拗劲”。改革中,什么祖宗、天命、人言都没用,天下只有他拗相公一人而已。这样做的后果更任性——害得老百姓被瞎折腾一番,进而影响到南宋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高层士大夫必须做到“内圣外王”,大概是被王安石这类人折腾怕了。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虽然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成效,结果却是招致诸侯“患楚之强”。他走的不是和平崛起的路径,导致原来倚赖于楚的诸侯都害怕楚国的强大起来,视为心腹大患,由盟友变成敌国。在楚国国内,楚之贵族尽欲害吴起。等到支持变法的楚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没地方躲,只好跑到楚悼王的尸体边伏地大哭。然而,那些大臣并没有因为担心射中悼王的尸体而住手,毫无顾忌,连射多箭,结果连吴起带悼王的尸体都中了很多的箭。按常理来说,吴起帮助楚国变法图强,楚国宗族是受益最大者,然而,欲杀吴起者却首推他们。个中原因与吴起的任性有着莫大的关系。吴起的任性到了连亲人都不要,他的母亲死了,都不回家看看;吴起娶的妻子是齐国人,可鲁国与齐国有矛盾,鲁国人因此不信任吴起,吴起正要被鲁悼王任命为将,为了取得信任,吴起赶紧将妻子杀掉。
商鞅也是一个有大脾气的人,有一次太子也就是未来的国君,驾车经过了一道只有现任国君才能行走的御道,一般人都可能会理解太子的作为,但正要推行变法的商鞅脾气很大,决定惩罚太子,借此树威。然而,太子错误再大,商鞅再任性也奈何他不得,只能杀了太子的司机了事。过后,太子再一次犯错,商鞅也只能处罚太子的导师。太子很生气,后果当然很严重。商鞅只好外逃,结果逃到一个宾馆投宿,因为逃时匆忙,没有顾得上带上身份证,结果被宾馆服务人员扭送报官,法官按照商鞅制定的法律(奖励告奸,打击游民)处以车裂,商鞅就这样死在自己制定的改革法制手里,也够滑稽的了。
王莽变法,史称王莽改制,他贵为皇帝,推行改革起来自然要容易得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舆论也是支持改革的。汉哀帝即位后,外戚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他的封国新都,闭门不出。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这一举动立即得到世人好评。人们哪里知道,这是王莽谨慎自保的策略。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后,王莽开始显露出他的任性脾气: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因为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王莽将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又不听劝谏。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罪名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王莽推行的改革,和他的脾气一样,一开始就是装样子,且朝令夕改,大多数只不过是复古求名,比如将奴隶必称“私属”,就有点类似今天我们将卖淫女改称“失足妇女”一样,而且在推行时也不讲方法和手段。
明朝的改革家张居正,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例子即可说明:一位知府年初时就要写好一份计划,且计划的内容不能太少,写好后自己留一份,给张居正一份。如果计划内容过少,张居正就要退回去让他重写。那么,人家只好多写,写多了,年底完不成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降职!他为官之初就效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的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心底里不同流合污,但表面上还是和人打成一片。《明史》说他“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就是有脾气,但不外露。等到大权在握以后,张居正的脾气日益见长。话说一日年轻的万历皇帝在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万历一听,顿时“色勃如也”,吓出一身冷汗。这一声大吼,代表的就是张居正的脾气,也为张居正日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对待同僚下属,张居正的脾气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史载,张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改革开始后,张居正脾气大到十九年没有见过父亲,父亲死了,按制要回家守孝。然而,自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张居正的宰相大人,借口公务缠身,请假不回。张居正死后,万历急不可待地废除了新政。清算他的人便以此为契机,大肆攻讦,成为他的一条主要罪状。
好的脾气来自改革者自身素养,来自于他意识中的民主和自由。民主,不是替民作主、替天行道,而是由民作主;自由,就是你有脾气,也要允许他人有脾气。老子说得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正是改革家所必须具有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