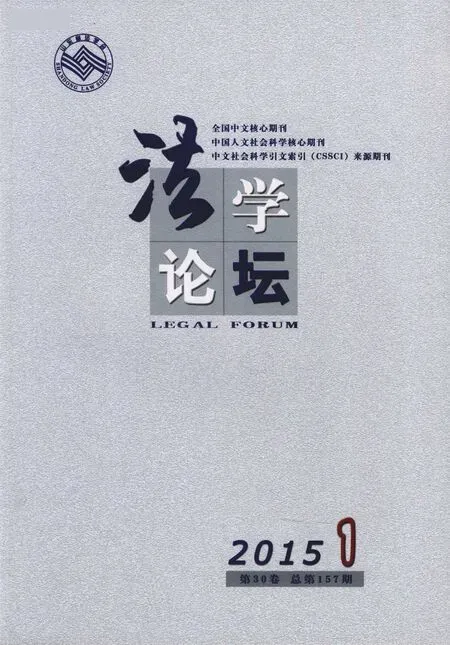论受贿犯罪的几个问题
2015-07-02高铭暄
高铭暄 张 慧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热点聚集】
论受贿犯罪的几个问题
高铭暄 张 慧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受贿犯罪严重危害政府的公信力,需要予以严惩。但是受贿犯罪的复杂性,使得该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尤其是贿赂范围的界定问题,受贿犯罪的数额问题以及影响力的认定问题,都需要在尊重社会文化、刑法基本原则和社会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前,贿赂的范围可以考虑扩大到“财产性利益”。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应该充分考虑情节的评价作用,在对影响力的认定上,要注意在主客观统一基础上的具体分析,仔细甄别。
受贿犯罪;贿赂范围;贿赂数额;影响力认定
《道德经》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行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权力的滥用,导致贪腐犯罪的滋生。日益猖獗的贪污贿赂问题,已经成为危害政府公信力、困扰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受贿犯罪是贪污贿赂犯罪一大组成,严厉打击受贿犯罪,是当前我国的一大要务。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受贿罪和单位受贿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扩大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增加“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从而使“两高”将罪名修订解释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007年《刑法修正案(七)》为弥补原有受贿犯罪规制范围的不足,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到目前,我国受贿犯罪的罪名体系基本形成,包括受贿罪、单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总的来说,受贿犯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类罪,贿赂范围问题、数额问题、共犯与罪数问题,以及主体的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与认定问题,索贿的特征与形式问题以及离职后受贿的性质、受贿款的去向认定问题等等,给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鉴于受贿犯罪的复杂性,本文只从贿赂范围的界定、受贿犯罪受贿数额起点以及情节因素的考量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司法认定分析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贿赂范围
贿赂是权力的滋生物,是公权与私利的交换中介。随着社会的发展,贿赂犯罪的形式不断发展,贿赂范围也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时代特色。而贿赂范围直接决定着贿赂犯罪的犯罪圈大小,反映着打击贿赂犯罪的力度,有着重要的标尺作用,需要予以准确规划与认定。
(一)目前贿赂范围宜限定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
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1979年《刑法》和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将贿赂范围认定为“财物”,《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还将经济受贿条款纳入其中。*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7页。在1997年《刑法》的修订中,“财产性利益”入罪的呼声较高,但是为了防止因界定面过宽所导致的打击面过大,*参见曹坚、吴允峰:《反贪侦查中案件认定的疑难问题》,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版,第132页。《刑法》还是将贿赂的范围限制为“财物”。之后我国《刑法》经过8次修正,贿赂范围未做变动。贿赂范围限定过窄,已经成为当前刑法理论界的共识。但是如何解决贿赂犯罪过窄的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
有观点主张仿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至“任何好处”。认为贿赂犯罪,本质上是制度缺失下的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只要符合权力寻租的行为都可以认定为是受贿行为。基于此考虑,从应然角度来说,贿赂范围可以扩大到任何好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范围界定为“任何好处”,因而出于在国际反腐中掌握主动权,实现与国际无障碍接轨的考虑,贿赂范围应该扩大到“任何好处”。*参见:《性贿赂应入籍刑法》,载《检察日报》2001年3月9日。有观点认为不能将伦理规范任意地上升为刑法规定,主张将贿赂范围扩大至“财产性利益”。还有的观点主张,贿赂的范围应该限定为财产性利益,并且在有限的范围内承认部分非财产性利益(例如信息、资格、学位等)的贿赂性质,并相应地设立“非财物贿赂罪”。当前,坚持原有的狭义贿赂范围,会放纵大量的犯罪行为,严重危害政府公信力。本文赞成将贿赂范围扩大到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则不宜纳入到贿赂范围中来。
一方面,我国当前贿赂范围的确限定过窄,有待扩宽。随着社会的多样化发展,贪腐犯罪的犯罪方式向着更为多样性、隐蔽性和新颖性的方向发展。贿赂内容亦是如此,其表现形式日渐多样性,给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需要对贿赂的形式和内容,或者说对贿赂的范围进行重新的认识与把握。贿赂范围的完善,也是在反腐国际协作中掌握主动权的要求。201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组抽签确定对我国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议,这给我国贿赂犯罪贿赂范围的调整提出了新的紧迫要求。当前贿赂范围的“财物”标准限定过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需要对其做一定的扩充。具体来说,当前贿赂的范围,可以考虑扩大到“财产性利益”。*参见魏东:《从首例“男男强奸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其实,当前我国相关的部门立法和司法解释,就已经将贿赂范围扩大到财产性利益。2007年7月8日“两高”联合公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列举了大量的新型贿赂犯罪,这一意见的出台实际上已经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其他财产性利益。*2007年7月8日,“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十种新型的收受贿赂犯罪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与阐释。即对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收受干股问题、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问题、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收受财物后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问题以及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等的新型贿赂的形式做了规定。2008年11月20日“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样将“一些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贿赂范围之中。而且,贿赂犯罪扩大到财产性利益也便于促进司法实践工作的展开,同时也确保了我国反腐体系、架构和机制的基本稳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严密了我国的刑事法网,有效区分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突出刑事打击重点。
其次,贿赂范围的扩大,不能无限制的扩大到“任何好处”。贿赂范围决定着贿赂犯罪的犯罪圈大小。出于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和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后盾法的地位考虑,刑法规制的范围不宜过宽,尤其是在我国人情社会的大环境下,贿赂犯罪需要予以严格的限制。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大程度上以人情为交换的媒介,馈赠礼物、访问拜会是人与人之间维持特定关系的重要手段。人情文化这一社会文化,根深蒂固且相对稳定,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影响深远。作为社会个体的人,深受这一文化的影响。国家工作人员亦是如此,其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了人情文化这个中国传统的特色文化中来。在人情社会中,好多“人情”的性质与贿赂的区分并不明显,如果将贿赂扩大到“任何好处”,会出现打击面过宽而过度侵入公民私生活的嫌疑,与影响我国几千年的人情文化和人情社会心理也不相符合,可能会导致社会生活与司法实践的混乱。另外,虽然出于刑法国际化和与国际接轨的考量,需要对我国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进行调整,但是也需要在尊重我国当前国情的基础上转化成国内法的形式,而不是生搬硬套。出于避免刑法打击面过宽而对公民私生活造成侵犯的考虑,当前贿赂范围应该扩大到“财产性利益”,而不能用“所有好处”概括。对于其他利益,可以考虑由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等加以规范。
(二)“性贿赂”是否入罪?
从古代的美人计,到现今为获取利益而提供不正当的性行为、性服务的现象一直存在。随着近几年来“性贿赂”事件的不断揭露,“性贿赂”是否入罪问题,在刑法理论界备受关注。支持性贿赂入罪的学者认为,性贿赂并不违背贿赂犯罪的本质,而且基于当前性贿赂的泛滥之势,需要刑法规制,而且性贿赂入罪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否定论者主要从刑法的谦抑性和司法实践角度入手,认为“性贿赂”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一种社会失范行为,这种失范行为应该与犯罪行为有所区分。
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的“性贿赂”行为的确比较多发,但是现阶段“性贿赂”不宜列入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首先,性贿赂入罪会带来司法实践上的操作难题,而且极易导致司法腐败的产生。“性贿赂”的隐蔽性特质使得其在认定、取证上存在极大困难,而且在实践中“性贿赂”的情况往往并不是那么纯粹,有的兼有两情相悦的情人关系,或者是存在转化现象(先有“性贿赂”后发展成“两情相悦”的情人关系,或是先有 “两情相悦”情人关系后感情平淡而出现“性贿赂”),这些情况的判定、时间点的界定等复杂情况的出现,给司法实践的认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退一步讲,性贿赂能够入罪,但是其缺乏具体标准而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规范操作,自由裁量权过大给贿赂犯罪的司法腐败问题埋下了隐患。而且,性贿赂往往涉及个人隐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此类案件不公开审理,极有可能造成司法腐败。其次,承认“性贿赂”还侵犯了女性的尊严。如果承认性贿赂的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变相承认性的可买卖性呢?这是对女性尊严的一种变相的蔑视和侵犯。当前,用党纪政纪来规范限制权力,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处罚限制“性贿赂”,而不必一定要将其入罪。而且在实践中,“性贿赂”往往与其他犯罪糅合在一起,“性贿赂”更多的表现为是一种手段,刑法对“性贿赂”的规制,可以通过处罚相关犯罪行为得以实现。
二、受贿数额问题
与国外不少国家采用的定性的刑事立法模式不同,我国采用的是既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刑法中的许多罪名通过刑事立法或司法解释,对“量”的设置,进行了规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或“数量较大”“数量巨大”“数量特别巨大”的立法和司法规定,是衡量不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程度的重要指标。受贿犯罪亦是如此。本文以受贿罪为例,对受贿罪的受贿数额问题进行分析。现行《刑法》对受贿罪采用了援引贪污罪法定刑的方式,“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383条的规定处罚”。具体来说,现行《刑法》对犯受贿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个人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个人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个人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和“个人受贿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四个档次分别定罪量刑。
(一)受贿犯罪数额起点的认定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即何谓数额?数额与数量是否存在区别,这是需要首先认定的问题。我们认为,数额与数量是存在区别的。从我国刑事立法中可以看出,在针对不同对象时,立法者分别选择数额和数量予以表示。例如,在经济犯罪、财产性犯罪以及贪利性犯罪中,采用“数额”的计量单位,更加强调经济价值的大小;而在毒品犯罪中,则采用“数量”的计量标准,客观的反映数目的多少。数额与数量在法律上的意义与重点有所区别,在刑法上,数额不能包括数量。*参见刘华:《论我国刑法上的数额与数量》,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数额和数量进行区分,有利于刑法的适用性和实践性,也与民众日常语言的表达相一致。
受贿罪作为一种贪利性的财产性犯罪,贿赂数额是衡量其社会危害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极大的影响着受贿罪的罪质程度和刑罚的轻重。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依照贪污罪进行处罚。《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在这里,如何理解“不满五千元”和“情节较重”、“情节较轻”在受贿罪中的罪与非罪问题呢?本文认为,这是对受贿罪在犯罪构成上的适度限制。受贿罪作为一种财产性犯罪,受贿数额是衡量其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贿赂数额存在着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变化,倘若完全不对数额进行限制会导致刑罚的泛化,而且与我国的社会文化和背景不相适应。近年来,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关于贿赂犯罪的起刑点,即起刑数额是否需要调整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在刑法学界,对于此问题,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例如上文所述,受贿罪分“个人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个人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个人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和“个人受贿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四个档次分别定罪量刑。但是,近年来受贿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合理性问题越来越受到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有学者主张受贿罪的起刑点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提高,也有的学者坚持对贪腐持“零容忍”的态度。支持贿赂犯罪起刑点提高的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发现的受贿犯罪呈现出犯罪金额数目特别巨大的特点,动辄几千万、上亿,如果完全按照5000元标准定罪量刑,问题可想而知。*当前在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贿赂数额十万以下的,一万对应一年刑期的情况,还存在贿赂数额十万元以上,几万甚至几十万也对应一年情况,罪责刑不相适应。当前受贿犯罪的起刑点应该提高到3-5万更为适宜,*曾凡燕、陈良伟:《贪污贿赂犯罪起刑数额研究》,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3期。对于起刑点以下的受贿行为,可以考虑以行政处罚等方式给予处理。反对提高受贿犯罪起刑点的观点认为,提高起刑点对于遏制贪污受贿犯罪不利,甚至会助长该类犯罪的嚣张气焰,反腐必须慎重对待廉洁“红线”。甚至有论者基于破窗理论提出对贪腐犯罪的“零容忍”政策,主张将任何腐败行为都消灭在萌芽阶段。也有学者在对极端化的“零容忍”调和的基础上提出“有限容忍”政策。*赵亮:《当代中国防止腐败犯罪刑事政策新论——有限容忍之提倡》,载《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刑法调整》论文集(下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7页。
本文认为,对受贿犯罪采用“零容忍”政策,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非一个理性的认识。刑法是基本法律,必须对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有所反应。反腐问题要避免矫枉过正。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该予以全面的把握,社会体制与政策因素、社会经济和伦理文化因素、法律内部协调问题都需要有所考虑。总的来说,在当前反腐的大背景下,原则上要把住刑法的底线,同时,结合特定地区具体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具体犯罪有关情节的考量,对一定数额以下且具备特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受贿犯罪给予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处理,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对策。*于志刚:《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数额的现实化思考》,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12期。
(二)引申问题——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关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唯数额论者将数额作为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更多的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数额标准在受贿罪定罪量刑中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数额并不是决定贿赂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唯一变量。
笔者认为,受贿数额仅仅是表明受贿人收了多少钱,并不能显示受贿人出卖了什么权力,造成了什么危害和负面后果,情节因素在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中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对于受贿犯罪,应该建立“数额+情节”的评价体系,数额与情节共同起作用,进而实现在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基础上的问罪与追责。目前,在刑法立法中,对于受贿犯罪的起刑点进行了明示数额的规定,这种规定导致灵活性不足,而且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对情节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够。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在立法上作出修改。在立法上,应该放弃对起刑点等数额的具体规定,建立情节和数额的共同评价体系。以受贿罪为例,立法上可以规定“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予以处罚”。可以考虑分为受贿数额较大或情节较重的,受贿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的等不同情况予以规范。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正是这样考虑的。该草案拟删去对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这种修改,既简洁又规范,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当前复杂的贿赂犯罪对司法实践提出的考验,实现罪刑统一。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的简洁性将给司法解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解释势必要对刑事立法条文包含的数额和情节作出具体解释,以便增强可操作性。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影响力”的认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寻租的方式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特点,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受贿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躲避法律制裁敛财的主要手段。2007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一直游离于犯罪边缘的“裙带关系”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严密了受贿犯罪的犯罪体系。但是我国“人情社会”的社会特色给该罪的司法适用带来了不小的难题,与其他的受贿犯罪相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关条文规定得过于模糊,对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关系密切人的规定过于笼统,对该罪的共犯认定和与其他犯罪的区别规定得不甚清晰,这些都影响到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司法适用。如何在尊重社会文化和心理、契合法律精神、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该罪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良好适用,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从“影响力”的角度入手,对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内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影响力”进行认定。
(一)利用影响力犯罪之主体界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但是成文法背景下法律语言的原则性、简洁性特征,使得该罪犯罪主体和“利用影响力”的界定与具体操作,存在不小的难题,也给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把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界定。对“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进行界定,分解来看,包括对“国家工作人员”与“近亲属”两个概念的界定,国家工作人员是近亲属的一个限制性定语。《刑法》总则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做了解释:“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明确之后,剩下的问题就体现在对“近亲属”范畴的把握上。
亲属,一般是指具有血缘或者婚姻关系的人。近亲属的这一概念,在不同部门法中都有所涉及,但规定并不一致。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将近亲属规定为“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将民法中的近亲属解释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4条中的“近亲属”解释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由于不同部门法对近亲属的解释不同,刑法在适用中选择哪一解释,抑或刑法对近亲属的认定倾向于哪一解释,在刑法学界有不同的见解。当前比较多的学者主张,刑法中近亲属的认定,范围不宜过窄。本文也持上述观点。《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游离于犯罪边缘的“裙带关系”加以规制,目的在于惩治特定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出于打击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现实需要考虑,《刑事诉讼法》中近亲属的范围需要予以适当扩大。而且在刑法适用中,近亲属的认定,需要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和观念相符合,这是现实合理性的要求。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近亲属——“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的限定,范围明显过窄,不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现实合理性较差,范围需要加以适当扩大。具体来说,目前“近亲属”的范围,可以考虑扩大到民法对近亲属的界定上。即在利用影响力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应该涵括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2、“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是一个兜底的条款,是对除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外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主体的兜底规定。刑法学界有学者对这一表述有所批判,“将关系密切的人这样具有巨大解释余地和空间的模糊性术语写入刑法,容易导致犯罪圈的弹性过大,这会是司法实践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于志刚:《关于“关系人”受贿的定罪规则体系的思考》,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4期。密切是对关系的程度的限制,那么如何认定“密切”关系的性质与程序呢?
首先,“密切关系”是指一种社会关系,并不存在合法与非法的区分。例如,情人关系这一不道德关系,事实上就可以被认定为密切关系。“密切关系”的认定,重点还在于对密切这一程度的把握上。“密切”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缺乏量化的标准,在认定上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结合具体的外在环境和客观条件予以具体把握。到目前为止,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关系密切的人”做出相应的解释,只是对类似的概念——“特定关系人”进行了解读界定。2007年“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特定关系人”认定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有学者认为,“关系密切的人”外延大于“特定关系人”,“凡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血缘、亲属关系,或者情妇(夫)关系,或者彼此是同学、战友、老部下、老上级或者老朋友,关系甚密,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影响的,都应当认定为关系密切的人”。*孙国祥:《贿赂犯罪的学说与案解》,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10页。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设立的初衷,在于对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影响力”寻租行为予以规制。“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应该大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如下图所示,其他关系密切的人的范畴包括和大于特定关系人的范畴。

当然,对“关系密切的人”的把握,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实质的分析:第一,根据当事人的身份进行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某种身份,可以作为考证是否具有密切关系的推定或者证据线索。需要注意的是,要对身份关系进行分类认定,例如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关系,通常可以推定为具有密切关系。而其他的身份关系,例如同学关系、地缘关系等,则只能作为一个证据线索,而不能直接推定;第二,密切关系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相互交往关系的具体情况、信任程度以及利益方面的关联等,予以评判和把握;第三,从行为反推,即从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加以判断,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事实上实施了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则不论结果如何,可以判定关系的密切。
3、“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类人员,有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其原本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即在上文所述的国家工作人员范畴之内;另一层,该工作人员已经离职,其离职的方式既可以是退休、离休,也可以是辞职、被辞退,不论其离职时间的长短,只要其离职之前有一定的职务,是国家工作人员,即构成本罪所说的“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该犯罪主体只有在其离职之后,利用其在职时所形成的影响力受贿,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否则,不宜认定为此罪。
(二)“影响力”的判断
如果说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职权受贿是一种刚性的权力腐败,那么利用影响力受贿可以说是一种软权力寻租。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把握的重点,在于影响力的客观存在且犯罪行为人利用了该影响力。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需要在程度上认定是否达到“利用影响力”,这就涉及到利用影响力的判断问题。
1、“影响力”是一种客观事前存在判断。 影响力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影响或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一种能力”。*李德民:《非正式组织和非权力性影响力》,载《中国行政管理》1997年第9期。关于“影响力”的判断,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影响力的判断是主观判断还是客观判断,是事前判断还是事后判断?
笔者认为,影响力的判断,是一种客观的事前判断。首先,“影响力”的判断,是一种客观判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就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在关于影响力的表述中,采用了一种客观的判断模式,规定影响力是“实际”或者“被认为具有”,而且这一客观判断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所以被规定为犯罪,根源在于具有“议亲”嫌疑的该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一群体,本身就因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而成为一个有着特殊能力的特殊群体,这不取决于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其影响力的存在,也不要求行贿人主观上意识到这种影响力是一种总的客观的存在。当然,尽管这一影响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判断,仍需要一定的判断主体的存在,即以社会上一般人的立场进行判断即可;其次,“影响力”判断是一种事前判断。影响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能力。影响力判断是对“密切关系”的一种深化理解,行为人在被认定为“密切关系人”之时,事实上已经做出了肯定影响力存在的判断。也就是说,行为人的影响力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处于一种待启动的境地。总的来说,影响力的判断,是一种事前的可能判断,而不是事后的认定。
2、“影响力”的判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现行《刑法》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定和描述,在该罪中,利用影响力的情况,可以具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的影响力判断,一类是其他关系密切的人的影响力判断,另一类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判断。这三类人员影响力的认定标准和程度有所差异,在实践中要予以具体把握。一般来说,基于亲情、血缘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可以说具备“当然”的影响力;“其他关系密切的人”的影响力的判断,要求具体特定的身份和特定的关系;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要求其在任时的职务或职位等给其离职后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且具有“足够”的特征。
[责任编辑:谭 静]
Subject:Several Issues on the Crime of Bribery
Author & unit:GAO Mingxuan,ZHANG Hui(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
“Things must first rot before worms”. Crime of Bribery do harm to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seriously, which need to be punished. However,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crime of bribery,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bribery, the sum of bribery and identify of the influence, all need to be analysis on the basic of respecting social cultural,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and social practice. Currently, the scope of bribery may expanding the “property interests”,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hould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role of evaluation of the episod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fluence should analysis detailed on the basis of the unit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he crime of bribery;the scope of bribery;the sum of bribery;the identify of the influence
2014-11-28
高铭暄(1928-),男,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方向:刑事法学;张慧(1986-),女,山东潍坊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刑事法学。
D924.3
A
1009-8003(2015)01-007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