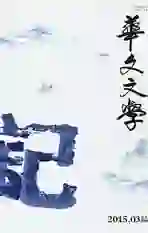论容闳自传中的记忆政治
2015-07-01潘敏芳
潘敏芳
摘 要: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1909年发表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记录了他为祖国的富强而殚精竭虑的追求历程以及因此所从事的外交、政治、教育等活动。在自传中,他开启了独特的记忆机制,既表现了时空交织的个体记忆,也表现了渴望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从他在自传中试图搭建东西方沟通桥梁的努力中可见,他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表现出杂糅身份的特点,隐藏着作者的归化意识。
关键词:自传;容闳;记忆政治;杂糅身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3-0045-06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社会开始了变革的历程,其中之一是派遣留学生去欧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之前,去到欧美等国接受教育的留学生可分为两类:一类通过自己的途径出国留学,或亲友资助,或美国传教士资助,如孙中山、容闳等;另一类是清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如李恩富、詹天佑等。晚清留学生作为和西方文明、文化直接遭遇的主体,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的自传作为记忆的载体,真实再现了他们的困难和渴望。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1909年出版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①跨越了1835至1902年期间的岁月,记述自己为实现祖国文明富强而殚精竭虑的追求历程以及因此所从事的外交、政治、教育等活动。容闳的自传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而自传中作者对于历史与记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反思则少有人提及。本文拟通过细读《我》,探讨该自传中所体现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思考记忆主体的杂糅身份的表征及意义,以及作者在杂糅身份中体现出来的归化意识。
一、华人男性气质的个人记忆
容闳自传通过书写历史寻求的是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并重新审视历史,建构自己独特的个人记忆。他的书写处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这个特殊的时空里,他所要对抗的是美国主流社会对于华人男性的刻板印象,他的个人记忆凸显出时代性并显示出对抗性。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期,几乎有一百万人从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印度移民到美国和夏威夷。他们被主流社会看作是“苦力”(coolie)、“黄祸”(yellow peril),永远的“异教徒”(Heathen),“不可同化者”,而中国国内的男子则是“东亚病夫”、鸦片吸食者。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出现了排华浪潮,以加州州长比格斯为代表,将华工视作“黄祸”,叫嚣“华工必须滚”,1882年美国政府甚至出台了正式的排华法案。早期的华工在排华浪潮中处于失语状态,只有少数华人,如留学生群体、外交官等通过创作将自己的记忆文本化以抵抗华工的失语状态。1887年,李恩富发表自传《我的中国童年》,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1889年,他发表短文“华人必须留下”以反驳当时美国社会甚嚣尘上的排华浪潮。1909年,容闳发表的《我》通过个人记忆的回忆和重构功能抵抗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
在自传的第一章“童年时代”,容闳回忆了自己去教会学校的原由,校长郭士力夫人将他安排进了女孩子的一个班,容闳写道:“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我幼小无助,远离父母。此外就是我是学校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把我和女学生安排在一起,不允许我混杂在那时还为数不多的男孩子当中。”不光如此,“我和女孩子们都不得出门到街上去玩耍,而那些住在一楼的男孩子,却有充分的自由出去活动”②为此,他策划和女孩子一起逃跑,并几乎成功。他随后得到了“逃跑主犯”的罪名。
不可否认,容闳的回忆是立足于现实的回溯性行为,建立在现实与过去的差异之上。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容闳清楚美国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要求。从古希腊开始,“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捷,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为此,西方世界特别重视体育运动对于高尚道德的培养。而中国传统社会要求的并不是具有强壮体魄的男孩子,而是有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的五常要求的男性,正如李恩富在自己的自传《我的中国童年》中写道,虽然中国没有“能使肌肉发达、体态优雅、生动活泼的所谓运动”③,但中国的孩子也有很多运动形式,这些运动也能锻炼他们的体魄。同时,李恩富也指出,安静是中华文化对男孩子提出的要求。
理查德·森尼特认为,记忆有回忆和重构功能,这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我们回忆的能力可以警示或非难我们对过去所编造的故事……我们赖以塑造记忆的这些故事反过来促使我们回忆某些意象或事实,而把其他的交给神经的垃圾堆。”“重构导致回忆”④。很显然,容闳在回忆中注意到了中西文化对于男性气质定义的差异,所以,在记忆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重构,以符合白人社会的期待。在郭士力夫人试图将他归类为女性,泯灭他作为男童热爱户外活动的天性时,他没有默默忍受,而是直接反抗,反映了华人男孩的聪慧、英勇和敢于反抗强权的优良品质。在家境困难之时,容闳开始“叫卖糖果”、“拾落穗”、用自己的英语知识获得奖赏,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职责。在耶鲁学习期间,他也不忘锻炼身体。1859年容闳亲访太平天国领袖,后冒险从太平天国占领区运出数千磅茶叶,这次经历使他获益匪浅,“我却从中得到了几笔比金钱更有价值的财富。例如我在这项事业中所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的精神、成功完成任务的坚强意志、敢于迎着异常困难及危险从事很少有人愿意做的事情的勇气。”⑤在美国水手欺侮中国人时,容闳和他们理论并要求他们道歉,“并告诉他在中国的美国人,很受人尊重,因此每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人,都应当小心翼翼地去爱惜他们在这个国家所受到的高度评价,而不要做任何有损于自己名誉的事情。”⑥身材高大的苏格兰人取笑他并出手打他时,他敢于“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他相信“天赋人权”的道理,“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的权利遭到侵害,他们就会产生道义上的勇气去维护和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利。”⑦
容闳在回忆中重塑自己的性格时,不自觉拉开了记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因而与美国社会对于华人形象的集体记忆形成对抗。其原因在于:第一、容闳的记忆文本不一定是真实历史现实的反映,而更有可能是对记忆的理解和重构。第二、容闳是一个知名人物,他的记忆会参与集体记忆的创造,正如赵静蓉所说:“从记忆研究的角度来说,其(传主的)特殊性体现为他们的身份是含混暧昧的,既为单独的个体,又是某个群体的代言人。”⑧因而他在传记中有可能主动修正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能被大众接受、且能流芳千古的形象。容闳为突出再现自己的男性气概,再现了自己与美国白人女性的跨国婚姻。他1875年和美国妻子克洛小姐(Louise Kellogg)结婚,杜吉尔牧师坦言:“他们的结合已引起许多议论,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竭力反对,也有人(像我一样)高兴这桩婚事。”⑨他的婚姻打破了美国社会的反异族通婚法案和晚清的婚姻禁令,他自己将娶美国妻子看作他的“幻想得以实现的又一佐证”⑩,从侧面表达了华人男性渴望通过和白人女性联姻来“宣称自己是美国人”(claim America)的愿望。
但是,容闳生活的美国排华浪潮甚嚣尘上,“黄祸文学”应运而生。黄祸文学的代表杰克·伦敦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他将故事设置在1976年,中国人通过自己不可超越的人口试图统治世界,最终死于美国的生化武器。该小说表达了当时社会排斥华人、丑化华人的倾向,与当时美国社会对于华人的集体记忆不谋而合。但是,哈布瓦赫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1}容闳在自传中塑造热爱运动、不畏强权的华人形象来抵抗集体记忆,从而暴露集体记忆的荒谬性,并为自己的个人记忆创造存在和延续的空间,使之成为反抗偏见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他的策略虽然忽略了中华文化对于男性气质的传统要求,但是它颠覆了“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对华人男性群体的气质建构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二、华人归化美国的集体记忆
晚清的留学生处在时代变革的最前沿,他们只身前往美国学习,能更真切地对比中美文化的差异,同时帮助中西方进行有效地沟通。早期的中国留学生属于离散主体,他们时常体验着黄秀玲所谓的“过时的挣扎”,“所谓‘过时的挣扎,是指亚美学者已对它相当熟悉,或是说它已被更顺应后结构和后现代词汇的议题所取代了。”{12}“过时的”挣扎其实一点也不“过时”,对于少数族裔主体来说,他们迫切渴望归化进入美国,当处于中美之间的夹缝地带时,他们更强烈地表达了这一愿望。
容闳的自传作为晚清留学生生活记录的经典文本,既是早期的华人移民的个人记忆,也是早期留学生、华人移民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在定义集体记忆时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13}当记忆的个体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身份处境时,集体记忆就会应运而生。《我》记录了作者皈依基督教的事实、教育救国的历史和跨域流散的历史,成为华人归化进入美国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容闳七岁时进入澳门的教会学校。1846年,勃朗教士打算离开中国,他“很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一同赴美,使他们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14},为此容闳得以有机会来到美国继续学业。对于勃朗教士带中国孩子回国一事,沃思认为他不可能带异教徒回美国,暗示容闳去美国之时已经信奉了基督教。但是,容闳从耶鲁毕业后,拒绝回到中国传教,他在自传中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其中第三点写道:“这样性质的誓约,将会妨碍我利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机会或事件去为之尽自己最伟大的奉献。”{15}容闳此时的矛盾心态赫然在目:首先,他通过皈依基督教表达归化美国的决心。尹晓煌认为容闳成为基督徒证明了他的美国化程度。{16}无独有偶,在容闳之后留学耶鲁的李恩富也皈依基督教,甚至为信仰基督教的事情和另一位华人王清福掀起论战。他们的皈依既是对西方文化的臣服,也展示了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生存策略,那就是通过宗教融入美国生活。容闳的自传中贯穿着基督教的精神,他以基督教的热忱献身于中国的崛起,并将美国看作自己的“第二祖国”,通过信仰基督教表达他已经美国化的事实。但皈依基督教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离,意味着他们脱离了文化母体,成为离散在外的华人。
但是,另一方面,容闳充分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与她的文明一样,带有一成不变的难有显著突破的民族性的印记”{17},因此基督教很难改变中国人们的信仰。以基督教名义进行的太平天国运动,只不过是一次“宗教狂热”,在两广地区和南京都没有留下“基督教的踪迹”{18}。所以,容闳虽然认为基督教代表了“伟大的真理”,但是他毕业后拒绝去中国传教,转而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
记忆的目的不仅在于回忆过去,而且在于重建过去,表达诉求。哈布瓦赫提出“记忆的集体框架”概念默认了集体记忆的存在,他将同一个社会中不同成员的记忆组合在一起,每一个个体的记忆都将充实这个集体记忆,而且,个人记忆表现出与集体记忆的高度吻合性。信仰基督教是容闳等华人归化进入美国时面临的相同经历,是他们的生存策略之一。在归化的过程中,华人清楚认识基督教在中美不同文化中的接受情况,并乐于融合两者之间的差异。相同的经验创造了一种凝聚感,这种集体共享的记忆反映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艰难历程。
容闳被取消美国国籍一事则是属于早期华人无法入籍美国的另一个集体记忆。容闳求学耶鲁时,于1852年10月30日在纽黑文(New Haven)加入美国国籍。他在自传中坦承自己1854年从耶鲁毕业时:“作为第一位中国人从美国第一流大学毕业,消息一传开,我自然是相当引人注意的……而我的国籍,理所当然地为我的事迹的流传和普及更增添了诱人的情趣。”{19}仅此一笔,就把他归化进入美国的事实一笔带过。但是容闳的美国国籍并不是可以终身使用的。事实上,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几年里,他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埃德蒙·沃思(Edmund Worthy)论述了容闳被取消国籍的背景{20}。1870年美国通过的《国籍法案》规定,华人没有申请公民的资格。1882年美国实施的《排华法案》规定,不能归化为美国公民的任何人在离境后不得再次进入美国,根据这两项法案,19世纪90年代身在中国的容闳不被认为是美国人,而只是“侨民身份”(alien status)。但是容闳在自传中并没有提及此事。在容妻去世至1895年的时间里,容闳与中国政府几乎断绝往来,留居美国,他在自传中略去了这段与文化母国思想抵牾的时间。至于1899年至1902年的逃亡经历,容闳在自传中只是简要地写道:“1899年,为了我的人身安全,有人劝告我必须换个地方居住。于是我离开上海,迁至香港,置于属英国人管辖区域的保护之下。我从1900年迁居香港直到1902年返回美国,当我抵美时,我的小儿子巴特利特·G·容刚好从耶鲁大学毕业,我正赶上观看他的毕业典礼。”{21}
美国著名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在评论汤亭亭的《女勇士》时提出了“再记忆”的概念。“再记忆”指的是“建立在作家个体记忆之上的一种创作性记忆,所以说再记忆是一种新的叙述。”{22}在“再记忆”的过程中,作家发挥充分的主观能动性,选择记忆什么、再现什么。他们拒绝简单地复制或一股脑儿不加选择的再现。容闳在自传中利用了记忆的遗忘、重构等功能,表达了自己对美国身份的渴望。他在自传中讲述了自己为中国所做的种种事情,如为曾国藩购买机器、创办江南制造局、调查秘鲁华工、19世纪后期试图创办国家银行和铺设铁路等,尹晓煌认为“容闳对中国进步的强烈兴趣与其说是因为他关心祖国命运,倒不如说是出于想提高美国华人地位的愿望。”{23}他的行为表现的是他的美国性而非中国性。他在老年时期积极地回忆过往,通过记忆回访过去,再现了自己身上所体现的美国性,并梳理了自己对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显示出认同美国的强烈渴望。因此,在容闳的自传里,读者读到了一个对中国教育事业满怀热忱、且兼具美国精神的教育家形象。他说的是中国的事业,渴望的是美国身份,反映了早期华人移民渴望融入美国社会的集体记忆。
三、记忆主体的“杂糅身份”
容闳在自传中塑造的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属于他的个人记忆,同时,作为中国早期出现的具有主体性的离散主体,他与自己家园和居住国之间的关系暧昧,他渴望成为“优秀美国公民”,更渴望中国的进步能帮助自己成为“优秀美国公民”,体现了早期华人希望归化美国的集体记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交织,体现了作者作为跨越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华人,在试图搭建中美沟通的桥梁时,身份上体现出的“杂糅性”,这是大多数华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象。
巴巴将“杂糅性”定义为“杂交性是通过重复歧视性身份结果而对假定的殖民身份进行的重新评价”。{24}赵稀方将“杂糅性”归纳为“杂交指的是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理论上,它与泾渭分明的本质主义者和极端论者的二元对立模式相对立。……从批判殖民话语的立场上说,杂交的效果主要是动摇了殖民话语的稳定性。”{25}可见,“杂糅”在后殖民语境下指的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文化相互渗透的结果。在亚裔美国文化语境下,则表现出中西文化水乳交融的特点。林英敏称之为“世界之间”。其实不管是“杂糅性”、还是“世界之间”、抑或是“跨域书写”,体现的都是早期华人在“脱亚入美”过程中的情感结构。王智明认为:
“作为国家政策一部分的留学运动,与中国遭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经验和国族情绪是不可分割的。出洋留学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新的主体性与情感,并在‘脱亚入美的过程中加速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从而深化了中西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26}
在王智明看来,这个“新的主体性”就是“翻译的主体”,容闳就是“新的主体性与情感”的重要代表,其翻译主体性“不仅在于强调其生命/自传的跨文化向度,更是想透过翻译机制来凸显亚洲生命在殖民现代性底下的挣扎与转化。”而王智明所称的“脱亚入美”情感结构,“不只是亚洲对西方的臣服,它同时也意谓语言交换,文化交流与政治协商等种种问题”。而在中西方的交流中,文化必然被协商,中国文化因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异域环境里也不可能被根除,跨文化的亚裔主体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杂糅的身份。
这种杂糅身份必然影响记忆主体在不同语境下的身份展示。容闳在自传中详细描写他在中国恪守孝道的事迹,例如他回国后跪拜母亲,耐心向母亲解释耶鲁学位的价值等,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孝顺尊重,符合中国传统的孝道。但是,杂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留母国的文化,而是作者渴望以杂糅求同化的努力。容闳在书写中借杂糅表达了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求同,进而归化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愿望,为此他征用了西方的文学体裁和意识形态。
容闳在创作中采用自传形式表现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学的影响。自传作为基督教徒阐述自己与上帝的交流的历史由来已久。艾布拉姆斯(Abrams)认为“第一部最完整的自传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写于公元四世纪”。{27}另一部重要的自传是卢梭的《忏悔录》。在这两部自传里,自我是对抗的势力战斗的舞台,其中一股势力高潮性的胜利(精神战胜肉体)终结了自我的戏剧。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自传传统计划鲜为人知,因为在倡导谦和的儒家学者眼中,写自传会被视为妄自尊大。”{28}容闳在开篇就写道:“1828年11月17日,我出生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之西南的南屏乡”{29},从而以传主的身世拉开的自传的序幕,这是他对美国文化传统的尊重。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哎咦——集团”在编写亚裔美国作家选集时,拒绝将容闳的自传收录其中,其理由在于:他们认为,这些作家(包括容闳)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在于都是“基督徒的传记或自传体小说”,践行的是“基督教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白人种族主义的爱”,并把他们归为“假的”亚裔美国作家。容闳的自传一直以来被看作历史资料而非文学作品,其作品的文学价值较少为评论者所讨论,但是,相对于其他被“哎咦——集体”所排除的作家如刘裔昌、黄玉雪、谭恩美等,容闳所再现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不是“白人种族主义想象的产物”。由于容闳早年在美国接受教育,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他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文学经典的影响,选择自传作为文学创作体裁也是顺理成章。同时,自传的文体预设了记忆的可靠性,赵静蓉将“可靠性”定义为“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关乎现实。”{30}。容闳的自传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文学创作,是西方文体的中国化,或者说是中国人经历的西式表达,体现了作者杂糅中西两种文化,进而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了解早期华裔移民的愿望。
容闳的自传体现了美国所推崇的个人精神,而非中国儒家学者“家天下”的处世规范。儒家学者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修养。容闳在自传中表现得相当入世,体现了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美国著名哲学家爱默生在超验主义哲学中首倡“个人主义精神”,“超验主义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个人使社会的最重要的组成因素,社会的革新只能通过个人的修养和完善才能实现。人的首要责任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刻意追求金玉富贵。理想的人是依靠自己的人。”{31}超验主义对个人的强调主要源于对加尔文宗教观的反驳和资本主义时期人被物化的反弹。综观容闳自传,他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对个人精神的强调,这使他有别于同时期的华人形象,表现出身份的杂糅性。他会晤太平军领袖,提出七项主张;在从产茶区运茶叶时,他被任命为一切运输行动的负责人,并身先士卒,下水挖掘淤泥。他去美国购置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他前往秘鲁拍摄华工受虐的照片,打击了非法劳工贸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塑造了千里走单骑的孤胆英雄形象,表达了作者认同西方对男性气质的要求,并在自传中完善自我,使他成为华裔人群中强调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的首要人物,以此建构了华裔美国移民的新的集体记忆。
容闳的自传描写了早期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再现了受基督教影响的华人移民的人生体验,表达了对文化母亲自强的渴望、并试图融入居住国的艰难历程。因此,他的关于个人记忆的自传演变为早期华人移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之后一批批的华人移民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创作正在丰富着他们的集体记忆,也让后来者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① 学界也将其翻译为《西学东渐记》,该书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本论文取其直译名,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略为《我》。
②⑤⑥⑦⑩{14}{15}{17}{18}{19}{21}{29} 容闳著,石霓译:《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6,69,75,25,15,41,108,114,44,309,1页。
③ 李恩富著,唐绍明译:《我的中国童年》,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④ 法拉、帕特森编,户晓辉译:《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记忆》,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⑧ 赵静蓉:《中国记忆的伦理学向度—对记忆危机的本土化再思考》,《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2期。
⑨ 勒法吉原著,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11}{13}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91,69页。
{12} 梁志英、唐中西、单德兴主编:《全球属性,在地声音:〈亚美学刊〉四十年精选集(上册)》,允晨文化2012年版,第141页。
{16}{23}{28} 尹晓煌著,徐颖果主译:《美国华裔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75,52页。
{20} 参见论文Worthy, Edmund H. Jr.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34, No.3(Aug.,1965), pp.265-287.十九世纪末年,容闳原打算试图利用自己美国公民的身份谋求美国政府的支持,争取在山东修建铁路,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已被取消。后容闳从上海逃亡到香港、再到美国,当时他既不是美国公民,又被清政府悬赏人头。那么他是如何再次进入美国的呢?根据沃思的考证,他是以美国人的气派、大摇大摆地通过海关进入美国的。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
{22} 转引自徐颖果:《文化研究视野中的英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24}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112.
{25}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109页。
{26} 王智明:《翻译的生命:容闳、留学与跨国主体性》,《欧美研究》2009年第3期。
{27} Abrams, M.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p26.
{30}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符号叙事——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记忆的真实性》,《暨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31} 常耀信:《美国文学教程》(中文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责任编辑:庄园)
On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Yung Wings Autobiography
Pan Minfang
Abstract: Yung Wing (or Rong Hong), Father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published his autobiography,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in 1909, a record of what he did tirelessly for the prosperity of China and his diplomatic,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rein. In this autobiography, he initiated a unique memonic mechanism via representing his personal memory interweaving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his desire for a collective memory of identity.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efforts he makes in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his autobiography that his personal memory, interwoven collective memory, is characterized by a hybrid identity, concealing the authors consciousness of naturalization.
Keywords: Autobiography, Yung Wing, politics of memory, hybrid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