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养式创新
2015-06-11同人于野
同人于野
创新的代价除了烧钱冒险,还包括让伟大的公司死亡,还包括容忍坏东西出现。
反击“智能设计论”
我想讲一个关于进化的故事和一个关于垄断的故事,听完你可能会发现,一般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错的。
进化生物学家约翰·恩德勒拿南美洲的孔雀鱼做过一次特别有意思的实验。他搞了十个鱼池来养这种长度只有两厘米的小鱼,每个池子底部有不同的鹅卵石或者碎石图案,并在一些池子中放入强弱不一的捕食者。结果仅仅过了十四个月,各鱼池的情况就变得很不一样。没有捕食者的鱼池中,孔雀鱼多有漂亮多彩的花纹,而那些生活在有捕食者的鱼池中的孔雀鱼却长得非常平庸,没什么色彩,身上的纹路也与池塘底部的石头相一致,显然是一种保护。
看来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文艺青年,长有彩色花纹的雄鱼更容易获得交配机会;而如果连生存都受到威胁,那还是低调点好。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简单实验体会一下进化的智慧。
鱼生育的时候,并不能主动选择自己的后代长什么样,遗传变异完全是随机的。面对自然选择,鱼与鱼之间并非厮打着搞“竞争”,而纯粹是各自分别和环境对赌,谁赌对了谁就生存和繁衍下去。表面上看盲目的变异和赌博似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但这其实是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环境的最佳办法。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你最好还是什么样的后代都随便生一点。
这里的关键词是“不知道”。跟一般人的直觉相反,进化其实是没有方向的,自然选择并不考虑物种的意见,物种能不能适应纯属偶然。进化看似盲目,却可能是在复杂世界中找到答案最有效率的办法。事实上,科学家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用模仿进化的办法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这个做法叫做“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的核心意义在于,如果我们把面对每种具体情况采取的动作,作为其所在策略的一个基因,最佳策略的最惊人之处还不在于哪个具体基因的高明,而在于这些基因之间的配合。让人设计一个基因也许容易,可是让人设计出不同的基因相互配合,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甚至很难想明白为什么这么配合对适应度有好处。
现在遗传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很多实际领域。比如工程师经常用遗传算法进化出来一个形状怪异的天线,它非常好使,可是人类工程师解释不了它为什么好使。
所以生物世界的神奇,也许就是进化论者对“智能设计论”者的一个最好反击。你无法相信有什么智能能把它设计出来,而进化出来的东西比设计出来的东西更厉害。换句话说,你既不知道未来环境会怎么变化,也没有那个智能去设计,所以与其操心给什么东西指引方向,还不如坐等进化的惊喜。
如此说来,进化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创新手段。事实上,进化也许是实现大规模创新的唯一手段。想想如果采用遗传算法来促进中国在某一领域的创新,先随机生成200个小公司……是一种什么景象。
该死就死的市场经济
人们对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常说的是计划经济下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的态度不够好,因为计划经济搞大锅饭,人们干活不为私利就没干劲。但市场经济更明显的好处其实不是商品质量好——至今中国很多商品的质量也不太好——而是商品种类多。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各种层次的需求都能满足。这其中的原理当然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任何人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立即付诸实施,而不必向上级请示,更不必等着上级指导。
市场的关键词不是“为私利”——难道计划经济中人们就是不为私利的?市场的关键在于“不知道”。政府计划不行,并不是说政府不够聪明或者政府的计算机不够快,而是政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没人知道未来会怎么变。市场经济,深得生物进化之道:
第一,随机变异。任何人开公司都是冒险,而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好处是你可以拿别人的钱冒险。没人知道哪个方向肯定对,但如果所有方向上都有人尝试,最后该出来的好东西必然能出来。
第二,自由交配。双性繁殖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神来之笔,它的效率比单性繁殖高出太多了。好东西要互相结合来产生更好的东西。乔布斯说苹果的DNA就是从来不单靠技术,而是让技术跟人文艺术结合。实际上大部分所谓新发明都是把旧的想法连接起来。这里关键还在于,有些东西你单独看它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一旦与别的东西结合就不得了。
第三,无情淘汰。如果环境永远不变,我们绝不可能看到这么多新物种;而当环境改变我们欢呼新物种出现的时候,别忘了有无数旧的物种因为适应不了这个改变而被淘汰了。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显赫一时的伟大公司已经不复存在。谈进化不谈灭绝,谈市场不谈破产的,都是文艺小清新。
所以要参与市场得有这样的精神:想生就生,该死就死。凡是能做到这八个字的系统,不论参与者较量的是商品、体育、艺术还是学术,不管其中有没有价格信号,都能繁荣创新。如果一个系统做不到这一点,恪守传统抱残守缺,那就别想继续发展壮大。
创新就得容忍坏东西
但是中国经济的成绩比纯自由市场经济还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可能在于“知道”。当前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很可能恰恰是因为起点落后。如果你落后于人,你最大的好处是你“知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根本不需要自己尝试,把别人已经证明好使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这时候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一帮小公司瞎搞,而是国家直接组建大公司搞垄断经营,集中力量办大事。你的任务仅仅是模仿和做大,创新是别人的事。
但是当你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自己搞点创新,甚至决心当领先者的时候,也许你还得效法进化搞自由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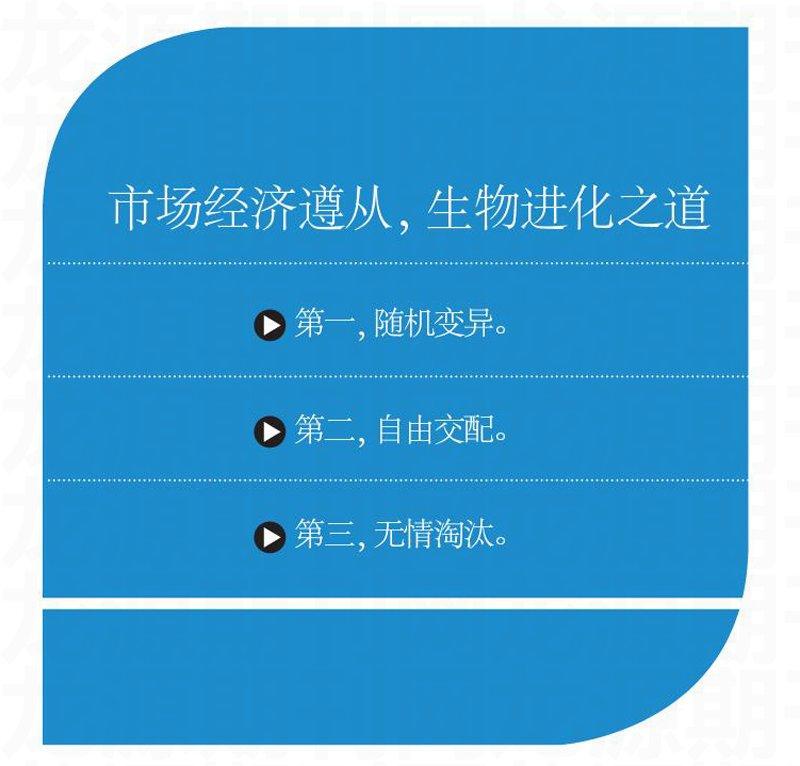
创新,也许是坚持自由市场的唯一理由。一般人以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是有竞争,其实竞争被高估了。考察历史上的著名垄断公司,我们会发现垄断其实很好。
AT&T 垄断美国电话业务的时代不管对该公司,还是对美国人民来说都是一段美好时光。20世纪初 AT&T 主席西奥多·维尔非常反感无序竞争,认为公司最好垄断,而且垄断公司有义务为国家服务。
维尔治下的AT&T把电话线路铺设到了不能带来盈利的边远地区,确保全国用户享受最高质量的通话,而且把电话业务的定价权直接交给了政府。即使因为垄断产生了利润,这些利润也没有直接分给资本家享受,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用于资助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搞基础研究。贝尔实验室给美国带来七个诺贝尔奖,其伟大成就包括晶体管、激光、太阳能电池、计算机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甚至还有天文学。
如果故事一直按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公司做大后变成垄断公司,然后与国家合作,甚至干脆收归国有,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必然之路。但是故事还有一个转折。
贝尔实验室曾经搞出过很多足以改变电话业务的创新。可是这些创新,都被AT&T给扼杀了。
比如录音磁带做的电话留言机,早在1930年代就被贝尔实验室发明,可是AT&T却下令所有相关研究停止,资料封存,包括录音带技术。而这仅仅是因为公司担心人们有了电话录音会少打电话。类似被扼杀的技术还包括DSL和免提功能等。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创新被称为“破坏性创新”:这个东西一出来就把别人的业务给破坏了。谁不希望自己干得好好的业务能够永远这么干下去?而AT&T这个例子说明,哪怕这个新东西对业务的可能影响其实没那么大,哪怕它是自己公司发明的,也不行。所以大多数人谈创新都是叶公好龙,在局面很不错的情况下没人真的喜欢改变。
历史证明AT&T对新技术的畏惧很有道理。有家公司搞了个可以给电话加上静音和免提功能的外设,这个设备一直被AT&T以影响通话质量甚至危害维修人员安全的理由打压。结果打了八年官司之后,法院裁定个人在家里给电话加外设是合法的。以此为开端,很多新的设备进来,电信业进入百家争鸣时代。
这是AT&T衰落的开始。
但那也是互联网兴起的开始。至今仍然有很多人为AT&T这么一个伟大的公司后来被以反垄断为名分拆而深感遗憾,可是你得把这当成是创新的代价。
世界上没有白给的好东西,搞创新也是有代价的。创新的代价除了烧钱冒险,还包括让伟大的公司死亡,还包括容忍坏东西出现。
效法进化,这当中的智慧是随便尝试,等东西出来以后让市场选择,而不是人为先行选择,因为也许你眼中的某个坏东西将来跟别的东西结合以后,恰恰能产生特别好的东西。
在互联网界,这个智慧叫做“先发表后过滤”。你怎么可以仅仅凭自己感觉它可能会造成伤害就禁止它出现?为什么不等它已经造成了伤害再行动呢?
现在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已经超过美国,如果真想像领先者一样做个创新型国家,就不能再有这么一厢情愿的幼稚思维了,得想想我们愿意为创新付出多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