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也都立了,然后呢
2015-0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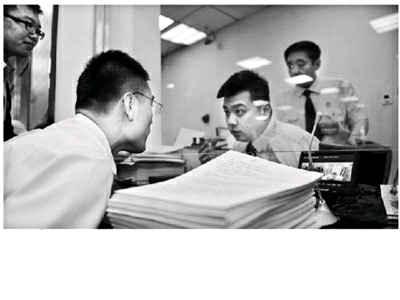
在山东济南,改革后的半个月内,行政案件立案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倍多。可以想象,一些多年来都立不上的陈年老案应该占了相当比例。
“至少有个案子在这儿,行政机关就不能不理你了。慢慢的,政府的法律意识,法院的权威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可能法院就能直接判了。”
南方周末记者 任重远 习宜豪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子懿
发自北京
当事人:法官,我来立个案可不可以?
法官:可以啊!
当事人:我没得工作挣不到钱,想找你们出个主意。
法官:你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当事人:我就是想告自己,立案了,你们就得开庭,总得给我个说法,帮我想出路噻。
法官:……
2015年5月1日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后,上述段子在法官圈中热传。
这项始于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改革让老百姓立案终于变得容易了,特别是常被挡在法院门外的“民告官”行政案件,一些地方增幅竟达十倍之巨。
对一些案件原本就呈饱和状态的法院来说,这意味着空前的工作压力。难立的案子进来了,凭法院现有的资源能否审好?一些法官表示谨慎乐观。
取消立案审查制
立案登记制度的确立,宣告了中国法院实施多年的立案审查制被取消。
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是不是合适,诉讼请求是不是合理,证据提交得全不全,这些原本可以在进入诉讼程序后由法官们审查的问题,要先在立案庭审一道,都符合条件了才给立案,然后转交具体审案的法官。
“其它国家都没这项制度,学界已经呼吁了好多年了。有时候材料不齐的,当事人要跑好多趟,这次补这个,下次补那个,跟医院似的,看一次病挂好几次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亚新说。
在这位民事诉讼法学者看来,法院通过立案审查提高诉讼门槛,和中国法院案件量的急速增长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一审民事案件受案量突破百万大关,1996年增长到300万件,还算比较平缓;1999年是个关键节点,突破500万大关,此后,立案标准就卡得严了些,基本处于缓慢下降趋势,稳定在每年400多万件。
直到2007年后,随着物权法、劳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出台,加上诉讼费用降低,案件又有了迅猛增长。2012年已超过700万件。
王亚新分析,最早的时候,法院是愿意收案子的。“那时候案子少,可以增加诉讼费,也是个政绩,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地位。但后来数量一上来,难以应对了,就开始卡。”
立案尺度松紧上的掌握,和法律的变化基本没有关系——在各级法院普遍提高收案门槛的那些年间,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民事诉讼法,在立案标准上都没有变得更加严格。
特别是“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很多时候不立案也不给理由,不出驳回或不予受理的裁定。即便是在北京,2014年法院行政诉讼的立案率也只有30%。其他地方的一些基层法院,有的甚至几年没有行政案件。
多名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怕的就是法院不收材料,也不出具法律文书——驳回了至少还可以上诉。
例如2007年遭遇强拆的贵州农妇顾光英,曾针对政府拆迁的信息向法院申请信息公开,但从基层法院、州中院到省高院,始终没有受理。代理律师最后不得不到北京,就这样一起简单的案件,向最高法院提起一审诉讼。
这次的立案登记改革即针对上述问题而展开。
最高法院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和申请,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案。材料不符合形式的,要及时释明,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应当补正的材料和期限。7天内无法判定的,应当先行立案。
很多省份的高级法院都向下级法院派了督导组,监督当场立案的情况。一些法院开设了咨询窗口、拿号机等便民措施。
案子多了怎么消化
如先前人们所料,全国各级法院的受案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015年5月,辽宁省全省受理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3.85%。
在山东济南,改革后的半个月内,行政案件立案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倍多。可以想象,一些多年来都立不上的陈年老案应该占了相当比例。
多位学者和法院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四中全会提出立案登记制前,大家都没想过会这么改,而且改得这么快。怎么应对突然增加的案件量?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方案。
“学界是一直在提。但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反馈来看,没觉得会真动,也就没特别研究应对措施。结果中央一决定,很快就全面推开了。”王亚新说。
增加的案件主要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虽然增幅比例大,但整体基数较小,2014年,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只有15.1万件,不到民事案件的三十分之一。
针对民事案件,王亚新认为,除了法院内部挖掘潜力,技术上的应对措施也有一些。
例如物业、供暖等合同纠纷,常常是一个公司对几百上千的业主和消费者,可以合并审理。
“原来尽量不让并案。因为这样就有了数据上的运作空间。分成几百个案子,结案率、调解率什么的就都上去了,也是个业绩。”王亚新说。▶下转第4版
◀上接第5版
这意味着,现有的审限制度可能也需要改革。对于复杂的群体诉讼等案件,应当给予更长的审限。
小额诉讼程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据估算,如果法官使用小额诉讼程序,预计可使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案件得到迅速的处理。
在王亚新看来,需要对法院现有的一些考核指标进行改革。“过去有调解率的要求,法院为了要诉前调解的指标,踢皮球式地让你先走一遍多元纠纷程序,老百姓的体验并不好。以后就应该不看这些。真的繁简分流,把这些措施用起来。”
据接受采访的法官们介绍,目前除了立案和加班多了些外,急剧增长的案件对法院产生了哪些影响,“大概要过一个审限周期后,才看得出来”。
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法院,压力感来得更快更直接。
本轮司法改革的一大重头戏,降低法官数量、提高法官权力、待遇和责任的员额制目前还没推开,已经让不少城市基层法院的年轻一线法官感到压力,甚至有了离职的打算,以至于北京市不少基层法院纷纷出台文件限制法官离职。
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工作量增加最多的恰恰也是他们。法官们呼吁,希望尽快出台保障措施稳定军心。
“两项改革的方向都是对的。但放在一起出,对一线法官们的压力还是太大了。现在涨工资没怎么见着,责任越来越重。”上海某法院副庭长说。
王亚新的担心也与之类似,“不能让法官们成为司法民工”。
“民告官”还是 老大难
如果说民事案件立案门槛的卡紧主要因为案多人少,开门后可以通过法院内部挖掘工作潜力来应对;行政诉讼则涉及整个社会的权力生态,案子立上以后,法院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6月1日的《人民法院报》刊登了一篇《怎样正确理解立案登记制》的评论,认为行政诉讼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社会转型法律规定不明确等原因,也导致有的法院有时选择性立案,将一些棘手案件拒之门外。
在一位上海基层法院副庭长看来,现有的行政体制下,很多案件其实超过了法院的解决能力。
“虽然这轮司法改革的精神是要树立法院的权威,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但一些复杂的案件,涉及当地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政策,有很多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在里面,光强调法律权威,让年轻的法官就那么直接去判,是不现实的。法院也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
比较典型的,是近期一审宣判的安徽花炮企业整体关停案。2013年12月27日,安徽省政府发布45号通知,要求全省75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必须于2014年底前整体退出,并规定限期吊销和注销企业的相关证照。(详见南方周末2014年11月13日《政府一纸令下 安徽再无花炮厂?》)
24家花炮企业后来联合起诉省政府,2015年4月,合肥市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为省政府证明45号通知合法性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然而判决同时认为,45号通知决定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整体退出有利于国家、社会,如撤销会给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不予撤销。法院虽然确认45号通知的行为违法,但只是要求安徽省政府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在案件代理律师、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涂四益看来,法院的判决是自相矛盾的,“既然确认了文件违法,赔偿损失就是顺理成章的。法院只判决省政府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缺乏可执行性。”
涂四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案件当初立起来就很不容易。合肥中院经过三个月的沟通协调后才决定立案,目前,双方都已经提起上诉。
这段时间,地方政府也在做企业的工作,希望他们撤诉。“地方上做企业的,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有三家企业一度想和政府签了协议。”涂四益说。
即便难如人意,在全国行政案件胜诉率不足百分之十的背景下,判决省政府败诉的结果已经非常罕见。
“过去你告省政府基本不立案,撤诉的也比较多。”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说。他曾专门研究过行政案件的撤诉问题,很担心现在会重复昨天的故事。
“19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行政案件很少,平均一个庭一年不到10个案子,后来就抓立案数。数字上去后,发现判不出去。当时又没有调解,只好动员撤诉,最高的时候到了57.4%,后来最高法院说太高了,不能无条件地动员撤诉。那判不出去怎么办?下面就开始卡立案,立案数增长的势头基本就停滞了。”
何海波认为,在整个司法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很难指望法院倒转乾坤。立案登记改革后,行政案件肯定会大幅增加。但最终的结果,驳回起诉、调解、撤诉的估计会占很大比例。
“法院对案子做实质性判决的比例不会很高。”
但在前述上海某法院副庭长看来,案子能立上仍是个积极的变化。“至少有个案子在这儿,行政机关就不能不理你了。现在虽然还是要靠沟通协调,但慢慢的,政府的法律意识,法院的权威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