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禅者禅也
2015-06-01于仲达
文 于仲达
林谷芳:禅者禅也
文 于仲达

一
2009年8月27日下午,在北大国学社湖畔会议室,我们静候一位禅者的到来。
小雨微润,天色渐渐晦暗下来。透过湖畔茶舍的窗向外看去,如烟似雾。我内心默念着《心经》,不由得生出几分虔敬心来。凡夫如我,心心念念的,不过是心的起伏而已。
大约1点50分,一个清瘦的身影出现在会议室门口。顺眼看去,一位老者,满头银发,布履白衣,清癯如鹤,淡淡笑容,儒雅睿智。人如其言,清澈淡定,一席话下来,听者心静清凉。我得以有此机缘,从近距离观察一个台湾的文化人。
现年65岁的林谷芳,据说他一年四季都如此,一身布衣,再冷,也不过是脖子上搭一条白色围巾。面带微笑,侃侃而谈,显露出素雅淡泊、平常随意的禅者之风。他有很多身份:民族音乐学者、文化评论家、大学教授、琵琶演奏家、作家、禅者等等。“禅者”可能是他比较重要的身份之一。
林谷芳,台湾新竹人,1950年生。从1988年开始,林先生到过大陆200多次。第一次到大陆,他就用35天跑了11个省市。为何乐此不疲呢?“我要把以前读的关于中国的书,在那块土地上做一个完整的印证。”“大陆是一个参不完的‘大公案’,我要去参,一直参。”对于“恢复汉服”、“推广读经”等大陆当前一些热门现象,林先生认为,“所谓‘恢复汉服’,把中国想得太简单了。我认为,在文化复兴中,不是拿哪一个朝代的衣服出来,那就有点泥古不化了。我们应该要回到中国人的美感当中去,去选择民族的服装,不能把中国文化做小了。”谈到传统,林先生认为,今天读经的范围要扩大,不能只读儒家,更不能只读儒家某一类型的典籍。再者,经典是前人的生命智慧,读经在态度上“要跟前人有生命的对应”。如果不是用这种态度读经,会把世界窄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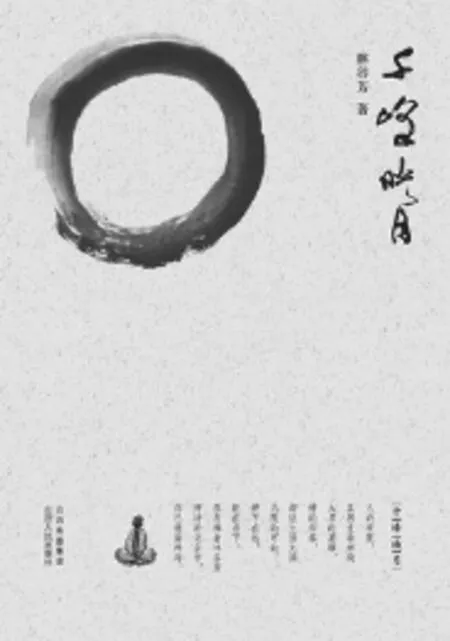
林谷芳著《千峰映月》书影
二
无论冬夏,林先生时常往返两岸,修禅、讲禅、游历、著述,他执着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当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智慧,也企望两岸回归共同的文化母体,弘扬中国人令西方尊敬的生命哲学。他静气凝神地说:“无论冬夏都穿单衣,是我这些年习禅的结果。平常人的身大于心,而修行人的心大于身。习禅,让我的心影响到身。”
林先生著有不少禅书,我较早读到的是《如实生活如是禅》一书,当时就有直指本心的感觉。阅读林先生近年来的著作,比如《千峰映月——中国人生命中的禅与诗》《一个禅者眼中的男女》《十年去来——一个台湾人眼中的大陆文化》《画禅》《禅,两刃相交》《如是生活如是禅》,可以感受到一个现代禅者的生命智慧。禅宗何以能安顿林谷芳先生的生命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书中获得答案。林先生在《千峰映月》一书中精彩的譬喻,让人顿悟:
参禅是剑刃上行,冰棱上走,一有依恋,就难得透脱,非得云山海月尽皆抛却,否则即无“随缘作主,即事而真”的可能。
世间的两难,在禅宗其实都属余事,两头俱截断,无心应自然……
禅者的生活,是最简单的生活。
林谷芳在《如实生活如是禅》一书中提到:“吃饭,一胃之纳;睡觉,一卧之榻。”——再有钱,吃再多也就一个胃,却还要追求无限的食欲;原来在一个小房间里睡得舒舒服服,现在有了五间十间的大房子,每天还为了要换哪一张床而烦恼。
林先生整个的生命散发出一种自在、洒脱、安然、灵动、悠游的禅气,令世人生出羡慕和向往之心。他踱步而来,一袭布衣,一双布鞋,满头白发,宛若一团清雾,让人顷刻间神清气爽。有人评价说:“林谷芳的气质,内外通透。”据闻,白岩松曾做过林谷芳的访谈,他说:“以禅者而言,终年一身布衣,也是一种执着。”
一个对禅感兴趣的人想参禅的话,要经历哪几步过程?林先生认为:
我想开始应该接触尽可能多的禅门故事,先不用想那么多,可以把这些当成有趣的故事来读。当这些故事跟你有相应的时候,你已经初步踏入禅境了。第二步,你必须对禅有一个根本的了解,有几本书对禅有比较全面的介绍,第一本是南怀瑾的《禅海蠡测》,第二本是我自己的《禅——两刃相交》,这里面牵涉到实际的修行。如果不涉及实际的修行,铃木大拙的书可以读一些。学曹洞禅也可以读铃木俊隆写的书。第三步就是要实际的修行。实修有很多方法,要锻炼心志、打破惯性等等,这里是有一套训练方法的,不能空口说大话。第四,在这些基础之上你可以去读灯录,像《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等,如果跳过修持这一关直接去读,你是不会读懂的。
关于修持,林先生认为:修行的意义在于如何把你的身心转换到更高的层次。修行是化抽象的哲理为具体的证悟。禅修持有两种重要的方式,一个是打坐,一个就是参话头。人们可以根据个性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方法。如果把话头禅与默照禅二选其一去实修,然后再阅读历代灯录,很多讯息就会出来了。
林先生用一则禅宗公案“以用显体”开示大家:
马祖与百丈一起散步,头顶有一群野鸭飞过。
马祖问:“那是什么?”
百丈不假思索地回答:“是一群野鸭子。”
马祖问:“飞到哪里去了?”
百丈答:“飞过去了。”
马祖用力捏了一下百丈的鼻子说:“他不是在这里吗?你怎可说飞过去了?”
林谷芳解释道,这则公案的意思是:人不能追逐概念、外物,应该回归到本心的直觉去看待万事万物,而不是跟风跑。禅是实证的学问,而不是说理的学问。“以用显体”不是“以体显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禅的道理是无形无相的,而它的体证绝对是有形有相的,因此可以勘验一个人的语言、行为是否合乎禅意。禅其实是生命的归零,而且是彻底的归零。我们之所以能力受限、认知受限,是因为我们受限于习气惯性,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解放自我。比如,“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这里不是说坐禅是错的,但机械的坐禅会陷入一种形式当中,很多人说禅宗是不坐禅的,这是极大的误解,但坐过头了就要打断。禅看似是摸不着边际的东西,其实就在打破你的惯性,如果你以为虚无的东西就叫禅,那是错的。
凡夫以心逐物,心没有一刻是停的,无论是学者,还是老百姓,都如此,没有内心安静的时刻。从禅来讲,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妄心的追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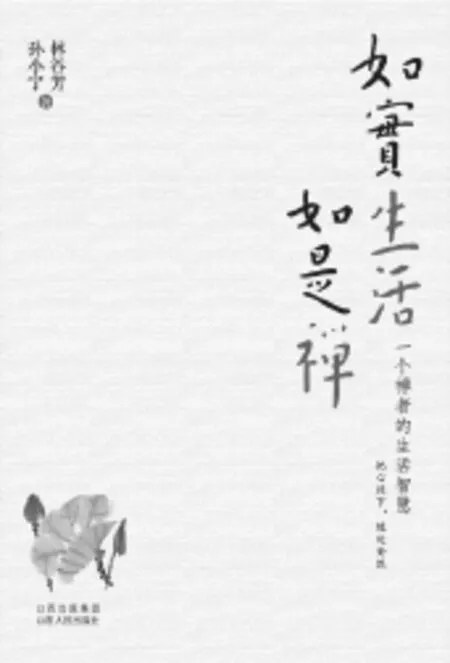
林谷芳、孙小宁著《如实生活如是禅》书影
这个禅宗公案启发我学会“透”,用禅透过公案、透过话语、透过各种行为,从自己的惯性中跳脱出来,那些原来不成问题的变成了问题,人就开始会观照自己,观照活在惯性里浑浑噩噩的“我”,观照某些权威,回到自己生命的本质,很多答案就会出现。
禅能够使我们的心理、肢体、生活、生命惯性得到一种彻底解放。林先生启发人在此反思、观照,而在参悟中会发现“无一物中有尽禅,有花有月有楼台”,原来是我们习惯于已看到的事物而把自己框住了。所以禅是透过活泼手段把原有的习见、惯性打破,看似是把一切都放掉了,其实是“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叶有楼台”。
作为一个悟道者,林先生提醒,就是要通过不断重复一些微不足道的动作,我们的思想才能脱离对过去和未来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活在当下,我们的洞察力才能磨炼得像刀一样锋利。“不要以不以为然的眼光、感情和想法来对待平常的事物。”当你碰到一件普通的事物时,不要轻视它,而是要把它也视作一件珍品,给予它同样细致和体贴的对待。
三
再次邂逅林谷芳,是在2010年5月16日晚,地点在北大二教309室。
这次,林谷芳演讲的内容与禅艺术、禅修行有关。
作为一名现代的禅修行者,林先生每出现在一个地方,总会给躁郁的人带来一丝清凉。
在林先生看来,我们不停地给人生做加法,才造成了生命不可负荷之重。当追逐成为一种习惯时,生命需要停歇,需要做减法,就是在修禅。林先生有时候把禅定义为生命的减法。减法就是有一个归零,看自己要的是什么?看自己的生命状态、自己的身心状态是什么?
林谷芳先生提出四种归零:阶段性归零,人生的归零,当下的归零,绝对的归零。
我们做一件事情、努力一个阶段后要忘记它。心理学上所谓的高原期,就是有一个阶段你怎么学都不会有增长。曾经有一个画家怎么画都无法突破,于是扔掉画笔出去游历;两三年之后,一挥笔就上了一个层次。这个方法对生命的学习非常重要。
前面三个归零我们任何人都做得到。生命总有一个它可以荷担的重量,所以就必须在减法的基础上“慢活”和“乐活”。减法的这种简单却是跟生命有深刻的关联,你不会丧失自我,不会有过多的负担,你跟人群的关系其实也都存在。我们在一个社会的漩涡里,人生的价值绝大多数都是别人赋予的,而且还会变,我们想能够认清这个事实,就能理清什么东西对我们真的有价值。
林先生说:“人从出生,就一直在学习,也就是都在过加法的人生。人的上半生尽管学了许多的知识、生命态度与社会价值,但这些后来也形成了我们生命中大的负担,因此在下半段的人生里,还更得力行减法才可。”也因此,扩展自由是生命最大的价值。
损,或生命的减法,不是要人虚无,而在让人回归,让人有空间可以行生命之观照,如此,人才能役物而不役于物,就能转境而不为境转。
减,是因为加法是天生的惯性,但一加再加,生命就被裹在层层的假相中,能翻转这惯性,舍掉这假相,该立在何处就明明白白。所以,减法看似在追寻一个超越的境界,根底的,它就是个立命之学。
是的,为学日益,不是坏事。人类从蒙昧至文明,就是“日益”的功劳,个人自童稚到成长,靠着启蒙建立自我,也是这日日增益的加法,但一味地加,正应了庄子的另一句话:“夫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林先生启发我,回归生命主体来观照事物,这学问也才称得上真学问。老庄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无哲理。的确,我们太需要一种融化知识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其实就是“道”,而不是“技”。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的知识、生命态度与社会价值,在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时候,也无意之间桎梏了自己。更让人担忧的是,许多伪知识伤害了自己,瘫痪了自己的判断力。没有知识或文化,固然有所欠缺;可是,人为知识或文化所桎梏,也是缠累。
林先生常念“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用一个不执着的态度,来看待世间美好的一切。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抛物线。年轻时候,很多事物没有尝试过,总有憧憬、梦幻、理想,难免会有加法,但是当世事的历练之后,必然会在减法上下功夫。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立的时候还是加法,不惑就有减法,可到了五十知之天命、六十而耳顺,整个人都放下了。
如何在一个生命的无常之中,透过当下的安顿,打破这个无常?林谷芳说:“人的有限,正因生命缠绕太多的葛藤,禅的归零,却让生活充满无限的可能。禅不在远,就在当下。”这个化解了我内心的疑虑。通过与生命结合,得到禅的感悟,我们才会从焦虑的人格中得到解放。
林先生有一双禅眼。禅眼观物,从容淡定。禅者不假外求,当下安然。禅者认为,生命是一场加法与减法的观照。禅者的活法是减法,解除生命外在的累赘。禅者不是逃避来自现实的困境,而是用更积极的态度来解决生命中的不安然问题。
为什么林先生的人与文让我觉得如此亲切?我觉得重要一点就是,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智慧。我觉察到,知识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有时反而是遮蔽。林先生启发我,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静观的方法,不能以心逐物,令我浮躁之心顿扫。他说:“我自己虽然被称为学者,生命的学问是全体的学问,学业里的知识是没有办法解决生命问题的,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这句话。我是大学教授,跟大家谈谈所知障的问题,我的所知,因为太专业了,反而构成我生命的一种障碍,那么抽象概念的意义,本来就不能解决实际、可触可摸的学问。”“有时候的确生命体践得像握你的手一样,就是禅所讲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作为一名禅者,林先生以出世间法观照世间法,往往点中要害。谈及爱情,他说:“爱情要回到人的本性去看,人是一个有机体,如果把某些情感、行为用某些想法概念附在上面,是人的迷失。感情有它的面相、特质,就像人类有它的精神层面,也有吃喝拉撒一样,永远有一个对应。也因此每一个人的爱情都不一样,并不因为所谓的不纯粹,就减损了它的价值,就像人不可能有一种人叫纯粹的人。 ”
作为一个禅者,林先生也投身社会和文化的讨论。谈及于丹走红现象,他说:“十几年前,台湾的作家林清玄也写过类似的作品。有一次我曾和台湾佛光山道场出版社的总编辑提到这个问题。我说,我不反对这种浅的东西,因为文化的生态应该有不同的层次才丰富。就像我去年来时,大陆红的还是易中天,但今年来就是于丹了。林清玄在书里告诉人们要简单过日子,他却用台币5000万买了房子,一个月交的贷款就是30万。当时,我对那个总编辑说,你们出他的书,难道不心虚吗? 我说我不是教条,但我觉得总要有点内外的统一性。后来,林清玄因为再婚的消息披露报端,闹得沸沸扬扬,他的书渐渐地在台湾就没有市场了,这也是很自然的。林清玄的写作,和一个文学家的写作不一样,一个文学家尽可以想象,因为他写的不是自己,而是想象。但你今天既然谈的是你自己,你的人格就已经被投射,和作品合而为一了,你不能只享有尊荣,而同样要付出代价,这是必然的。回到于丹的事情,如果她谈的都是孔子、庄子说的,跟自己无关的话,她当然可以如此作为,但她说的是自己读《庄子》的心得,那和她签名签十几个小时的行为,就形成了一种自我矛盾,自我颠覆。这不需要做解释。”
可以这么说,这种“内外不一”的现象,尤其在大陆文化界十分严重。文化明星们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倚赖一套系统的诠释,让自己安心,太执着于某一角色。可是,他们缺乏深入观照这种诠释的能力。
四
作为一位禅者,林谷芳的睿智还表现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有时他会带着“问题意识”,谈论一些公共话题。譬如对于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思,特别值得深思。他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殊胜的道德固可以理教杀人,傲人的学问更常让知识分子自设牢笼,也因此谈生命的安顿,知识分子还常不及黎民,不能自我安顿的生命却夸夸其言于天下大事,虽说言不必因人而废,但其间的吊诡、异化,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这段话是针对什么而说的?其实,只要联系一下知识分子的传统,不难理解。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有很大的关怀,好像我们要负担起天下大事,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话语往往跨越一个界限。曾经有段时间,知识界一片骂声,“知识分子”个个激烈,以启蒙者自居,高高在上指导、规训众生,谩骂祖宗,批判传统文化。如今呢,他们中的一些人忙着变卖祖宗遗产,个个油光满面,充斥在荧屏上,开口“国学”,闭口“文化”。其实,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有太多的烦恼、无明和妄想,有太多的贪、嗔、痴、慢、疑等习气,有太多我见我执,有太多的所知障。“知识分子”中或许有一两个心性至纯的,然稀有少见,倒是不缺“文化小农”、“二道贩子”和“学术明星”。知识的东西它是生灭的东西,是能所对立的观念,是概念,是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我们的生命观,开阔我们宇宙观的视野,但是并不能解决生命的迷茫和无明,一个拥有知识的人,他没有办法断除我们内在的贪、嗔、痴、慢、疑等负面情绪。“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以为自己比众生高明,然后拼命地通过制造奇谈怪说、领导舆论、彰显优越感、占据制高点等等来填补自己内心深埋的欲望。
这里,我一直有个疑问:知识多了就一定是好事?我看未必。我们不少知识人不缺少知识,倒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依禅宗的角度来看,知识是分别、判断和妄想,信仰是超越分别、判断和妄想。有时候我们对是非善恶是那样的坚持和执着,拿它穿凿世界,对所有的事情指手画脚;而不懂得心灵转化,把世界、人和自我看得过分简单,结果世界没有被拯救,自己反倒需要拯救,类似的悲剧还少吗?老期待着振臂一呼,老期待着改变别人,老期待着改变世界,但是别人和世界就那么容易改变吗?其实,人有时候要变化真的很难。知识让我们有了一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让人们错误认为或虚幻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外在的世界,我们可以控制它,我们可以改变它,而且它让我们错误以为什么是善恶美丑。这种虚荣心反而成为我们去了解真实、做一个真实人的障碍。庄子云:“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回顾过去曾经受到过的来自“知识分子”的蛊惑,不禁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为什么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变成社会负担呢?林谷芳从“禅者”的眼光反思道:
从禅讲,过了那个临界点,你对待问题的方式就失效了,这个时候需要调整。此外,当我们一直想改变社会,这个社会不随我们的意念而改变,人就容易焦虑,而时间又一直在流逝,过了五六十岁发现这个社会好像没照我的意思走,人就焦急,就开始愤世嫉俗。所以许多过去很从容的人最后都变成“老愤青”,也接纳不了别人的意见。可大家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拥有话语权。他们态度是坚决而且是神圣的,没有沟通的余地。
受此启发,我们再来反观国内知识分子流行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否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呢?长期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太执着于这个派那个派,结果,我们是否距离心中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呢?从“道”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超越各自的视角。当人类面对生存问题时,其他价值都是次要价值。对人类而言,惟一的普世就是存在。林先生说:“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拉车与刹车。公共知识分子扮演拉车的角色,让这个社会更合理。但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应该是一直互补、一直调整,也就是动态而有机的,否则副作用就出来了。”此语一出,真的令人深思呀。
的确,“公知”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要避免出现副作用,这样就应该做到不执着,避免过度化。知识人往往有一种优越感,似乎占有知识越多就真理在握。一开口就是“我认为”,若问他“我”在哪儿?他却不晓得。“公知”特别爱执着于自己的见解,就是所知障。今天,只要你仔细留意当今某些学者或专家的言论,就不难发现,有不少人其实都有执障,他们总以为这个世界需要他们去拯救,其实是他们自己更需要拯救。某种程度上说,书读得愈多的人,就执着得愈深。执着什么?名、利、色,执着自己的身份、事业、成就、声望、见解、专业和导师。他把内在的心态架构在一种执着、意识的分别、刚强的自我主义之上,并且希望长远地保护这种自我意识。由于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对一切环境的存在就会产生一种本能上的分裂。什么叫做意识的分裂状态呢?就是我们内在不能统一,总是偏于所执,执着在某种假相上。意识形态的分裂,就是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统一性的看法,所谓统一性的看法,就是内心无所着、无所住,一切因缘所生的这一念,用观照的力量马上就突破它,知道缘起自性本空。
禅宗有一句话,叫“开口即错,动念即乖”。那些开悟的大德,他们的本性、内在里面有大智慧,是不会轻易掉进问题的陷阱里去的,更不会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看看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何曾懂得沉默的智慧?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做学问,应该一天比一天增加,修道应该一天比一天减少。佛法在心,不在语言文字。重要的是转凡成圣,转识成智,转烦恼成菩提。也正因此,笔者决心破“三执”。由于弄文字爱文学的原因,我与文人、文化人曾结下恶缘。所以,我的“破执”首先从文学、鲁迅和“知识分子”开始。其次是破人我执、法我执和破空执。“三执”破除以后,就会轻松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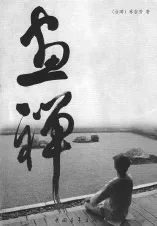
林谷芳著《画禅》书影
五
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也是林谷芳思考的问题。
在如此急遽的变动中,人如何安顿自己?这是一道生命根柢的大公案。他表示,修行的人,最该懂得设身处地,这是我很真诚的一句话。但尽管如此,正所谓“魔焰炽盛,亦可全真”,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观照,让自己活得更纯粹一些。
2007年,为了心灵困境的安顿,我曾苦苦寻求并信靠基督信仰。然而,半年多的聚会与祷告,似乎并没让我彻底更新生命。这个时候,我不由纳闷:这个宇宙间的独一真神固然能抚慰我内心的痛苦,可是似乎不能契合我的心性。更主要的是,我无法说服自己信服“道成肉身”。虽然,我一直读《圣经》,困惑并没有彻底解决。我在想,能否有其他的方式让我得到真理?真理的表现形式只有一种吗?
林谷芳先生说:“宗教都有一套对生命的诠释,这个诠释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总有证验、总有论理,问题是你跟它相契否?而这相契在人生的安顿、境界的对应上是否有效?”就拿林先生来说,天生有宗教人格。而大多数人,则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因缘与契机,转向皈依宗教。我大约属于后一种,与基督信仰似乎不太相契。当然,并非说明这一信仰就不好。
后来,我读到林谷芳的《千峰映月》。该书认为,中国人的生命困境、心灵牢笼,并不需要用西方的精神舶来品来化解,它自有一种中国式的解决方式。禅宗作为佛教中最重要的一支流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魅力和神韵的一道风景,它成为许多古代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和心灵归宿,在当今社会,在中国人面对人生藩篱时,禅依然能能够引领我们发现从容淡定的生命境界,为生命找寻到真正的解脱。这种见解让我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传统。
之后,我陆续阅读了大量佛学书籍,又在北大修了楼宇烈和周学农两位先生的佛教(禅宗)专题研究。仿佛转眼之间,就有种“一朝忽觉梦惊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感觉。我所苦苦探求的真相,原来一直深埋于自己的母体文化里,而我竟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十分惭愧。
我们这个民族曾有无数次的跌倒,每一次都是通过“重释经典”而爬起来。起来的那条褪是“经济”,跪着的那条一腿叫“文化”。戴震从我们民族的经典里,只读出了“杀人”二字,胡适从我们民族的经典里,只读出小脚、麻将;鲁迅从我们民族的经典里只读出“吃人”二字……他们是故意“误读”了,如果仅仅只有这些,我们民族不会如此旺盛。令人赞叹的是,直到现在,中国文化依然还是西方文化无法征服的“他者”。
人类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是物化世界观的泛滥,是物性对人性的宰制。人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文化制品所主宰,人从目的的地位下降为工具。对营营役役的当代人来说,当遭遇生命困境、面对心灵牢笼时,往往习惯于选用西方的精神舶来品来化解,却生生忘记了它自有一种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我们习惯于看着西方,心灵却在旷日持久的荒地上抛荒。该如何安顿困顿的心灵,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宿命、一种纠结。
身为中国人,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液,不是哪个人想全盘西化就能全盘西化的。对于这一点,激进派自己也承认。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激进,与其说是一种姿态,还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国文化的惰性太大了,不如此地批判就无法让它有丝毫的改变。汲取这种智慧,就能很好地平衡你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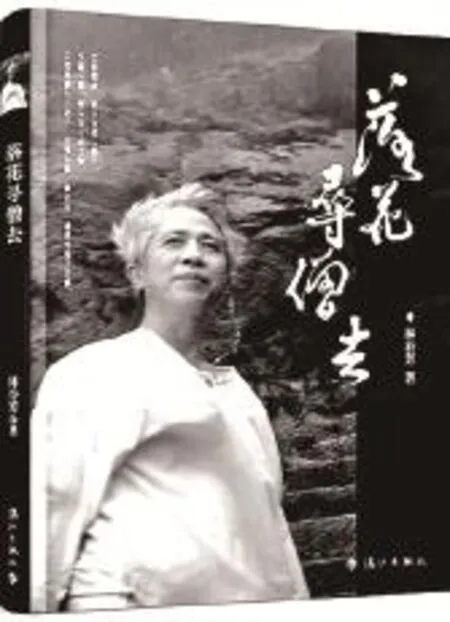
林谷芳著《落花寻僧去》书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天地日月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深深地探究着一个命题:人类生命的核心或者说生命的支点在哪里? 我们读经典,不需要别的理由,只这一个理由就够了:那里面有一种安身立命的“中国式生命智慧”,可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灵。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智慧,是建立在对世界的通透的认识之上。按林谷芳的理解来说,儒家具有社会性,或者说“人间性”;道家具有美学性;佛家有宗教性。儒家重人伦日用,更多地关注现世,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敦礼明伦。敦,即敦厚,敦礼就是看重礼、重视礼,把礼看做是社会构成的根本。道家具有美学性,美是一种创造。完全强调内在的东西,没有任何标准,放弃一切努力,放弃创造,那显然是不行的。道家的内在心性的安顿,也是平衡儒家而来。道家,特别是庄子,其关注的主要是个体生命的安顿。安顿心性,体验自性,解脱欲望,超越知识,解除矛盾。中国人强调反己内求,强调内在心性,讲“万物皆备于我”,这是一种心性的推展,而不是对物质的控制。佛家有宗教性,对于生死实现了绝对的超越,既不执着于生,也不执着于死,而是任生任死。在佛教看来,任何生命都免不了一死,但死的只是肉体而不是灵魂,形灭而神不灭。儒、释、道三家,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中国文化恰好有儒、释、道三家来承担,儒家处理了人与人的关系,道家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处理了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古人说,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就是说用儒家的思想治国,用道家的思想养身,用佛教的思想治人心。佛教天台宗人孤山智圆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认为儒佛相为表里,可以互补,到晚年他甚至宣称自己的思想“以宗儒为本”!其实,三家都可以用于治国、治身和治心。中国文化就是生命、生活和生存的一种智慧,而不是一些简单的知识。
其实,从中国文化的特色来看,“世俗”也并非全是缺点。就禅宗而言,本质也是不离人伦日用的。禅宗把不离世间求出世间,“即世间求解脱”,不离世间法而行出世间法的理论做了论证和实践。这里有一个禅宗公案:
唐朝时,有两位僧人从远方来到赵州,向赵州禅师请教参禅。
赵州禅师问其中的一个:“你以前来过吗?”
那个人回答:“没有来过。”
赵州禅师说:“吃茶去!”
赵州禅师转向另一个僧人,问:“你来过吗?”
这个僧人说:“我曾经来过。”
赵州禅师说:“吃茶去!”
这时,引领那两个僧人到赵州禅师身边来的监院(寺院的管理者之一)好奇地问:“禅师,怎么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未曾来过的你也让他吃茶去呢?”
赵州禅师称呼了监院的名字,监院答应了一声,赵州禅师说:“吃茶去!”
一句“吃茶去”,一碗“赵州茶”,代表着赵州禅师的禅心。
禅的修证,在于体验和实证。语言表达无法与体验相比。参禅和吃茶一样,是冷是暖,是苦是甜,禅的滋味,别人说出的,终究不是自己的体悟。所以,万语与千言,不如“吃茶去”三个字。
对于赵州禅师来说,日常的生活就是禅法,吃饭睡觉都是修禅;对于那位初学者来说,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他领悟不到其中的真味。
佛教的主旨是关注人内心的力量和遮蔽,激发人自身的力量去发现,去寻求觉悟,它的根本精神在于基于内心的缘起法则。发现、拯救、觉悟,这一升华修行过程完全作用于内心,这是它独有的特点。佛教重内观,人之心便是一个世界,它要令人改造这个世界。这不就是成佛在世间吗?这样一种活在当下的精神,能说是消极吗?
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套用这种研究方法整理或诠释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时离其原来的意蕴相去甚远。表面上看,中西文化这两极好像极端对立,其实不然。就人的生活和生命本身的意义来讲,平衡把握得好的时候,这两极之间应该有一种张力。应该看到,没有一种完美的文化体系。当下我们研究国学,就是要融会中西,超越分别,超越批判。
林先生对于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解读,让我耳目一新。它启发我,作为个体,必须在社会连接里面感受自己(儒家);但如果没有道家这种自然的折射和纵浪大化之间的安顿,那么不仅生命没有安顿,即便面对现前的人世,人都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顿。它并不是居在斗室里自怜自艾的忧愤,而是在江河之中、上善若水之中化解这些恩怨。由此,对于传统文化的功用,我不再如先前仅仅拿西方文化贬抑自己的文化,也不再仅仅认为只有基督信仰才具有超越性。深入认识自己的文化,对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超自然,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林先生谈文化的重建、生命安顿,让人觉得法本亲切,道不远人!在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中,禅宗和道家是很重要的,二者虽然有中国的风格,取自于中国文化土壤,但面对生命的问题是具有普世性的,比如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如何安顿自我等。儒家则比较表现为具体的社会性和民族性。因此,禅宗和道家是中华文化可供西方“他者”参考的,“我们可以让西方尊敬的是我们的生命哲学”。林先生从老庄哲学里提炼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夫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提倡“生命面对面的学问”。确实如他所说,“能回归生命主体来观照事物,这学问也才称得上真学问”,特别是禅宗也讲求“如实的感受”。林谷芳曾在长沙的两岸文化论坛上,以“三家均衡”与“生命体践”谈台湾在中华文化弘传上的生命特质,当时曾引起与会者相当的回响,认为正是当下问题的契合之道。回到共同的文化母体,由此就可以看清两岸文化人的互补性,也才能共同来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斯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