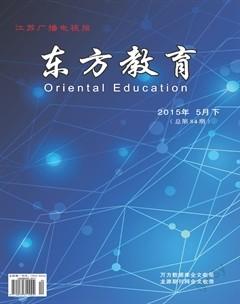战争中的女性:沦陷与救赎
2015-05-30乔石
乔石
【摘要】电影《我们的父辈》作为近年来反思二战的经典之作,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在展现战争的残酷与无情的同时,更注重个人在战争中的苦难与挣扎,尤其是女性在战争裹挟下的沦陷与救赎。电影既刻画出女性作为战争中的普通一员的境况,又细腻地表现出女性特有的视角,十分难得。
【关键词】《我们的父辈》;沦陷;救赎;女性
《我们的父辈》是一部德国人关于二战的自我审视的作品,以“我们的父辈”威尔汉姆自述的方式还原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在这部迷你电视剧中,五个年轻人在战争伊始,正值青春年华,他们对人生怀着甜蜜的期待,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期许。可战争爆发,他们的人生轨迹已被改变,注定在战乱中挣扎,注定会用鲜血甚至生命為这场战争付出代价,也注定会被这场战争烙上痛苦的印记。
哥哥威廉是一名军官,他代表着战争开始时德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德意志无往不胜。最初,他对于上级的任何指令都努力完成,随着战争的一步步僵持,他从勇往直前的勇士变成厌恶战争和杀戮的普通人;弟弟弗雷德汉姆是个偏爱文学反对战争的年轻人,他被迫走向战场,从一名厌恶战争的“胆小鬼”变成一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哥哥的女朋友夏莉是一名对德意志引以为傲的护士,从一开始憧憬着奔赴前线到在救护中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夏莉完成了她特有的蜕变。而他们的好朋友维克托和格雷塔——一个犹太人和他德国女友——在战争中则举步维艰。格雷塔为了救维克多,委身于高级军官,希望借此为维克多换来逃离的通行证,但这张通行证却将维克多送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本以为她委身的男人可以依靠,到头来却被他送进监狱。
一、时代洪流中的女性
战争,通常被认为是男人的专利。因为战争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暴力,残酷,血腥以及不择手段,正是战争所拥有的这些特性使其成为男性释放多余荷尔蒙的合理途径,战争也成为男人心里残存的梦想游戏。该剧在导演上帝视角叙述下的女性是丰满的,性格刻画得相当细腻,并没有因为其叙述视角的缺席而变成一个扁平人物。在反思二战,反思希特勒法西斯的大背景下,女性同样作为被时代裹挟的一份子,她们和实际参与战争的男主人公一样,身上也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夏莉在五个人的圣诞聚会时,高兴地向伙伴们宣布自己已经获得了护士资格,非常天真地怀着爱国心准备去前线做护士,来到战地医院面对护士长的询问,她会自豪地说:“代表全德国的妇女同胞!”经过第一次面对鲜血不止的伤员,她会慌乱不知所措,但是当她作为一名德国战地医院的护士去挑选莉莉亚作为帮手的时候,她的身上还是有着一种膨胀的骄傲。在法西斯的宣传下,最年轻单纯美丽的姑娘,应该富有人道主义的地方——医院,因为这样一种时代的要求,夏莉会变成一名帝国的护士,也会响应号召去举报犹太人莉莉亚,尽管莉莉曾帮助她脱离窘境。
而格蕾塔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浮更加明显,她和维克托因为种族的差异,两个人相爱本就不易。“水晶之夜”开始,事态急转直下,年轻的德国女孩格蕾塔能为爱人做的,也就是送他远离是非之地,为此她付出了自己的身体。让人难受的正是眼睁睁看着她的付出其实没有任何回报,盖世太保只是为了得到她的肉体,却转手把她的爱人送往了集中营。
而另一方面,格蕾塔又有着成为歌星的梦想,为此她会继续跟盖世太保保持着关系,因为他能帮助她成就梦想,成为歌星,去到巴黎,米兰演出。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中,格蕾塔通过出卖自己的肉体,完成了自己的理想,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看起来她仿佛是时代的宠儿,可是她却因为一句“我们不会赢的”,而被定为散布失败言论罪最后被枪毙。其中固然有盖世太保想摆脱她以孩子为威胁的原因,但不得不说格蕾塔既是时代的宠儿,又是时代的弃儿。
当时代需要她作为歌星去安慰在前线热血奋战的时候,她可以享受专车专机等各种优厚的待遇,可是军人只是觉得她是一个慰问品,甚至是玩物。不管是积极响应时代召唤的夏莉还是最后成为时代弃儿的格蕾塔,她们原本都只是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善良的女子而已。时代的不幸不光落在了在炮火下丧生的男性身上,而女性亦以别样的方式承担着时代的痛苦烙印。
二、爱情与肉体
关于爱情,剧中有两条明线:夏莉与威廉,格蕾塔与维克托,或许还有一条暗线:维克托与波兰女子。
夏莉与威廉本是相当合适的一对,男才女貌,只因为战争爆发,两人都要前往前线,两个相爱的人为了不让对方担心,彼此都没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当夏莉在得知心爱的人威廉战死的消息后,选择了与主管医生发生关系,或许,主管医生只是威廉的代替,夏莉只想通过肉体的发泄来缓解爱人丧生的痛苦。故而当夏莉发现威廉并没有死的时候,她选择了悲喜交加的逃离。
对于格蕾塔而言,当她用肉体与盖世太保交换一张爱人逃离柏林的通行证的时候,她承受的巨大痛苦与误解我们都可以看到,战争将爱情硬生生地毁灭,只剩下赤裸裸的肉体交易。而当她继续沦落,为着自己的歌星梦而用肉体向盖世太保献媚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不适,因为她在用肉体交易的方式满足着自己的私欲。
而与维克托一起患难与共的波兰女子,最后在游击队中,当维克托被质疑是否是犹太人的时候,她毅然回答:“正如你所说,我和她睡觉,所以我清楚他犹太人。”虽然她知道维克托就是犹太人,而她和其他游击队员一样认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俄国人一样讨厌,死了比活着强”。但是她会依旧选择挺身保护维克托,她的这种行为是善良的,但是她用来证明维克托不是犹太人的方式却是值得玩味的。其实这还是她在用自己的肉体在证明,尽管她与维克托之间只有经历患难的情谊,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中,肉体无疑更令别人相信。
从男性视角出发,一方面,女性可以运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某种所谓的“正义”的事情,另一方面,女性运用自己的肉体在战争年代去谋求生存却是受到歧视的。那我们对于女性的要求是否过于苛刻呢?本片中的男性视角叙述决定我们不会照顾到女性作为区别于男性的第二性的存在的特殊性,如果还是依照男性视角的标准去作价值判断,不免显得武断而不近人情。
三、救赎
本剧最后出现的一个比较神奇的人物——莉莉亚,她曾经因夏莉告发而被捕,而当苏军战士冲进医院想要强奸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夏莉时,她却作为苏军政委,夏莉的拯救者出现了。不得不说,莉莉亚的出现显得太巧合了,十分突兀,但是想想莉莉亚最后说的话,我们或许会明白,导演的良苦用心。冤冤相报何时了,莉莉亚和夏莉这两个女性最后的和解,或许正是导演所寄予希望的救赎所在。而这或许是因为女性善良的本性,在战争过后还存有一丝善良,这也为和平带来了一丝女性的曙光。
参考文献:
[1]《<我们的父辈>:德意志零年》,《文艺风象》2013年11月。
[2][荷]伊恩·布鲁玛:《正常的纳粹》,《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3月16日。
[3]《帝国风雨后,战争中的一代》,《经济学人》(Economist)2013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