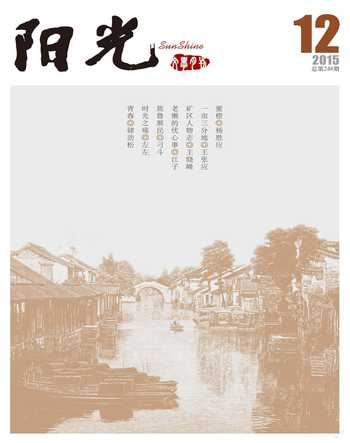致鲁顺民
2015-05-30刁斗
刁斗
之 一
顺民兄:
一晃就分开半个月了,很想念,这源于在鲁院时的愉快交往。
有一件小事必须提及,就是甜水园购书事件。
这在别人也许极无所谓,可在我这里,它是一个情结似的东西,甚至,我已经把它上升到我们有缘分的高度来看了。多年里,我几乎没逛过街,现在想想,我老婆和我认识十九年了,即使给她打溜须的年代,我也没正儿八经地陪她逛过街。但差不多从上大学时起,在沈阳也好在北京也好,我就养成了个习惯,隔一段就要逛逛书店(我的开销主要是买书买烟,但买这两样不算逛街吧),同时,出门的话,每到一地我也一定要走进书店,只停一天也要去书店,没什么合适的书买,就退而求其次地买一本可买可不买的。这样做,是习惯,是需要,是爱好,若言重点儿,也可以说是仪式。但这回在北京,居然迟迟未去书店。
这几年到北京,主要去海淀图书城(距我姐家相对近些),也去西单图书大厦,这回一到北京,我也一直想找机会去这两个地方。可不知为什么(我认为与SARS无关,因为它一点也没影响我行动;大概是路远导致了脚懒吧,总觉得时间长着呢,什么时候去都来得及),就一日日地拖了下来,而这拖,是让我心里极难受的(三个月去一回书店和一个月去一回无论如何也不一样),晚上躺到床上一想到书店还没去呢,我都恨自己。好在这时,春雷一声破乌云,横空出了个鲁顺民,因为有了你,我对自己的责备才没发展成认己为敌。你无法想象,第一次你告诉我这附近有个甜水园图书市场时,我都差点儿主动和你握手向你致意了,但我不大喜欢握手,尤其不喜欢和男人握手,就没握。接下来,我们就去了,我也就稍微可以原谅一些自己的懒惰了——毕竟,没跑海淀、西单也举行了购书仪式。
我说这一堆话的意思是,虽然我们交道仍然不多,但买书一事,已然让我把你看成了朋友,是老天爷派你来帮我缓解因购书习惯带来的精神焦虑的。我估计,若没有这一次甜水园之行,我去一回北京待半个月却连书店都没逛,那我到家的第一件事,也许就是冲着镜子抽自己嘴巴了。谢谢你受老天之派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当然,海淀、西单没去,甜水园没好好逛一番,这是美中不足,使我对自己仍有遗恨。
所以写到此处,我要说也谢谢来自谢泳的问候,并请你代我向他致意。这不是虚礼,是诚挚的,因为你给我讲过他隔上一段就要跑到北京买一堆书然后由邮局寄回太原自己却仍留在京城乱走一气的轶事。另外,一并也请你给韩石山代好,其理由,除了多年前我办刊物时他支持过我,还因为他无私地将论文选题赠予谢泳,还不惮对名流开刀却很真诚很激烈地鼓励后进。
多年里,我一直有感于许多同行的不读书。他们聪明,有才华,但只吃在学校时读过的书的那点儿老本,结果,十年前与十年后支持不同论点的却总是相同的论据,写出来的东西只有知识和时尚,全无鲜活的思想的泉涌。这非常可怕。我自知不才不慧,所以不敢懈怠,这样,即使考虑到买书所花皆血汗钱,为了不糟踏血汗,也可保证读书不辍。
其实这次去鲁院,本来只打算读几个月书,是几天过后,有些手痒,才借了那个三分钟能蹦出一个字的电脑。可惜,书未读,字未写,波动之心尚未安定,就他妈满北京城闹SARS了。
不知何时或者是否还有机会能去北京过上几个月学生生活,真希望这机会还有,且能快一点儿长一点儿。我一直喜欢学校生活,但因为不会外语,就没法去考硕士博士;还是因为不会外语,就弄不来职称,也就没法去大学里教硕士博士。妈的,当初好好学外语多好,光谈恋爱和写小说了。不过,让我现在选择,我还是要让谈恋爱和写小说并列第一位,至于学外语,也许现在我能把它排进前三名里。但愿鲁院能圆我三两个月的学校梦。
我这边一切都好,祝你和我一样好。
之 二
顺民:你近来好吧?我想会好的。
有个很不重要的事想请教你,但愿不会让你多费脑细胞。
有一回看电视,知道贵省煤矿砸死人后还可以隐瞒少报,现在我忽然想关注一下具体理由。那事是这样的,比如,死了二十个人,可矿主买通有关主管部门后,只上报说死了八个,而对那另外十二个死者家属的打点办法是再多给点儿钱,这之后,没人追究,也就等于此事变小了。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能回想起来电视里的解释,好像是某一死亡数字是个杠,比如八,如果死亡不足八人,可以算小事故,可以略经整顿后继续开矿,可以不追究矿主的法律责任,诸如此类吧;而死亡人数若超过八人,矿主则将面对更多一些的麻烦,如算大或重大事故等等。我想知道,对于那些开矿的人来说,是否真有那个人数杠杠,有的话,是几,没死到那个数和死过了那个数都将怎样?
这问题看上去有点儿乱糟糟,但我能知道最简单的一句半句也就够了,所以你只简单过问一下即可。你肯定需要挂几个电话才能搞清,甚至你根本不认识与煤矿有关又懂法的人,若不认识那一路人,不过问也无妨,千万别把它当一回事。我之所以想了解这个,只是小说中有处背景我想带一两笔,可当时看电视时我完全没想到去关心这种细节问题,没想到我的笔下,还会有死于矿难又被隐瞒了的匿名者。我的想法是,如果搞不清楚矿上的条律具体怎样,我就替煤炭部(有这部吗?)编个法规,或者干脆不用这一细节;如果我小说里的政策和国家实际执行的政策恰好一致了,那当然更好一点儿。所以,因为有了晋地的你,我才想到以现在的方式也“深入生活”一番,但愿不会对你构成太大的骚扰。
千万别花太多工夫去打问,不认识这路人就算了,真没关系。
之 三
顺民兄,若能拣起小说再写,实在大好,但以你对中国文化之兴趣,以你周边那些老韩谢泳等术业气氛,以你现在仍须兢兢业业做编辑的现实状况,似乎你也有操练另一套文章的方便之处。我不了解情况,定向还得靠你自己,但我以为,专一倾情地做好一件自己更有把握做好的事,这才要紧。我一直以为,我等凡人,不能有毛泽东那般大才,便只可或书法,或诗词,或政治,或军事,不可奢望四归一;同样,我等凡人,自然也有功利心虚荣感,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为了名声,也当抓住根稻草不松手,让它一直把我们引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去。所以,定下来的目标就要咬牙走下去,宁可为之花些苦功夫傻气力也在所不惜。我的意思是,不要当“作家”,而是要成为或小说家,或诗人,或批评家,或散文家……总之,固定的名声,单一的名声,一精百傻的名声,才有可能是大名声。
我不知道方文给你开了什么书目,但我以为,书虽好,却也如女人一样,来与不来全凭缘分,来了能否两情相悦亦是缘分,悦完是否有让人回味的后劲仍是缘分。在我看来,照单吸纳,未免学究气一些,还是听天由命地胡碰乱摸着结缘的好。其实咱俩逛书店时,我多次遇到过我非常钟情的小说,却很少推荐给你,主要是我凡事都愿意持随缘的态度,不想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而每个人的审美趣味实在是可以大相径庭的。有些书,评价再好也不必非收罗于架上,感觉一下再选择无妨。另外,买书之事细水长流较好,就像我还住房贷款,每月那么点儿不觉得吃力;若抢购般地一网打尽,对咱这工薪族也是负担呢。
我的读书体会是,既要凭兴趣来,又不能由兴趣去,这其间的度,就卡在个人爱好与功利用项那个接壤点上。
我一切如常,就是忙得坐不稳屁股。我希望一周之后能开始写作。
之 四
“在一种体裁里进行创造,就是为这种体裁增加新东西。为这种体裁增加新东西,就不是适应在我们之前业已存在的东西,而是要改变它,超越它。如果说艺术等于人加上自然,那么创作就等于艺术家加上体裁。艺术家内在的能力,不是把他的手引向体裁的相似,而是把它引向差异。”这是我这两天读的法国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里的一段话,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与你的土改有点儿关系,就抄给你。土改的东西,像小说又不是小说,不知成了什么样子,但我希望它是小说,小说的内部空间最大,易有张力易有弹性。只是,让它是小说或似小说时,又不能拘泥小说规约,根据材料打破些东西,最好。比如,受你启发,我也买来奈保尔写印度的《幽黯国度》翻了一下,也许我不会像你那般喜欢这种主题太大的东西,但它的形式感很启发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它看成小说呢!对了,孙惠芬有本书就不是(似)小说,但我激赏,我还写过篇文章,一并附上给你看看。我希望你的土改是一本有力量的书,并不在于它是否是个大题目,而是因为,依我看你,你有能力马踏稀泥。
今天上班,收到《作品》了,一气看下来,就是很好。
你再买书,国内作家的,慎买。挺贵的东西,若感觉不好,心里不舒服。我意还是看那些已成经典的,或新近出笼但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写的,像上边提及的那本小册子,二几年的讲演,三几年才出书(作者前言中认为尚未过时,就出了),如今七八十年过去了,却让你感觉就是说当下,对批评与批评家的解析,真是刀刀入腠里敲骨又吸髓了。
之 五
顺民:倏忽两周,就结束了豫晋之行。与以往的这种出行相比,此番读书最少(只读了克里玛《爱情与垃圾》的一百页),说话却最多,与你,与聂,与吕的交流,构成了此行的一个聊天三重奏,无疑这是又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阅读:与你的散漫而无所不及的对话近于自省,你我间的理解与默契,和谐与会心,其宝贵程度简直让我对友谊有了新的感想——当然,这又不是言不及义的“友谊”一词涵盖得了的,这是一种精神世界才有的奇迹;与聂的智性的一见如故且直逼本质的对谈,有奢华之嫌,但由于他我均是诚挚之人,那言辞也就回归了朴实,蕴满了真情,有了士大夫坐而论道的古雅与超然,具体的所指倒不重要了;与吕的随意又简约的东拉西扯,由于时间所囿,看似漫不经心,如同某些山水国画的淡淡点染,但志趣相近的同行间那种一声顿挫一道目光,也就什么都有了,尽在不言中了。这样,有了这三重奏,有了你聂吕,我的这次行旅,便成了我多年里类似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由于它是那么完整而美好,我对它后期那种必不可免的世俗化走向也都能欣然接受了(我不是不能与凡人接语,我就是凡人,我从不自命清高,我在精神享受时并不拒绝物质享受;但我对暴殄天物般的炫示式享受难以接受,尤其是当那天物并非由我的劳动换来,而系民脂民膏时。说实在的,从我走过的这几处山西城市的外观来看,与许多地方比,山西的发展建设可能算慢的,而当你讲到拨款十万用于村里只有两千五时,我觉得制造这一重罪恶的人中也有我一个。我也明白,任何存在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天下本无公平可言,但我仍然忍不住要为那不公的存在而愤懑扼腕)。如果不是考虑到我的存在已对锐锋甚至山西作协构成了牵累,而你夫人的骨伤也让我不忍心再霸占着你,我真想不惊动任何人地花着自己的宿费在简朴的“唐久”(是这店名吧)再滞留几天,把老聂也喊来,咱们三个无主题地乱说一通,然后再作鸟兽散,多开心。当然就现在这样我已觉得足够好了,所以,宁可冒着被你指斥为多余的危险,我也要说一句谢谢你,至少,我得谢谢你夫人病中对你的放行。请再次代我问候她。
一气说了上面的话,娘子关后的行程倒觉得没什么可说了。你们走后,我有着充分的与民同乐的思想坐一回林海雪原式的小火车,可感觉上石家庄方面的约定不那么可靠,我就希望能早一点儿赶到那里,然后立刻回到北京。尤其是当我买完车票,见到价格只为四元五时,我简直惊呆了,如此的票价将带给我怎样的行程让我不敢想象。于是我当机立断奢侈了一回,打车前往石家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抵石十分钟后,最后一趟赴京的大巴就出发了,我赶上了它,也就于当夜到了北京。你来电话时,我刚刚把背包放到姐姐家的地上。
你这两天也休息得差不多了吧,恢复你的黄河写作了吗?望你沉心静气地把东西写好。与老聂通话时代我问好。
之 六
顺民:显然这酒是喝糊涂了,你挂的还是旧居电话吧,那已有一年半不属于我啦,而这小灵通的号,就在这信址上嘛,白天基本都开机的。
其实我一共就出去二十天。过完春节,去了海南,在三亚待的日子多些,海口只住两夜,见了王雁翎。然后去了宁波,关在屋里待了六天,想去杭州上海之类看看,又不爱动,就直接去了北京,和我妈说了两天话,外人连个电话都没打,就回来了。
我今年计划写个长篇,从元旦起,一直在忙它。想法是在鲁院时出现的,与学习班有关,自觉是个挺好玩的东西,荒诞无厘头的一路。我很希望今年内写完,也不知老天是否允许,这些天里,忽而兴致勃勃,忽而信心全无,就在这其间冲来撞去。倒也总是这样,这么多年,我的写作总是在犹豫迟疑中进行,长篇的问题是,它折磨你的时间太久,这有点儿像海枯石烂的恋爱,太忠贞不渝了也辛苦呀。可又不能不爱,所以不能不写。当然了,对我这受虐心理的人来说,折磨亦是快乐,辛苦亦是满足。由于这长篇,四个多月来,我一个其他的东西也没写,包括报屁股。一心不会二用,这也是上帝对我这专一之人的格外要求吧。但下半年,若这长篇能够草完,进入修改状态,我肯定要出去的,甚至带出去改,届时看我去哪儿吧,争取路经太原,与你聊天,我很想你。
时间这东西力量无比,心中有它,对什么也就都可以散淡应之了。单位之事,即使不越来越好,也会让你越来越无所谓,因为虽然那事还在,可自己心态变了,那事的或好或坏,也是都要随之转化的。我想,一个人,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只是自己的工作,自己安身立命的资本与根基。你再少喝点儿酒吧,有那工夫还不如找个姑娘聊天。
刁 斗:1960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曾当过新闻记者和文学编辑,居住沈阳。已出版的著作单行本有:诗集《爱情纪事》,随笔集《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长篇小说《私人档案》《证词》《回家》《游戏法》《欲罢》《代号SBS》《我哥刁北年表》《亲合》,小说集《骰子一掷》《独自上升》《痛哭一晚》《为之颤抖》《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重现的镜子》《实际上是呼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