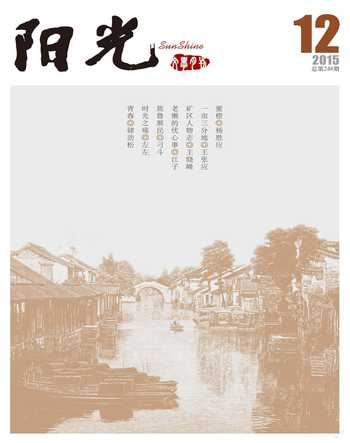青春
2015-05-30储劲松
二 厂
二厂是我的“发配充军”之地,也是我人生行旅的一个驿站。
我的毕业派遣证上写的分配日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八月,真正被一家县级国有供水企业接纳则是翌年元旦过后。其中的原因和过程颇为复杂,简言之,公司当年为职工子女就业考虑,委托一所建筑工程类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六名学生,谓之定向委培生,但他们的子女都不争气,考分离录取线隔了几座山,于是连我在内六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草窠里捡了个粑,代替职二代们去拿了文凭,又替他们来到公司,准备接手他们父母辈的事业。这自然令公司上下羞惭恼怒,于是公司高层一致决定拒不接纳。但在那个时代,派遣证就像尚方宝剑,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结果,公司的主管部门甚至县政府都被惊动,公司一把手被免职,而我们六匹年轻的狼长驱直入。在工作有了着落之前,那东奔西走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甚至准备请律师打官司的凄惶的几个月,则让我终生难忘。
梁子早就结下了,而且结得很深,虽然我们都很无辜,但人还未到就命定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六匹狼正式入侵之前,公司做出两个决定:一是年内不给班上,到元旦过后再正式报到;二是全部放到二厂,公司总部一个不留。关于第一条,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公司是为了节省月奖和年终奖;关于第二条,明里说是为了让我们到最艰苦的环境中接受锻炼,将来如何如何,实际上就是发配充军,说是报复也未尝不可,因为与我们一道毕业的公司一位高层主管的女儿,并没有受到接受锻炼的“特殊优待”,而是上班第一天就直接在公司总部做了办公室文员。后来我们知道了她也是定向委培事件相关者之一,不得已进了一所技工学校,身份被定性为工人,而我们则赫然是干部。顺便说一句,当时整个公司近百号人,在我们进入之前有院校背景的只有几个人,其他的都是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的老职工以及他们的子弟。
二厂就是第二分厂,在离县城七八公里处的一个乡镇,如今那里是一片被称作县城副中心的开发热土,而在二十年前却是一个荒凉而毫无生气的小镇。二厂坐落在镇子边缘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厂区的几间青瓦平房还是当年三线厂从大别山大撤退时遗留下来的,早已残破不堪。那年元旦收假后第一天,六个不满十九岁的“童子鸡”到公司报到,并点头哈腰地接受了一番堂而皇之的岗前教育,之后一人骑着一辆老永久加重自行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山区国道,一路呼啸着从县城冲向二厂。吹着口哨,沿着百步水泥台阶进到厂区,心情原本不错,可是望见与公司豪华典雅的总部大相径庭的荒草丛生蛇鼠出没的厂区时,我的心顿时掉进了冷水盆里。
从前我个自命不凡的人,胸有鸿鹄之志,不像现在这么灰扑扑地堕落了江湖。虽然只是个中专毕业生,但在高校门禁仍然森严的上世纪末,中专生算不上“天之骄子”起码也能算个“地之骄子”,理想中的上班应当是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写写画画,而不是当一名工人。原本,当年考取中专的人是学业最优秀的一批人。现实的残酷性正在如此,它偏偏安排我在破败的乡镇中破败的小厂里当了一名几乎不需要任何技能的开水泵的青工,每天枯索地独坐在密封的机房里,守着一块电子仪表板,看看上面显示的电压、水压、水塔水位,在纸上作作记录,再就是擦擦水泵上的灰尘,打扫厂区的卫生,其他时候无事可干。实在说,我颇有蓝田之玉落尘沙的不遇感。
起初几天,我们六个既是同学又是同事的年轻人,一道上白班,跟在老师傅后面学习开水泵,一道下班,回附近的二厂职工宿舍十一号楼吃饭睡觉,只要姓李的那位老师傅不在,几个人每天嘻嘻哈哈倒也不觉得日子十分难过。
老李是厂里的老杆子,在小字辈面前固然有高高在上的资格,加上我们如同发配宁古塔的罪臣一般,不受公司待见,于是他自以为更有严加管束的责任,每每喝得醉醺醺之后,便摇着巨腹坐到我们中间耳提面命。他响亮地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不落一人数落一通,都是些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小事以及莫须有,经他上纲上线,每一件几乎都足以打发我们回老家。举个例子,上班头两天,我们带着过去的课本以及文学书到机房里看,与其在机房里无所事事,不如读读书增加一些知识,这本应当是受到前辈鼓励的事,但到他眼里就成了不务正业,于是举报到厂长那里。还好厂长是个明事理的人,热情表扬了我们一通,又叫我们不要与他计较。据说后来他又告发到公司经理那里去了,事情不了了之。但这足以让涉世未深的狼们惶恐多日。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春节期间的某一天,我正和老水在机房里吧唧着口水谈县城丝绸厂里的漂亮妹子们,老李突然来了,打着饱嗝儿呼着酒气,指点我们要尊重老前辈,并详细告知我们他家的具体方位和行走路线,大约是叫我们去拜年。那时我们年轻气盛,并未让他如愿。
接下来就是独立倒班,那开水泵的活计不是开飞机造火箭,说到底是从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都可以胜任的。厂里的职工本来就只有寥寥十数人,倒班过后,就只剩下当班者一个。水泵在运转时,厂区里只有淹没一切的轰鸣声,一旦水塔水满机器暂停运转,就静得能听见蚂蚁走路。十八九的青春原本热血,却被围困在离地两百米高不见人烟的山中碉堡里,好比笼中困兽。我常常站在厂区围墙边上,面目呆滞空洞地望着前方的那条流向县城的大河,觉得自己是个被遗弃的人,每天数着秒虚度年华,那河里流的似乎不是水,而是群虫挠心般的寂寞和忧伤。
白天尚可勉强打发,躺在厂区野草坪上晒晒太阳,看看飞鸟,读读古诗,想想心事,一天就慢腾腾地过去了。到了晚上,就很难熬了。几盏昏黄的白炽灯照着厂区,一个人坐在机房里,望过去就像明灭的鬼火,偶尔一声鸟叫,能把人吓得魂飞魄散。刮大风的时候,厂区高高的柏树被吹得东摇西晃,像人影在出出没没。于是想到鬼。那些日子,厂里的几个青工常在我们面前谈鬼,说某一天他们晚上值班,听见泵房里的凳子被拖得哗啦哗啦响,从门缝偷偷往里看,有两个青面獠牙的老鬼正在拖着板凳干架。又说某一夜,他们看见一群鬼坐在厂区院子里,就着一堆火抽水烟筒。诸如此类。青工们说得有鼻子有眼,当时自然是不信的,可是夜里竟不敢出门,连撒尿也在备好的啤酒瓶子里解决。有一天晚上我值班,金海和发祥这两个与我关系不错的老青工偷偷摸进厂来装鬼,躲在一棵树下喋喋哇哇地乱叫,把我三魂吓掉了二魂半,身上汗毛根根竖起。
那年的腊月三十,正好我值班。我早早在家吃过年夜饭,就骑着自行车往二厂赶。漫天的大雪狂乱飞舞,我穿过茫茫雪地和烟花爆竹的热闹,把自己锁进差不多与世隔绝的被大雪静静覆盖的碉堡。我带着一只微型游戏机,打俄罗斯方块,从除夕一直打到初一早上八点同事来接班。出厂区大门时才想起厂长年前曾交待我贴春联,赶忙返回取来对联胡乱贴上。
驮日子过山顶,说的就是那时我的生存状态吧。心里一直郁闷、迷茫、仓皇,甚至绝望,不知路在何方,与一个十八岁少年花红柳绿的梦想远之又远,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哪天才是尽头。多年以后,一位朋友在诗作中这样写道:“如果你还在思想,就可能过得比较艰难。”
远在县城的公司总部在我心中仿佛圣地,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天堂,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公司高层慧眼识珠,调我去体体面面地坐办公室。况且,那里还有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姑娘,装点着我孤独的瘦梦。直到现在我仍然想问一问,那些在公司总部办公室里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姑娘,是否明白一匹少年狼当年蚀骨的忧伤?
十一号楼
十一号楼是二厂的职工宿舍,砖混四层,奶黄油漆涂面,上三层有的住人有的空着,底层是厂里办的并不景气的三产肥皂厂。十一是它的编号,在小镇莲花村千园岙地片,这样的宿舍楼总共有二十余幢,另外还有许许多多高大的厂房和办公楼,在当年大别山里那个荒凉的村庄以至整个镇子,它们是鹤立鸡群的村中城,十分抢眼。它们是颇有些来头的,原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兵工厂长宁机械制造厂,生产军用雷达。其时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美国出兵入侵越南矛头直指中国,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逼迫还债,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国家从安危考虑,决定搞“三线建设”,并要求各省“搞兵工厂”,于是大别山里这个封闭的小县,一下子迁移进来五个兵工厂,本地人谓之“五大厂”,职工六千余人,长宁机械制造厂是其中之一。八十年代初,形势趋好,“五大厂”陆续迁出大别山,所有房产全部移交本地政府并被分作他用,二厂分得原是兵工厂供水站的厂区和宿舍群中的十一号楼。
我只是十一号楼短暂的住客,因为在二厂上班不很久,我就调回了县城总部,继续接受锻炼,做管道工。但我对十一号楼是有特殊感情的,虽然接到调令离开的时候,我仿佛从前谪仙流放遇赦,卷起铺盖急吼吼就走了,连回头望一眼也没有。
我们住进十一号楼之前,厂长就已经安排人把房间用石灰水重新粉刷了一遍,并购置配备了煤气灶,给每个人买了一张简易工人床。六个人除了一个家在本地不住外,五个人分得两个套间,我和老水、力峰住三楼三号房,文明和显亚住二楼一号房。在二厂惟一的好处,就是住房比公司总部宽敞,从学校十人一间的拥挤宿舍里搬出来不久,一个月交两三块钱就能住到六十多平的房子里,也算是一种惊喜。正式搬进去那天正好单位发工资,六匹狼揣着一把钱就骑着二八大杠呼啸着往城里奔,买锅碗瓢盆,买洗换衣裳,买青菜豆腐肉,开始了新的群居生活。
厂里没有食堂,除了我们几个,其他有家有室或者虽是单身但开小灶,所以我们自给自足吃伙食团。轮流买菜烧饭洗碗,吃完了往贴在墙上的纸上划个圈儿,月底结算各自的伙食费。工资不算多,但在小城也的确不算少,只是我们都是农家出身俭省惯了,并不舍得经常吃肉,嘴里长期淡出鸟来,金月、老房这两位老职工于是隔三差五叫我们去他们家改善伙食,厂长也常常把烧鸡烤鹅夹到我们的碗里。十八岁的年纪,吃自然不是最重要的事,个个都有远大的理想。不当班时,就在房间里下棋、练字、抽烟、扯闲篇,或者看专业书准备自学考试拿大专本科文凭。房间的墙上贴着廉价买来的励志字幅,“有志者事竟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诸如此类。闲得发慌时,就结伴去兵工厂的老厂区瞎逛。那里有兵工厂留下的电影院、澡堂、医院、冰棒房、防空洞、五金仓库、职工培训中心等等设施,当然都是遗迹,房子大都空空荡荡,门窗被贪小利者拆得七零八落,有一些房子被附近村庄里的农民占去改作了猪圈牛栏鸡舍,实在没什么好看的。不过那里有一个小型的菜市场,还有台球室,倒也还算热闹,最关键的是,那里偶尔会有年轻女子出现。
饱暖问题初步解决之后,女人对少年狼突然间具有了无穷的诱惑力。然而二厂阳盛阴衰,只一个女职工而且早已结婚生子,十一号楼周边那些楼上住的多是乡镇企业的青工,他们的女人只能偷偷地望望,县城又那么远,城里的女子根本没有机会结识。几匹狼可谓如假包换的没尝过女人滋味的童男,真实却又不明就里地渴望着,半夜躺在床上睡不着,扯女人经扯到浑身发热,第二天掀开床铺,总能在某匹或几匹狼的床单上发现可疑的地图。几个已婚的老青工,又偏偏爱在我们面前大谈男女欢愉之妙,惹得少年狼拼命舌舔干唇。有一天,一名老青工偷偷带着正在恋爱中的女朋友溜到十一号楼过夜,据说还把单薄的工人床弄出了不小的动静。这原本是件幽密的事,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向来有些邋遢的他忽然把被单洗了晾晒在阳台上,暴露了秘密,经一名过来人窃笑着指点,十一号楼忽然间有了暧昧的意味。那夜的床谈因之多了些知其所以然却不知其然的探讨,那夜的清梦因之更多了些朦胧和焦渴。然而女人都在城里,女人远在天边。
如同一树李子,虽是一同开花一同结果,果子却有早熟迟熟之分。上班不长时间,在另几匹狼还在不着边际地过嘴瘾时,文明和老水私下里已经在结伙搜寻目标了。一个初春之夜,这两个家伙背着我们从县城丝绸厂驮回两个妹子,去二厂厂区喝酒。据说其中一个长发飘飘长得很像其时正红的歌星周慧敏。据说那晚他们喝了整整一捆啤酒,然后又骑着车一人车屁股后面驮一个,跑到县城大河的沙洲上谈恋爱。还是据说,据老水说当晚下着雨,老水和他带的那个妹子早早散了,而文明和小周慧敏搂抱着躺在沙洲上,冒雨一直交流到下夜三四点。事发后,这二位尤其是始作俑者文明受到另几匹狼激烈地声讨,被迫请喝了一场啤酒了事。每个人包括老水都巴巴地探他的口风:“你这个杂种,到底搞到手没有?”文明这哥们儿却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管一味奸诈地坏笑,酒喝得够高了,笑得头都埋到裤裆里了,仍然没套出什么实质性的话来。只透露说随便摸了,至于摸了哪里,怎么摸的,摸到了什么,问了一百遍,硬是屁也不放一个。这事当年是个谜,而且必然是个永久的谜,因为一年多前文明就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永远闭上了那双炯炯又坏坏的眼睛。去年底他的祭日,几个当年踌躇满志的少年狼而今灰头土脸的中年猫相约了,驱车数十里山路,去他老家背后山坡上给他烧纸,我们还在问:“文明你这狗日的,当年到底搞到手没有?文明你这混蛋,怎么丢下父母妻儿一个人跑到阴间享清福了?”
一周只用上两三个清闲的既不用动脑也几乎不用动手的班,如果不时刻想着到公司总部去高就,并且不想女人的时候,十一号楼里的光阴还是很闲散的。阳光总是很好,我也总是喜欢坐在阳台上给过去的同学写信,无非是现实的工作生活和空而又远的理想,重复来重复去的相互不厌其烦。或者读书,写写日记,与在厂区碉堡里一个人心事满腹黯然神伤相比,十一号楼多了些人间烟火味。
二厂的职工差不多有一半是原来兵工厂的遗民,也是镇子上的原住民,十一号楼里之前其实只住着几个同事以及他们的家属。厂长姓程,是厂里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官,自然也是十一号楼的楼长。是个矮壮谢顶的半老头儿,早年离异,带大儿子过,大儿子与我们一道从学校毕业,分在县城里公司办的三产一个小机械厂当车工,并不常回来,所以等于是独居。他是个极爱整洁的人,厂区和十一号楼因之几乎一尘不染,也是一个十分讲原则的人,老职工并不敬他甚至还老在我们面前说他的不是,然而他对我们却仿佛严父,生活中悉心关照,工作上严格要求,为人处世方面也经常提点。那些日子,他经常宽慰我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虽然不免空洞,于我却也是希望和安慰,并且我的调动,他也的确是在公司经理面前说过不少好话。他还对我说过:“你性格清高又倔犟,将来可能要为此多吃些苦头。”后来也都应验了。
二厂惟一的女同事胖胖憨憨的金月,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大姐。家里有好吃的必定老海碗装了送来,我们的被子脏了她必然拆了洗好再做好,我从十一号楼搬走的那天,天刚好下着小雨,我都敞着头骑车出门了,她还撵上来送给我一件紫色的塑料雨衣。她的丈夫与我同宗,在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教英语,也是个人缘极好的人。好些年以后,我早已从公司调出当了一名记者,在一个乡镇采访吃饭时偶然遇见他们,我恭恭敬敬陪了他们夫妻俩一杯酒。人生行旅中遇见的这些好人,是应当铭记并终生感激的,虽然那些事他们早就忘了。
十一号楼我近二十年没去过了,不知道三楼三号房墙壁上,我当年用铅笔给想象中的情人写的诗还在不在?
安装队
我承认,十八九岁时我有着一架与自身资历、阅历和能力极不相称的瘦硬的骨头,也就是厂长所说的清高又倔犟。并且这种瘦硬一目了然,像草标一样随时出卖着我,让我为此付出代价。我不是为此检讨或是感到羞愧,青春原本就应当是一把青霜剑,而不是一根蔫黄瓜,即使不是刺伤别人就是刺伤自己。如果时光倒流,我想我仍然会不计后果地在脖子上插一根草标。只是有点儿不巧的是,新任的公司经理也是一根亮晶晶的麦芒。
到二厂上班后不久的一天早晨,厂长召集所有职工开了个短会,主题是迎接新任经理到二厂视察。新经理比我们迟三天到公司,是第一次来二厂,对于全体职工来说自然是天大的事。厂长一声令下,整个厂区顿时如临节庆,擦桌子,扫机房,除杂草,挂横幅,在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又齐刷刷站在围墙边眼巴巴望着通往山脚的水泥台阶个把钟头后,经理终于在公司部分高层的簇拥下莅临厂区。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瘦削,黑脸,目光凌厉,眉宇间有杀气,眼扫到我时,我身上感到凉。据说是从建设局放下来重用的。夹道鼓掌欢迎之后,头头们挤在简陋而整饬的厂办开了个短会,随后经理分别找职工单独谈话了解情况。新官上任,这些原不过是履行程序。但待经理走后,厂长忽然对我们几个人说,新经理此行有考察我们几个中专生的素质、准备调一两个人去公司总部的用意。厂长话未落音,我骨头都凉了。
“公司安排你们到二厂基层锻炼,对此你有什么想法?”搁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冠冕堂皇大而无当的虚话我张口就来,可当时我说:“我认为是浪费人才,公司职工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应当把我们分布到各部门充实力量。”经理两道眉往中间挤了挤。“专业之外,你有什么特长?”“我会写作,会吹口琴,会弹吉他,会写美术字,会主持晚会。”经理的脸上起了乌云,顺手拿了一本杂志看。“你认为,怎样才能增加二厂的供水量?”“自来水最大的用户是企业,所以我认为首要的是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怎么扶持?”“……”我语塞,然后很不靠谱地东扯西拉。经理把杂志往桌子上一扔说:“好,你可以出去了。”
经理走后,厂长悄悄对我说:“经理对你印象好像不是太好……本来公司认为你是个不错的苗子,唉!”随后的那些日子,我站在厂区围墙边看河水东流的次数更多了。
然而几个月后,公司突然下了一纸调令,调我和文明到公司总部工作。厂长把盖着鲜红公司大印的文件递到我手上时,就像打入冷宫多年的妃子重被召幸,我激动得发抖。呜啦!
我和文明被分在公司的给排水工程安装队,做管道工,而不是坐办公室。公司一位高层找我们谈话时说,这是让我们继续接受锻炼,但并没有说明这锻炼的时间是几个月还是几年。这叫我丧气。后来有人告诉我,经理说我头上长角,得狠狠地磨磨。
我穿着廉价的西装,用二八大杠驮着笨重的管道套丝机、三角架,肩上扛着管子钳、铁锤、扳手、水龙头、弯头、束接、闸阀这些死沉的铁器家伙,跟着老胡走街串巷,给用户安装水管子。我家住城郊,这个小城里有我太多的熟人,于是我尽量把头低着,怕他们看见了笑话,一个念了书回来的人干着出苦力的营生,毕竟不是什么荣耀的事。当初中考的时候,全县数千名考生我考分排前十,因而才得以走中专,录取通知书到达的那天,家里摆了七八桌酒席,其荣耀远胜于今天学子考上重点大学,远亲近邻则把我当作他们教子的榜样。
我没脸见人。事实上,我家下屋的一位婆娘就跟她的三个儿子说:“念书有么屁用,你看上屋劲松,念那么多书把家都念空了,回来还不照样出蛮力。”她家的三个儿子后来果然都没念书,早早当建筑包工头或做生意去了。
老胡是我师傅,年纪与我父亲相仿,是个五大三粗的忠厚人,言语不多而诙谐,不如那些嘴滑的讨头头们喜欢。他耐心地教我测量、套丝、安装。然而我不肯学,不是把套丝机弄坏了劳烦他修理,就是把水龙头拧断了惹用户不高兴,还把工具往地上掼得哗啦响。师傅脾气好,从不恼,他总是慢条丝理地吸完一根烟,把烟屁股砸到地上,咕咚咚喝完一碗茶,捋一把满脸的络腮胡子,然后起身一个人忙活,只叫我帮他拿拿工具。在安装队队长面前,也从不说于我不利的话。文明虽然比我务实卖力多了,他的师傅却常常在队长面前打他的小报告。在公司八年,我做过多次学徒,但我只承认老胡是我师傅,虽然他一流的管道工技艺我几乎什么也没学会。
那年夏天县城东区大改造,地下所有的供水管道全部改线,安装队十几名队员全体上阵。铺设口径两米的铸铁管道是地道的力气活,光几百个接头就是浩大的工程量。几个临时请的小工负责抬管子,老师傅们负责技术,我和文明以及另两个学徒卫东和王进打下手,用钢锯锯管子,用手和膨胀水泥。死热的天,敞着头暴晒,一天身上脱一层皮,和水泥的手烂得大窟窿小眼。一天上午,公司经理开着小车来巡视工程进展,正好站在我和卫东边上。我和卫东坐在沙土上,一边两手插在盆里扑哒扑哒地和水泥,一边满嘴跑火车,不像其他人噤若寒蝉。经理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俩,皱着眉毛,一脸愠色。卫东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会意,四只手在盆里胡乱一顿扑腾,经理锃亮的皮鞋被水泥溅了个满天星。
秋天的时候,公司举行管道安装大比武,要求安装队所有队员全部参加,师傅带徒弟,俩人一组。比武场设在公司大院里,七个三角架一字排开,每组各显其能,公司高层以及办公室的几只蝴蝶站在二楼走廊上观战。后来,他们又走到院中督战。老胡手脚如飞之余,扯起一根用于防漏的油浸麻丝,举起来对观战者说:“你们看看,像不像大经带?”比武场上顿时笑翻,几只蝴蝶花容失色,经理原本兴致勃勃,这时脸顿时往下一拉。然而老胡是元老级别的老杆子,又从无谋个一官半职的野心,经理对他也无可奈何,于是转而批评他的徒弟技艺生疏,徒弟无能师傅有错。我发了血性,把手里的管子钳往经理脚下哐当一扔,国骂一句,“比他妈个×!”说完我就从车棚推出二八大杠,骗身上马,扬长而去。
据说当天的比武不欢而散,经理极为震怒,在办公室砸了茶杯。第二天下午,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在门口看见我,语重心长地说:“小储你是个好苗子,不过要学会能屈能伸。”我默然,心里盛满感激。后来的一段日子,我好像没有冒犯过任何人。
其间,公司搞技改、建水塔、办元旦晚会、搞文明创建,经理亲自安排我做过几次写写画画或者监工的事,每次我都全力以赴。经理对别人说过,储劲松那小子是有点儿才。每回活计结束,我都巴望着经理能够加以委任,起码调离安装队,但我一次次失望。
第二年春节大初二,我拎着烟酒到经理家拜年,本心也存着套套近乎的念头,更想问问什么时候结束锻炼。然而在他家的沙发上我如坐针毡,直到飞一样地逃离,什么也没套什么也没问。经理也只顾专心喝他的功夫茶,肚子里肯定是热的,但他什么体己的热乎话也没说。
我在安装队待了一年零五个月,这才调到生产技术科做了科员,如愿坐上了办公室。那已是又一任新经理手上的事了,也就是之前劝诫过我的那位副经理,并不老的老经理被东区管道改造工程绊倒了。平心而论,他是个有水平有能力的人,公司在他手上蒸蒸日上,我不喜欢他,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一根麦芒。后来几个月我还梦到过他两三次,不是什么好梦,内容也大致差不多:他胡汉三又杀回来了,重新坐在经理宝座上,黑着脸打发我回了安装队。
储劲松:1970年代生于安徽岳西。现供职于某宣传部门。出版有《黑夜笔记》《书鱼记——漫谈中国志怪小说及其他》《风霜冷白》等多种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