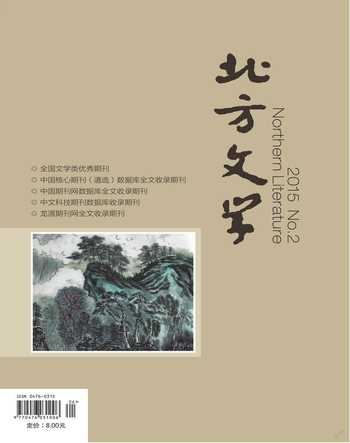当代小说家的“生命创作”
2015-05-30余聪聪
摘 要:文学的指向是多维度的,而生命无可置疑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作为人学是关乎现实世界中鲜活的社会个体的生命形态的书写。而优秀的小说总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关注生命体验,叩问生命的价值,并给予生命以温暖。当代小说家正是以这种热忱的文学姿态书写生命,凝结于文字之中却又游离于文字之外,得以抽象出生命的真谛所在。
关键词:时代性;生命体验;可能性存在;温暖生命
当代作家邵丽在其中篇小说《刘万福案件》中说到:“‘真正的小说——看清楚它的人物,琢磨透它的细节,从而对他们的生命进行评价。”[1]
一、时代与生命的体验
文学的每一次转变都见证了生命的发展历程,时代的发展总是被重重地打上上帝与人为之手的烙印,在两者之间左右摆动。当代小说家正是立足于生命价值倾向,自觉地使自己的小说创作关注和评价寄身于时代下普遍而又具体的生命存在。
时代性的社会进程为小说家提供了某些必要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他们须因应这种生活变化,以时代性的生命体验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创作新的文学范式与规律,乃至新的美学况味。当代小说家需要的是基于其时代性的生命体验创作出严格意义上的“时代性小说”,而作品正表现出当代人的生命特质。作者曹寇在其《塘村概略》小说创作谈中说到:“在我看来,人类来到世上与其说是为了追求幸福,不如说是来感受痛苦的。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验和痛苦,既不俯视,也不仰视,就这么认真看它一眼。用一条狗看另一条的眼神。”[2]《塘村概略》最深刻的地方抑或说最为根本的意图就在于揭示当下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人的基本境况和生命形态。的确,当代小说家对于世界和人的感受与诸种时代符码交错纠缠,经历着某些别样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这也就自然表现出他们所拥有的鲜明的生命创作的文学姿态。
“我很害怕这篇《无家别》会成为无效的写作,我至少要说服自己,才能写下去。换言之,如果我要写一个关于‘我的故事,我得为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寻找到新的叙事逻辑。”[3]作者计文君从2000年开始写小说,至今为止几乎全部作品都与那个叫“钧州”的地方有关。那里有着和中国其他城市相似的当代命运,它是作者的文学生命之乡——用自我的文学生命容器来盛放从动荡繁复的现实世界领受得来的生命经验。作者在《无家别》中所刻画的失败者“我”和可以被称为“成功人士”的代表季青都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基于此,我们应追问,生命在这个繁华而又薄凉的现实中究竟该寄身何处?
二、生命个体的存在性意义
当代小说家以新的要素结构小说文本时,最终必须、也只能落实和回归到“对于人的描述”这一文学亘古的要义上。那么,当代小说家如何以小说的方式来呼应文学伟大的精神传统?小说对于人的生命的关注正是当代小说、当代小说家应有的文学观念。通过小说对人的生命进行评价,也就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生命的本质、更为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意义,从而创造生命的价值,这无疑是文学是人学的本质要求。当代小说家积极关注鲜活的现实生命形态,并将自身对现实生命形态的探索与思考注入小说创作当中,使得读者在阅读和鉴赏小说的过程中推彼及己,以更为合理的方式建构自身生命的有效力量,使之丰富、充盈、坚韧。
邓一光的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充满了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量——坚韧、热切、忧虑、真诚。作者从鲜活的现实生命形态追寻生命可能性的存在,对生命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追问,寻求生命的释放与救赎。小说中,作者关注的是底层生命也需要尊严的存在,是从生命内部获得的与世界平等的力量。“始终相信可能性的存在,至少一部分,它们的确存在,只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它们在哪儿,”[4]这是邓一光对生命存在可能性的诠释。小说描述了一个挣扎于生存困境和心理困境中的少女,兰小柯;一个对音乐执着却身患重病的教师,左渐将;一个患有智障却有着音乐天赋的男孩,兰大宝。他们原本都将自己的生命定位为没有光亮的悲剧的存在。最终,兰小柯在合唱团指挥左渐将的引领下,逐渐淡薄了对世界的敌意,正面理解生活和爱,最终和哥哥兰大宝一样,实现了生命的救赎;而左渐将用其最后的生命之光,照亮了兰氏兄妹的生命路程。生命存在着可能,她让一个卑微却高傲的灵魂彻底升华完成救赎,热爱自己原本千疮百孔的生命,寻得生命个体的成长与发展的可能性,使生命犹如“百合”一般地绽放。
三、生命的劝慰与温暖
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生命的更替都不可避免地会衍生出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毋庸置疑地会给人带来痛苦。但是,如果我们认同其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无可逆转的方向性趋势,当代小说、当代小说家就不该过分沮丧于这个大势——人类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去,你说它好也罢,坏也罢,那个方向都是无可避免的。而对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进行过度的描黑,只会徒增人的悲伤。小说家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小说写作需要与时代相勾连的同时,应该以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方式,给予鲜活的现实生命体态某些劝慰性的温暖,从而做到温暖生命。
弋舟中篇小说《而黑夜已至》,即是他基于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境况以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明确的文学意图尝试当代城市小说书写的产物。小说围绕着一个时代性的“我”来展开,来呈示“我”以及“我”周边的同处于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更多的人的相对普遍的生命形态,它叙述并揭示出了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尤其是其内心的隐疾——人性的“黑夜”。但同时,作者试图呼吁一种治愈性的、温暖的文学创作倾向,期望构建带有光明属性的文学理想。小说中“每个人都在憔悴地自责”,“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他们惴惴不安地活着,反省自己的罪恶,并且心怀忐忑地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赎罪”,以求让自己生活得更安心。小说以“而黑夜已至”为名,毋宁说是在呼召“黎明将近”。
人,终归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珍贵的,他需要黎明,需要温暖,在显豁的城市化进程中亦如此,甚至这种需要还显得更为迫切和紧要。小说、城市小说需要叙写这种黎明与温暖,当代小说家更要自觉地在自己的小说文本中积极构建这种黎明与温暖。
四、重塑生命的创作
这个时代在迅捷、快速地发展,以技术力量的飞跃式发展为表征,既往的、经典性的文学经验,的确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去描述我们在新境遇之下的新困境,这也催使我们在结构作品时产生了新的范式与规律,乃至新的美学况味的需要。当代小说家的写作就要糅合历史记忆、现实生活经验以及母体文化,在虚无的现实中注入人文温情。
生命不仅仅是物体活着的一种外在表现和过程,生命与激情、规则、理性和灵魂相互交织,是一个有灵魂的身体,而其灵魂正是从人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出发。当代小说只有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才能枝繁叶茂、扣人心弦。曹寇在《塘村概略》中讲述的只因为有着丑陋的容貌,一名普通大学生被镇上居民乱棒打死的“群体性‘无罪暴力”一事。其中所传达的是“群体性庸常之恶”,那些被日常生活惯性所裹挟的精神世界成就了隐秘却又颇为壮观的群体性庸常的生命形态。在此,作为个体生命的我们需要对这个时代、世界保持相对独立清醒的判断,呼唤灵魂的苏醒,寻得人性的突围。弋舟在创作《而黑夜已至》中除了真实反映生活的本质,还对人鲜活现实的生命体态进行了描述,并给予那些祈求得到救赎的生命体必要的劝慰和温暖。“因为,我从来相信,时代浩荡之下的人心,永远值得盼望,那种自罪与自赎,自我归咎与自我憧憬,永远会震颤在每一个不安的灵魂里。”[5]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似乎也应当着眼于这个方向:追求生命的圣洁化,呼唤灵魂的苏醒,寻找由生命外在通向灵魂深处的觉悟。
参考文献:
[1]邵丽:《刘万福案件》,《人民文学》,2011年第12期。
[2]曹寇.创作谈:塘村概略[J].北京: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
[3]计文君.创作谈:无家别[J].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增刊第2期
[4]邓一光.创作谈:你可以让百合生长[J],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4期
[5]弋舟.创作谈:而黑夜已至[J].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5期
作者简介:余聪聪(1993-),女,江西上饶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