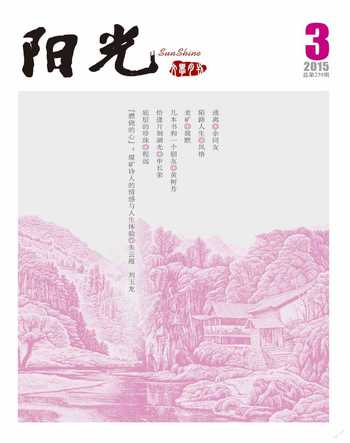“燃烧的心”:煤矿诗人的情感与人生体验
2015-05-30朱云霞刘玉龙
朱云霞 刘玉龙
朱云霞:刘老师,您好!我看到相关材料说您从1974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以写煤矿题材的诗歌为主,最初是什么样的冲动或者说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始写诗的呢?
刘玉龙:我最早发表文学作品是从1974年开始,一直比较喜爱诗歌,也就进行一些创作。作为老三届的学生,我1969年到农村插队,其间曾经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新闻写作,工作之余也有一些诗歌创作。1973年底回到煤矿工作之后,才发现煤矿是一块盛产文学的富土。当时回到煤矿工作是立下必须下井当采煤工的生死状的,这一井下的经历对我以诗歌写煤矿有很大影响,因为进入井下就特别容易产生联想,更能激发写诗的灵感。1975年,我有一首诗歌发表在徐州唯一的文艺刊物《徐州文艺》上,算是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在此之前,一些诗歌只是登在宣传栏上,当时宣传栏的影响力非常大。当时有一个徐州工人业余创作组,很多作品通过这个创作组得以发表,那是一个强调集体的时代,很多诗歌最初发表都是以单位的名义署名,比如我的作品都是写徐州矿务局新河煤矿。事实上,后来在井下当采煤工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发表了一些诗歌,有了一些影响,开始引起单位的关注,大概在1974年底就从井下提拔上来做宣传工作。当时非常著名的诗人孙友田专门从南京到徐州来,提出想把我从徐州调到南京的文联(当时作家协会还未恢复工作,主要是文联),但是单位不同意,孙友田就送了我一本诗集。算起来,因为诗歌和诗人孙友田相识相交已经30多年了。我最初开始创作的时候,主要就是以煤矿为书写对象,而就整个诗歌创作历程来说,写煤矿的诗歌占我作品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我最早的诗歌都是煤矿诗歌,而且我认为我写的最好、最多的诗歌也是煤矿诗歌。
朱云霞:也就是说,其实最早开始煤矿诗歌创作跟您的个人工作经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主要是个人的特殊感悟和个人的才情在煤矿那个特殊场景中的诗情的爆发。渗透情感的文学作品才是最有力量的,您写煤矿的诗歌中总有一种对煤矿特殊的关切、热爱和深情,读这些煤矿诗歌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如同一幅幅画卷被打开——煤、矿井、矿工以及矿工们的工作、心理、情感,都在诗歌中展现,能否谈谈是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什么样的情怀让您对煤矿如此情深?
刘玉龙:我认为文学就是一个“情”字,表达的是人类复杂多样的情感,而诗歌更注重抒情。如果诗歌或者文学作品没有真情,没有感情贯穿就不叫文学作品。我对煤矿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情感,有几个原因。首先从个人角度来说,我的家庭是矿工之家,我父亲是煤矿工人,我的大哥也是矿工,所以我非常熟悉煤矿和矿工的生活,我认为我和煤矿有着血缘关系;第二点,我自己又是矿工,尽管在井下的时间并不长,但就是在井下工作的这些体验成为我诗歌创作的基础;第三点,虽然后来我成为煤矿的领导,但成为领导后更有一种深沉的责任感,觉得要对得起矿工和煤矿,深切体会到矿工是如此可爱、可敬,非常伟大也很可怜。所以,我对煤矿的感情可以说是在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工作体验中形成的刻骨铭心的感情,在深入煤矿生活的过程中,诗歌一直伴随着我。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在第一时间写了一首诗《致开滦矿工》,当时看到地震的影响后,就对煤矿工人有一种深切的担心、牵挂和怜悯,那时候的情感是我对煤矿最丰富、最复杂的情感,有一种心痛和担忧。在我心里,我和矿工是亲如一家的,是兄弟姐妹一般的情感。所以,我当领导之后的诗歌写作,非常愿意写矿工,而且有一种职责,替他们说话或抒情,他们的天就是我的天,因为煤矿中的死亡几乎无法避免,矿工用生命换来的光明值得赞颂和书写,而矿工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品质也值得学习和肯定。许多诗歌,就这样同煤矿和矿工发生了关系,并且是同我的灵魂和情感血肉交融,留下深深的轨迹和清晰的影子。有一首孙友田非常赞赏的诗歌《湖中的父子》写父子晚上的对话:白天父亲在湖中打渔/儿子下井挖煤/都在捕鱼/父亲捕的是银光闪闪的鲤鱼/儿子在井下捕的是金光闪闪的黑鱼/晚上的时候/两个酒杯相互问询……
朱云霞:您的诗歌如此质朴却又如此感人。作为诗人您将文学之根植入煤矿,作为煤矿的领导您也一直以代表煤矿工人的声音为己任。煤矿行业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的丰富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很特殊,能否结合您个人的经历谈谈煤矿语境中的文学创作,比如在大型的煤矿中,是不是都有很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您觉得文学或者诗歌在煤矿这样的环境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读者主要是矿工吗?能否说说,您在创作的时候想过是要写给谁看吗?
刘玉龙:的确,在我看来煤矿不仅盛产煤,还盛产文学和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其实都是在自发的状态下进行创作的,写作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去预设读者,尤其是作为一个想要表达内心情感的诗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的确是面对矿工的,因为这是自己最熟悉的群体,写的对象是他们。而关于煤矿诗歌的读者,我认为不仅是煤矿工人的,要看诗人作品发表的时代和刊物。以我自己来说,到1990年代诗歌成熟之后,发表的期刊比较丰富,不仅是在煤矿领域了。当然,煤矿领域中确实有很多作家,也有很多并不是很有名,他们的作品的读者主要看刊登的刊物了,有不少依然是在基层单位很艰难地写作,我在单位时也很注意帮助那些写作者,毕竟文学作品,尤其是好的文学作品值得提供关注的渠道。
煤矿领域中的文学的确非常特殊,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作家,以中国作家协会来说,担任过副主席或者正在担任副主席的作家如谭谈、陈建功、刘庆邦。而且,虽然在孙友田写煤矿诗歌的时候是受到时代文化鼓舞的,而到了后来其实很多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是受到了压抑的,只是不少作家一直保持着创作的热情,1970年代的文学路上挤满了各种热爱文学的青年。而文学对于煤矿来说不是特殊意义这么简单,首先文学和矿工的生活其实密不可分,是矿工生活中的水、空气和盐,可以说即便没有煤矿作家的创作,煤矿工人在井下其实也在无意识地进行着文学创作,就如同《诗经》中的哼唱,在井下其实随处都留下了矿工的文学印记,比如他们写的很多打油诗,非常有趣,因为在井下除了闪闪的矿灯的光彼此无法看到对方,在黑暗中声音是最好的特征,看不到却可以进行丰富的对话和交流,黑暗所激发的想象和灵感非常丰富。井下的黑暗提供了想象光明、想象太阳、拥抱太阳的最好方式,所以煤矿出诗人。此外,就煤矿来说,这个行业很特殊,不是一个个人化操作的空间,煤矿需要矿工们不同方式的合作,是一个链条,而在井下也需要形成集体感,要交流和对话,他们在黑暗中的幽默语言和交流方式也为很多诗人或者小说家提供了想象和素材,刘庆邦的《我怎么写起小说的》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朱云霞:就您个人的创作来说,我觉得在诗歌集《燃烧的心》中,充满了力量、热情和激情,而在2000年前后的诗歌属于比较沉静、沉思,更内敛,有很多对生活、生命和人生的深刻思考。
刘玉龙:这种变化其实跟最切身的体验有很大关系。前期确实有着非常的激情和热情,这是源自跟矿工的密切交流和对他们的深厚情感,那时候曾经发表过一些创作感受,曾经在《中国煤炭报》发表了《煤炭诗的追求》;而后期的沉思其实包含了另一种情感和思考,尤其是在社会改革时期,让我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站在矿工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的处境、未来及他们的生命。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突如其来的潮水》,那时候,我正在办公,办公室突然就拥进几百矿工,他们都是来问工资的事情,当时很多领导都不在,我安定地接待他们,我没有说话,当时就写下了这首诗:突如其来的潮水向我涌来/突如其来的潮水从瓶中涌来/这里不是金山/没有法海/没有许仙/没有白娘子/……闹剧的因因果果都与我无关/任水漫过脚……骨子深处我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我跟他们的情感很深厚,有一种使命感,不再是自发的去创作,而是融入更多的思考。其实我觉得后来做领导后的诗作,因为写得有些名气了,再加上当了领导约束的东西反而少了,反思自我的力度更多了,如我在诗歌《心灵独白》中说:我出卖过我的灵魂/在那个年代不需要打上标签/我出卖过自己的眼睛/出卖过自己的耳朵/也出卖过自己的肝脏/但是我不会出卖裸露在天地间的一枚雨花石……这枚雨花石是自己的良心,面对下岗、裁员、无法发工资等等问题作为领导者无能为力只能执行政策,而作为一个作家我不必出卖自己的良心,我可以从更人性的角度去表现和思考矿工们,作家需要心灵有最广阔和最自由的空间。当然我诗歌的转变其实也跟一件事情有极大的关系,国务院有一个命令是关于煤矿企业破产的问题,提到煤炭资源枯竭没有开采价值的煤矿都要关闭破产,那时候作为煤矿的领导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知这样的消息的,非常突然,像徐州矿务集团下的董庄煤矿等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话,大量的煤矿工人就要下岗,就引起更为深切的思考和触动。其实我的工作有好几次都可以离开煤矿的,可以调到不是这么基层的单位,但是我对煤矿的感情,和这些矿工的感情无法割舍,工人们也曾写过信挽留我,他们真的很可爱,其实我自己内心都放弃了调动的机会,煤矿和矿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后来煤矿发生很多变动需要改革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陷入了更深的思考和反思,当时写过这样的诗句:被突然起来的飓风挤压倒下的/何止是大树/鸟巢连羽毛也……经过烈火烧就的眼睛/在黑暗中看真相比太阳底下看还分明/阴谋的同行者很多/不光是凶恶的狼还有善良的羔羊……原来我说爱人无需再爱/原来我说恨者无需再恨/用意志的眼睛或者向西或者向东/太阳升起的地方总有自己的精神绿洲……这种晦涩的语言和诗歌基调也是那时候对现实工作和生活的感悟和思考。从那以后写的诗歌,相对来说就不再有之前的热情和激情,而是对生活、对人生的更多的沉思。像我最近写的一首诗《茶馆》表达的是对现实语境中“人走茶凉”的反向思考,其实并非如此,这个要从不同角度思考,有些时候人未走茶就凉了,而有时候人走茶未必凉。
朱云霞:作为一个一直坚持创作的诗人,您的创作历程从1970年代至今,从纵向的比较或者个体感受来说,您觉得1970年代到现在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刘玉龙:从创作环境来说,我觉得目前的自由空间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但是近年来文学并非一种上升的趋势,而是下降和倒退,作品的商业气息太重,金钱化导致庸俗化。按照阶段性来看的话,“文革”前不用说了,多是标语口号性质的诗歌,而改革开放那段时间,由于思想刚刚解放,诗人们为之一震,外界尤其是西方文学开始进入国内,对诗人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个时候是诗坛最繁华的时候,诗人非常活跃,老人们“归来了”,中年诗人非常活跃,青年诗人不断带来新的诗歌风尚,像北岛、顾城、舒婷、海子、西川,出现了太多有活力的诗人。而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后半期以来,诗人的激情、热情和胆量相对减弱了,进入了比较理智的写作之中,可以总结成两种趋势:一是由“大我”到“小我”的转变,二是由“开放”向“封闭”转变,所以也会体现出对整体的淡漠,大爱的缺失,转入到“微我”和“自我”“小我”甚至是“无我”。我也一直持续阅读诗歌界的新诗,但是我觉得让我认同的诗歌越来越少了。而且感觉诗歌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了,诗人们形成自己的群体,阅读和诗评的范围也很小,这是令人堪忧的。而目前的诗歌呢,又带有很浓厚的很强烈的商业操作的痕迹,我也经常接到一些诗歌类的会议的邀请,但是总感觉商业味很浓,让诗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我,甚至是被贴上非常廉价的标签,这样的会议无法引起我的兴趣,大都放弃,太没有意义了。而一些曾经知名的诗人们,现在已经“不接地气”了,写的诗歌多是苍白无力的,单薄和虚无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诗歌界的面貌就是如此不乐观。比如刘庆邦写的《一碗清汤面》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去河南一个煤矿去专门了解工亡者家属的生存现状,其实是无法写出这么优秀而又“接地气”的好作品的。
朱云霞:我想煤矿诗歌的特征应该是在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总体特征的涵括下,又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说到刘庆邦的小说,想起来您也有不少诗歌是写这样一个群体的,比如诗歌《一位工亡者的妻子》《今夜无梦》《生者与死者之间》。
刘玉龙:是的,这个群体非常值得关注。我当时写工亡者妻子的时候,是真的看到身边矿工妻子的悲剧。当时有一个女人就因为丈夫在矿井伤亡了,思念太甚而疯了,她天天晚上都跑到井口去看,去等……当时也有人向我反映这个问题,觉得她已经疯了,是不是把她遣送走,我跟他们说,就让她在那儿站着吧,不用去送她走,等她站累了她自己就会离开的,她虽然疯了,但是并不会闹事,这样的精神病患者真的非常值得人关怀和同情。所以在《一位工亡者的妻子》中这样写道:矿山天黑时披上夜衣/她天黑时穿上黑衣/井口立成一块望夫石/焦急盼望丈夫从煤海归来/树上叽叽喳喳的喜鹊/都知趣闭嘴/丈夫等不来了……
朱云霞:您的煤矿诗歌就关注的范围来说,不仅有对煤、煤矿语境、矿井工作环境及矿工的丰富表现,还以悲悯的情怀和深挚的情感表现工亡者家属的样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表现了您作为煤矿诗人的情怀与精神向度。所以您的诗歌也获得了很多认同,我想多次获得煤矿文学领域的最高奖“乌金奖”应该是最好的说明。应该说目前这个奖非常特殊也非常有意义,不知道您如何看待“乌金奖”这样一个文学评价机制?比如您获得第三届“乌金奖”时的申报程序是怎样的呢?
刘玉龙:我的诗歌在第三四五六届“乌金奖”中都有获奖,毕竟这个奖项是煤炭系统对文学的最高肯定,这也是煤炭系统中的文化表现与其它行业不同之处。这个奖项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级的评价方式,评委们都是国家一流的作家、评论家,比如雷达、谢冕、肖复兴等人,所以说能得到业内同行及文学界对我的诗歌的肯定和认同,是一种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但每一次评奖阶段其实也是对前一次写作的终结,是诗人需要超越自我开始新的写作的信号,所以回顾自己这几次获奖经历,总感觉到人生短暂岁月匆匆,有一种对人生的复杂的感触。至于国内文学界的评奖吧,我觉得以前还是比较认真严谨的,现在可能有些奖项不是那么有价值,也有不少都打上了经济利益和感情色彩的烙印。而“乌金奖”其实有个非常特殊的因素,就是不会受到经济的影响就是其资金来源能够得到保障,是有专项基金的,由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管理,其中开支之一就是“乌金奖”的评选和筹划,所以这个奖项不用去寻求市场利益的推动。
我当时申报第三届“乌金奖”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程序是《中国煤炭报》刊发了评奖的启事,现在也是这样登启事,个人按照要求可以将作品邮寄过去;另一个是经过单位选送。因为是五年一评奖,所以对作品的要求是五年内的,并且是跟煤矿有关的,评奖的过程其实也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并不容易,所以这四届获奖也贯穿了我创作历程中的20年。这个奖也为当代文坛培育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第一届的获奖的陈建功、周梅森等。评奖不仅是一种奖励,还能提供一定的文学交流,并且推荐优秀作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或者推荐作品参加更高层次的评奖,比如参加全国工业题材类的文学评奖等,从多重角度为煤矿作家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
朱云霞:除了“乌金奖”对煤矿文学有比较大的影响,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应该说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协会,对煤矿文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你怎样看待这个协会?以一个煤矿诗人来说,您觉得这个协会对煤矿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刘玉龙:我是在1993年加入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当时全国煤炭系统的作家,也就100多人吧,现在协会的作家比较多了,大概400多了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协会,有自己的刊物可以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也有自己的基金可以评奖,可以组织作家采风交流,此外还可以推荐优秀的作家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协会非常重视年轻作家的培养,以不同的方式为年轻作家提供学习、研讨及交流的机会,也可以成为签约作家等。所以这个协会对我们煤矿系统的作家来说非常重要,有这样一个协会统领大家,让大家觉得很有系统性,我们觉得很踏实,有归属感。
朱云霞:那您觉得近10年来煤矿文学的创作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刘玉龙:近10年来的煤矿文学,从诗歌的角度来看,我个人总结了三个特点:一是,作者越来越多,因为每个大的矿务局都有自己内部的刊物,所以发表的渠道是能够保证的,也有一些全国性的以煤矿文学为主的公开文艺刊物如《阳光》等,从作家的世代来说,老、中、青创作共同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接一浪,一排接一排;二是,目前煤矿作家的写作范围扩大,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书写煤矿领域,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三是,现在煤矿作家的作品发表的刊物也越来越好,这是因为他们写作的质量确实越来越好了。
朱云霞:通过您的总结,或许也可以做这样一个思考:现在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确实对文学创作带来很大冲击,在中国当下诗歌发展并不乐观的情况下,其实煤矿诗歌的发展相对于以前来说反而能够在量和质上保持进步,还算比较乐观。您曾在《煤炭诗的追求》一文中写道:“煤炭诗的追求,应该紧紧伴随煤矿生活的源头,同矿工结成同甘共苦的伙伴,达到思想与艺术的有机统一,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结合。而真正达到这种境界,需要煤矿诗人长期不懈的奋斗努力……用生命和经历写诗,用灵魂和良知写诗,用技巧和语言写诗,使煤炭诗的质量达到新的高度,为当代诗坛奉献黑色的玫瑰。”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优秀的书写煤矿的诗歌出现。
朱云霞:女,汉族,安徽太和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中国煤矿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本文为作者主持的中国矿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中国当代煤矿诗歌研究(项目编号:2013W18)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当代煤矿诗歌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013SJD75002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刘玉龙:男,汉族,江苏徐州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徐州矿务局董庄煤矿党委书记,《徐州矿工报》总编。在《诗刊》《阳光》《工人日报》《人民日报》《雨花》《桥》等杂志发表诗作三百多首。出版诗集《一方热土》《燃烧的心》《旅途的箫声》《悄悄走来秋天》等。其诗歌曾获第三四五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