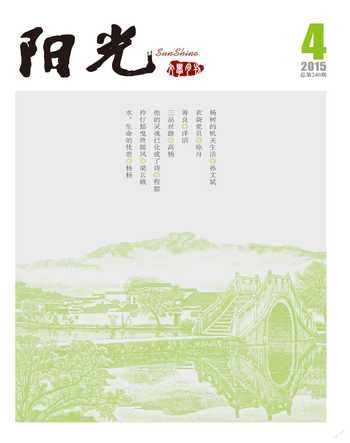笨人憨福
2015-05-30侯孟
侯孟
矿上的夜没有安静的时候,上半夜有上零点班下四点班工人的说话嚷嚷声,下半夜矸石山上的矿车排矸声响过一阵后,似乎要静下来了,拉煤的火车一声吼叫,就像湖中投入了石块,震得矿区的夜又静不下来了。
轻轻重重远远近近的响声,原本不影响许国萍的睡眠。快三年了,她已经习惯了矿上的夜,回到村子里夜里躺下时的那个静,她反倒有些适应不了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习惯也养一方人啊!可今天还是在矿上的土窑洞里,还是听着和以往一样的响声,许国萍却仰躺侧卧睡不着。躺下时,看挂在墙上的月份牌是三十号,实际在床上已经挨到三十一号了。三十一号,就是月底啦。月底,就是一个月过完了。过完了一个月,还有下一个月嘛,担心啥哟?不由人不担心啊!许国萍的丈夫韩松在井下上完三十一号最后一个夜班,就要离开矿上回村里,三年时间的农民轮换工合同到期,他被矿上辞退了。
许国萍曾经到过出煤的平硐井口,等待到点未回家的韩松。站在井口朝里望,脑袋后边的风从耳旁晃过,不情愿地被拽进了黑黢黢的巷道里,反渗出阵阵阴气,让人禁不住打寒战。那会儿,她感到了丈夫韩松在井下生活的恐怖,也原谅了他笨猪似的形体。韩松做不了饭,洗不了衣,眼里没巧手上笨。但他下井很少缺班,每月交到许国萍手里的工资厚厚一沓子。狸猫灵,吃肉。熊猫笨,吃竹。天下动物,老天爷总会让活下去。韩松不会日鬼八诈骗外人,也不会花麻俏嘴哄家里人。当年,是韩松一副男人的好脸子和粗粗壮壮的身板儿让许国萍有了嫁给他的想法,而忽略了他笨拙表现的细节。相亲见面时,韩松碰翻茶杯,茶水差点儿溅污了她身上的连衣裙。那条湖蓝色胸前绣着花的连衣裙是特意为相亲而挑选,第一次穿上身的。还好,只溅了几点儿。望着他手忙脚乱脸色通红不知所措的窘样儿,许国萍当成了一种初次见面的激动,一种善良诚实的反应。当她处理完这个意外,收拾干净桌面,又倒出一杯热茶时,心里完全接纳了韩松。直到结婚多少天后,她才知道自己判断错了,韩松是真笨,笨得让人没脾气。他只能干庄稼地里的营生,村里让开发商占了那几亩地后,他就不会干其它营生了。许国萍对自己的哥哥说,让韩松跟上你去贩菜吧!不到十天,哥就对她说,贩菜不一定非得灵巧人干,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干得了。我这个妹夫呀,咋说呢?人家是买的没有卖的精,他可颠倒了个个儿。开上农用三轮车拉个菜吧,为躲人,能把车开到沟里。无利谁也不早起,多个人是为了多赚点儿,韩松这样干下去,不说赔本赚不到钱,伤了咱兄妹的和气,就咬破瓷碗毁了牙,两不合适啦!贩菜不成就干别的吧。有人在村里建起了肉鸡加工厂,号召村民养鸡。许国萍去打问清楚,在院子里搭起了鸡棚。每天,她支使着韩松拌食、喂水、清粪。而当她生娃坐月子,在娘家住了一个月回来后,鸡棚空了。不是鸡养够分量送了加工厂,而是传鸡瘟,全死光了。扶不起的刘阿斗啊!许国萍心灰意冷,再不动员韩松干啥营生了。缺粮少菜没了零花钱,有公公婆婆给。许国萍断了添新衣、买首饰的念想。会走路的娃儿一哭闹,她就撵到了公婆那里。亲孙子,命根子,爷爷奶奶买好吃的好玩儿的哄去吧!只是风吹雨淋的窠儿不可能永远护住不会飞的鸟儿。公公感到头疼,忍着忍着忍不下去了。到医院检查,诊断出了瘤子。当儿子的六神无主,当媳妇的拿事作主,劝婆婆拿出开发商补偿土地的钱,送公公到省城大医院做了手术。做手术钱不够的时候,许国萍又求了自己的哥,哥拿出三万块钱,保证了公公上手术台。手术以后,公公再干不了重活,也扒闹不回钱了。那阵子,许国萍常常睡不着觉,天天思谋着咋样撑起这个活不下去的家。她把娃扔给婆婆,拉上韩松去找哥,要一起跟上哥贩菜。哥告诉她,西山有家煤矿正招下井的农民合同工,叫韩松下煤窑去吧,听说下煤窑没啥技术,只要吃得苦就能挣下钱。
世上无路求有路,明知下煤窑是个危险的营生,也去干吧!韩松进了矿,成了挣工资的农民轮换工。开始,许国萍也有些担心,害怕韩松磕着碰着出个拐。两三个月下来,韩松没伤筋没伤骨,身上连点儿皮也没蹭破过。许国萍这才稍稍心安。有一天,韩松说,你们说我笨,我也自认了。我这笨人干活慢。干活慢,井下四周的情况就看得清,有了危险就躲得开。你放心,能干的人才敢和危险碰。听了这些话,许国萍庆幸韩松终于找到了个适合干的。从此,她心里慌张少了。可是笨人终究让人轻看,一个班接一个班的碰凑在一起干活,工人们肯定晓得了韩松出工不出活的笨劲儿。要不,三年合同期满,咋会不让他干了呢?一个月前,韩松迟迟疑疑说,劳资科通知,干到月底就离矿。她问,辞退了多少人?韩松哼哼唧唧地说,好像没几个。她真想开口骂,笨猪,死笨的猪!人家咋会留下你这个笨猪呀!但她张开口,没有骂出声。猪骂不成牛,也骂不成马,骂死骂活,韩松照样是个猪性子,不会改变丁点儿。
知道了韩松要被辞退的事,许国萍就开始为今后的生计发愁,晚上就睡不着觉。随着韩松被辞退日子一天天临近,她晚上睁眼的时候就更多,闭眼的时候就更少。失眠让她的脸变成了寒露后的荒野,没有了色彩,只剩下了衰败冷意。她不甘心,她想保住韩松下煤窑的营生,保住了韩松下煤窑的营生,就保住了她和娃儿有吃有穿的生活。冷水要舀,热水要烧。思来想去,许国萍决定去求劳资科长。
劳资科长是个前脑门秃,戴眼镜上岁数的人,听了许国萍的求告,慢条斯理地讲清用工政策,便低头看办公桌上摊开的文件。许国萍不敢泄劲儿地说,韩松一天班也没误过。用谁也是用哩,你把韩松留在矿上,他一定比现在干得更好。科长瞥了许国萍一眼,继续看办公桌上的文件。许国萍再求再说,他也是庙里的泥菩萨,看上去慈眉善眼,就是不哼不哈。许国萍闭了嘴,咽着口中的唾液。但她不离开办公室,离开办公室就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不能走,不能走啊!她强迫自己站在科长面前。科长端起保温杯喝了几口水,眼睛专注的仍然是文件。许国萍扫视房间,提起摆在门口桌上的保温壶,给科长杯中加满了热水,摇摇壶,转身出门去水房续水,不等走到门口,保温壶便被科长夺下,放回了桌上。科长没正眼看许国萍,坐下把文件又翻开了一页。许国萍讪讪地站了几分钟,抿一下嘴,房间里左右看看,拎起房角的拖地墩布,去盥洗间涮净,拎回办公室,见有人和科长说话,科长带着笑意听着。许国萍没有进去,还拉闭了办公室的门。等和科长说话的人出来,她才进去用墩布拖地。科长没有抬头,说了句,没有见过这么麻缠的!许国萍不接话,一下一下用劲儿拖着地板,但墩布避开了科长坐的椅子,不能打搅科长办公啊!就这样一个星期连着五天,上班来,下班走,按着八小时工作的时间点儿,许国萍天天“陪”着科长。有人进来和科长说话,她就站在门口。没人找科长,她就在科长眼前晃,或者干点儿活,或者默默不语地站着。这天,科长望着许国萍倔死驴的神情,说了句,找队里吧,队里留韩松,矿上再考虑。
许国萍进了队部的门,光头队长满脸怒气,正指着一个工人训斥,韩松不干,换别人干嘛!出不了煤,挣的钱!见许国萍进来,他挥手让挨训的工人离开。挨训工人睄见许国萍,擦身走过,扔下了一句话,领着兵,打不了硬仗!
队长认得许国萍,气哼哼地问,干啥?
许国萍知道来的不是时候,但她又不能不说,硬着头皮说了让队里留下韩松的话。
也干不了,还想留下?
干不了,也干了三年啦,他笨,我知道。可笨,干了三年,总比个生手强吧?
强个!回家保他的命吧!走!走!别在我这儿待!
许国萍不走,队长气呼呼的离开了。队部不是机关办公室,队部里要么工人来一堆,要么没人来。许国萍无法像对待科长那样麻缠队长。
回到土窑洞里,许国萍坐下想,科长让队长说话,是不是科长不想承担责任呢?有人说句话,他就不辞退韩松了。找队长不行,还找谁呢?犄角旮旯儿都想到,矿上有个副矿长是自己嫂子表弟的妻哥。
许国萍提拎一兜子鸡蛋,敲开了副矿长家的门,副矿长没让她进门,说有事情到办公室说去。去办公室,许国萍没敢提拎鸡蛋,用纸包了韩松一个月去掉零头的工资。见了副矿长,先说明亲戚关系,再说韩松的事情。副矿长听了没有说办也没有说不办。嗯嗯当间,许国萍把钱塞到办公桌上堆放的报纸下面。副矿长嘴上说,你这是干啥嘛!却没有往出掏钱。许国萍觉得事情十有八九成了。那天韩松从煤窑里出来,见许国萍脸上阴天转了点儿晴,饭桌上多了两个菜。他没敢多问,却心里高兴,夜里在床上把许国萍压得好舒服,多少天没有过过好日子了!
副矿长收了钱却好像没有办事,劳资科正式辞退韩松的通知还是下到了队里。韩松回家嗫嗫嚅嚅说出来,许国萍好半天没说话,背过脸,出了窑洞。韩松吃了饭,不见许国萍拾掇碗筷,出窑洞,见她蹲在院子里抹眼泪。韩松低下头站在许国萍身边,想劝却不知该如何劝,想拉她起来,刚刚伸出手,犹犹豫豫又缩了回去。许国萍知道韩松立不起杆子的“凡胎”相,不哭了,站起身,眼含尤怨地盯了他一眼,转身进了土窑洞。许国萍口没出声,韩松却好像听见她在骂他,死去吧!没用的笨蛋!死去吧!死去吧!
谋不来道,求不来路,熬垮了身子,今后咋活呢?睡吧!睡吧!许国萍睡不着,眯起眼,强迫自己入睡。——睡眼迷离中,看见韩松下班回来了,她有些奇怪,为了早点儿回家,韩松早出井了吧?韩松笑眯眯地告诉她,矿上下了新决定,不辞退他啦!许国萍一激灵,坐了起来,窑里黢黑一片,天还没有亮。原来是做了一个梦。她叹一口气,梦是真的多好!可人常说梦与现实是反的,韩松留矿肯定不可能了。千刀万剐横竖一死,辞退就辞退吧!老天爷不会饿死瞎眼雀儿,何况有胳膊有腿的人呢?尽管一夜没睡好,许国萍天亮还是起了床,孩子已经送回村里。昨天归置了些东西,还有些没有拾掇,起床收拾吧。韩松出井吃了饭,哥开来农用三轮车,拉上窑里的两个箱子三个包袱锅碗瓢勺铺盖卷儿回村去,嫁鸡随鸡,嫁猪随猪,嫁个扁担扛上走吧。
许国萍卷起了被褥,洗了脸,梳了头,习惯性地拿起洗菜盆,开门到了院子里。院子里有她种下的三畦蔬菜,高的是豆角,矮的是辣椒,不高不矮的是西红柿,土埂边还拢着一溜儿葱。她摘了一把豆角、一把辣椒、两颗西红柿,蹲下拔葱时,见畦里的土有些干了。以往,她天天都要给菜浇几桶水。吃上水,菜才长得旺。这几天,心知住不了几天了,也就懒得再浇水,看看就要蔫下来的蔬菜,她心里有些不忍。
进窑里熬好米汤,熘了馍,炒好菜,约莫着韩松该回来了,还不见回来。许国萍拿起手机打,手机嘟嘟响没人接——或许韩松正在澡堂里洗澡哩!洗吧!能把身上积了三年的煤黑洗掉,带一身白净的皮肉回村里也算聪明了一回。
许国萍拾掇了一阵子,出院子瞭韩松回来,看看院子里的长豆角、圆西红柿,不落忍它们蔫下去。瞭不见韩松,从窑里拿上水桶出院下路边的沟渠里担了几担水,泼洒到菜畦里。心想,这窑自己不住了,别人也要住哩。谁住,谁吃菜吧!好不容易长成这样子了!
浇完菜,还不见韩松回来。许国萍心中就有些不快。昨天晚上,韩松要去上最后一个夜班时,许国萍就劝他别上了。他说多上一个班多挣一份钱,还说临走和工人们再告别告别。真是笨人猪脑子,当盐不咸,当醋不酸,人家不把你当盘菜,你拱着上啥桌呢?这会儿还不回来,真成了架子猪了。
许国萍赌气不想韩松了,进窑里继续拾掇。手里拾掇着,心里的不快慢慢发酵,开始发毛了。煤窑险,煤窑怕,煤窑是阎王爷管的二牢房。韩松刚到矿上时,许国萍并没有跟到矿上。韩松下窑,她也想干点儿营生赚点儿钱,钱多不扎手嘛!她拾掇出鸡棚,又养起了肉鸡。只是有一天,同村去矿上下窑的二虎子被矿上送回了尸体。二虎子一家里人哭得那个惨啊!让全村人心里都哆嗦。婆婆那几天住儿媳妇屋里跑得勤,嘴上不提儿子,只是说孙子娃她能照顾得了。许国萍心里明白,老鸟护雏,婆婆担心儿子哩!谁让婆婆生养个瓷壶盖盖儿不透气的儿子哩!怨归怨,毕竟婆婆的儿子是自己的男人,孩子的爸。许国萍关了鸡棚,到矿上租了个土窑洞住下,伺候着让韩松睡安稳觉,吃热乎饭。自从许国萍到了矿上,韩松只要不加班,下班就准时回家。今天,为啥回来迟呢?上最后一个班,不至于再加班吧?出井,这耽搁,那耽搁,也不至于耽搁这么长时间吧!她寻见手机,又打,手机嘟嘟响,还是没人接。
许国萍在窑洞里待不住了,发毛的心得有个着落。她打算到井口,到队部去问问。
出了门下了坡,刚走到大马路上,许国萍就见哥开着农用三轮车奔过来。
哥!你来了。
来了!你去哪儿?
去井口!
哦。你知道啦?
知道啥?
韩松工伤!
啊!
你不知道啊?
韩松……工伤啦?
救护车拉上人走了。工人们嚷嚷说,工伤的是韩松。
许国萍感到天一下子黑了,自己的骨头架子突然就散了一地,身子塌下来软到了地上。
哥赶紧从车上跳下来搀起许国萍,妹子,挺住!赶紧上车到医院!
一直走到医院门口,许国萍还是懵懵懂懂,没缓过神来,只是知道进了医院,到了手术室门口。
断了条腿,捡了条命。他娘的,矿上辞退不了韩松这小子啦!
听见光头队长的叫骂,许国萍突然看到坍塌的堤坝堵上了,清澈的水浪一波一波漫上来,淹了她的身,润了她的心,她的心怦怦跳开了。
韩松,你笨人有憨福啊!矿上不能辞退你了!
侯 孟:本名侯福明,男,1956年7月出生,祖籍山西省平遥县,就职于山西焦煤集团霍州煤电集团公司。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1981年在《汾水》发表文学作品。 1999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原色》。获第四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长篇小说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