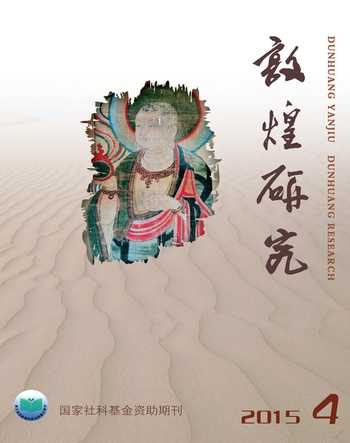《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过”当为“濄”字考
2015-05-30包朗杨富学
包朗 杨富学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写本;濄;溢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4-0097-05
Note on the Word GuoSeen in Turpan Manuscripts
—Plus a Discussion with Mr. Wang Qitao
BAO Lang1 YANG Fuxue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Arts,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2.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Religions and Cultur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raph and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of “qupo-shuiguo(渠破水)”suggests that the common word “(guo, blaming and penalizing)in the book Turpan Manuscripts should be explained as “濄”(guo, overflowing), though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its interpretation and structural form. Since the left structural part of the word can be written as both“言”and“氵,”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the proper structural form of this word should be “濄(guo),”which means overflowing.
Keywords:Turpan Manuscripts;“guo();”Dunhuang manuscripts;“guo(濄);”overflow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过”字多见,学界对其释义及录文做过诸多探讨,尤以王启涛先生为胜。王先生所著《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解释说:“通‘过。即‘过的繁化俗字,责备惩罚。”[1]近期,其新著《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给出的解释为:“‘过即‘过,也是处罚。”[2]表述不同,意思并无二致。对于这一解释,笔者不敢苟同,这里拟采取先释义后解形的方法对“过”的形、义进行一番考察,以就教于王先生及诸位同好。
一 “过”字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
出现与前贤的录释
“过”,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有十见,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下文简称《考释》)列出其八,均见于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1,2,3卷(文物出版社,1992、1994、1996年)。今以图录本为据,列举录文及原图片中“过”字之异写,为便于比较说明,字形忠实于唐长孺的录文,而在后面的括号中标明厘定字。例句出现的先后主要采用王启涛《考释》之顺序,以便比较。
1.《高昌延昌二十四年(584)道人智贾夏田券》:“渠破水过,田主不知。”(第2卷第250页,简作2—250,下同,不另注)可厘定为“過”;
2.《高昌夏某寺葡萄园券》:“渠破水过,仰治桃人。”(1—283)可厘定为“过”;
3.《高昌道人真明夏过田券》:“渠破水过,仰耕田人了。”(1—354)此字漫漶不清,仔细辨认可见左边为“氵”旁或“讠”旁,故可厘定为“濄”或“过”;
4.《唐西州高昌县张驴仁夏田契》:“渠租过水。”(3—89)可厘定为“过”;
5.《高昌某人从寺主智演边夏田券》:“若渠破水过。仰耕田了。”(2—252)可厘定为“过”;
6.《唐贞观十六年(642)二月某人夏田契》:“渠破水过,仰。”(2—293)为草体“过”字;
7.《高昌某人夏镇家麦田券》:“使净好,若有灾汗,随□若渠破水讁,仰耕田人了。”(1—386)可厘定为“过”;
8.《唐某人佃田残券》:“□破水旱,随大匕□破水讁,壹仰□获指为□。”(3—80)可厘定为“过”;
9.《唐永徽四年(653)付阿欢夏田契》:“渠破水讁,□耕田人承了。”(2—210)可厘定为“过”;
10.《唐贞观十四年(640)张某夏田契》:“渠破水过,仰耕田人承了。”(2—25)可厘定为“过”。
除了吐鲁番文书十见“过”外,敦煌写本中也有此字。朱雷先生在研究敦煌写本P.3964《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时,将敦煌写本与吐鲁番写本结合起来进行了考察,录“过”字为“谪”,并解释说:
在麴氏高昌立国到唐代之西州时期,但凡土地租佃契约中,除规定佃户交租外,皆有一项规定有关用水浇灌的责任,即“渠破水谪,仰耕田人了”。由于租佃人取得所租耕地,就应保证该段土地之渠道的完整。若有损坏,因渠水流散,所造成损失,官中必然要责罚。“谪”字,诸字书所引诸类古籍,皆作“责”、“罚也”。[3]
刘进宝《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因袭朱先生之说,有十处引用“渠破水过”,除一处空缺外,余则均将“过”字录作“谪”字[4]。王启涛《考释》虽将“过”均录作“过”,然看其“责备”义的解释[1],与朱、刘“谪”字倾向一致。陆娟娟博士学位论文《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研究》有37处引用了“渠破水过”一语,且辟专条解释“过”字,释其义为“责罚”[5]。遗憾的是,但凡遇到“过”字,或空缺不录,或因袭唐长孺先生录文作“讁”,或录作“谪”,或录作“过”。同样的一个“过”字在同一作者的同一篇文章中有四种处理字形的方法,前后极不统一。
就字面意思观之,“渠破水过”是由两个主谓结构的词语(水利名词+动词)并列而形成的一个并列短语,“渠”后跟的是与其自身相伴而生的动作和状态“破”,缘何“水”后跟的动作却不是与水本身相伴而生的动作和状态,反而是更换了主语,变成人的动作“责任”呢?很难解释得通。
朱先生所谓“官中责罚”之语,乃出自推测。王启涛《“渠破水讁”考》虽提及“道路和水渠维护责任人,对不及时维修者,要给予惩罚”[6],但就他所引的惩罚规定看,受处罚的应该是检校疏决不力的“主司”,老百姓若连带遭受惩罚获罪,除非达到“毁害人家,漂失财物”的程度。据理这种洪水泛滥的程度只能出现在“近河及大水有隄防之处”,绝不会在租种的田地中出现。所以从官方规定的惩罚对象和惩罚涉及的地点来看,王启涛所引证的受惩罚的材料不能证明耕种土地的人要受惩罚。倒是所引用P.2507《开元水部式》的“渠堰破坏,即用随近人修理”、“诸水碾硙,若拥水质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硙即令毁破”、“其蓝田以东先有水硙者,仰硙主作节水斗门,使通水过”的诸般规定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租地契约中要加上“渠破水,仰耕田人了”这一条,不过是租地人为了摆脱官方规定的责任而向承租人附加的条款。所谓的“随近人”,除了耕田人本人及其亲属外,在有契约关系的租地条约中,主要就是指租地人。
二 “过”字释义
为解释“渠破水过,仰耕田人了”之语,王启涛先生于《考释》第582页引敦煌写本P.2507《开元水部式》“若渠堰破坏,即用随近人修理”之语,当是对“渠破水过,仰耕田人了”之句的最佳脚注。王先生接着引用的“水溢渠坏”可以说是“渠破水过”的同义语:“水溢渠坏”与“渠破水过”词素相同者有二,仅词序略变但不影响其意义。根据双音节词回溯单音节词理论[7],“渠破”义即“渠坏”,其构词原理是先拆双音节词“破坏”成两个结构语素“破”和“坏”,然后再分别与“渠”组合成“渠破”和“渠坏”;根据对举成文的原则,余下的“水过”就只能解释为“水溢”了。
原指水泛滥。《礼记·王制》:“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孔颖达疏:“水溢,谓水之泛溢。”亦作“水泆”。《管子·山权数》:“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后来,水溢有了“水满漫出”之意,如唐人赵嘏《水溢芙蓉沼》即描写了水漫芙蓉池后的感想,诗题中的“水溢”即“水漫”之意[8]。
如是,王先生的工作已接近鹄的,可惜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终致错过了目标。他接下来列举了高昌残敕中“窟川溢”、“风雨破坏”等,“川溢”义同“水溢”,正好解释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同时出现这两个词语的原因及其渊源关系,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水过”可初步确定释为“水溢”、“水漫”。
王先生言“过”通“过”,当无大误。确切地说,“过”、“过”应是古今字。“过”的释义应为“溢”,而非王先生所谓的“责备惩罚”。“过”有“溢”义,《周易·节》:“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徳行。”宋·易祓《周易总义》卷16注:“泽之上有水,过乎,溢者也。过溢则为有余,有余则宜堤防之。”易祓将“过”释作“溢”;又将“过”、“溢”连言,符合古汉语同义连用之例,是“过”、“溢”同义之又一证。“过”、“溢”连言之语料很多,如《魏书·甄琛传》之“欲令丰无过溢,俭不致敝”,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38之“没则瀎减,进则过溢”等。同时,“溢”亦有“过”义,《庄子·人间世》:“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郭象注:“溢,过也。喜怒之言常过其当。”张衡《东京赋》云:“规摹逾溢。”薛综注:“逾,越也;溢,过也。”
最后,就王先生自己运用的对举成文的思路推理,“过”也当释为“溢”。《考释》第581页引《高昌某人夏镇家麦田券》文句将“若有灾汗”和“若渠破水”进行了对比,并指出:“‘灾汗即‘旱灾。‘灾汗与‘水过相对成文。”按,“灾”乃灾害总名,“汗”才是具体的灾害,这是古代汉语构词法中典型的“大名冠小名”例[9]。根据“相对成文”的原则,“水过”亦水患总名,“过”才是具体的水患。农田之水患,除了“渠破”即漏水以外,“水溢”即水漫冲垮田塍也是其中之一。“渠破”、“水过”代表水漏、水涨两种影响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
众所周知,吐鲁番地区干旱少雨,修渠治水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有人通过阻水而达到以碾硙灌溉的目的。《通典·食货二》“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硙,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许顷”,最终造成了“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的结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在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春正月辛酉,敕毁白渠支流碾硙以溉田”。《开元水部式》所谓“于公私有妨者,碾硙即令毁破”,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情况。之所以要毁破碾硙,原因还是阻水导致“水溢渠坏”,目的是疏通水道“使通水过”,可见当时修渠治水是多么重要。
出租田地者把田地租给了他人,按照当时的规定或习俗还要负担修渠治水之事,这是租地者所不能容忍的,但官府又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在民间就出现了权变的方法,出租田地者把田地租给他人后,连带把修渠治水的责任也转嫁到他人头上。
如果我们把“渠破水过,仰耕田人了”这句话翻译出来,也会发现把“过”解释为“责罚”、“责备”不合逻辑。“渠破水过,仰耕田人了”全句的意思是“渠堰破漏和田水漫溢都靠耕田人负责解决”。“了”在此处当“解决”、“了结”讲,这种意义古籍中并不鲜见,以“了局”为例,即可管窥一斑。《初刻拍案惊奇》卷25:“只愿得遇个知音之人,随他终身,方为了局的。”《红楼梦》第90回:“家中又碰见这样飞灾横祸,不知何日了局。”“渠破水过,仰耕田人了”翻译时如果颠倒顺序,且只看其中心意思,可译作“耕田人负责解决渠堰破漏和田水漫溢这些农事”,把“漫溢”换成“责罚”显然逻辑不通。而事实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渠堰破漏和田水漫溢”不过是“渠堰维修养护和水利施工”的代称而已,是以部分农事活动代替全部农事活动。所以,从全句的意思看,“过”也应解释为“水溢”。
鉴于上述原因,故笔者认为,“水过”释为“水溢(水漫出来)”即“漫溢”比较确切。
三 “过”当为“濄”字考说
在汉语中,能够表示“水溢”之义且字形又近于“过”的汉字,只有“濄”。易言之,“濄”是正字,“过”是“濄”的俗体讹字。由“濄”向“过”讹化的过程复杂:应该是先将“氵”连笔成“讠”,于是有第10条录文的“过”字;后在求雅求正心理驱使下,又将“讠”旁变成“言”旁,终有第2—9条录文中的“过”字。这个讹化的关键在于:水旁与言旁形近,故可互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敦煌俗字典》“諳”条在列出“諳”的俗字“湆”后说:“‘言旁俗字多作‘讠,与‘氵旁形近易乱。”[10]同时,《敦煌俗字典》在列出“諒”的两个异体俗字“过”、“过”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此字(笔者按:即‘过字)左边应该是‘讠旁,因与‘氵旁相似,故讹为‘氵旁。”[10]244
“氵”旁、“言”旁相混不仅敦煌文献多见,即使是在霞浦新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也可发现将“氵”讹作“言”旁者,《兴福祖庆诞科》第4页第3行(总第23行)“欲乎宣过,口中吐出白莲花,将尔披陈”句中的“演”作“过”就是如此。霞浦摩尼教文献与敦煌摩尼教文献同源,摩尼教又深受佛教的影响[11]。“宣演”是佛教常用词语,略举二例:《佛说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我今以佛威神力故受持此法,随其力能流布宣演。”《法华经句解》:“宣演敷布以法教化利益令喜。”义为“宣扬传布”。实际上,“宣演”也是个普通词汇,南朝时宋人何承天《答颜光禄》即有“区别三才,步验精粹,宣演道心”之语。明确了“宣演”是个固定词语后,我们再来比较“演”字在霞浦文献中的写法,即可证“氵”旁有写作“言”旁者。
同时,有文献可证,“濄”的意义可解释为“水溢”。《尔雅·释水》:“水自河出为灉,济为濋,汶为灛,洛为波,汉为潜,淮为浒,江为沱,濄为洵,颍为沙,汝为过”。其注曰:“此十者皆大水分出,别为小水之名也。”[12]
另外,从字的分化来看,“过”、“濄”是古今字,今字“濄”的“溢”义是古字“过”原有的一个义项,这符合古今字分化的规律。古今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古字兼义过多,为了表义明确,于是古字分化成几个甚至几十个今字。前文论证过了“过”有“溢”义,然而“过”还有其他几十个义项,据《汉语大词典》所列,“过”有32个义项,当然这些义项中没有“溢”义,但这并不是说“过”的“溢”义不存在,从上举的一些文献的零星记载中我们可窥一斑,没查到的文献可能会更多。为了明确表示“溢”义,在“过”的左边加上义符“氵”,“濄”字产生。惜乎,“过”、“濄”两字的“溢”义字典未载,是以今人忽略。
从古今字的角度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第1条录文中的“过”字,从图片看实作“過”,也许是因为出土文书的残缺,导致“過”左边的义符丢失。尽管这样,也提示我们考虑,“过”、“濄”可能都是“過”的分化字,即“過”与“过”、“過”与“濄”是两对古今字。
最后,从语音上看,“过”、“濄”读音相同或相近,这也是二字释义得以相通的一个基础。“过”、“濄”上古音完全相同,皆为见母歌韵;中古可以说基本相同,确切地说,也绝大部分相近,“濄”为见母戈韵合口一等平声果摄,“过”为见母过韵合口一等去声果摄[13],二者在声母、等呼、韵类和韵摄上完全相同,稍微的区别在于声调和韵目的不同。据陆法言《切韵·序》所言,中古时期“梁益则平声似去”,此为举“梁益”而该西北,盖指西北方言中平声、去声相似,从听觉上很难分辨。西北范围较广,中古时期,吐鲁番方言与梁益方言有某种因循关系或未可知。因此声调的差别并不能妨碍语音上的绝大部分相通。而“戈”、“过”虽属于不同的韵母,却属于同一个韵类,也属于同一个韵摄。综合语音的各个要素来看,“过”、“濄”在中、上古应该是绝大部分相同和相通的,至少应该在方言浓重的地区读音相同。
“过”、“濄”相通,皆有“溢”义;而“过”字义、字形又皆与“濄”有重合,所以笔者认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过”应该是一个俗体讹字,其正字为“濄”,义为“水溢”,即“漫溢”之义。
参考文献:
[1]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M].成都:巴蜀书社,2005:581.
[2]王启涛,编.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M].成都:巴蜀书社,2012:1263.
[3]朱雷.P.3964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唐沙、伊州文书中“地水”、“田水”名义考[M]//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325.
[4]刘进宝.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J].历史研究,2003(2):127-128.
[5]陆娟娟.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86-87.
[6]王启涛.“渠破水讁”考[J].艺术百家,2010(4):199.
[7]包朗,李榕.古汉语词语释义新模式——双音节词回溯单音节词模式引论[J].时代文学,2010(3):135-136.
[8]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2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499.
[9]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56:52.
[10]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4.
[11]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与敦煌文献之关系[C]//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5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09-425.
[1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0-221.
[13]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