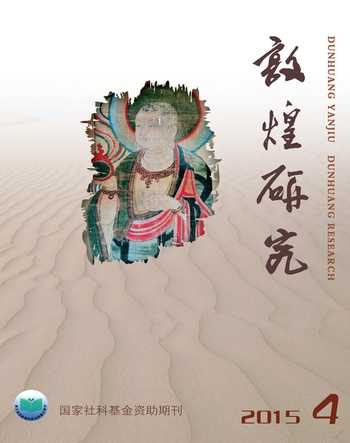《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文本研究
2015-05-30廖旸
廖旸



内容摘要:《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为一种未入藏的炽盛光陀罗尼经,陆续发现于敦煌、黑水城、大理佛图塔等遗址,并有多种传世本被逐渐公布。本文汇总相关材料,尝试把握该经从中唐到明代的时代特征,冀有助于将炽盛光经法的相关探讨推向深入。
关键词:《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大理佛图塔写经;炽盛光佛。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4-0064-09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ahābalag-Tejaprabha-Tathāgata-rī-Dhāraī-Sūtra
LIAO Yang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Mahābalagu-Tejaprabha-Tathāgata-rī-Dhāraī-Sūtra, a kind of Dharani Sutra not recorded in Chinese Tripitaka,tells about Buddha kyamuni preaching mantra and its magical power to the gods of heavens, constellations, planets and stars gathering at uddhāvāsa Palace in the top heaven of the“Form Realm.”In the last century, some relevant documents or fragment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Dunhuang, Khara-Khoto, and the Fotu Pagoda at Dali, and various surviving versions of this text have gradually been publicized. This paper collects relevant materials and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ext in the period from Middle Tang to the Ming dynasty, hoping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f the text and the cult of Buddha *Tejaprabha
Keywords: *Mahābalagua-Tejaprabha-Tathāgatarī-Dhāraī-Sūtra; Dunhuang documents; Khara-Khoto documents; Buddhist manuscripts found in the Fotu Pagoda at Dali; Buddha *Tejaprabha (jvala)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汉文大藏经内有两种短篇的炽盛光陀罗尼经(《大正藏》Nos.963、964),《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传为唐不空(Amoghavajra.705—774)所译,《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失译者名,二者系同本异译。另一种异译《〔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未见入藏。三者经题相近,为行文简明故,下面分别称为不空译经、失译经及藏外经。藏外经曾流行于西北,数见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现品,也出现在云南大理等边地,明代的多种写刻本还表明,它在中原腹地同样受到尊崇。下文枚举目前所知的遗存,对部分文本内容稍作探析,并尝试勾勒出各时代特征。
一 现存唐——明时期藏外经写刻本概览
目前来看,年代明确的藏外经最早出现在敦煌遗书之中,今藏甘肃省博物馆(甘博〇一六,原编2490)。厚白麻纸、绳装册页,页面14.8×10.3厘米,为八种经合抄,末一种即《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1]。另第一种《劝善经》末书“贞元拾玖年(803)廿三日下”字样[1]137,时值唐德宗治下、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这为探索藏外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藏外经译出的年代应该更早。
披露较早的另两例敦煌写经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P.2194、P.2382),卷轴装,保存非常完整,前者更是包首、地杆等俱全。此二写经字体工整,是抄经生用心之作①。
上博48(41379)为43种文献合抄,厚白麻纸写本、包背装方册。根据其中所书“同光二载”(924)、“清泰四年”(937)等后唐年号知其为五代时释敬念之物。第18种抄藏外经,墨笔楷书14行,前后经题与起首处作树形标记[2]。
西夏的炽盛光佛及星宿崇拜特别引人瞩目②。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汉文文书中包括藏外经的三种刻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TK129、130、131)③。三件文书个别字词有出入,由卷装改经摺装,完残程度不同,TK129保存状况最优,存15面,每面19.5×7.5厘米?譼?訛。此外还发现了相应的西夏文译本《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緽铜柏碅緽皏菢娇緳蟶蛙萂竀紴綒茸碃瞲其。Танг 144, инв.№ 809, 951)写本和刻本各一?譽?訛。
除以上五种写刻本而外,1983—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黑水城发掘时,还在F9和F13两处遗址发现若干与藏外经有关的残页(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其中四片在发表时被归入藏外经,即经后太阳星、土星与火星真言的部分?譾?訛;从真言内容看这一判断准确无误。还有至少两三片未能识别或误断,即M1·1412[F13:W17-4]?譿?訛、M1·1492[F13:W60](图1a)?讀?訛与M1·1466[F9:W4]?讁?訛。按其中土星真言与神像残片分别出自F9、F13坑位,但可以缀合(图1b)。因此这些残片原应属于同本,竹纸、经摺装,面约15.8×8.2厘米。发现品中F13:W17与F9:W42被认为是同一书[3],但F13:W17-4当属本经。另外,F9:W4?譹?訛版心高度相仿,残高16.1厘米,与前面提到的尺寸仿佛,只是版心位置偏上,且字体小于星神真言,难以遽断是否同组。然其内容为藏外经启请的最后六句,则殆无可疑。此残片文字最全,若据以推算,大致22面、每面5行、每行15字,各残片在原本中的位置可以复原(图1)。
西夏诸本较敦煌本多出经前启请;与下文将要讨论的同题佛经如明成化嘉德本比较,TK129阙启请前三韵,TK130阙前两面、较TK129又少五韵,TK131仅存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及其后一面。但西夏文译本的启请文[4]内容完整,可证当时汉文启请全貌当与后世所传大致相同。经后还出现星神真言,TK129并书尚座袁宗鉴等善众“乾祐甲辰十五年(1184)八月初一日重开板印施”的发愿文。西夏学学者对这段发愿文给予了高度重视。既是“重开板”,则最初雕版的年代还应在1184年之前。换言之,此前应已形成启请+经文+真言的格局。TK130和131的版式接近,孟列夫认为即重印TK129所依据的原版,进而推测它们可能属于12世纪70—80年代[5]。
在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成果中,从第464窟清理出藏外经的两块残片(图2),为白麻纸刻本,经摺装。标本第464:6存3面、每面5行,残14.0×18.4厘米;标本第464:9为插图,仅存1面,13.9×6.2厘米。此前研究尚未揭示两块残片的内容与相互关系。从材质、版式(上下双线边框)、大小(页面约14.0×6.1厘米)等物理属性来看,二者高度趋同。而从内容来看,前者为藏外经前启请的第14—28句?譺?訛;后者为1身有头光的女子立像,画面中部虽残损,不过幸运的是其右手持毛笔清晰可见,垂左手持卷轴尚可见端倪,表现九曜中的水星神殆无可疑?譻?訛。虽然独幅星神像并不必然隶属于藏外经,但结合同窟发现的启请来看,它们正好体现了藏外经在西夏时期的形态特点。学界认为第464窟为西夏窟,从此残片的字体、人物造型、装饰纹样?譹?訛等细节来推测,此件当亦为西夏之物。推算全件经书约32面左右(经末星神像与真言各占一面),尺寸袖珍,适在掌握,既方便随时礼颂赞叹,更可随身携持避祸趋福,作用等同于符咒。同窟还清理出未完工的二十八宿十二辰木雕板残件(标本第464:95)?譺?訛,辅证星命观念的盛行。加以留意,敦煌和黑水城等地发现的文书中或许还会发现更多藏外经的遗存。
1981年在维修云南大理下关佛图塔(俗称蛇骨塔)时,在塔门过梁两侧发现经卷,大部分被认为是元代文物,少部分或属大理国时期[6]。其中,《妙法莲华经》卷7(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可能为大理国写经,纸本、墨书,经摺装,页面28.5×11厘米;背面抄《摩利支天菩萨经》与《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卷末在“造经施主释妙慧”等人的发愿文后署“至正二十九年(1369)岁次己酉二月二十五日终”?譻?訛。其时当明洪武二年(1369),而云南仍在元梁王与大理段氏控制之下,因此本文视之为元写经。有趣的是,《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中部?譼?訛插入藏外经以及“稽首般若大佛母”、“稽首能仁薄伽梵”等礼神文字?譽?訛。考发表的影印知《灌顶经》与藏外经均有错简?譾?訛,经重新拼对可得完整的文本(图3)。佛图塔本题作“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陀罗尼部分逐句详记句义,九曜真言的顺序也与众不同,这是古老形态的遗留还是地方特色,由于资料匮乏,尚难展开充分的讨论。
元代包含此经的合抄本曾见诸著录,尚未检得实物。明代此经写刻本存世较多,其中年代明确者如下:
1. 明宣德八年(1433)佛弟子福坚施金书经中有此经和《消灾吉祥陀罗尼经》?譹?訛。北京房山石经宣德三年(1428)巡礼题名中出现过“奉佛弟子……韦暹法名福坚”[7],北京大觉寺宣德五年铸铜钟之内壁铸助缘施主信官人名中有“韦暹”[8],或即一人?譺?訛。
2. 明天顺六年(1462)刊插图纸本刻本,北京智化寺藏。经摺装,面43×15厘米,扉画34.5×90厘米[9]。智化寺藏经书卷帙浩繁,而此刻本是其中开本最大的一册,尤为壮观。
3. 明成化十三年(1477)纸本刻本一册。2010年3月22日中国嘉德四季第21期拍卖会“古籍善本 碑帖法书”专场lot.4723。经摺装,24.8×54.8厘米,面5行、行15字。
4. 成化十五年(1479)刊插图本。卷首画四面连式,另外有文内插图、卷末附图?譻?訛。同年刻本亦见著录于1944年中法汉学研究所举办的明代版画书籍展览会目录,巴黎杜让氏柯青馆(M.J.-P.Dubosc)藏,经摺装、绵纸,“未题画人名氏 卷首冠图,四面连式;书内插图,单面方式;卷末附图,单面方式。北京刻,未题镌工名氏”?譼?訛。该书称此为不空译经,但从经题和描述来看,当是藏外经?譽?訛。
5. 成化十六年(1480)施写本(日本京都东寺宝菩提院藏),缀于日本明应八年(1499)写、正德二年(1712)补修的楞严咒诸尊图会之后。该图会被误定名“梵文炽盛光佛顶陀罗尼诸尊图会”,传为印度僧人指空(Dhyānabhadra,?-1363)集(《大正藏图像部》卷4第81—162页)。
6. 万历十八年(1590)刻本与《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合装本(上海博物馆藏),5行、行15字[10]。
7. 万历三十八年(1610)洛阳福恭王朱常洵刻本,4行13字、左右单边。为明代藩府本之代表作,疑在京刻?譾?訛。同年尚有内府刻本(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4行、行11字[10]1100。
明代此经包括内府与藩府本,从年款看分布在宣德八年至万历三十八年,涵盖了明代早晚期,足见其在明代社会、尤其是宫廷贵族当中流行不衰。在藏外经最初流传的故地,则可举出甘肃张掖大佛寺藏木雕版?譿?訛。
二 藏外经正文、启请录文及相关探讨
现以甘博本为底本,选录经文,并附唐、西夏时期其他汉文本及明大佛寺本的对勘(附表)。
明大佛寺本虽有藏传佛教影响,但仍保留了西夏特色。此外,藏外经陀罗尼中“瑟■哩”只出现了一遍,这个特点仅见于藏外经的敦煌诸写经,而不见于不空译经、失译经乃至藏外经的黑水城及之后诸本,这一点值得留心?讀?訛。俄东方文献研究所藏上图下文的纸本刻本一种(Дх.1390复原见图4),原被归入敦煌文书,府展宪考定为黑水城所出土的西夏文献?讁?訛。这种上图(尊像或曼荼罗)下文的形式常见于唐宋时期独幅单行版画,后晋开运四年(947)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曹元忠施造《大圣毗沙门天王》(图5)?譹?訛与此版式特别接近,40×26.5厘米,特别是下部均为15栏、每栏7—8字,上下双线边框等做法,如出一辙。推测俄藏炽盛光陀罗尼版画以炽盛光佛为中轴进行对称构图,上部应表现炽盛光佛九曜,即日月罗计四神在上部侍立佛两侧,下部分布五星神;残32.1×22.8厘米,推测复原尺寸约为36.0×31.5厘米。下部原有15栏文字,存11栏,起首两行可辨认出“□□大威德 炽盛光 /消灾吉祥陀罗尼曰/”字样。陀罗尼之名与不空译经、失译经和藏外经皆不能完全吻合;但陀罗尼本身则同于唐五代藏外经的敦煌写本,由此推测,其与藏外经关系更密切。
1944年四川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发现的盛唐后期(756—766)刻本《陀罗尼经咒》(国家博物馆藏)印在半透明薄皮纸上,尺寸为31×34厘米,对角卷裹置于银臂钏内佩戴?譹?訛。图4复原之后的尺寸窄长一点,原件为细密麻纸[11],未裱在白麻纸上之前应足够薄软。由于以前的陀罗尼刻本多发现于随葬品中,研究者更强调其度亡之效验,而事实上,这种习俗同样通行于现实生活中。比照考古发现可知,人们将其卷紧放进空心手镯之类饰物中、作为护身符随身佩戴,以求时刻庇护。此件残损较重,无法得知其末尾处是否具发愿文或年款等信息,推测其功用应与五代《水星与计都陀罗尼符》(纸本、设色。大英博物馆藏,Ch.lvi.0033)?譺?訛等相当,祈祷佛与星神护身保命。明代刻写的藏外经往往描绘写有梵文或藏文陀罗尼的“大圣炽盛光如来拥护轮”,智化寺本拥护轮下方汉文题记如是描述拥护轮的用法:
若人恒常志心持诵、佩带者,一切灾障并诸间断恶梦恶境、种种不祥,尽皆消除,福寿增延,吉祥如意,凡所祈求,随愿成就。[9]146
明末四大师之一释真可(字达观,世称紫柏尊者,1543—1603)指点持诵炽盛光陀罗尼之法,也正是“或制轮佩身,或以真言意持”[12]。俄藏炽盛光陀罗尼版画虽非拥护轮的形式,但其刊行原应用于信徒随身佩戴而求守护,大致不误。
启请为诵经或持咒前奉请神祇的启白。不空所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上卷经文前即冠“读诵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前启请法”?譻?訛。但大多数启请显系汉地信徒的创作,作为一种文体通常作七言偈颂,以“稽首”、“皈命”、“仰启”、“奉请”等字眼起首,在宗教实践活动中往往配以音乐,彰显神佛之庄严与信众之虔诚。据探讨,金石文书材料中可以见到尊胜、大悲、大佛顶等陀罗尼的启请,有年代可考的实例可举出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宏正大师遗界记石幢上的“佛顶尊胜真言启请”[13]。现以黑水城TK129为底本,录经前启请如下,根据其他版本将其所阙前六句在〔〕中补入:
〔仰启五星尊重主,天中自在炽盛光。行乘赫奕紫金车,车中复居红莲座。其花八万四千叶,叶叶皆放火焰光。〕光明上照尼吒天?譹?訛,下烛泥犁十八狱。前将五星为侍者,后以释梵作威仪。眉间放大日月光,光中化佛无边亿。八万恒沙诸世界,慈悲应接苦众生。二十五有诸含灵,既向皆蒙罪消□(灭)。若有恶星临命者,须念炽盛光如□(来)。随处念者现神通,恶星退者?譺?訛命延永?譻?訛。或现身为大元帅,震动乾坤万国中。或现勇猛圣金刚,摧灭降伏?譼?訛诸外道?譽?訛。纵有运逢灾患者,土星刚(罡)曜照临身。公私口舌及冤雠,一切灾殃皆解脱。我今称念真言教,愿降神通护我身。十缠九结永消除,万善千祥悉圆满。
这段启请对探讨炽盛光佛形象及其构图的发展有特别的意义。其形成时间的下限当在1184年袁宗鉴等重印该经之前。这里对时间上限的范围略作推测。五代宋辽以来逐渐出现炽盛光佛正面端坐的静态、对称构图,而从启请可知,他乘车巡行的形象仍旧深入人心。目前所知最早的相关图像为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张淮兴施绘绢画《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像》(大英博物馆藏,Stein painting 31, Ch.liv.007)[14],画中佛坐青色莲花,在佛身焰光、所穿的红色袈裟与红色车身、车轮之间显得格外清净而醒目,并呼应土星神、金星神足下青云。同出藏经洞、年代约为五代的纸画(P.3995,法国国家图书馆藏)[14]pl.43样式接近,除增加罗睺、计都而外,另一重要的变化容易被忽略——莲座已潜移默化为红莲。此外,英法藏画所表现的佛乘车偕星神巡行天界的画面,尚无启请第10句言及的帝释、梵天。宋开宝五年(972)钱昭庆印施不空译经(日本上之坊藏)卷首扉画上眷属人物增加,有可能已出现帝释和梵天的形象?譾?訛。从英藏绢画到法藏纸画、再到上之坊本扉画的3/4个世纪,应即启请形成的时间段;这也与启请文体的成型大致呼应。
三 藏外经的时代特点
在汉译佛经中,藏外经的演变是相当显著的。与最初的敦煌唐本比较,黑水城西夏本有一些明显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经名前增加了“金轮佛顶”字样,西夏文译本同。对金轮的强调与自五代起视觉艺术中的炽盛光佛形象以金轮为持物相呼应,以后遂成定式;
2. 在经名和“如是我闻”引起的正文之前,增加七言“启请”共计32句;
3. 经后附加九曜(梵navagraha“九执”)每月降下日期与真言;
4. 多本(包括汉文、西夏文文本)九曜真言并附相应的星神像版画,其中内蒙古文研所藏本还出现了扉画(见图1a)。
明代此经在形式与内容上又有新的特点:
1. 经前往往冠以多面连的扉画,这一点在西夏时期已见苗头,不过西夏所见构图为侧面说法图,而明代则为传统的巡行图;
2. 经中在经文与后附星曜真言之间,或插入“大圣炽盛光如来拥护轮”,即在智火中现八叶莲花,莲瓣内用梵字或藏文书写陀罗尼?譿?訛;
3. 从图像志角度看,经后伴随真言的星神像呈现出汉藏结合的面貌?讀?訛;
4. 陀罗尼与星曜真言的音写用字经过重新审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5. 星曜增加紫炁、月孛而成十一大曜,真言内容则改从失译经所附九曜真言。
小 结
综前所述,目前所见未入藏的此本炽盛光陀罗尼经存敦煌唐―五代写经四种、西夏刻经残片一种,黑水城西夏写刻经(含西夏文译本)六种,大理佛图塔元写经一种,明代写刻经近十种。关于它与入藏的两种炽盛光陀罗尼经的关系,一说它是独立的敦煌藏外经[15],一说是失译经的简本[16]。不空译经和失译经很近似。相形之下,藏外经在宣说陀罗尼前没有叙述需要立道场持念陀罗尼的数种情形,之后也不谈及如法建立道场、结界护持,文字极其简明扼要。不空译经和失译经提到的“帝座”、“分野”、“本命宫宿”等概念隶属中土传统文化观念[17],而这些术语在藏外经中尚未出现。参照真言格式类型、汉化程度来看,炽盛光诸经轨中藏外经年代很早,并可能早于不空译经与失译经。约在西夏时期形成的启请与九曜真言成为藏外经的独特之处。特别要注意的是,启请中提到的一些元素,例如现身为大元帅或勇猛圣金刚、口舌等等,不见于本经经文,但可征于不空译经与失译经,充分说明时人对二者皆有所接触。上博藏明万历十八年刻本与不空译经合抄,宣德八年福坚施金书经则与包括不空译经在内的多种佛经合抄,炽盛光陀罗尼经的不同译本并行是特别的现象。
在本文论及的约800年间,藏外经从不足300字的小经衍变为精美的艺术品,书风画技无不上乘,个别经文更用泥金书写,煌煌凝粹,极尽庄严。它可能在敦煌译出,最初只在敦煌及其周边流传,随着元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进程而广泛传播。藏外经为进一步了解炽盛光佛信仰提供了新的材料。其结构的历史演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不但有助于揭示炽盛光法的演变,也堪称探索佛经内容与形式在汉地迁衍的生动范例(图6)。
参考文献:
[1]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第4卷[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42.
[2]上海博物馆,编.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4.
[3]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223.
[4]聂历山,著.文志勇,崔红芬,译.十二世纪西夏国的星曜崇拜[C]//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69.
[5]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M].王克孝,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160.
[6]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管所,下关市文化馆,下关市佛图塔实测和清理报告[J].文物,1986(7):52-53;杨世钰.大理古本经卷的发现与研究[G]//白族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17-318,322.
[7]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75.
[8]于弢.皇城的晚钟[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68.
[9]北京文博交流馆,编.智化寺藏元明清佛经版画赏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142-153.
[10]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第3册:子部[M].北京:线装书局,2005:1100.
[11]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J].敦煌研究,1996(2):92.
[12]钱谦益,纂阅.紫柏尊者别集: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跋[M]//卍新纂续藏经:第73卷.1663:406.
[13]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9-73.
[14]彭本人,编.海外遗珍:中国佛教绘画[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pl.16.
[15]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1.
[16]陈万成.景德二年板刻〈大随求陀罗尼经〉与黄道十二宫图像[M]//中外文化交流探绎:星学·医学·其他.北京:中华书局,2010:33.
[17]萧登福.道家道教影响下的佛教经籍:下[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5:858-859,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