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为何要攻击诗人
2015-05-30李石
李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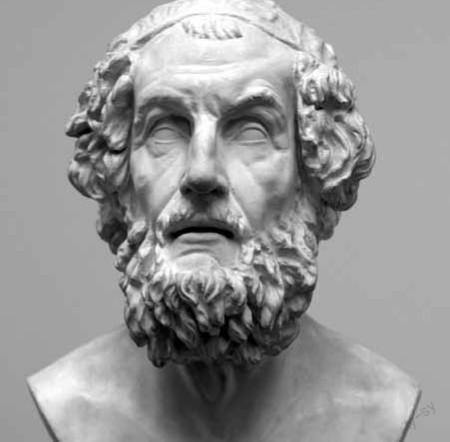
对于热爱古希腊文化的现代读者而言,如果他们阅读诗歌,那么他们很难忽略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巨著;如果他们喜欢哲学、关心政治,那么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部不得不读的经典。尽管不少学者对于在西方历史上是否真的有一个叫荷马的诗人存在争议,但事实却是,几乎每一个古希腊人,包括生活于现代的大多数读者都真诚地相信,在公元前12世纪,有一个叫荷马的诗人,曾在遥远的古代吟诵并谱写过许多气魄雄浑、脍炙人口的诗歌,他对于天神生活的瑰丽想象、对特洛伊战争的宏伟描述、对战争英雄的神伟事迹和悲剧命运的歌唱,至今都活在人们的历史文化记忆中。而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有着跟荷马一样的历史神秘性,原因在于,他和中国的孔子一样,是一个述而不作的哲人,我们后代读者对于苏格拉底的印象,大部分来自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经过柏拉图的天才之笔,苏格拉底成为历代哲人的偶像。苏格拉底在世人面前唯一标榜的是自己的无知,他催促希腊雅典公民们去思考、去审视自己的行为,其终极目的是要努力地去探讨什么是人类的正义,以及如何实现城邦最大程度的善。但是,苏格拉底却在《理想国》中表明,为了城邦的利益,他必须将诗人驱逐,即使是被雅典人奉为他们的精神导师的荷马,在苏格拉底的理想城邦中也不受欢迎。
这让人纳闷,苏格拉底为何要跟诗人过不去?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说,哲学和诗歌之间的争吵古已有之,似乎把哲学放在了与诗同等的高度去评判。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古希腊,诗歌比哲学具有更为渊源久远的历史基础。在古人的思维里,诗人是神圣的,是神和凡人沟通的中介。诗人是天生具有非同凡人灵气的一群,他们可以感应到神的存在,领受神的馈赠和点拨,并向所有的凡人宣告神的旨意,歌颂神和英雄的丰功伟绩。因此,诗人是一种荣誉,人们必须通过诗人(或祭祀、神职)来了解神的意图,规范自身的行为。因此,当苏格拉底试图攻击诗人,实质上是作为新起之秀的哲学在挑战诗歌的古老权威地位。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苏格拉底喜欢辩论,习惯光着脚,游荡在城邦的街巷寻找对手进行论战。同时期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的《名哲言行录》记载,在辩论中,有时苏格拉底和人们出现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受到了人们的拳打脚踢,甚至他的头发也被扯脱;苏格拉底总被人鄙视嘲弄,然而他内心却承受了所有这些暴力虐待。一次苏格拉底被踢,有一个人对于他居然如此平静地承受这种暴力感到十分惊讶,苏格拉底回答说:“难道我应该遵守驴子的法律,假如他踢了我的话?”这是第欧根尼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然而,在柏拉图的著作里,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却是一个正直智慧、处处受人尊敬的人。不过,不管是柏拉图还是第欧根尼笔下的苏格拉底,都经常喜欢质疑雅典的习俗和权威,甚至故意为难那些自视甚高的人,目的是证明这些人不过只是一群白痴。因此,苏格拉底自然会得到一些青年的爱戴和追捧,同时也受到许多人的嫉恨。其中,苏格拉底在和一位名叫阿尼图斯的诗人辩论时,他运用巧妙的论证证明了诗人是无知的。这在阿尼图斯看来,是傲慢的苏格拉底对他的嘲笑和奚落,也打击了他作为一名诗人一贯以来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苏格拉底眼里,诗人的创作完全是在神的支配下完成的,是神依附在他们身上传达神意。如果苏格拉底的论证仅限于此,那么他并非在否定诗人,反而把诗人看成是神的宠儿。但是,让所有诗人无法接受的是他随之而来的结论——既然如此,那么诗人是无知的,诗人写诗凭借的并不是智慧和技艺,而是神赐予的灵感,因此,他们在作诗这一行当上其实是无能的。也就是说,诗人并不是一个智慧的群体。那么,城邦中谁才是有智慧的人?是苏格拉底。这是当时的女祭司的答复:在所有活着的人中苏格拉底最有智慧。因为这句话,苏格拉底遭受到无数人的嫉妒。
第欧根尼说,诗人阿尼图斯首先煽动著名的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反对苏格拉底,而阿里斯托芬本人某种程度上对苏格拉底、甚至对哲学家存在鄙夷的态度。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里,苏格拉底被塑造成“诡辩派”的代表,并被安放了不敬神的罪名。在此,阿里斯托芬充分地运用了艺术虚构的权利,让苏格拉底去教育一个老农民。在这个顽固健忘、愚蠢无知、只想通过学习论辩技巧而赖掉债务的世俗老人面前,严肃的苏格拉底处处难堪,高贵正直的苏格拉底成了他眼里那种“下贱的”“脸色苍白,光着脚丫子的无赖”、“可怜虫”。阿里斯托芬甚至通过一些流俗的台词满足自己作弄苏格拉底的快乐:“壁虎把屎拉到苏格拉底的嘴里,真有趣!”《云》里的苏格拉底,不关注人事,只思考大自然的现象和规律,他不相信众人相信的神,但把天上的“云”当作神。阿里斯托芬的目的是讽刺苏格拉底像一个翻云覆雨、狡猾多变的诡辩派。最为重要的是,老农民将其儿子送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学习口才,但儿子学成之后,因跟父亲发生口角而暴打父亲,并通过诡辩证明儿子可以打父亲。老农民被儿子驳得无言以对,认为是苏格拉底的诡辩论教坏了他的儿子,悲愤之下纵火烧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由此,阿里斯托芬完成了对苏格拉底“不敬神”“败坏青年”的形象虚构。关于喜剧《云》,后来的法国哲学家施特劳斯将此看作是阿里斯托芬对于苏格拉底攻击诗人的一次报复。
但是,苏格拉底攻击诗人所遭受的报复不止于此。诗人阿尼图斯还说服了政治家美勒托以“不敬神”“腐蚀青年”的罪名把苏格拉底送上了法庭。最终,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经过了两轮的自我申辩,被陪审团认定有罪,即“苏格拉底有罪,他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但是,这个罪名和苏格拉底攻击诗人这件事上有什么关系呢?关于那次审判,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这些原告人数很多,他们对我的控告已经有好多年了。最离奇的事情是我甚至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们,只知道他们中有个人是一名剧作家。你们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已经看到,戏中的苏格拉底盘旋着前进,声称自己在空中行走,并且说出一大堆胡言乱语,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对此,研究古希腊的权威专家罗念生先生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的论证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罪证之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在苏格拉底的年代,戏剧诗对于当时人们的既定观念的影响多么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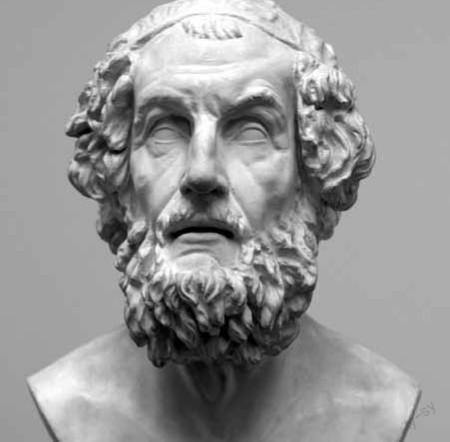
因此,某种程度上,苏格拉底是值得同情的。他被雅典民主制判处死刑之后,本有机会用金钱赎买他的性命,他的朋友也计划花钱买通狱卒帮助他逃到其他城邦。但是,他都拒绝了。在《克里托篇》中,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愿意接受朋友的劝告流亡,而自愿选择接受死刑,是因为他要用死亡的方式来证明雅典人的错误。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一只牛虻,不断地游窜于城邦之中,去叮咬那些不思考的人。他也曾说也许雅典人会因厌烦而像拍死一只蚊子一样拍死他,结果雅典民众真的这样做了。因此,我们通过柏拉图之笔,大部分人愿意记住的就是那个为了自己认可的真理而宁愿被城邦鸩死的伟大哲学家。
可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苏格拉底对诗人特别是荷马本人的严厉批评。正如前文所说,苏格拉底攻击诗人是为了一个理想城邦的正义利益。那么,诗人为何会跟城邦的正义利益相冲突呢?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寻找到对应的答案。首先,苏格拉底指责诗人败坏道德。荷马的史诗世界,是一个神人混合的世界。荷马表面上是写神,其实还是写出了真实的人性,他毫不避讳地描写了神的贪婪自私和彼此间的相互嫉妒,苏格拉底认为这些邪恶的人性会教坏青年。《伊利亚特》是以描写阿基琉斯对阿伽门农的愤怒开始的,在特洛伊战争中阿伽门农抢走了阿基琉斯的女奴,阿基琉斯愤怒罢战,于是希腊联军节节败退。苏格拉底认为这是阿基琉斯对上司的不敬和傲慢。更有甚者,荷马还毫不忌讳地在诗中描写了大量神灵之间的乱伦以及神和凡人之间的交媾。这些行为,在苏格拉底理想国里都是不允许的。其次,苏格拉底批评诗人助长了城邦公民的哀怜癖。比如 《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听说挚友被赫克托耳杀死后的心神错乱、号啕大哭;比如《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因回乡路之颠沛流离而哀痛呻吟、痛哭流涕。苏格拉底无法容忍诗人在作品中表现人物的这种不加节制的失控情绪,因为这些都只会不断地滋长人们的悲哀之情,让人们甘愿被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所辖制。而一个理想的国家必须要以理性对民众进行统治,诗所唤起的哀怜癖只会软化人们的心灵,瓦解人们的意志,从而忽略了对秩序、刚强、正义、美德的追求。因此,必须把诗人从城邦里驱逐出去。
当然,在哲学和诗的冲突背后,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人类的两种不同思维之间的对峙,是人类理性意识、哲学意识开始萌发后对诗的权威地位的挑战。挑战诗,实际上是挑战一种古老的神话思维,这种思维把人世种种不可知晓的事物解释成某种神灵安排、命运使然。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通常把瘟疫、地震、战争的失败以及类似的灾难,都归咎于神的愤怒或者是未能注意的预兆。我以为在关于通俗信仰的这个问题上,希腊的文学与艺术或许是害人不浅的。”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正处于人类理性思维逐渐崛起的时代,那时候的智者学派声称要以理性去考察和衡量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而在以荷马为代表的感性原始思维的神话时代,人们出于恐惧与无知,无法解释发生在天上和地下的许多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比如雷电、风雨、地震、洪流、战争、瘟疫等等,于是就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都归结于神灵的支配,臆想着有一个神圣的力量支配着地球上的一切。在荷马笔下,特洛伊战争是因赫拉、雅典娜和阿芙洛狄特之间为争夺谁是最美丽的女神而引发的;所有英雄都是神和凡人的后代,对于神灵有着虔诚的敬畏,他们心中涌动着人类鸿蒙之初最原始的本能情感。他们对于自己交战时的勇敢、激情、愤怒、嫉妒、恐惧,以及战争的胜利和失败,都归结于神灵的暗中支配。因此,神就成了他们一切道德行为的标准,他们把神的旨意当成了唯一的信仰和正义。而实际上,他们却可以在神的借口庇护下心安理得地做出许多并不正义的行为。史诗的神话崇拜对于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也因此给人类对真正的道德和正义的思考带来了难度。因此,随着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崛起,宗教神话需要受到重新的考察。苏格拉底一直宣称的事情就是人的无知。实际上,宣称自己无知不仅是一种巨大的勇敢,还意味着一种探索无知的努力。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不可知的神灵的盲目迷信,是可以通过反复的思辨、考察去理解清楚的。但是,由于诗的存在,由于人们对荷马的普遍崇拜,作为后起之秀的哲学思维、理性思维很难一下子撼动这种原始思维。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此,他以理性的目光来重新思考和定义什么是勇敢、美德、正义、友谊等等。如果像《荷马史诗》里边的英雄一样,将自身的行为放到神灵引导的幌子下,那么势必会产生大量的道德盲点。苏格拉底希望人们通过理性的哲学思辨去考察自身的命运,但是史诗却总是展示人们对于未知命运的情感悲伤和无奈,由此,他攻击诗人、攻击诗人的始祖荷马就不足为奇了。
最终,苏格拉底成功了,通过自愿赴死而稳固地建立了哲学本身的气候,让西方的理性思维之光闪耀。但是,理性的过分强大也造成了对原始艺术思维的压制,以至于后世的尼采不得不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指责苏格拉底对于人类的神话、诗和感性的伤害。因此,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哲学思维还是诗性思维对于人类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荷马史诗》的翻译者、荷马神学研究者陈中梅所言:“人需要借助理性的光束照亮包括 《荷马史诗》在内的古代秘索思(muthos或mythos)中垢藏愚昧的黑暗,也需要在驰骋想象的故事里寻找精神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