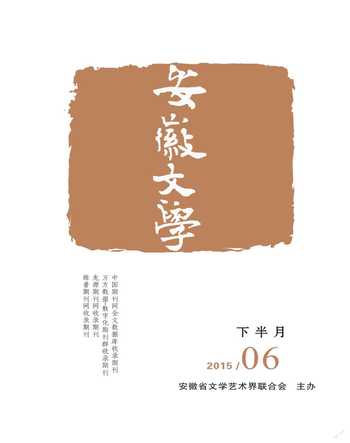从读者反应批评视角解析《三寸金莲》的尴尬境遇之原因
2015-05-30吴静
吴静
摘 要: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自问世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评论界一直缺乏对其作出客观的、深度的评价,即使在现有评价中对待它的态度也相差甚远,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因此,笔者试图从读者反应批评视角,研究文本提供的东西与读者个人“主观”反应之间的关系,通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召唤结构”等方面,探寻形成读者反应的主要因素,从而解析《三寸金莲》遭遇尴尬境遇的原因。
关键词:《三寸金莲》 读者反映批评 期待视野 空白点
“读者反应批评”是接受美学的衍生物,从20世纪西方文论史的总体背景看,接受美学被认为是更为宽泛的读者反应批评的一支,它主要研究读者在整个文学接受中的作用,将读者置于文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本文试图从文本提供的内容与读者个人主观反应之间的关系入手,解析《三寸金莲》出版后遭受争议的原因。
一、褒贬不一的《三寸金莲》
《三寸金莲》是冯骥才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讲述封建社会中国妇女裹小脚的秘史。主人公戈香莲在奶奶为其裹脚后嫁入大户人家佟家,改变了自己贫穷的命运。为了在佟家获得地位,与妯娌白金宝明争暗斗,在第二次赛脚上完胜白金宝,一举成为佟家掌权者。佟家因为伙计活受算计,家道败落,佟老爷奄奄一息时不忘给孙女们裹脚,戈香莲偷偷送走女儿莲心。随着放脚风潮的兴起,大脚被拥护,小脚遭到抵制,戈香莲为了维护佟家的尊严,为了坚守小脚阵营,与天足会首领牛俊英展开激烈争斗,不料牛俊英竟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莲心,因而深受打击,绝食而亡。作品把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缠足史通过戈香莲一人的缠足血泪史表现出来。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化功底,将女人神秘的小脚清晰展示在世人面前,触碰了他人极少触碰的中国文化中的隐秘部分,读完后震撼人心,不禁令人拍案叫绝。可正是这样一部小说,却遭遇了巨大的争议,个中原委值得我们探讨。
评论家夏康达认为《三寸金莲》是“当前文坛上的一部奇书”,[1]对其予以很高评价;而陈墨则批评它是“一堆裹脚布式的乱七八糟的失败了的文本”,[2]直接否定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同一部作品,评论家们看待他的态度却相差甚远,而且其中贬斥者数量不在少数。因此,冯骥才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在国内,我似乎还得了‘莲癖的雅号。幸亏我是80年代写的,若倒退到世纪初,真会被当做侍弄小脚的狎邪男人。当然我还听到一种严肃的规劝,仿佛我由‘现实主义堕落下来,从紧皱眉头的忧国忧民忧吃忧穿忧分忧不正之风,沉沦到为有闲者解闷解乏找乐写一种赚钱盈利沽名哗众的玩意儿。”[3]此外,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分类也各不相同,它被列为“历史小说”“传奇小说”“津味儿小说”,对此,作家本人却不认同,称“其实全是胡扯”。[3] 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他的作品完全被误读了,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会使评论家纷纷误读呢?
二、期待视野的偏离
“期待视野”的概念是由姚斯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从类型的先在理解、从已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从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中产生了期待系统。”[4] 读者的期待视野也直接关系到读者对作品的态度和评价:或认同或排斥。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实际上的阅读可能一致,也可能会发生偏离。在《三寸金莲》中,文本提供的东西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恰恰发生了严重偏离,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使作品和读者达成“视野融合”,从而导致作品被误读和否定。
究其原因,首先,《三寸金莲》这部小说的题材有其特殊性,写中国古代妇女裹小脚这件事,它被许多人定义为“国耻”,往往不愿被人们提及,更别提写成小说供所有人阅读,似乎是一块令人羞辱的伤疤被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一样,一些读者对这部作品一出版就持否定态度。其次,在接受这部作品题材的读者中,读者的期待视野却与文本中的呈现产生了偏差。因为题材的敏感性,读者多半对“三寸金莲”这个现象抱有彻底批判的态度,完全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作者在作品中不仅花了很多篇幅讲述小脚的文化,而且时常描写小脚的美,让人感到作者对小脚似乎持赞美态度,使读者不能接受和认同。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佟家两次赛脚大会,通过去他家赏小脚各自显摆小脚学问的几位名士之口大谈小脚里的文化。如在第五回“赛脚会上败下来”,作者借山西名士自称“爱莲居士”的吕显卿之口把小脚的“形”介绍得十分清楚:“小脚美丑,在于形态。所谓形态,形和态呗!先说形,后说态。形要六字具备,即短、窄、薄、平、直、锐。短指前后长度,宜短不宜长。窄指左右宽度,宜窄不宜宽,还须前后相称,一般小脚,往往前瘦后肥,像猪蹄子,不美。薄指上下厚度,宜薄不宜厚;直指足根而言,宜正不宜歪,这要打后边看。平指足背而言,宜平不宜突,如能向下微凹更好。锐指脚尖而言,宜锐不宜秃,单是锐还不成,要稍稍向上翘,便有媚劲儿。向上撅得赛蝎子尾巴,或向下耷拉得赛老鼠尾巴,都不足取。这是说小脚的形。”[3] 作者似乎更不吝啬描述小脚的“美”,如第八回“如诗如画如歌如梦如烟如酒”里,作者这样描写戈香莲用小脚踢毽子的美态:“舞来舞去的小红鞋,看不准看不清却看得出小、尖、巧、灵,每只脚里好赛有个魂儿。忽地,香莲过劲,把毽子踢过头顶,落向身后,众人惊呼,以为要落地。白金宝尖嗓子高兴叫一声:‘坏了!香莲却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来个鹞子翻身,腰一拧,罗裙一转,一脚回勾底儿朝上,这式叫做‘金钩倒挂,拿鞋底把毽子弹起来,黑乎乎返过头顶,重新飘落身前,另只脚随即一伸,拿脚尖稳稳接住。这招为的是把脚亮出来,叫众人看个满眼。好细好薄好窄好俏的小脚,好赛一牙香瓜。”[3] 作者对小脚的此类描述深受读者诟病,因为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小脚应是丑陋的被批判的对象,但在小说中却被赞美,明明丑陋不堪的小脚到了作者笔下怎么就这么美了?这与他们的期待视野偏离得太远,令他们无法接受,这就成了《三寸金莲》遭受非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至于作者为何大写小脚文化和小脚的美,作者已经在《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三寸金莲不是国耻,而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有必要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阐述;而不写小脚的美只写小脚的丑,很多人就不能理解妇女们裹脚的原因。但是作者的这种想法并不为多数读者所知,至于作者借“三寸金莲”这一文化现象反思中国文化的自束缚力等深意,就更不被多数读者所理解了。
三、“空白点”的缺乏
文本的召唤结构是由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提出来的,他主张作者在作品中常常留下一些“空白点”,这些“空白点”吸引读者,并召唤读者进行合理的想象来填补这些空白,使之具体化,促使读者自主地探寻作品的意义。《三寸金莲》中自然也少不了“空白点”,但是似乎它的“空白点”缺乏探寻作品中心主旨的导向性。如以下三个空白:第一,活受卖画。天生残疾长得歪歪扭扭且口齿不清的活受在众人眼中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个工具,没有人正眼看他,精明的佟老爷正是看中他这一点,安排他看守自家的古董仓库,把他当成了一个不可能兴风作浪的工具,可谁知佟家最后衰落的直接原因就是活受跟牛汉章勾结卖光了他家的古董字画,这是出乎读者意料的事情,活受为什么要卖画坑自己主子,作者并没说。第二,香莲送女。佟家突然败落,佟老爷因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而病入膏肓,在奄奄一息之际,命令佟家下一代孙女全部裹脚,但恰恰在这时,香莲的女儿莲心丢了,并且谁都找不到,小说后来才交代是香莲自己把莲心送走了,至于为什么送走女儿,小说却只字未提。第三,牛汉章不还莲心。香莲当年是把女儿莲心托付给了牛汉章,嘱咐他不论到哪都来信告诉她莲心的下落,可是牛汉章却音信全无,其中的原因也无从知晓。
文中这三个“空白点”尽管能吸引读者的兴趣,发挥想象力填补空白,找寻原因,但是,无论是“活受卖画”还是“牛汉章不还莲心”都与小说主旨关系甚远,对他们的填补不能够揭示小说主旨意蕴,唯独“香莲送女”这个“空白点”,值得读者探讨其中的意义,与主旨联系也较紧密。香莲因裹小脚嫁入佟家改变了自己贫穷的命运,又因赛小脚在佟家赢得了权力和地位,可以说是小脚成就了她。但是面对女儿必须裹脚的命运,香莲却瞒着众人偷偷送走了莲心,小脚的受益者却不愿自己的女儿再裹脚,是出于母性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这一点是可以展开思考的。然而,文中像这样的“空白点”却不多见,想必这也是评论界对这部作品无从下手的一个原因。
题材的敏感、期待视野的偏离和空白点的缺乏是站在读者反应批评视角下解读出的《三寸金莲》这部作品一直受冷遇和争议的原因。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当人们能更加客观地认识三寸金莲这段历史时,或许就能读出作品的深层意义,理解作者反思文化的良苦用心。正如冯骥才自己说,他对这部作品的生命力抱有信心,他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能读懂这部小说。
参考文献
[1] 夏康达.当前文坛上的一部奇书:读《三寸金莲》[J].当代作家评论,1986(6):81-84.
[2] 陈墨.失败的文本:评小说《三寸金莲》[J].文学自由谈,1988(2):25-31.
[3] 冯骥才.金莲话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208,14,71-72,111.
[4] (德)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等,译.沈阳:沈阳人民出版社,198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