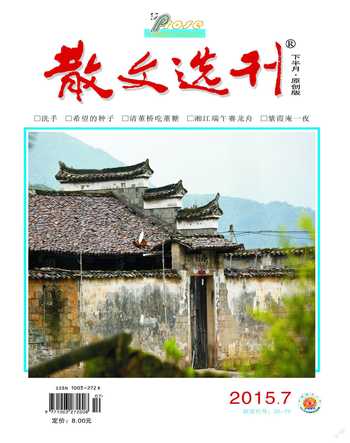阿信
2015-05-30黄耿辛
黄耿辛

中央美术学院花鸟画室来了一位日本留学生——梅园信子,大家都叫她阿信。阿信虽然比不上日本电视连续剧中的阿信长得漂亮,但也长得白白胖胖,梳着飘逸的长发,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似乎会说话,因为她和大家保持着一定距离,大家就都认为她高傲,背地里都叫她“鬼子”或者“倭寇”。她星期天常常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去看报纸,所以有人就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又背地里叫她“川岛芳子”。
阿信花钱很大方,但对同学却很小气,下课时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是一块橡皮也不会落下。别人借她一把小刀,她也会及时要回去。春节后全班同学去西双版纳写生,中国同学每人吃、住、行总共才花了一千多块钱,她一个人就花了两万多,光是少数民族的银器、工艺品就买了一大提包,有人说她是日本鬼子扫荡。她的挥金如土让我们这些捉襟见肘的中国同学恨得咬牙切齿。同学从十元钱一夜的竹棚遥望阿信住的星级酒店气不打一处来,有的人认为她花的是日本鬼子在抗日战争中从中国抢的钱,是不义之财,应该重新搞一次土地革命,吃大户,但这也只是发发牢骚,出出气,落个心理平衡而已。
课间时大家常常拿她开心,让她唱歌,她眯眼一笑:我不舒服。久而久之,每次让她唱歌她都说不舒服,大家在私下说,八年抗战打败小日本,她在中国学习当然感觉不舒服。小马拿一把扫帚,弯腰表演鬼子进庄,配上那刺耳的音乐,把个阿信笑得前仰后合。大家问她:“看不看得懂?”她笑着说:“这是你们电影里的。”
高冠华先生讲课讲到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轰炸,他在重庆险些被炸死,如果被炸死,今天就给我们讲不成课了。阿信泪流满面,呆呆地坐着,说不清是悲痛、愤怒,还是无地自容。她突然扭脸跑出教室,就在大家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阿信在卫生间洗了把脸若无其事地回来了,又专心致志地听讲了。
阿信来中国学习已经四年了,她先在语言学院学了一年中文,之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花鸟、山水、人物,每个画种各学一年,她说要多学点东西回去。她父母开一家建筑公司,很有钱,不会为路费发愁,但是四年中她从没回过家。大家问她想不想家,她说:“想。”眼里含满了泪水,问她回不回去,她坚定地说:“不回去!”
阿信很用功,不管是花鸟画,还是书法,她都学得很认真,她写书法的样子很可笑,她不是坐在椅子上写,而是跪在一个小凳子上写,样子很像小学生在练字,小马说:“阿信,你是不是每天在为我们磕头哇?”阿信不抬头继续写,自言自语道:“我不是给你们磕头,我是在给颜真卿、王羲之老先生磕头。”我们常常画得晚了就在教室的桌子上睡觉,因为教室里的暖气烧得暖和。有时我们想睡觉了,阿信还在认真地练字,小马说:“阿信你赶紧走吧,教学楼的电梯里时常闹鬼。”阿信仍不抬头地说:“我不怕。”小马说:“阿信你再不走,我们就要脱衣服了。”并摆出要脱衣服的样子,阿信无奈,只得悻悻地走了。
阿信皮肤很好,猜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大家问她多大岁数,她有时说二十五岁,有时说三十五岁,一直到她离开,大家也弄不清楚她的准确年龄。问她结过婚没有,她一会儿说没有,一会儿又说早已结婚。问她有没有孩子,她说没有,有人说:“阿信你三十多岁了怕是生不出来了吧?”她认真地说:“生得出来。”有一天,她私下给小马说有两个男孩,名叫一郎、二郎。有人说:“你出来这么久,日本这么开放,你男人怕是有了别的女人了吧?”阿信含着泪,没有说话。
一天,阿信的一位日本朋友来到教室,阿信介绍说他是位陶瓷专家,可看上去的装束却像一个建筑工人。他对老王桌上一个调色的小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爱不释手,说是中国元代宫廷里的珍品,老王一把抢过来锁在抽屉里,说就是喂狗、喂猫,也不能让日本鬼子拿走。老王家在东北,在抗战中家里死了九口人,恨透了日本人。
阿信一直要请大家吃顿饭,大家等着吃这顿饭已经等了很长时间,早已失去了信心。为了这顿饭,阿信做了精心的准备,东西大部分是从日本寄来的,这顿饭很丰盛,但是大家并不满意,认为日本人花花肠子太多,不实在。包装也太浪费,一块点心竟包七八层纸。
阿信在花鸟画室一年的学习很快就要结束了,她说临走一定为大家唱一首歌。那是在中国画系的结业典礼上,她和几个日本女留学生一起为大家演唱“四季歌”,第一段是日文,第二段是中文,她们唱得那样投入,那样深情,似乎把这一年里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融入这首歌里。从她那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大家看不到她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