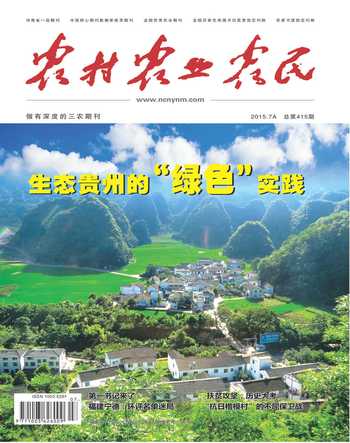扶贫攻坚,历史大考
2015-05-30卞瑞鹤
卞瑞鹤

改革开放后的 30多年里,中国向贫困宣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出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从 1978年到 2014年,累计减贫逾 7亿人。随着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倒计时。
“扶贫开发工作依然十分艰巨而繁重,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年如期脱贫。”6月 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吹响了中国扶贫的决战号角。
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两条曲线,折射我国扶贫难度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扶贫无疑是最成功的,然而不得不承认,越是在最后,扶贫难度越大。
根据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广、仍是我国贫困的“多、深”主要现状。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7017万,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6个省区的贫困人口都超过 500万;全国还有 14个连片特困地区,除京津沪 3个直辖市外,其余 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目前,全国还有 20多万人用不上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7.7万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不通客运班车,83.5万个自然村中不通沥青(水泥)路的自然村数 33万个,占 39.6%;贫困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弱、病、残的失能群体,其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比重超过 40%,位列第一,远高于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等其他原因。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近年来的扶贫数据,呈现出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从扶贫资金上看,无疑是越来越多: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222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增加,2014年达到 433亿元,4年几乎翻了一番;但减贫人数却越来越少: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减少 4329万,2012年减少 2339万,2013年减少 1650万,2014年减少 1232万。两条曲线,折射的是扶贫难度的增加。
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小康标准和西部地区的肯定不一样。”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表示,“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到 2020年,目前 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问题都能得到保障。”
扶贫“怪现象”
近年来,政府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一些扶贫项目不接地气、不做周密的计划,只管把资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视。有农民甚至反映:扶贫项目,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这种“政府越投钱群众越吃亏”的怪现象,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觉。
在西部某地区,为帮助群众脱贫,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项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 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 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 7万只。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为啥政府投入巨资,帮助群众打造的富民项目却成了 “伤民产业”?当地干部反思道:产业培育只重视生产环节,对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产业链建设“缺课”严重,结果是投入越多、产量越大、风险越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反受其累。
“产业扶贫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资源,科学规划,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盲目上马,可能会起反作用。”当地农业干部说。
富农项目之所以成了“伤民产业 ”,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习惯行政主导,忽略群众意愿和市场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脱贫”中,硬性规定 70%的资金必须用于产业发展,其余的 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这种刚性切分资金的要求,看似没错,实际不接地气。”某基层干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地区发展、农民增收的关键原因。没有基础设施,谈不上产业发展。同时不少农民也不愿意搞产业,搞产业‘看起来很美实际上何其难也。一位基层干部说:“政府要求大部分钱必须搞产业,大伙儿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搞啥。最后产业没搞起来,基础设施也没改善。”
传统的扶贫方式,资源虽然到了贫困乡镇、贫困村,但得到这些资源的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家,容易出现“扶强难扶弱、帮富不帮穷”的问题。比如,某贫困村实施一项产业到户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种子)免费发给贫困户,让农民发展产业。对这种到户扶贫,农民并不买账,“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 74岁的农民说,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锄头抡不了两下就犯累,根本没力气搞上面安排的特色农业。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在宁夏西海固村民常宗义家,一道“Z”形裂缝由上到下贯穿窑洞。尽管危窑住了多年,他却难以享受国家的危房改造补助。
他说,当地政策是改造 54平方米补助 2.2万元,不足的部分要自己筹款。假如重新选址盖一座砖房,个人还要掏 6万元左右。“我连 3万元都没有。借钱给儿子结婚,还欠着 5万外债没还上呢。”
国家补助两万元就能盖得起房的,常常不是最穷的人家。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乡长王正奇说,最需要帮助的穷人,因为掏不起自筹资金,有补助也不敢要,反而享受不到扶贫福利。
汪三贵分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最早是重点扶持贫困县,后来扶持贫困村。普惠性政策让贫困地区发展普遍提速,但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受益多,条件相对差的人受益少。“要真正瞄准生产生活条件最恶劣的贫困群体,改变‘大水漫灌的套路,实行精准化、针对化、差异化扶贫,做到一户一策。”
“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这是对不同特点群体采取不同扶贫策略的“大精准”思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认为,对于一些特别的群体,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
树立“大扶贫”思路
让 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走出“锅底”,不仅是扶贫办一个单位的事,也不仅是贫困地区的事,而是全中国的大事,需要举全国之力。
众多干部群众、专家学者都认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特别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向来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事实证明,对口帮扶方式可以解决很多贫困地区自身难以解决、中央又照顾不到的问题。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成德宁说,在扶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要强化对口帮扶的制度安排。我国从 1996年就启动了这项工作,东部 18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 10省份,但是一直缺少量化约束,没有纳入目标管理,下一步,可考虑给发达省份下指标,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拿出资源投入扶贫。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成德宁说,在扶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要强化对口帮扶的制度安排。我国从 1996年就启动了这项工作,东部 18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 10省份,但是一直缺少量化约束,没有纳入目标管理,下一步,可考虑给发达省份下指标,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拿出资源投入扶贫。
有专家建议,对各中央部委也应建立类似硬性约束,落实其扶贫责任。
事实上,各部委一直是扶贫的参与者,都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由部委领导甚至“一把手”任组长。很多部委还分别联系一些贫困片区,分别出台过专门的扶贫政策。然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不同部委扶贫力度不一,并且由于政策设计出发点不同,缺乏有效整合,扶贫政策合力尚未形成。
“就像烧水,不能总是在五六十摄氏度,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我们有各种各样黄承伟以此比喻扶贫资源的分散, 的资源,只因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到了地方上就各自为政。要把资源集中起来,精准发力。”
在 5年多的时间内,让几千万人脱离贫困,这项艰巨的工程,需要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来完成。我国已将每年的10月 17日设为“扶贫日”,不少人将“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汪三贵说,中国扶贫特点是政府主导,资源项目都是从上到下实施的,比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一些小的扶贫项目,专业性民间机构和企业可能做得更有效。而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面,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的突破创新,应当树立“大扶贫 ”思路。只有贫困地区内外、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共同行动起来,才能下好扶贫攻坚这盘大棋。
“盯人防守”实现高效帮扶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看来,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扶贫开发的政策,关键在于落实,在于各级领导干部有没有把老百姓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
“贫困县领导不关心扶贫”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地方仍是“GDP第一”,把大量精力花在招商引资搞开发上。以扶贫名义要来资金、转手就挪给其他项目的行为时有发生。还有个别地方“穷县富衙”,高耸在贫困区中心的办公大楼格外刺眼。
河南省扶贫办主任张成智认为,出现这些问题,一是有些官员政绩观有偏差,二是考核体系不完善,对贫困地区缺少约束。“这项改革落实到位,要用硬手腕推进,与官员的 ‘乌纱帽挂钩,由中央督查,做不到的就要处理人,一票否决。”他说。
“以前地方上政绩考核多以 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干得好没奖励,干得不好也没有处罚。”汪三贵说,随着各地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成为考核“硬指标”,扶贫开发将从“可有可无”转为 “主要工作”。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代,只有“盯人防守”才能实现细化到一家一户的高效帮扶。
同一片贫困地区,同样的扶贫政策,有的村富得快,有的村富得慢,差别往往就在于有没有好的带头人。老支书、老村长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很多,而一些地方尝试“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山东、“第见效更快。在安徽、河南等省,一书记”非常得到贫困群众认可,并出现了一批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典型,如安徽小岗村的沈浩。
成德宁认为,“第一书记 ”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局面,就因为他们整体素质较高,能得到各级部门特别是财政支持,能调动多方资源。这一做法应在更大范围推广,覆盖全国所有贫困村,并且通过“第一书记 ”带出更多的致富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