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风光影间的真实与虚幻
2015-05-30顾闻
顾闻
“杜可风”这个名字,占据着太多人的回忆。《阿飞正传》、《重庆森林》、《花样年华》……我们对于香港电影最绚烂的印象,似乎都来自他手中的镜头。人们钦佩他的才华,爱慕他的风趣,但我却觉得关于他,更多的应该是感谢。在他捕捉到光影之中,人们感受到了虚幻中的真实。
画影之间金牌摄影师闯入当代艺术
2015年6月9日,杜可风与张恩利的首次艺术创作联展在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中心腹地的震旦博物馆中呈现。消息一出,自然引起各方轰动——作为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这三个字本身就拥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能自然而然地将世人的目光聚集在一起。
原本在电影界如鱼得水的摄影师,突然闯入当代艺术圈,总令人感到些许好奇。在采访的开端,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将这个问题先抛给了他,而这位“随性”大师却在落座后,随口说了句:“瞎混混嘛。”这个答案立刻就把整个采访的基调从紧张严肃,转变到了轻松幽默。而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对于每一件事,杜可风都怀抱着好玩有趣的态度来做。
“我和叶晓薇、乐大豆都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他们一直想策划一个展览,于是就找到了我和张恩利。”杜可风说,他之前和张恩利并不相熟,“他们希望将我们两个‘拼贴在一起,那个点子我觉得挺好玩的,就说好的,我们一起来做吧!”
此次展览是杜可风与张恩利的首次合作,采访正值布展期间,杜可风坦言压力有点大,因为张恩利的作品基本都已经完成,并放置到位,而他则要思考该如何将自己的作品与张恩利作品进行融合。“虽然说创作部分是我们分开完成的,但我觉得当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时,它就成为了一种交流,我们之间的、我们与观众之间的。我的一些作品在创作上有自己的想法,但也会以张恩利的风格为出发点,慢慢吸收,进而加工成我自己的东西来呈现给观众。”
在他看来,这次的合作形式和拍电影的过程非常相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都是在解决问题,而不是创作。拍电影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各种困难,比如天气不好怎么办,女演员迟到了又该怎么办。很多事其实都是在意料之外的,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用一种乐观的情绪来面对,在现场根据状况进行调整,并迅速地做出反应。”
至于如何看待这次展览的结果,这位大师又摆出一如既往的酷酷的姿态称:“无所谓,在我看来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我很享受这段经历,至于作品好坏,表现的意图如何,全由观众说了算。”
缘起中国 误打误撞进入电影圈
在“杜可风”这个名字诞生之前,他是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的Christopher Doyle,不仅是家中的老大,也是除了父亲以外唯一的男性。贫困的生活让他在18岁时就选择离开家乡,踏上了漂泊的旅途,但那时他却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年轻的他跑过船,干过钻井工人,做过牧牛人,学过中医……“我当时就像是环游世界一样地各地跑。”回想起过往的岁月,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人陷入了沉思,“后来我在印度待了三年,每天用十几种语言和别人交流,但每一种也只是学点皮毛而已。这时候我不禁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生活,突然发现如果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应该从学习语言开始。”
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外国人便跑到香港学习中文,不仅爱上了含蓄隽永的中文,也对当时的女老师一见钟情,“她是一个女诗人,很有才气。也是她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杜可风,才有了我今后的生活,”他感叹道。不过杜可风也并没有一直待在香港,“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没钱了,正好当时的女友说要去台湾练功夫,于是我就跟着她去了。”当我们正惊讶于他如此轻率地决定自己的人生去向时,他又补充半句“女人嘛”,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留下我们一脸错愕的表情——果然如传闻中一样,大师是一个“恋爱大过天”的人。
而台湾之于杜可风,则是“梦开始的地方”。当时,无酒不欢的他经常混迹于各大酒吧之间,某天他走进当时位于台北忠孝东路的“艾迪亚”餐厅,并在那儿结识了赖声川。“他是我在台湾的第一个朋友,”杜可风这样告诉我们。彼时正是台湾剧场、音乐、新电影的萌芽期,也因为了这一次的偶遇,让杜可风逐渐走上了文艺的道路,1978年,他参与创建了台湾的第一个业余实验剧团“兰陵剧坊”。
一切都像是一种偶然,没有任何的刻意。或许很多人的成功,除却自身的天赋与机遇之外,还有冥冥之中的注定。就如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摄影”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杜可风日趋平淡的生活中。
当时他的一个朋友正巧要拍摄客家民谣纪录片,闲来无事的他便决定参与这个项目,两个人花费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在台湾拍摄素材。虽然辛苦,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简直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回想起第一次与摄影机的“触电”,杜可风的感觉差极了。不过这却并没有让他放弃,反而激发出了他对摄影的浓厚兴趣,并开始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学习拍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进剧组担任摄影助理、拍摄实验电影、纪录片等。这些努力不仅换来了奖项,也让初出茅庐的他逐渐开始获得业内的关注。1981年,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力排众议,选择杜可风在其新片《海滩的一天》中担任摄影指导,这部片子除了让他获得1983年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之外,也让其真正发现了自己的摄影潜能,并决定全力投入电影的拍摄工作中。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杜可风迎来了创作中的转折点。如果说杨德昌是他的伯乐,那么王家卫则称得上是将其潜力发挥到极致的人。1994年,《重庆森林》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至今仍被很多影迷和评论认为是最具杜可风质感的片子。
王家卫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搞前卫实验,在这点上,杜可风与他一拍即合。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作品中的独树一帜,例如降低快门速度让某一帧萦绕在观众视线中,或者干脆完全把画面定格起来等,杜可风将这些都玩得炉火纯青,而通过不断的练习,他也越来越享受拍摄的感觉。
随后,《东邪西毒》、《春光乍泄》、《花样年华》……一部部脍炙人口、色调绚丽的香港电影在杜可风的镜头下陆续问世,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而这个非科班出身的澳大利亚人,也在自己亲手打造出的迷幻世界里,创造出了真实的人生奇迹。
也许会有很多人羡慕杜可风的运气,认为他一路走来都有贵人相助。但我却始终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这并不是宿命论,而是有些人身上的才气与光芒无法遮挡,无论在何时何地,总能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与他共同披荆斩棘,开创天地。对于杜可风而言,“摄影”就是这么一个必不可少的存在,是他与外界交流的桥梁,也是他向世界证明自身价值的重要工具。
以人为本每个合作者都是好朋友
伴随着摄影技术的愈加精湛,杜可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除了老搭档王家卫之外,他还和关锦鹏、赖声川、陈可辛、陈凯歌等著名导演都先后有过合作。2010年,他又和崔健合作拍摄了《蓝色骨头》,并获得了第8届罗马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提起这次合作,杜可风直截了当地说:“老崔是我在内地结识的第一个朋友,我们认识20多年了。他要拍戏自然就会找我。”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的每一次合作都是以“友谊”为出发点,至于剧本的好坏,这位随性的大师似乎根本没有在意过:“你看过莎士比亚多少作品?在他的成千上万页中,我们看过的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篇而已。对我来说,拍电影也是这样。剧本、文字并没有什么意义,我更在乎的是合作的那个人,我与他之间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大部分的合作者都是先成为朋友,然后才在一起工作的。”
虽成名于中国,但杜可风凭借独一无二的摄影风格受到了世界各地导演的喜爱。他曾赴好莱坞拍摄Gus Van Sant的《1999惊魂记》和Barry Levinson的《飞扬的年代》等。而在忙完上海的展览之后,他又将即刻飞往南美,进行新电影的拍摄。“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导演,如今已经86岁了,一生只拍过六部电影,但每一部却都是经典。”
杜可风口中的大师级人物是Alejandro Jodorowsky,他不仅是导演,同时还兼具了演员、画家、诗人、制片人和作曲人等多重身份。从第一部电影《凡多和莉丝》开始,就一直在走魔幻现实主义之路,特别是代表作《鼹鼠》(《El Topo》)的问世,让Jodorowsky成为一位有着浓郁个人风格的著名导演。不知是否被导演的神秘特质和丰富人生经历所吸引,杜可风看上去对这次的合作充满了期待,不过关于影片内容,他还是遵循着职业道德,除了告诉本刊导演擅长拍摄超写实的、夸张的影片之外,其余一概保密。而这也愈加引发了我们的好奇,这两位大师级人物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又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惊喜,看来答案也只有在影片上映的那天才会揭晓。
不知道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杜可风算不算是一个容易被友情绑架的“性情中人”,因为他曾说过:“有些电影连我自己都不想看,但是如果朋友找到我了,那么就算再烂的片,我也会帮他完成。”但也许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拍电影就像是在谈恋爱,在合作过程中难免会有摩擦和不同意见的产生,这时候他往往会选择包容,“有时候会退一步,因为固执己见没什么好处,大家都是为了作品。而且有时候退后反而会让人进步。”
因此在他看来,每个合作伙伴都是促使他不断进步的良师益友。“王家卫曾经问我‘老杜,你只能这样了吗?这句话仔细想想很有意思。有时候我累坏了,情绪不好,就会爆粗口,然后觉得我就这样了,不想再干了,你能怎么样?”说到这里,他自己都被这样“孩子气”的耍赖方式逗笑了,“但有时候我冷静下来,又会觉得其实他说得对,也许我还能做得更好。所以这句话对我很重要,我现在也会经常这样告诫自己。”
最爱酒吧 最爱张国荣
看过杜氏电影的人都会发现,他对色彩和光线的运用非常好,但这一切也并不是刻意为之,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对色彩的感觉。不同于常人的方法,他偶尔会选择到酒吧去寻找灵感,“摄影师需要将脑海中的想法用画面来演绎出来,而在酒吧里‘观光,更容易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
杜可风曾说,拍摄是一种舞蹈。在《阿飞正传》中,他首次将三十几公斤的摄影机扛在肩上,开创了他闻名的手持摄影技法。据他所说,在这部电影里他用了很多种方法来处理,但是后来又发现,这些方法只是方法而已,不是一个制作过程,必须放弃和脱离这些东西才能进步。所以如果你现在问他,他的摄影风格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从来就没有研究过,“如果我知道的话,就会不断去怀疑它,否定它。所以我不会去框定自己的任何可能。”因此在每一次的拍摄中,他都不循章法,手随心动,在片场执掌着长镜头摇移游走,像极了一个舞者的即兴表演。也许对于大师来说,最好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但每一部片子却又都渗透了他的灵魂,让观者在第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带来久别重逢的惊喜之感。
杜可风告诉我,他在拍电影时,是百分之百地将自己代进每一个演员的视角中,陪着他们哭笑,感同身受。“其实说到底,电影只有三方:他们、我和你们(观众)。镜头在我手中,我是最靠近角色的人,如果我不爱这些角色,观众怎么会去爱呢?我不让演员信任我的话,观众又怎么会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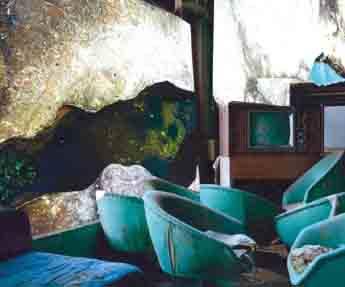
而说起与杜可风合作过的演员,个个都是“大咖”级别的人物:梁朝伟、张国荣、张曼玉、林青霞、舒淇等都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对于杜可风而言,他则是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不过虽然是朋友,他也坦言私底下与他们很少有来往,如果不在片场,一年可能也见不到一次。“但我相信,你对别人的肯定,他们都会感觉得到,这是一种精神的鼓励。”
杜可风坚定地告诉我。
而当我问起他最爱的演员时,一向开朗的杜可风突然收敛起了笑容,几乎是避开我们目光,望向窗外,说出了三个字:“张国荣”。空气在那一刹那仿佛被凝固,晃眼的光线下,分明看到他的眼睛里似乎泛出了微微泪光。
时间拉回至2009年,在《东邪西毒终结版》的首映式上,杜可风在看完张国荣的片花之后,当即落泪。“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他有时候会问我一些问题。我们爱他,他永远存在,因为他也爱我们。”这是他的原话。他曾在很多场合公开谈论过与张国荣的感情:初见时一见如故,默契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他陪伴着他适应全新的工作环境;他享受与他一起工作时的轻松:“连光都用不着操心,因为他的脸本身就会发光。”他欣赏他对待电影的热情和执念。
但如今,感觉上却觉得“张国荣”这个名字已然成为他心中的禁忌,这些“不足与外人道”的情愫,说得再多也无法让别人感受到哪怕万分之一。人们对于自己所真正挚爱的,往往会不愿多谈,仿佛说多了就是一种亵渎,这种落寞,怕是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最有体会。他曾在访谈节目中说过:“我一辈子最荣幸的事,就是作为一个摄影师,能在张国荣和观众之间充当桥梁。”
可能是因为从小生长在澳大利亚,海边的生活和自然环境造就了杜可风率性不羁,不走寻常路的性格。和他在一起,能够轻而易举地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活力,而这和年龄真的没有半点关系。在中国,人们常说“三十而立”,认为在这个年纪就应该确定好自己人生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但人生从来就是一场马拉松。
如今63岁的杜可风曾说过他的生命是从有了“杜可风”这个名字才开始的,他在32岁时开始拍摄电影,确定未来要走的路,开始一个崭新的人生。我们不会用“大器晚成”来形容他,因为其天赋是在日积月累中显现出来的。过去的那段岁月,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人生的经历,也是我独有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些,就甭拍电影了,这个跟你用什么镜头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