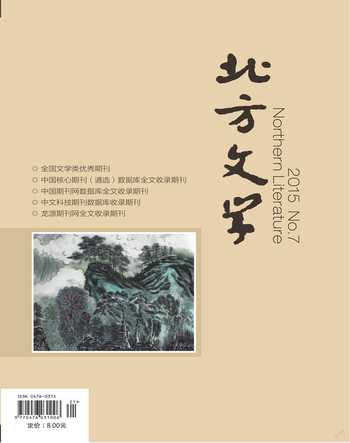生活的爱(小说)
2015-05-30李明剑
李明剑
凌晨,四点多钟。
下班的人们潮水般从厂区涌出来,她也夹在人流里,柔美的灯光照在人们幸福而欢愉的脸上,抬头望望天,天显得格外的空,高天上散布的稀落的星,灿灿地眨着笑眼。
一出车间门,她却感到了寒意,已经是初秋天气了。
她双手拢得紧紧的,这时,她不由得又想起了家。她的家离厂有两百多里,那路在山里七弯八拐,车子一过,卷起漫天尘土。她家就住在马路边,村子的名字叫枫叶坪。一条小河在村后款款流着,河上有一座两孔的石拱桥。小时候,她常常到小河里去玩那些光滑的鹅卵石,去捉螃蟹和鱼虾。有一次,她搬开水中一块大石头,看见一只好大的、铁灰色的螃蟹横行着急逃。她伸手就抓,那家伙一下子就钳住了她的手,她痛得哭起来……尽管小河留给她的是这种贫瘠的记忆,但她梦中总有小河的一切。
她慢慢长大后,那小河更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她,她知道小河的源头是什么,是山中那千百条清溪,但她不知道,小河流到了哪里。她常常独自一人坐在桥上,痴痴地望着小河消失的远处,远处是苍茫茫的群山。
村前有株两人合抱的大枫树,有一年枫叶红了的时候,她认识了他。那天,她有事到县城去了一趟,村子离县城有二十多里地,办完事往回没走多久,她感到了腿脚的酸胀。
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开过来,拖斗上只有一个人。她向路中间靠了两步,笑着向司机挥了挥手,司机没理她,拖拉机急速地从她身边开了过去。她不死心,抬脚就追,酸疲的脚使她跑得格外费劲。
拖拉机突然在前面停了下来,她看清楚了,拖斗上那个人用手拍了一下司机的背,还附耳说了句什么。
她气喘吁吁地跑到拖拉机边,那人伸手过来拉她,她红着脸避开了那人的手。
“哪里的?”拖拉机再次开起来的时候,那人问。
“枫叶坪。”她答。
俩人再没有说话,直到拖拉机停在村前高大的红叶的枫树下,她向开拖拉机的说了声“谢谢”后,才偷偷地看了他一眼,他脸孔的棱角很分明,极有魅力。
他俩第二次见面是在三江镇,这镇子偏长得像只狗舌头,一条古旧的青石板路横穿了整个村镇。
三江镇是个圩场,一个赶圩的日子,在挤攘的人流中,她看见了他。不知怎地,她很大声的跟他打招呼:“嗳——”
他惊讶地回过头来,一认出她,立刻就笑了。
“到我家坐坐。”
“你家在哪儿?”
“就这儿。”
她没有想到他是三江镇人,就在这天,她知道了他家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娘,她也知道了他家的屋子很黑,很旧。
有人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后背,她的回忆被打断了。回头见是同车间的小文,便笑了笑。
“吃夜宵去。”小文说。
“我不想吃!”她又笑了笑。
小文一个人独自向厂门口的夜宵摊走去了。
尽管她来厂已两年多了,可从来没去吃过夜宵,她的钱都有用处。甚至每月的营养品发下来,她也会卖掉,捏着那少得可怜的几十块钱,默默地呆站好一会儿。有一次,有人发觉她掉了泪,小文知道了问她,她说:“没什么!”竟笑得很舒坦,她不愿把心中的秘密告诉别人。
自从那次她到他家去了一趟后,他们的往来密切了。有一天,她歇在了他家里,她在他怀里蠕动着说:“娶了我吧!”
“等我弄点钱就把你接过来。”他的声音微微擅抖。
“钱少简办行吗?”
“不。”
他的激动深深地感染了她,当时,她只觉得他爱她,但没过几天,她明白了他如此激动的真正原因,她哭了。
三江镇的背面是一座石土相杂的山,他就是在山上的自留地里,无意中挖出了一个不知埋于哪朝哪代的瓷罐,瓷罐里有一尊金菩萨……
这一切她都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天,她担着水桶正出门,他娘遣了人来,那人见到她时神色好慌张。
她来到他家里,他娘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手里捏着广州公安局的一纸通知,抽泣着说:“我要他交给国家,他不肯,他说要修房,还要添置好多东西……”
不能听下去了,她发疯似地跑上山,找到那个藏金的地方,两块石矶之间有个圆滑的凹坑,被翻出的泥土黑得像牛粪,于是她想起了他,他翻土时一定赤着背,他的背多宽绰呀!
她返回他家,抱着他娘说:“娘,我不回去了。”
她说这话并不是因为她和他有了那种事,她觉得他干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为了对她的那份爱,因而,她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她要等着他,尽管要等几年,而他回来后还背着一个释放犯的罪名。
不知不觉间,她踏上了到后山去的路,这段路没装路灯,幸喜还有些微弱的天光,人稀了些,喧器被扔在背后,后山有半片密密的林子。听说,她现在走的地方原先也是林子,跟那半片连在一起的,后来,厂里花钱买下了,起了很多仓库,仓库里放的全是烟叶。
枫叶坪和三江镇都种烟,烟不择土,随便开垦一点荒地就可以下种,收下后送到收购站,烟厂再派车到各收购站拖到厂里,存在仓库做原料。
她到潇水市来,就坐的拖烟叶的车子。
那天,娘(她现在已经这样叫他的娘了)和她站在村镇前的马路边。没过多久,前面就开过来一辆“黄河”牌大卡车,后面挂个拖斗,车厢和拖斗里装的烟叶高高的。娘一摇手,车就停了。娘畏颤颤地趋向前,给探出头来的年轻司机递上去一根纸卷烟。
她以为他不会接那支烟的,她看见了车门上印着的五个红红的字“潇水卷烟厂”。造烟的厂子,好烟有的是,这种廉价的纸卷烟他是看不上的,但他却毫不迟疑地从娘手里把烟接了去,做了一个很潇洒的动作把烟夹在耳朵上。
“什么事?”还是他先开的口。
“……搭个便车,去潇水市。”娘说着把她推到了前面。
“上车吧!”
她从娘手里接过包裹,望着娘多皱的脸,鼻子酸酸的。
“在家不要累着,我每月给娘寄钱。”
“这年月,钱不好挣,挣不着就回来。”
“嗯。”她呜咽着应了。
她上了车,他开车好猛。树林、田野、群山闪电般向后掠去,她怯怯地望着他说:“这样,会出事的。”他笑出了声,没理会她,一手到耳上取烟,一手到兜里取打火机。
天啊!他的双手都离开了方向盘。
“这样,会出事的。”她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你这女孩,心眼倒好!”他吐了口浓烟,手搭上了方向盘。
她红了脸。
“到哪去挣钱?”他问。
“……”
“你叫大娘什么?”
“娘。”
“男人的娘?”
“我的娘。”她第一次撒了谎。
车子不久就进了山。山里的路没有直的,一味地盘盘绕绕,车速慢下来,她把眼光投向窗外,窗外是连绵的群山,高高低低,各展秀姿,山顶上浮起白乳般的雾。
车子停在潇水市的东风大桥上。
“潇水市有亲戚吗?”
“没有。”
“到我们厂打工吧,可以在我表哥家租个房。”他盯着她,眼里放出很亮的光……
突然吹来一阵夜风,她更感寒冷了,山野里各种小虫似乎也疲倦了,叫唤声断断续续的。她想起了那年轻的司机,好久没见着他了,那次在邮政局门口碰见他是在两个月前,她去邮政局给娘寄钱。
“你好!表哥怎样?”
“好!”
“总想去坐坐,总没时间,现在的人,忙呢。”
他俩只这么对了几句话就各自走开了,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望着他的背影,他没有回头。
第一次在这条路上走是刚刚到烟厂那天,他带着她,他给她讲了些好怕人的事情。他说这片林子有很多荒坟,每当天气热燥的晚上,就会有点点鬼火在林间飘荡着,厂里买下半片山起仓库时,推土机推出来好多朽了的棺材和白骨。
穿出围墙就上了山坡,山坡上有一条黄泥小路,路边稀稀落落有几座房子,除最偏远那一座是一层外,其余都是两层以上的。一层屋的屋主人是个跛子,二十五六的样子,那司机把她带到他家时叫他表哥,她也跟着叫表哥。
“坐吧!坐吧!”表哥一瘸一拐地忙得不亦乐乎。
她就在这屋子住下来,表哥安排了她一个单间,之后不久,她知道了表哥为什么是个跛子。
表哥没跛的时候,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他拼足劲攒了一笔钱,在烟厂的后山上买了地皮,准备起一栋房子。起第二层时,一次他挑砖上脚手架,架子上一颗马钉突然松落,他从两米多高的地方直跌下来,折断了腿,架子上还跌下来一个人,这个人跌死了。
她知道这个故事后明白了,为什么其它打工妹宁肯在别的屋子挤也不愿到这屋子来,她渐渐地感到害怕,她甚至还朦朦胧胧见到了那跌死的人,那人的脸面平平的、红红的,没有眼睛,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
有一天半夜,她看见窗边浮着两团鬼火,经久不去,她吓得大叫起来,表哥闻声跑过来,她紧紧地搂着他,把脸埋在他的怀里。
他没有动弹,两眼只定定地望着窗外的两团火。
“我怕。”她几乎哭起来。
“那是磷火,不是鬼火,别怕,我赶走它。”他的两颗滚烫的泪滴落在她的脸上。
他轻轻地推开她,转身到屋外去了,不一会她听到了急骤的一清一浊的脚步声,那两团鬼火晃了几晃,向脚步声远去的方向远去了。
她的心渐渐地安定下来以后,才发现自己穿着睡衣睡裤。
房门半开着,她看见表哥拿了张睡椅守在门口,嘴上有一支烟。她的心颤了一下,表哥是从来不抽烟的。
“鬼火,你不怕。”她红着脸问。
“你怕?”他反问她。
“嗯。”
从此,她每次上晚班,表哥都要等她回来,而她睡下后,他会把椅子搬到房门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转过弯就看得见表哥的屋子了,他一定在等着她。这时,她记起了他那当司机的表弟问她的一句话:“男人的娘?”
一股暖流在她心中悄然升起,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在原地站了片刻,再起步时她感到自己的脚好沉重,蹲在广州班房里的男人怎么样了呢?
“咯咯咯啊——”夜风送过来鸡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