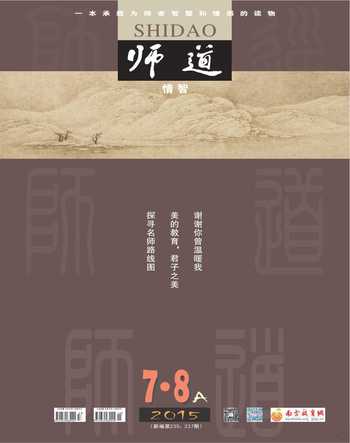美的教育,君子之美
2015-05-30吕伟超
吕伟超
于某春夜,初读《学记》,纸上奥义,心中疑义,时而交织,时而对立,一时间,灯花如魅,风雨来袭。
某日晨起,再读《学记》,思之辩之,微言大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凭栏远观,陌上花开,孩儿们匆匆上学去——青青子衿,呦呦鹿鸣,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在礼与诗之间,求学问道,于行旅中,留下谦谦君子的流风。
君子问学,究竟所为何来?又某夜,斜倚窗前,复读《学记》,天空灰蒙,星光暗淡。我知道,两千多年前,曾经有过一片群星璀璨的星空,那是轴心时代的星空。那时,不同地方的人们,在各自的星空下,建造属于自己的理想国。在西方,柏拉图们用知识和真理修筑理想国,在中国,读书人却沿着一条心之所安的道路,修建君子儒的教育乌托邦。教育究竟为了什么?《学记》指明:教育乃是为了成人之美。
成人之美:目的论
自有人类以来,即有教育,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教育发达史。不管人类的教育活动如何发展演变,“教育为了什么?”也即教育的“目的”问题,一直是教育理论中无法回避的“元问题”。在不同的教育场景中,人们从不同的立场,给出了色彩缤纷的答案。教育“为了报国”,为了“中华之崛起”,为了“分数”,为了“出人头地”,为了“探求真理”,为了“面向未来”,当然也有为了“混口饭吃”的。以上无论是“大实话”,还是“正确的废话”,都无法真正抵达“教育的目的”这一问题的本源,对于“教育究竟所为何来”这个问题,不禁愈想愈疑虑重重。及至读了《学记》,此间疑惑,忽有豁然开朗之感。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论著,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据郭沫若考证,为孟子弟子乐克正所著,《学记》系统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教育思想。《学记》,一千两百言,以“教育目的论”开篇:“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记》并非专门的教育理论论著,它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因此对《学记》所阐述的教育观点,须将其置于整个“礼”的体系中,方能准确理解。《礼记》为孔门弟子后学所著,是儒者在礼崩乐坏的乱世,对三代旧梦的追忆。三代之美好,不管是否确有其事,或者只是“信而好古”的美好想象,生逢乱世的儒者,以古礼为思想渊源,寻求治乱救世的良方,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在孔子看来,人心败坏是乱世之源,治乱之要在于治心,而治心之方在于教化,通过教育,“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学记》认为,“化民成俗”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儒家认为,只有谦谦君子才能担当起“建国君民”的大任,进而“化民成俗”,复兴“礼仪之邦”。
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首先是“郁郁乎文哉”之“文”,如颜渊所言“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外,根据《学记》的记载,“诗教”亦被推崇,“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学生要反复诵读《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等诗篇。学生习诗的目的,既非文学欣赏,也非学习创作,而是为了确立志向。因为在儒者看来,文学是儒业,诗教是儒者人格培养,心性修养的教学手段。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这个意思。《学记》既为孔门后学所作,那它必然会受到孔子这一教育思想的影响。诗教意不在修辞,修辞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养成君子的气质与特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文教,还是诗教,皆为政教。由此可见,《学记》所阐述的教育目的,核心是教人学文习礼,主张通过“礼之用”达到修己治人,学而成士,成人之美,最终建立美美与共的君子国。
当我与一位教师朋友探讨这一问题时,他哂之曰:“化民成俗,这未免也太虚无飘渺了吧。”诚然,在教育越来越以承载知识和真理为目标的今天,在知识拜物教的教堂里,谈论君子儒的教育理想,人家自然是“道不同而不相与谋”了。可是今天,当我们面对比孔子当年所面对的,还要凶险万分的江湖,愈加诡异的人心,无礼可崩的欲海狂澜时,当我们发现知识和理性对此非但无能为力,甚至还在推波助澜时,我们还会觉得“化民成俗”的教育理想,只应存在于古代的乌托邦里吗?
完全之美:知识论
轴心时代,道术未裂,孔子主张以六艺化成天下,崇尚诗教,希望通过德性教育重建道德理想国;而柏拉图却认为诗歌只是混乱的想象,只有知识才是判断事物的标准,主张用理性教育重建道德理想国,并宣布理想国不欢迎诗人。自此,东西方教育走向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分野,其实这本无所谓高下优劣之别,它只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生活理解的产物。如果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星球,各自相安无事,相信皆可独立发育出个性独特之文明,而不必去比什么高低。只是造化弄人,近代以来,分属同一星球东西两方的打太极者和掷铁饼者,硬是被放到了同一赛场里比赛,于是才有了科学主义的完胜。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对西式科学范式的知识和教育的全面归顺。中华教育道统之不传也久矣!
今天,学生们相信只有数理化的砖头,才能构建起知识的大厦,传统的六艺之学成了过时而奇怪的东西。他们对定理、公式、元素周期表谂熟于心,相信科学范式的知识可以展现出清晰的世界图景。殊不知,科学知识的张扬和道德知识的隐匿,最终使世界的意义日渐模糊。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应该如何全面、完整、辩证地看待“知識”的问题。世界可以以物质的方式呈现,也可以以精神的方式呈现;可以以理性的方式呈现,也可以以德性的方式呈现;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究,也可以用玄思的方式去理解;可以证明,也可以体悟;世界既可以言说,又无法言说。我们必须用全面的眼光去审视知识本身,《周礼·地官·保氏》指出:“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孔子认为完整的教育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包罗万象,相比今天科学范式的知识而言,是一种更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从《学记》里,我们也得以一窥这种知识观,“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在这种知识观的关照下,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是和谐统一的。人与世界并非主客二分,世界是敞开的,教育浸润着人的情感,带着生命的温度,因诗意,而美好。
再者,六艺知识体系并不排斥科学,六艺中的《易》,就属于教人“如何知天”的科學知识。只是古之君子们认为,易(科学知识)不能解释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人们更需要用德性和审美去善待世界。其实我们今天更需要反思的,恰恰是狭隘的科学范式的知识论和教育观。科学能造出飞机,却找不到飞机,至少在搜寻马航失事飞机这件事情上,科学并没有表现得比巫术更加高明。科学能给出清晰的卫星云图,却也制造出沉沉雾霾,科学不断创造新的文明,却又以更快的速度毁灭文明。科学主义主导下的教育,已经不只是剑走偏锋,甚至有走火入魔的危险。今天,我们可否从传统六艺知识论和教育观中,找到对现代性进行救赎的有益资源呢?如果我们通过学诗以言志,学书以记言,循礼而行事,习乐以正心,学易以知天,习春秋而明理,最终长大“成人”,这样的教育,岂不是更加完全,更加美好?
优雅之美:习得论
有人说,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今天的中小学教育,那一定是“苦”,学生学得苦,教师教得苦。读了《学记》后才发现,教育原来曾经可以那么优雅。《学记》中许多有关教与学的论述,今天读来,依旧有醍醐灌顶的愉悦之美。“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这是多么优雅的学习状态,一边学习,一边游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师长交流,与朋友论道。如此,学习才成为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最近在看徐志摩的恋爱故事,徐志摩恋上林徽音,不只是因为林徽音漂亮的容颜,而是因为她诸艺皆通的才情与优雅,林徽音号称民国女神,可这样的女神,却是从传统六艺教育的背景里,款款出场的。反观我们今日之学校教育,一边高喊素质教育的口号,一边却恨不得把音体美等所谓“副科”逐出校园。其实,六艺即人文,洒扫应对,一样可以做得从容优雅。反观现实中,有一些学校,为了应对上级的卫生检查,发动学生大扫除,大有把房子拆下来洗一遍的“狠劲”,却少了那一份从容和优雅。
受儒家教化观的影响,在教学法上,《学记》反对满堂灌,“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主张启示与熏陶,“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灌输得来的知识,最终都将“还给”老师,“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而经启发得来的知识,则往往印象深刻。记得我读小学时,背过一篇课文,是讲一个叫张秉贵的人的,多年以后,这篇课文的内容,我已完全没有印象,不知张秉贵何许人也,却单对一个“秉”字印象深刻。当时,语文老师教我们用“秉”字造句组词,他手握一根蜡烛,作游园状,在黑板上写下:“今夜谁与吾秉烛夜游,听花语,观鬼影?”并说如果哪位同学晚上敢来教室秉烛夜游,我一定让他照见鬼影。到了晚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跟着两位胆大的同学,到教室“秉烛夜游”去了。进了教室,举起蜡烛一看,只见黑板上的句子被改成了“吾谁与归”,边上则画着一个农药瓶上常见的骷髅头,在烛光里摇曳,吓得我拔腿就跑。这个促狭鬼老师,让我从此对“秉烛夜游”这个词情有独钟,至于那篇课文的内容,却早已望到爪哇国去了。直到有一年,我到北京出差,在王府井百货商店,看到了张秉贵糖果专柜的介绍,才明白张秉贵是何许人。能譬喻然后能为师,这岂不是一个有趣的启发式教学的例子?
《学记》一千两百言之后,世界已不知经历了几番沧海桑田。今天,面对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我想,《学记》作为我中华教育理论之源泉,依然可以面向未来,开显其本源的意义。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
祭祀之礼,从来是庄重而美好的。
(作者单位:温州城市大学 )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