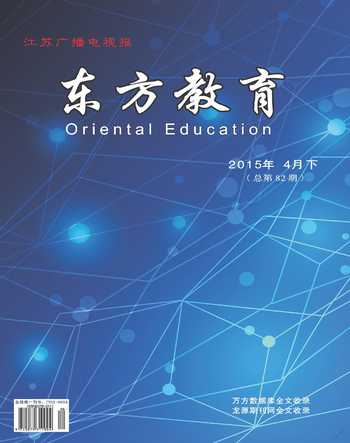从《围城》中女性形象塑造看小说中的男权意识
2015-05-30夏媛媛
夏媛媛
【摘要】《围城》是钱钟书相当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其幽默的比喻、辛辣的文风一直为众多读者所推崇。但在小说中充斥着男权意识,本文以女性形象塑造为切入点,分析了小说中男权思想的根源,探究了作品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女性形象;男权意识
钱钟书的《围城》对于人性的批判有着近乎夸张的深刻,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形象都有着可笑可鄙的劣根性,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陷入深刻的反思。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文化思潮有着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仍有着深切的亲缘性。在探索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对文化人格做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的同时,他本人却未能逃脱创作主体中东西方文化传统的遗留,其中相当明显的就是“男权意识”,作者始终站在男性的角度,去审视批判女性价值,对女性的行为和意识做主观的甚至歪曲的臆断,单从分析作者對小说中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就可见一斑[1]。
《围城》中的女性形象绝大多数都是自私虚伪、爱慕虚荣的,聚集了女性性格特质中的典型缺陷。苏文纨明明“最不喜欢小孩”还要对孙太太说她“最喜欢小孩”;明明讨厌鲍小姐,还要叫她“小宝贝”;她不希望唐晓芙与方鸿渐来往,因而千方百计从中阻挠;在与方鸿渐决裂后,又在唐晓芙面前恶意中伤方鸿渐,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个“得不到的东西就要将其毁掉”的恶毒的女性形象。范小姐是作者塑造的另一个丑陋的女性形象,她自说自话为自己制造了诸多的追求者,又攻击自己的“假想敌”孙小姐,在主动接近赵辛楣的过程中,作者又不遗余力、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刻画了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小丑角色。即使像唐晓芙这样还算“真纯”的“一个真正的女孩子”,作者的描述也是比较中立的,从唐晓芙的对白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机敏聪明,善于交际的女孩子,在方鸿渐试探性的问她,能否“在她的朋友里凑个数目”时,她断然说自己“没什么朋友”是“不见世面的乡下女孩子”,而她和方鸿渐第一次吃饭后回家,她父母都打趣她说:“交际明星回来了!”在与方吃饭时,她那一段“女人傻不傻”的论述也让方困惑她究竟是出于“天真”还是“手段老辣”。可见,唐晓芙仍不是作者承认的完美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只是作者站在一个较远的角度去审视,不愿走近揭示她内心深处的狭隘污秽,美感仅仅建立在距离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对女性仍是持否定的态度。小说中女性形象之间并无任何真友谊,更无相助,只有互相的争斗、诋毁,即使是苏唐姐妹之间也是虚情假意,各有打算。足见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否定的是多么的彻底。
《围城》中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处心积虑”的追求爱情。无论是苏文纨、孙柔嘉对方鸿渐还是范小姐对赵辛楣,作者始终站在男性角度,执拗的以传统眼光认定女性在恋爱婚姻中应该且必然充当被动的角色,一旦稍有主动,便被认定是“勾引”、“引诱”。既然不能主动表白,那耍一些女人的小聪明来暗示,有被认为是“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这无疑充分暴露了作者创作主体中浓重的男权思想,未能从妇女自身的角度去了解她们的世界。女性对于情感的渴望相对于男性来说更强烈,而作者基本上无视这种女性特质产生的根源,简单而粗暴的刻画了一个个“迫害”男性主人公的女性形象,使得男性主人公能够俨然以“女人先引诱他”这一受害者的形象坦然接受叙述者的同情。
《围城》中的众多女性都将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放在选择丈夫上,即使是苏文纨这样出国留洋回来的女博士,也毫无例外地将全部的心思放在周旋于男人之间“看男人为她争斗……斗法比武抢自己”似乎她留学多年仅只是为了增加寻找“如意郎君”的资本,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毫无施展才华的抱负。正如方鸿渐与“你我他”小姐会面,看见一本《怎样去获得丈夫并且守住他》的书后有一番议论:“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女性以家庭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将生命的全部依附于男人,这在当时那个男性处于社会领导地位的历史大环境下并不奇怪,“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传统的残余,虽然当时女权思想已初现端倪,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潮呼之欲出,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群体中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男性历史意识在千年积淀中已深入人心,因此男权观念不仅表现在男性对女性的否定和轻视上,甚至连女性自己也无法摒弃长久以来对男性的依赖,即使是自视甚高的汪太太,也甘心嫁给比自己大20岁的汪处厚,做续弦的官太太,因为“她知道这是男人的世界,女权那样发达的国家像英美,还只请男人去当上帝。女人出来做事,无论地位怎样高还是给男人利用,只有不出面躲在幕后可以用太太或者情妇的资格来指使和摆布男人。”汪太太作为小说中个性比较独特的女性人物,代表了那个时代中有着较为清醒认识的女性形象。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性自我意识逐步觉醒,传统的女性角色信条逐次消解,她们有了一定的权力要求;另一方面,在女性潜意识里依附思想及顺从观念又或轻或重地制约着她们的思想行为,在向传统的女性角色告别时,心理还缠留些依依惜别的情愫,甚至甘愿退让到一个更为安全的位置[2]。小说中的女性多半都属于后者。作者在塑造这一系列形象时,一直受到男权意识的潜在影响,男权话语模式根深蒂固,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塑造了一个个以丈夫为职业来体现自身价值的女性形象,这种对女性价值观的否定和对女性行为意识的曲解,无不笼罩着作者创作主体中潜藏的深刻的男权思想。
五四以来,女性解放浪潮不断掀起,但在文化心理整体结构中,难以排除男权观念的思想沉积。女性角色意识已从封建樊篱中苏醒,但作为一种新的角色形象的构建有其多样复杂的因素,加上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此时对女性角色形象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并有或深或浅的男权意识的辙印。因此,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基本上是男权话语一统天下的。《围城》这部小说的作者也一直是站在男性的角度,顺应男权意识的审美习惯,深刻尖锐的批判了女性人格中的心理缺陷,但是由于对女性心理特质产生的历史根源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小说在塑造形象时有许多“失控”的地方,这种“失控”是潜意识的、非恶意的,因为当时大部分作家都不自觉得用男性眼光观察审视社会,因此小说中渗透着男权思想也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创作现象,是符合时代背景的。
参考文献:
[1]彭卫红.《论小说<围城>的男权意识》.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03
[2]李晶.《走不进的围城——以女性视角挖掘<围城>的男权意识》.凯里学院学报. 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