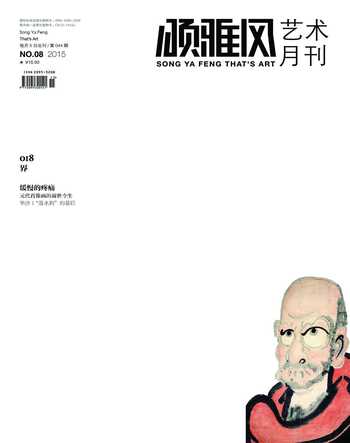身份的界限
2015-05-30李璠
李璠

所谓身份上的“跨界”只不过是后鉴之明,历史真正的面貌是一系列的初心和偶然。高名潞那时只把绘画当作乐趣,却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的信手拈来终成为了今天追溯历史的图像文献。而我们则有幸在一个批评家的绘画里看到了艺术史最生动的案例。
他是匹兹堡大学的艺术史教授,他是85美术新潮的精神领袖,他是“意派”理论的发起人,但满头银发的他今天却选择折回青春的起点——70年代。但那时,他确实只是插队到内蒙古的文艺青年,也是在地平线那边孤寂的守疆人——高名潞。
“不会画画的理论批评家不是好的策展人”。高名潞最近的个展“孤寂的地平线——高名潞的70年代”证明了这不仅仅是一句戏谑的话,细细琢磨起来,还是真有些许道理的。尽管如今高名潞的头衔被冠以中国当代重要的美术史家和美术批评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潮美术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精神领袖,但其原点却与画画相关。刚刚初中毕业16岁的高名潞响应号召,到最偏远的内蒙古“上山下乡”。在那里,高名潞像每个普通的知识青年一样放牧、干农活,但在闲暇时间,他重新拾起童年的兴趣,开始用画笔记录内蒙古的风景、周围的朋友以及自己的生活。时隔近40年,高名潞携这批70年代的近百幅作品出现在北京艺坛。展览以时间、题材为基本线索,包括了“少年心气”、“草原岁月”、“乌盟风景”、“师生友人”、“都市印象”、“长征路上”、“走向85”七个部分近100件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对展览的反应,很多业界人士,不论是艺术家还是策展人,忙不迭地赞叹着一个艺术批评家所进行的美术创作,好像高名潞做了一件远在他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
如今,看到这个展览,也有同感。人在真正做事情的时候,多数不是因为身处何境,而是事情本身构建了境。所谓身份上的“跨界”只不过是后鉴之明,历史真正的面貌是一系列的初心和偶然。高名潞那时只把绘画当作乐趣,却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的信手拈来终成为了今天追溯历史的图像文献。而我们则有幸在一个批评家的绘画里看到了艺术史最生动的案例。比如,1973年创作的《乌兰察布的家》,虽然看上去有点像印象派,但高名潞却澄清,那时候的创作跟莫奈、印象派还真没什么关系,是属于比较自觉的状态,“我没有想过要有什么样的风格,可能有些作品也会更写实,这跟我的感觉有关。我的创作没有固定的观念,就是面对这个景、环境,特别想将其挖掘出来。”与今天的语境不同的是,这些40年前的风景和人像,画的时候更多是尊重了他自己的感受,很少想到要给公众、给别人看。“自开始做美术史论研究之后我再也没有画过画,这些作品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还是能勾起我很多的回忆,这些作品谈不上具有多少观念性,它更像是我个人生活化的记录。现在看到这些画,我还能清楚地想起以前的人和事。”
与70年代略带抒情的绘画不同,80年代,高名潞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贡献是方向性、革命性和理论性的。和许多经历过80年代改革开放后,高度自由文化环境的人一样,高名潞的著作或是言谈中常会流露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在他看来,80年代的纯粹不是虚无的,虽然有理想主义,但都很实实在在的。那时讨论的问题虽然听着很大,说的问题好像很不着边际,实际上说的大家都理解,知道他在说什么,大家进入的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文化状态,而且是能够探讨某些真问题,寻找一些问题的状态。虽然当下我们要面对社会,面对生活,但这其中的假问题太多,真问题是艺术家要在这里面表现什么?艺术家的创作又提升了什么?
1989年,《美术》杂志编辑部通知高名潞在家学习马列思想,暂不参加编辑工作,不发表文章、出去讲演。90年代初,高名潞像大部分选择出国的同学一样选择去美国哈佛。这一选择,无意中让高名潞获得了一个相对冷静的思考环境,并从西方艺术批评界吸取了能量。跨出了中国国界,意味着新的视野和新的环境。同时学习英语和理论,吃的苦也很多,但高名潞把那种苦和上山下乡时吃的苦称之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苦。其实,那个时候的高名潞确实是一个在地理意义上真正跨界的勇者。“在哈佛那几年的面壁生活对于我来说,从80年代中国的现实环境下一下子换到美国,就是有点无所适从。回头想想,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不断地检验自己能不能够承受那种压力。”
如今的艺术界,充斥着纷繁复杂的艺术流派和语言晦涩的艺术理论,而“孤寂的地平线”展览上那些安静的素描、水彩、油画以及黑白老照片承载的是满满的回忆和历史的温度。高名潞的部分艺术笔记、艺术史写作手稿和图像文献,也为观众了解中国当代文人与艺术提供了最富有想象的切入点。正如策展人盛葳所言:“70年代是一段失落和被遗忘的历史,无论怎样,它都曾经鲜活地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火热80年代。”那些肖像,是高名潞在插队时,画给最为亲近的朋友的。红润的脸庞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印记,而带有苏联写实的风格却又是那个年代最直接的表达。在整个70年代,高名潞创作了数百件水彩、素描和油画作品。这些作品不但是其个人兴趣和审美理想的载体,更是他整整十年生命的证据。“我画他们的时候,很投入,带着感情”。高名潞的这些作品是怀旧情绪的出口,更是时代界限的反复印证。
界,不正是对那些我们回不去的地方的标定吗?感谢还有这样对来时路的回顾和梳理,才让我们看清了我们当下和历史的距离,也能明白我们身处何地,思考我们走向何方。另一方面,70、80和90年代,哪里才是历史的断代和界限?似乎又是一个无从解释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就像高名潞的70、80和90年代的经历一样,首尾相续,记忆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