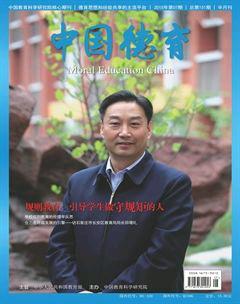以生态智慧破解现代危机
2015-05-28卢风
卢风
一、现代科技片面重视工具性知识是产生现代危机的重要原因
现代科技进步带来了公共知识(客观知识或可编码知识)的迅速积累与工业文明的物质繁荣,驱除了部分迷信,但现代科技忽视了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智慧,包括对自然的敬畏,对人之有限性的体认,对修身的重视等,导致了现代人的狂妄、浮躁、贪婪。正因为如此,许多现代人失去了心灵的平和、内在的自由和宇宙意识。
现代工业文明于20世纪末发展到顶峰,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物质建设成就,也是在此时暴露出空前的危机。这场危机除了表现为核战争的危险之外,更凸显为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与现代科技的进步方向有内在关联,与人类失去了真正的生活智慧也有内在关联。
今天,人们常常惊叹“知识爆炸”。拥有这么丰富的知识,我们为什么又陷入如此深重的危机呢?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小聪明有余而大智慧不足。我们建起的化工厂、制药厂、汽车制造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我们制造的空调、电脑、机器人、手机等,无不体现着现代科技的聪明,但我们对河流、湖泊、海洋、土壤和大气的污染,我们所招致的近在身边的雾霾和殃及全球的气候变化,又昭示着我们的愚蠢。总之,我们在每个实验室、每个企业、每个部门内部的具体工作中都透着前无古人的聪明,但这些聪明汇总起来的整体效果和长远效果,却折射着现代人的愚蠢。
省识现代客观知识的局限性,找回真正的生活智慧,关乎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
那么,知识和智慧的区别何在?
所谓知识就是可按语法规则和逻辑规则明晰表达的一切陈述(包括数学公式)。如今,典型的知识就是现代科技知识。知识可发表于报纸、期刊和书籍上,存贮于图书馆、电脑硬盘或网络云端中,可体现为今天的数据库或“大数据”。在数字化时代,知识就是可数字化的陈述。知识是外在于人的工具,你需要使用某种知识时,可到图书馆里或网络上去搜索,用完以后可立即置诸脑后。当然,你若能记住很多知识,用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不过,在电脑可随身携带的今天,你大可不必记太多的知识。
人类有两种智能不同于知识,一是技艺,一是智慧。
书画大师的书画技艺是不可能被数字化而存储于图书馆和网络云端的,尽管你可以把他们的作品存储起来——他们的书画技艺与他们的个人生命和艺术活动不可分割;著名中医的望闻问切技艺也是不可能归结为任何口诀的——他们的医学技艺是与他们的个人生命和诊疗活动不可分割的。简言之,个人特有的技艺是不可能程序化、标准化的,从而不可能被数字化,即不可能被完整地保存于电脑硬盘和网络云端中。一个艺术大师死了,他的技艺也便随之消失了——当然,他的作品可保存下来。
智慧同样不可能被程序化、数字化。这可用道家和佛家对智慧的描述加以说明。《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言,圣人死了,其智慧便随之而去,他留下的言论(记述于文本)不过是他留下的糟粕而已。《六祖坛经》记载:僧法达见六祖慧能,说自己诵《法华经》而未解经义。六祖说:“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之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法达即高声念经。未等法达念完,六祖就开始讲解《法华经》的微言大义。值得注意的是,六祖不识文字,而能深得佛的智慧。可见,智慧不依赖于文字,也不可归结为文字。智慧指人在重大选择关头所表现出的洞见、远见,指对环境之复杂变化所做出的灵动反应,指做出正确伦理、政治选择的能力,特别指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利害的决策能力。正因为如此,领导者特别需要智慧。一个社会或一种文明由有智慧的人领导才能可持续发展,由小聪明有余而大智慧不足的人领导则十分危险。与技艺类似,智慧与人的生命和实践不可分离。一个哲人死了,他的智慧也便随之而去——当然,他的语录或著作可以传世。
综上所述,我们可把人类智能划分为三类:知识、技艺和智慧。知识是可数字化的,而技艺和智慧都不可数字化。
知识和智慧虽然不同,但二者之间有关联。为获得智慧,必须学习知识,即学习知识是获得智慧的必要条件,没有丰富知识的人是不可能有大智慧的。但获得知识不是拥有智慧的充分条件,有知识甚至知识渊博的人也未必有智慧。智慧体现为哲人的知行合一。六祖在教导法达时强调了这一点:“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也就是说,学佛的人不可不诵经,但只有领会了经义且诚心践行,才是获得了智慧,否则就只是口头念经而已,甚至为经所困。同样道理,仅仅能熟背《论语》《道德经》或佛经并不意味着你有了智慧。仅当你笃信儒家、道家或佛家的基本原则并在生活中身体力行时,你才可能真有儒家、道家或佛家的智慧。
正因为智慧体现为人的知行合一,故智慧与道德不可分离。根据中国儒家传统,我们不会认为极聪明而无德行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也不会认为无德行的人会真聪明。因为知(智)与仁一体两面,都源于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有大智慧的人也是德行圆满、境界极高的人。
西方现代性轻视智慧与技艺,而极端重视知识。现代科技之得在工具性知识的迅速积累和进步,其失则在智慧的匮乏。现代工业文明依赖于标准化的生产线和生产流程,而相对忽视技艺。现代企业和政府的决策依赖于统计和计算,而相对轻视智慧。现代科学技术甚至自觉地与道德剥离(宣称科技价值中立)而极端重视客观性和专业化。致力于标准化生产的公司越来越多,越做越大,追求权力扩张的现代国家(以美国为典型)与大公司合谋,现代科技则自觉地为大公司和国家服务,于是失去智慧的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现代政治以及现代军事相结合,永无休止地扩张征服自然的力量和军事力量,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无法消除的核战争危险。
培养生态智慧,走向生态文明,是走出现代危机的根本出路。培养生态智慧,需要生态学和生态哲学。
二、生态哲学指引下的生态智慧
是破解现代危机的法宝
学习知识是培养智慧的必要条件。但是,现代性知识阻碍人们追求智慧,所以,突破现代性知识框架的局限,建构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知识框架,是培养生态智慧的必要条件。
生态哲学是吸取了生态学知识营养的新哲学,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是未来时代的时代精神——它将指引人们去追求生态智慧。
生态哲学的要点如下:
生机论自然观 与迄今为止仍占主导地位的物理主义自然观相对,生机论自然观不认为大自然只是物理实在的总和,而认为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是生生不息的,如普利高津所说:“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
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 现代科学排斥智慧与技艺,与其独断理性主义的哲学预设密切相关。独断理性主义包含物理主义自然观和逻辑主义知识论。根据物理主义自然观,万物都是物理的,即都是可以根据物理学而得以说明的,换言之,所有学科(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的知识都可以奠定在物理学基础之上。物理学可最终被确立为“终极理论”,即关于自然之终极定律(the final laws of nature)的理论。把握了自然之终极定律就意味着“我们拥有了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the book of rules)”。逻辑主义知识论包含两个关键性命题:一是知识统一论,一是完全可知论。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科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已清楚地表明:物理主义是大可质疑的,尽管它仍是主流科学的基本信念。知识统一论是站不住脚的。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已清楚地表明,科学知识不是在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的,人类知识发现不可能穷尽大自然的无穷奥秘。谦逊理性主义一反独断理性主义,但仍然高扬理性的旗帜。它相信人类理性能确保知识的不断进步,但不认为人类理性能发现什么终极定律,从而不认为人类能拥有“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所以,科学不应以发现自然的终极定律为目标,而应以确保人类安全和理解自然为目标。回顾现代科学进步的轨迹和科技应用的后果,我们既能看到它带来的“知识爆炸”、技术发明和生活便利,又能看到它所导致的毁灭人类和地球生物圈的可能的危险。试图沿着现代科技进步的方向前进而只享受它所带来的便利却回避它所带来的危险是幼稚的想法。谦逊理性主义力倡科技的生态学转向:由征服万物的科技转向保护地球、确保民生的科技,即放弃满足各类野心家之野心的研究项目(通常都耗资巨亿),而大力研发绿色科技、低碳科技、生态科技。谦逊理性主义也呼吁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仅有科技所提供的客观知识不足以培养智慧。理性并不局限于科技领域的实验和计算,也可体现为人文领域的切问近思,体现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体现为对德行和境界的追求。唯当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融合起来时,才能培养起大智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物理主义自然观和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人类没有必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因为人类认识了自然便能征服自然。唯当接受了有机论自然观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我们才会承认:人类必须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无情惩罚。
自然主义价值论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教条,据此,科学与道德、科学与伦理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是完全不同的;用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去为伦理规范辩护是无效的。这个教条既严重阻碍了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也严重阻碍了现代伦理学研究。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其多部著作中对这一教条进行了系统反驳。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克里考特(J.Baird Callicott)在对大地伦理和地球伦理的系统论证中则决然摒弃了这一教条,旗帜鲜明地捍卫自然主义价值论。根据自然主义价值论,事实与价值是互相渗透的,科学技术是有其价值预设和价值导向的,伦理学是可以获得合理论证的,伦理学与实证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可以互相支持的,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是有内在关联的。克里考特所精心论证的地球伦理就体现了自然科学与哲学伦理学的融合。
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 现代道德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才有道德资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道德关系,非人存在者没有道德资格,人与非人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道德关系。当代生态哲学正着力阐述并论证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非人存在者也有道德资格,人类对非人存在者应该担负道德责任。利奥波德首倡且为克里考特所精细论证的大地伦理则强调,人类有维护生态健康的道德责任。
辩证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 现代政治哲学过分凸显了个人的权利,而弱化甚至遮蔽了个人对社会和地球生物圈的责任。生态哲学不仅强调个人不可独立于社会,还强调人类不可独立于地球生物圈。每个人都生活在多层级的共同体中(如家庭、工作单位、社区、社会和生态系统)。个人和共同体总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系统也是人类所属的共同体,利奥波德称其为“大地共同体”,所以,每个人不仅对社会负有责任,对大地共同体也负有责任。在70亿人的人均生态足迹过大的今天,人人都有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责任。
人文主义社会观(发展观) 迄今为止,人们认为发展的根本标志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根据生态学,我们很容易明白,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当物质财富的增长达到极限时,只能谋求社会的综合发展。生态哲学主张以人文主义去界定发展,即不把物质财富增长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把由财富分配不公到财富分配公平也看作一种发展,把由严重社会冲突走向社会和谐也看作一种发展,把由社会道德败坏走向社会道德提升也看作一种发展,把由文化贫乏走向文化繁荣也看作一种发展。如此理解发展,我们才会明白,当物质财富增长达到极限时,社会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活观和幸福观 现代性的基石是独断理性主义,其要害则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生活观和幸福观。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之下,多数人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在于创造财富、拥有财富、消费财富。现代社会似乎是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但价值多元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多种价值观背后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似乎也逐渐呈现价值多元化趋势。但有人认为,当下中国的价值观是“高度统一”的,这种“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就是“以权钱为中心”的价值观。说价值观高度统一不太确切,但说物质主义是今日中国的主导性价值观没错。这个主导性价值观既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根源。浸淫于物质主义,我们便因贪婪而不可能获得智慧,因无法割舍大量消费而不可能诚心地节能减排,从而不可能驱散雾霾,降低污染。
在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指引下,我们才可能获得生态智慧。那么,什么是生态智慧?
象伟宁教授在清华大学做学术报告时说:生态智慧就是在那些经过时间考验、造福万代的生态工程和研究背后的生态理念、原理、策略以及方法,生态智慧对当代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具有普世性的指导意义。我觉得象教授说的是生态学知识和生态哲学理念而不是生态智慧。生态智慧是在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指引下而养成的判断能力、直觉能力、实践能力和生命境界(涵盖德行)。生态智慧与人的生命和实践不可须臾分离。仅把生态学或生态哲学当作谋生或谋求功名利禄的手段,不意味着你具有生态智慧;仅能熟记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教科书的内容也不意味着你有生态智慧。仅当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内化为你的判断能力、直觉能力、实践能力和生命境界时,你才有生态智慧。
生态智慧是正确的生活之道(a way of life),这种生活之道,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当越来越多的人有生态智慧且最有生态智慧的人们走向领导岗位时,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水到渠成。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