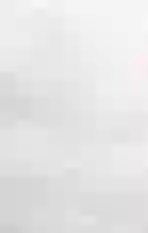当编辑,好玩
2015-05-19王秀云
没想到能当编辑,更没想到能当一名被部分作者认可的编辑。3月2日,我跟一位作者电话联系修改小说题目,对方问:你贵姓啊?我说我姓王。对方沉吟一下问:姓王?那您怎么称呼啊?我说我叫王秀云。我报出这个名字之后,对方的声音立刻就不淡定了,高喊:你真的是王秀云吗?我说是。对方大喊:我天天祈祷我的稿子能到你手里,哎呀,这是真的呀。我甚至听到他妻子附和的声音。说实在的,这样激动的声音让我愉快,但我克制着,淡定地说:你的祈祷灵验了。
我清楚地知道,有这种感情和期许的,多是基层普通作者,他们和当初的我一样,苦心创作,发稿无门,觉得文坛就是一座难以攀援的珠穆朗玛峰。我所做的只是告诉大家,文学是温暖的,可以融化积雪和冰层,路,从来就是在的。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缘分,毛建军、张亚丽、田韬、陈奕纯、罗尓豪等不少作者,都是多次向《北京文学》投稿不中,我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他们的作品,视如珍宝,生怕不能通过,他们的作品获得广泛认可,我对自己的判断力越来越有信心。这期间的故事太多了,我为毛建军小说人物的命运流过泪,并且追着其他编辑看,一次次追问他们哭没哭;为张亚丽的文字流过泪,那样的文字是有光芒的;去年年底,我为田韬多次流泪,这位老作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致力于创作,有扎实的文字功底,我在自然来稿中看见他的作品,和他多次交流,几易其稿,作品刊登后被各大选刊广泛转发,他却在兴奋地和我通电话三个小时之后猝然离世,我为他无缘享受文学成果而深深遗憾。生命无常,文学有情,我相信他在天之灵一定为文坛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欣慰。
我相信,面对文学的泪水不是酸涩的,而是带着文学的温度,我和他们的文字相遇,这是文学对我的馈赠。他们帮我证明,做编辑,这条路,走对了。
想起刚到《北京文学》不久,那天下午,人们都回家了,我那时在单位对面住,就继续留下看稿子。剩我一个人,行动立刻就不那么职业了,我把椅子从逼仄的空间拉出来,歪着身子,左手肘压在扶手上,跷着二郎腿,用这个不舒服的姿势竟然看了一篇三万字的散文,看完稿子想坐直了,却已经很困难,因为腿麻了,那篇散文就是毛银鹏的《父亲》,我后来给删到了一万字。毛银鹏来单位夸我,正被我碰上,夸得唾沫星子乱飞。从那时我就觉得,当编辑挺好玩。
我必须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他,也许我的编辑生涯也就停留在这个境界:好玩。如今还有多少这样的职业啊。我此前在企业、机关工作,多少心血付诸东流,没有感谢,没有回报,甚至没有一分坦然和平静。当编辑,付出就有回报,真心换来真情,读书写作,多好玩啊。可我后来读到了他,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说什么口音,身高多少,眉眼高低,甚至我到目前为止就读过他这一篇文章,不足3000字,但就是这个人,这篇文,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意识到,当编辑,仅有好玩是多么浅薄。
那是《北京文学》创刊六十周年系列活动,我负责编辑《北京文学史》这本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享誉文坛的汪曾祺成名小说《受戒》背后,竟然还有一个像小说一样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编辑,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顶着各种压力,让《受戒》得见天日,这位编辑叫李清泉。李清泉,这个名字就这样进入到我的编辑工作中,我得承认,在文学史中读到李清泉这三个字,我的编辑生活不一样了。和前辈比,我有很多局限,我做不到像他那样,但他们确立了我工作的方向。我担心错过好稿子,有时,错过一篇好作品就是错过一位作者的一生;我为漏掉吴君、周朝军等人的作品而痛惜,尽管有的作者言语不逊,让我很生气,但我在文学面前变得更加宽容;我尽量让文学成全汪赛良、田新艳等作者,我来自底层,清楚地知道,能发一篇稿子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当然,也许我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什么,但做我该做的吧,万一有用呢。
总起来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喜欢,一切都是好玩的。我能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无穷的乐趣,无穷的,这个词一点都不夸张。一大堆自然来搞,我先就从邮票和信封上看到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云南的繁花,新疆的沙海、海南的椰子树,四川山村的鸟语花香,东北那疙瘩的大豆小麦,京城小巷的历史古迹,有时还能看到异国风情,这个过程多么美好,不去欣赏会错过多少乐趣啊。稿子更是别有洞天,讲究点的装订成书刊,随性的甚至有用纸条手写,我发过一位中关村的作者,把一张A4纸撕成三条,写了三首诗,诗歌写得非常棒;有的用一个硕大的信封,打开发现只有二十几个字的旧体诗,有一次一位外国留学人士,用大量篇幅介绍自己的天才经历,可只写了500多字的稿子;也有很多打悲情牌,把自己经历的苦难人生当做文学的敲门砖……看见这些,我每每都忍不住笑起来,享受文学生态园的万紫千红。
做编辑时间不长,但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有的作者非常淳朴,跑几十公里就为了给我送一盆栀子花,我不好意思告诉她,那花很快就干枯了,可以安慰她的是,我们编辑部刘红用这个花盆养了富贵海棠,已经开花,和栀子花一样漂亮;有的作者会耍小聪明。有一次,一位作者冒充张艺谋编辑团队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一部旷世奇作,我急不可耐等着他寄过来,看了三页就知道上当了,退稿之后,他打电话骂街。甚至遇到过骗子,他寄来的稿子,竟然抄袭茨威格的《麦哲伦传》,他要是抄袭一水平差点的作家或许能蒙混过关,可他作案的段位高过了自己的能力,我后来看到他的作品在别的编辑名下发表,并在凤凰卫视堂而皇之宣传,这种如鲠在喉的恶心如今想来也是一种趣谈。
不想上纲上线,好像自己真多好似的,不能不顾客观现实,把自己夸得太狠,因为我还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而且知道问题在哪里。严格意义上说,我并不是一个好编辑,一个好编辑,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一位研究巴西文化的作者寄来一篇稿子,在这篇作品面前我看到自己的短处,我跟我们的总编校袁建民老师说:这篇作品让我仰望了。仰望作者开阔的视野,仰望作者深邃的思考能力,仰望作者能用英语给我写回信,我只认得一句:Dear Wang, Thanks for your message……他提出希望能见一面,就作品有关情况再谈谈,我没有勇气答应他的要求,因为我的知识储备不能支撑这样的谈话,我为此而惭愧并深深遗憾,只能实话实说,我不懂外语,我对现代艺术不很了解,至今,没有出国机会……
我不是一位好编辑,我起点不高,入行时间短,又有现实的很多困境在干扰我,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这一点,我很自信,我原本能做好,能做很好。
至今,我当过农民,做过老师,曾在企业做文秘,也在机关做过小干部,回首人生路,当编辑,是我所有职业生涯中最好玩的经历。
谢谢文学,谢谢《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