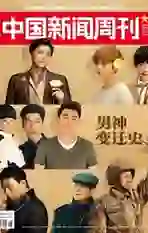臆想中的中产阶层
2015-05-14万佳欢
万佳欢
根据2014年10月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的中产阶层(按报告的定义,个人资产为1万至10万美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占全球的中产阶层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谁也不会否认,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产群体迅速增长。十几年来,媒体和学者们不停地谈论“中产阶层”,但到现在为止,“中产阶层”仍然缺乏公认标准,成为最热门、也最受争议的社会学概念之一。当一些中产已经加入移民大军,一些中产为了房、车、孩子发愁时,“中产”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名词。
中国中产: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狂奔
大多数时候,中国中产阶层只是关乎消费方式的一个概念。
有人这样总结中国中产的三大爱好:汽车、房子、理财。在某种程度上,中产存在于汽车广告里。作为当今社会最能反映某社会阶层消费能力和欲求的商品,汽车被广告商精心包装成为中产阶级的象征性符号。
中产还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房地产广告里。“中产阶级荣耀领地”,“国际典范,中产意境”,房地产商们几乎要在在媒介构成的社会环境里 “制造”出一个中产阶级。
“赶时髦”的心态是中国社会最不缺少的东西。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急于按照“中产阶层”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出国旅游成为当下中国中产的大众化社交行为之一,仅在2015年春节的7天时间里,上海虹桥机场出入境人数就达到36.6 万,比去年上升了 40.9%。游客们从韩国、泰国、日本乃至美国、欧洲带回来满手机的照片,以及一堆奶粉、化妆品、手表或手袋。以日本为例,春节期间奔赴日本的大陆游客多达 45 万人次,为这个国家贡献了 1125 亿日元(约 60 亿元人民币)的消费额。
钻石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伦敦和巴黎的钻石销售额中,有50%来自中国买家。10年前,中国在全球钻石市场中的份额只有3%,如今已攀升到15%;过去5年里,中国对钻石的需求一直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在反腐形势的打击下,中国奢侈品销售量下滑,但这并不影响国际品牌对中国市场的看重。他们把主要客户群定位在新兴的中产阶层。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很多商业报道里,常常出现这样一句话:“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和日益提升的富裕水平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市场”。
已故社会学家陆学艺曾表示,“中国中产者一直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狂奔”。他们热衷品牌消费,渴望通过投资理财累积财富,追求泡酒吧、听演唱会、旅游的娱乐休闲方式。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西方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穿阿玛尼、拎LV的人群。保罗·福塞尔在《格调》里写,中产阶级(西方叫作“中间阶层”)是“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
这位文化批评家毫不掩饰自己对中产阶级的轻慢,在他看来,中产阶级胆小、思想传统、生来幼稚、循规蹈矩,这群人“衬衫总是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外套总是过分的深色,领带模仿企业家的风格,发型仿照50年代的样式”。
学者许子东曾说,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而在中国,大家把中产阶级当作一个崇尚的对象,一个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很少有人关心中产阶层的内心世界。精神匮乏成为很多中产者的普遍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帕提·沃德米尔在2014年5月报道,一些年轻人出现在寺院里,他们完全不符合信徒的典型形象(较为传统的地区的老大妈),他们身穿的标志性“制服”:抓绒衣加运动裤,牛仔裤加跑鞋。文章指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正在转向宗教以寻求心灵的平衡,因为他们过着“非常有压力和紧张的”生活。
中产vs伪中产
中国中产究竟算不算中产?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论证已经延续了很多年。
19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家和城市私营业主的兴起,“中产阶级”一词开始在大陆出现,虽然只存在于学术论文里——那个时候,人们还对这个词避之不及。
2000年以后,“中产”一词开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这被认为是政府试图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一个政策信号。此后,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中产收入标准,但有人提出应以年收入5000美元为底线,有人认为最少也得是30000美元,差距极大。
争议在2005年达到了高潮。那段时间,“中产阶层”一词屡次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很多场合提及,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调查结论:年薪6万元到50万元是界定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
这个定义把很多人吓坏了,它意味着中国一下子冒出了2亿多中产者。2006年,有评论家干脆发文称,“中国‘中产阶级是伪命题”,“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传统农耕社会的快速解体和重新定位过程中,阶层的迅速分化和快速重组尚未完全实现,不敢轻言中产阶级”。
2008年,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教授指出,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许多富裕消费者,但这群人只能算作中国的财富新贵,并不是新的中产阶级。
古德曼在《中国的新富:未来统治者,目前的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无论从其产生的途径、政治性以及在社会所占比重来说,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中产阶级特征只是表现在其生活方式上。”
但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至少在各种报告、调查和蓝皮书中,中国中产者人数在迅速膨胀。
2006年前后,美国美林公司还在大胆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而到了2010年,据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估算,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人数已达到8.17亿。
同年,一份来自“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3%(2001年只占15%),并且还在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甚至“蚁族”都是中产的后备军。
这一年,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其中称北京的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接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60%-70%的社会比例。一个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的时代似乎正在来临。
很少有人赞同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达到这样一个规模,几乎每一次报告都会引发一轮对“被中产”或“伪中产”的争议。大多数被访问的中产感慨自己有中产之名、无中产之实,有媒体惊呼“8亿中国人‘被中产”:呼吁了那么多年的“橄榄型”社会,居然就这么实现了?
中产与“伪中产”之争甚至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有评论员认为,“中产阶级”一词之所以被主流学者过分强调,与中国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不无关系:因为这个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代表了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它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因素。
“伪中产”之“伪”
在“伪中产派”看来,有一个最大的论据足以支撑他们的观点:中国中产者缺乏自觉性和自我认同感。
这几年,社会学者和媒体界定中产阶层的方法大多是统计分析民众收入数据。而在西方,中产阶层并不是通过一串冷冰冰的数字为人认知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观认同意义上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中产阶级”概念,它们分别来自于政府、社会学者和公众舆论的描述。
在社会公众意识中,中产阶级通常是“高收入和高消费的企业主,职业经理人和精英知识分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李春玲在她的论文《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中指出,公众舆论心目中的所谓中产阶级与社会学家提出的概念界定有很大不同——他们应该是社会学家所界定的中产阶级当中的少数上层;他们在中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比例不会超过10%。
公众认同感跟社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相比而言,西方的中产阶层之所以很快就认同自己是中产者这一现实,是因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使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一整套保障权力与社会福利制度,大多数民众都能达到衣食无忧的中等生活水平。在1960年之后,就连一些西方工人也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而很少有中国中产能够痛快地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被中产”的说法大多来自都市白领,虽然眼下衣食无忧,但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安定。
大多数“中产者”是焦虑的。2014年初,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一炮而红,有分析说,这档节目触及了内地中产阶级的焦虑——那帮在溺爱中长大的第一代“小皇帝”如今是中产阶层的主力军,他们很想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养育第二代“小皇帝”。
认同感还与安全感相关,而从食品安全到环境污染,令中产者们害怕的东西很多。2月,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公共事件,原因之一即是雾霾问题关系到当下日益庞大的中产群体的切身利益。
“中国中产阶层的行为方式、生活状况都很难跟西方的中产阶层做比较,因为两者生存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条件很不一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指出,“国内的中产人群并没有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然也难有相应的行为方式。”
在社会急剧转型中,中产者有一些自身诉求,他们也能够通过网络这样的最新手段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但他们并没有政治话语权——正因为此,很多学者才不同意“中产阶级”的概念,他们认为,政治话语权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来说十分关键,毕竟要形成一个阶级,就会有一定的发言权。
如果中国中产阶级有固定的价值观、立场、观念和认知,它们将构成整个社会共识最稳定的基础。但现下的问题是,它们还没有形成。正如已故社会学者陆学艺所说:“这(价值观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不是中产阶层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还没有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