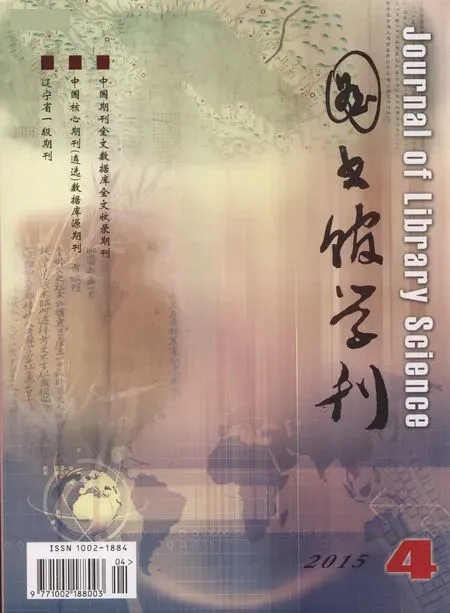敦煌写本残卷《大通方广经》考辨*
2015-05-13华海燕袁佳红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47
华海燕袁佳红(.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47)
敦煌写本残卷《大通方广经》考辨*
华海燕1袁佳红2
(1.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2.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47)
[摘要]重庆图书馆所藏一轴古代写本残卷,实乃《大通方广经》卷中的一部分,原出自敦煌石室,后方辗转至此。该经内容既能纠补《大正藏》之阙失,其所附题识更汇集了民国张海若、徐鸿宝、严天骏、李权4人墨宝及钤印,颇为宝贵,具有很高的历史、版本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大通方广经》年代题识敦煌遗书重庆
[分类号]G256.22
*本文系重庆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古籍目录著录实践中相关问题的探讨——以古籍普查为例”(项目编号:12XWQ20)研究成果之一。
重庆所藏敦煌卷子不多,其中三峡博物馆藏有20余件[1],私人性质的陈宝林博物馆藏有10件[2],重庆图书馆也藏有一件敦煌写经残卷。前二者已有公布,现再介绍重庆图书馆所藏,以祈有助于学界。
1写卷概况
重庆图书馆所藏卷子裱在一张白纸上,为卷轴装,卷子左为徐鸿宝和张海若之题识,右为李权题识,下为严天骏题识,白纸长170厘米,高57.2厘米。卷子为硬黄纸,卷长41厘米,高26厘米,乌丝栏,书23行,行17字,间有16字。该卷子保存完好,且首尾完整,卷子右下角钤朱文印“重慶市圖書館藏善本”。
重庆市图书馆珍贵古籍目录著录为:“释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写本。”[3]亦有人认为并非《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而是《大通方广忏悔庄严成佛经》,亦称《大通方广经》。“《大通方广经》卷中……此外,本经卷中尚有敦煌遗书十一号,北敦9594号、北敦10548号……渝图1号。”[4]105
《大通方广经》,“又名《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方广灭罪成佛经》。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三卷。……此经系《佛名经》之亚流。谓持诵佛名、忏悔发愿可灭罪得福云云。自《法经录》以下,历代经录均判伪经。陈文帝有据此经而作的《大通方广忏文》,据此,当产生于南北朝时期。”[5]733-734隋《众经目录》、唐《开元释教录》等均判为疑伪经,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录,后亡佚,幸赖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此经始重现天下。
2写卷来源
由于时代久远,重庆图书馆并无文献记载该写卷入藏时间及情况,《重庆图书馆馆史(1947~2007)》亦未涉及,但从民国史料和卷子旁各家的题识可以考见该卷子的源流。
2.1徐鸿宝运送古籍至重庆
根据古籍特藏中心的工作人员告知,此卷极有可能是来源于抗战胜利初期徐鸿宝所护送至重庆的古籍之一。考究民国史料,发现徐氏运送至重庆古籍共两次,一次是在1945年前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同时还承担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敌伪图书文物的任务。比如徐森玉先生先后接收上海敌伪图书一百二十四箱五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册,南京敌伪图书六十九箱三万四千五百二十五册,运送重庆罗斯福图书馆”[6]5。另一次是在抗战爆发后“为抢救沦陷区一些著名藏书家旧藏散失在市场上的珍贵古籍善本,当时留在上海的郑振铎、张菊生、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联名电请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抢救收购。……当时决定所购善本古籍,将陆续经由香港转运重庆保存,但是除第一批有八十余种宋元善本由徐森玉带走经由香港运送往重庆外”[6]6。则该写卷极有可能来源于此两次运达古籍中的一种,而重庆图书馆今藏之古籍多来源于此。
当时徐鸿宝对此批古籍留有中英文目录,不过在重庆图书馆未见此类目录,或是由于当时抢救的大批珍贵古籍文献后来均运往台湾,所以其古籍目录极有可能藏于台湾国图。因为当时的环境极不稳定,收购与运送古籍的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主持参与此事的郑振铎、张咏霓、何炳松等均用化名,所以当时珍贵古籍入藏重庆图书馆(时称罗斯福图书馆)很有可能就私下进行,未曾留下目录账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抑或是邓仲和赠予徐氏,徐再转藏于重庆图书馆。无奈斯人已逝,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只能稍加揣测。
2.2各家题识
该卷子旁有多位名人题记,不仅可以考见卷子的流传情况,还使该卷子本身极具艺术价值,下为各家钤印:

徐鸿宝 张海若 严天骏 李权
2.2.1目录版本学家徐鸿宝题识
此卷出自敦煌,為/仲和先生所藏,風格端凝,氣力充滿,/無經生庸俗之習,酷似孔祭酒碑,是/初唐名手書也。鄭重展觀,自幸眼/福非淺。壬戌冬至,吳興徐鴻寶題。
钤印“森玉長壽”,作于1922年冬至。
徐氏生平事迹,《民国人物大辞典》和《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均有记载,王函《学者徐森玉古籍整理事略》、邓啸林《鲁迅与徐森玉》、郑重《徐森玉》等亦有所论及,他与郑振铎、傅增湘、顾廷龙等交好,今录顾廷龙先生于1981年2月21日所题跋于此,以志其抢救古籍文物之劳瘁,对其生平亦可了解一二:“徐鸿宝先生号森玉,别字圣与,浙江吴兴人。博识精鉴,世罕其俦。一生对文物之热爱,研究,调查,保存等方面,不辞辛劳,在抗战中遍历津渝沪各地,有出生入死之危,在所不顾,建国后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年动乱中蒙受诬陷,迫害致死。”[6]1422-1423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国百科网均记载森玉先生卒年为1971年,但《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却记录为:“徐森玉(1881-1967),名鸿宝,以字行。”[7]742另据其子徐文堪《先父徐森玉二三事》载:“(徐鸿宝)‘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党羽迫害,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8]248可以纠正《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之误。
2.2.2书画篆刻名家张海若题识
仲和與余交,冣諗此幅,年前由秋史夫人交來題識。屢晤仲和,亦未經道及/,疑另為一人。久之亦無索者,庋諸畫軸中漸忘之矣。月前面詢仲和,始悉此幅為/胡西樵同年所贈,而嚮森玉乞題者,蓋厤有年所也。敦煌寫經,泰半流入東/西洋,全幅至不易得,六朝人書尤不易覯。余友徐蘭如君曾贈得六朝殘幅,/迩來檢尋,已失所在,得此珎翫,忻慰奚如。然此幅在森玉處閣置數年,/經過余所,抑又年餘,大有思主之意,敢瀕於懷璧之嫌,亟述其經過而歸/之。時丙寅重九前一日,獨園海若識扵二录石齋。
钤印“張溶”,作于1926年9月初8。
张海若书画篆刻造诣颇深,以善书汉隶闻名于时。此段题识即为其精绝汉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张国溶(1876-)字海若,湖北蒲折人,1876年(清光绪二年)生。清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咨议局副议长。1914年3月,被选为约法会议议员;同年5月,任北京政府政事堂参议。1916 年5月,任国务院参议。1924年5月辞职。嗣从事书画研究。”[9]943
2.2.3文化名人严天骏题识
敦煌寫經為有/唐冣著之作,近代/流傳及於海外,/國中反成吉光/片羽。仲和得此/帙,藏之數歲,丙寅/冬日甫出見眎,古/意溢於行間,洵墨/寶也。為識數語歸/之。玉溪嚴天駿題於宣南寓齋。
钤印:“巖二”“天駿”,作于1926年冬日。
“严天骏,字仲良,云南新兴(今玉溪)人,1871年生,1891年辛卯科举人。……著有《玉湖诗文集》《日京参观琐录》《行政随录》。”[9]1663严氏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二,故其钤印为“巖二”。另《民国人物大辞典》亦有相关生平简介。
2.2.4文史学家李权题识
丁巳戊午间,吾友鄧君良甫自隴貽延壽/經全帙,云得自敦煌石室者。予於書家源/流夙未研究,偶一展視意若為移,然終不/能領其妙處,姑藏之而已。越十年,仲和出是/卷囑題。予觀卷內題者若徐君森玉、張君/海若、巖君仲良,皆精鑒別,仲和又號稱書/家,於此卷既均爱玩不已,其為稀世珍可決/言也。亟檢舊藏与仲和同觀,仲和謂首尾完/全,尤為難得,慫恿善為裝潢。予於此卷雖不能賛一詞,爰述梗概以識,予愧即作此卷題/詞可也。/丁卯清明後十日,鍾祥李權博父/題於都門雙槐寄廬。
钤印“博父”,作于1927年。
李权为民国时期文史学家,学富五车,编有《钟祥县志》。此印章名源于其子李济。李济,字济之,是中国第一个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喜出望外的父亲(李权)尚不知道如何衡量儿子‘博士’头衔的价值,但他不久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博父”的号名,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李济后来的一些朋友如傅斯年、赵元任等,都善意地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10]82
从各家的题识可以考察该卷子乃为邓仲和之物,其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民国人物大辞典》有简要记载:“邓仲和,江苏江阴人,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生。无锡第三师范学校肄业。1918年去上海协泰棉布号为学徒,后升跑街。1922年在上海自设大庆棉布号,不久扩充为大庆纱布号。1930年开设安乐并线厂。1931年创办安乐棉毛纺织染厂……1979年7月,赴香港定居,在香港恢复大庆公司。1983年11月病逝。终年79岁。”[9]1497从落款日期可以看出该残卷是邓仲和先生得自丁巳年(1917),彼时正是敦煌石室瑰宝流出之际,仲和先生此卷恐来源于此。
3写卷年代考
由于该写卷是残卷,无头无尾,缺少题记,故无法考证其具体年代。但出自敦煌藏经洞却是无疑的,这至少可从3方面加以证实。
3.1名家题识
其一,古籍版本家徐森玉鉴定曰:“此卷出自敦煌,为仲和先生所藏。”而“(徐)先生深于录略之学,论历代典籍传写雕印之源流沿革,如数家珍,造诣所极,冠绝海内”[11]242,因而其鉴定结果有着极强的说服力。其二,民国时期张海若、严天骏、李权的题识时间分别是1926、1927年。从落款日期可以看出该残卷是邓仲和先生得自丁巳年(1917),而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是在1900年,彼时国人未曾引起重视,1910年学部始派人收运残卷至京。而从敦煌至京师路途遥远,途中又被盘剥搜刮裁剪部分卷子,该卷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北京的,那么应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流散出来的。
3.2其他敦煌写本《大通方广经》的题记
宇内其他源出敦煌藏经洞的几种《大通方广经》写本,卷末题记均标明抄写时间: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本,“开皇十年(591)”;S.4553,“大隋仁寿三年(603)”;日本滨田德海旧藏本,“咸亨四年(673)十一月二十日”[12]734(疑伪作);俄藏Дх.00180,“大业七年(611)”[13]122。现存4家题记除一条为唐时所作外,其余3条均作于隋朝,则此经当在隋朝就广泛流行,重庆图书馆所藏《大通方广经》残卷或当在隋唐之际写成。
《莫高窟第401窟初唐菩萨立像与〈大通方广经〉》称:“Дх.02985的题记:‘伏惟经戒大业七年(611)八月八日,正信佛弟子寡(?)妇女赵仰为之女写《大通方广经》一卷,共翟恩子卷合为一一部。又愿立者不迳地狱、饿鬼等苦,复愿写经功德施无边法界。众生同站斯福成无上道。’”[14]但查阅俄藏敦煌卷子,Дх.02985并非《大通方广经》,俄藏Дх.00180、Дх.02597、Дх.02980才是《大通方广经》,为卷中的一部分,首残尾全,末尾附题记。另有半片残片,故不录。同为乌丝栏线,与重庆馆所藏残卷字体相类。行17字,间有16字、18字。该文移录题记有几处讹误,根据原卷字体和上下文关系,应录为:“伏惟经戒大业七年(611)八月八日,正信佛弟子寡妇女赵仰为亡女写《大通方广经》一卷,共翟恩子二卷,合成一部。又愿亡者不達(逢)地狱、饿鬼等苦,復愿写经功德施无边法界,众生同沾斯福成无上道。”[13]122
3.3文字特点
“敦煌出土的隋唐古写经卷多以楷书写成,一行共十七字,字体精妙端正,并采用称为黄麻纸的黄染上等纸,经卷幅为二十五公分(一尺),此格式便于经阁收藏,必须维持固定尺寸。”[15]84重庆图书馆所藏写卷完全符合敦煌卷子的特征,且该卷内容不同于现存其他的敦煌卷子,可以肯定它不是伪造而是抄录之作。该写卷字体端正,较为清瘦,未变丰腴,应为初唐时期流行字体。“官经生书法往往精工细腻,圆熟简净,风格近媚,这与他们所受教育较高和享受天朝俸禄的优越地位分不开。经坊经生的书法则稍嫌恣肆,用笔的提按顿挫、结构的欹侧变化都较官经生书法丰富。而个人写经则比较随意。”[16]而目录版本学家徐森玉先生更认为该卷不是普通经生书写:“风格端凝,气力充满,无经生庸俗之习,酷似孔祭酒碑,是初唐名手书也。”
该卷为何人书写不得而知,或为官府抄经行为,或为自己抄写祈福,或是施主雇写经生而作,抑或是专业经生开铺所造经。但据四题记可以知道该经在六朝隋时较流行。因此,重庆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也基本应该是写成于同时。
4卷子内容
今将重庆图书馆所藏《大通方广经》残卷原文移录于下:
我扵尒時,皆以一切供養之具而供養之,是諸如來亦不見與我授記。善男子!我扵(住)[往]昔若干劫中,供養若干諸佛如來,尊重讚嘆,煩惚得除。具足聲聞威儀禁戒,淨脩梵行,學行布施,一切持戒及行頭陀,離扵憍慢瞋恚愚癡。忍辱慈心,如聞能說,懃行精進,一切所聞受持不失。獨處遠離,入諸禪定。出禪定已,隨所聞法,讀誦思議,是諸如來亦不見授記。何以故?所受禁戒多毀犯故,深著聲聞二乘行故,不聞《大乘方廣经》故。以是義故,若諸菩薩摩訶薩,應當遠離二乘之行,脩集大乘方廣经典,則得授記。若我以一劫若滅一劫說是佛名,不可得盡。善男子!我過是後,得見定光佛為无量大眾說是《大乘大通方廣》。我扵尒時得聞得見,從彼佛所受持,讀誦思唯其義,即得无生法忍,定光如來即授我記:“汝扵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是故善男子,授持是经典,疾至佛地,況消世間天人供養。善男子!是故大乘经典力勢寶藏不可思議,慧施破戒貧窮依儀寶珠。善男子!我已偈讃:
大乘如海水,小乘牛跡水。大乘如須弥,小乘蟻子城。
大乘如日月,小乘打火星。是乘名大乘,不可思議乘。[17]
由于该经已经亡佚,只有敦煌遗书中存有残卷,其中包含此段文字的卷子有北8217(盈24)、北8218号(露66)、北8653、散1511号、S.0538、S.6382。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本前段文字与之基本相同,但是后面的部分文字有异文,今录于后,以作比较:
其一,“我于尔时得闻得见彼佛所。受持读诵思惟其义。”[18]1347大谷大学藏本缺“从”字,且注释为:“所+(说)?”,因为此句不通,故疑为“说”的错字。北8218号(露66)和S.6382均有“从”字。按“:从”字加上为好,语义更加通顺。该句应断为“:我于尔时。得闻得见从彼佛所受持,读诵思惟其意。”
其二,大谷大学藏本末尾为散文:“善男子。大乘如大海。小乘中迹水。大乘如须弥。小乘蚁子城。大乘如日月。小乘打失星。是乘名大乘不可思议乘。”[18]1347重庆图书馆所藏卷子末尾为偈颂体,北8218号(露66)和S.6382也为偈颂体。《大智度论第八》:“摩诃衍法亦如是如偈说:摩诃衍如海,小乘牛迹水;小故不受大,其喻亦如是。”[19]86该条记录亦可佐证此句偈讃在佛经中常用,可知此段散文原来应该为偈颂体,以此可纠大谷大学藏本之误。
关于“牛跡”,大谷大学藏本录为“中跡”,其余S.0538、S.6382、北8217、北8653、散1511号均为“牛跡水”。牛跡:“(雜語)牛行之跡也。谓佛为牛王,佛之教法为牛跡。维摩經弟子品曰:‘无以大海内于牛跡。’”[20]719而无“中跡”之說。关于“火星”,大谷大学藏本为“失星”,但是明显的该句是说大乘如日月永不朽,而小乘则如火星(流星)一般稍纵即逝,因此大谷大学藏本或是校录有误。
5 结语
重庆图书馆所藏写经残卷应是敦煌石室之物,从题识中知道此写卷原本由胡西樵赠予邓仲合,奈何查阅民国史料,概无此人的相关记载,还望学界前辈知晓者告知,或许对了解此卷具体年代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杨铭.重庆市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目录[J].文物研究,1996(6).
[2]陈宝林.重庆宝林博物馆藏敦煌写经[J].敦煌研究,2012 (5).
[3]重庆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珍贵古籍目录[EB/OL].[2014-01-06].http://www.cqlib.cn/gczy/guji/sb/201002/t20100211_23 089.html.
[4]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5]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6]徐森玉.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M].上海:中西书局,2012.
[7]单锦珩.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M].下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8]徐文堪.先父徐森玉二三事[M].汉石经斋文存附录.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
[9]徐有春.民国人物大辞典[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10]贷峻.李济传[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11]牟润孙.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M].汉石经斋文存.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242.
[12]以上三条题记均摘录于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M].734.
[1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M].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96.
[14]赵晓星.莫高窟第401窟初唐菩萨立像与《大通方广经》[J].敦煌研究,2010(5).
[15]冈部和雄,田中良昭编;辛如意译.中国佛教研究入门[M].台北:法鼓文化,2013.
[16]耕之.敦煌写经书法之特征简论[J].书法世界,2003(8).
[17]重庆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唐写本.
[18]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M]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
[19]大智度初品中菩萨释论[M]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
[20]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书店,2011.
华海燕女,1981年生。博士,馆员。研究方向:古文献学。
袁佳红1975年生,硕士。特藏文献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重庆地方史。
收稿日期:(2014-12-04;责编: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