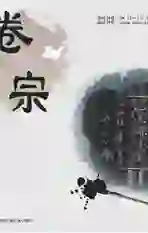狂欢理论视阈下的《檀香刑》
2015-05-12陆心怡
陆心怡
摘 要:《檀香刑》发表于2001年,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从小说问世以来,相关研究的论文有1300余篇。对《檀香刑》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檀香刑》的历史背景设定在1900年的“高密东北乡”,讲述了一起民间反殖民的斗争事件。小说以檀香刑这一酷刑为线索,将中国封建王权的残酷性与非人道性表现出来,成功的折射出专制权力赖以存活的黑色土壤和阴暗法则。
本文通过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分析《檀香刑》中的“审美与审丑”和“理性与非理性”,解读这一暴力刑罚背后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檀香刑;莫言;狂欢理论;悲悯情怀
1 对《檀香刑》的批判与赞扬
在《檀香刑》整部小说中,一共有六次关于行刑过程的细致描写,所用的酷刑一共有五种,其中包括斩首、腰斩、阎王闩、凌迟和檀香刑。每一场刑罚都让人印象深刻,而能被称的上是极致的莫过于小说结尾赵甲给孙丙施以的檀香刑。
徐兆武批评道:“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是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批评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的脚步走”。而李建军也说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他对暴力和酷刑等施虐过程的叙写,同样是缺乏克制、撙节和分寸感的,缺乏一种稳定而健康的心理支持。”余杰甚至将莫言等作家批判作对“传统文化中黑暗实力的皈依和对‘五四先驱者的人文主义立场的背叛”。
中国古代的酷刑与普通死刑相差甚远。酷刑被发明出来已不是为了单纯的处死犯人,更多的是“让观刑的群众受到心灵的震撼,从而收束恶念,不去犯罪”,并且供君王等统治阶级观赏,满足他们扭曲变态的心理。种种酷刑的存在,像是生长在中国旧社会的一颗恶性肿瘤,百姓已然意识到了它的危害,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陈规陋习,只要是有过先例的,都不能废除,不但不能废除,还要变本加厉”。莫言的笔杆,更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割下了这一深藏在中国古代旧社会的毒瘤,理智、客观并充满勇气的为读者展现其病理,剖析其病因。
莫言大可以选择在小说中忽略对刑罚的描写,这也并不会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作品也因此看起来更具有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但“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与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2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
2.1 狂欢理论的基本内容
巴赫金这样定义狂欢化的:“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个语言无法准确地译成文字地语言,更不用说译成抽象地概念语言。不过,它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文学地语言。狂欢式转化为文学地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地狂欢化。”
2.2 在狂欢中寻求二元统一
2.2.1审丑中的审美
巴赫金将审丑视作一种特殊的审美体系,即便是丑陋的怪诞之物,也是狂欢节必要的点缀物之一。“丑”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有着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因为第一,‘丑可彰显真实,张扬生命自由的本质;第二,‘丑可启善;第三,‘丑令世界精彩纷呈,绚烂多姿。”丑虽然属于非审美范围,但艺术家通过描绘丑来否定丑并表达对美的向往与憧憬,从这一角度看来,丑依然属于审美活动。因此,在巴赫金的审美视阈中,非审美的“丑”因为其生命里的张扬而升华为一种“美”的文化符号了。
2.2.2非理性下的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两者看似矛盾,但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被融合在了一起,共同透析着深刻的原始的生命哲学和人内心深处的狂欢精神。在这里,“非理性”表现在对感性生命的执着追求和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同时,这种狂欢又不是肤浅的感性游戏,它虽然保留着游戏的消遣与娱乐性能,然而又充溢着揭示、揭露、乃至抨击当下生存境况的历史功能。
3 狂欢视阈下的《檀香刑》
3.1 审美与审丑——极刑后的慈悲
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里面说过:“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就是一回事。”
罪恶、肮脏甚至血腥属于丑这一特殊审美领域,莫言在《檀香刑》中通过对血肉模糊场面、行刑场景的狂欢化描写,表现出他对暴力这一行为的否定,也是对中国封建王朝中种种陋习的反思,进而通过这种反思激起整个民族对历史的思考。无论是刽子手赵甲,封建统治者袁世凯,莫言通过对人性丑恶的深度刻画,表达出他对人心之美的憧憬。在这里,暴力之丑,人心之恶被升华成一种“美”的文化符号。因为“虽然狂欢未必总是破坏性的,但破坏的因素总是在哪里,它并非总是进步的或解放的,但进步与解放的潜能一直在场。”
美“是对现象的颂化和美化,因而是一种幻觉,是美的面纱”,而《檀香刑》掀开了这一面纱,揭示了隐藏在中国旧社会的毒瘤。这一种话语式的狂欢不是肤浅的感性与空白,也绝不是没有价值主题的无节制肆意描写,而是隐藏在酷刑背后的理性与悲悯,是一种残酷的慈悲。
3.2 非理性下的理性——生命意志的延续
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狂欢以其非理性中的理性精神,将理性与非理性统一在了一起,深刻地分析了人类生命本质地狂欢精神。这种“非理性”表现在对感性生命本质的追求,表现为“狂欢的感官效应”和“狂欢的自身形式”。
狂欢的感官效应是一种调动感官的力量,通过调动读者的听、嗅、看、等器官使人身临其境,受到感染和感触,达到发人深省的效果。六段惊心动魄的行刑场景,通过气味、声音、视觉刺激让人仿佛正在行刑场观看着一系列酷刑。这一种感官上的狂欢,更多的是唤起了读者对封建晚清王朝的反思,对存在了上千年封建习俗的讽刺与警醒。
而说到狂欢的自身形式,狂欢以其自身的疯狂、张扬、肆意等非理性的感性形式表达内心的希冀与渴望。表面虽然充满戏谑的意味,但体现尼采所谓的“生命哲学”。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赵甲矛盾的一生,为了讨口饭吃,成为了最残酷无情的刽子手,身份卑微却又替统治阶级行使着重要的生杀大权;孙眉娘在亲爹孙丙与情人钱丁之间徘徊的情感纠葛;孙丙满腔正气热血,却在最后惨遭檀香刑。小说中人物的矛盾、酸楚、无奈、冤屈,都无损于生命意志。正相反,外界的苦难刺激生命力的爆发,个体的痛苦与毁灭只是增加生命力的一种方式,它肯定了生命的永恒本质。莫言感性的狂欢化血腥虐杀描述背后是对人性以及封建旧社会的理性思考,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对永恒生命意志的致敬。在痛苦中有一种极强的生命意志魅力显现,任何文字上的道德追问与悲悯情怀在永恒的生命意志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她的身体已经皮肉无存,但她的脸还丝毫无损。只剩下最后的一刀了。师傅感动地看着她的惨白如血的鹅蛋脸,听到从她的胸腔深处,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读到咸丰年间一位被凌迟的美女这一段时,读者难免感到不适。过于血腥和暴力的场景被不间断被描写了十一页,钱雄飞是如何被凌迟,从第一刀到最后毙命的第五百刀被处死。带来感官刺激的抽象语言背后是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这一种感性是巴赫金所描述的带有蕴含着理性的感性。
4 结语
暴力刑法描写也好,人性丑恶刻画也罢,莫言的写作目的并不是流于表面的感性。这种感性既不是缺乏克制的语言狂欢,也不是流于表面的道德追问。他的感性是对血性个体生命的敬重、是对不朽生命意志的崇拜、是对封建晚清王朝历史的反思。莫言用语言所构建的乌托邦因素“不是为了抽象的思想,也不是为了内心体验,而是由整个人,完整的人,用思想、感情和肉体一起演出和体验的。”
本文通过分析巴赫金狂欢话语言,将审美与审丑、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统一应用在《檀香刑》之中,体会莫言书写残酷刑罚背后的慈悲与大爱。
《檀香刑》是莫言极具个人标签的一部小说,这种崇尚生命意志的个性与勇气是可以超越时代进而得以延续下去的。尽管在某一历史阶段,由于价值差异、审美差异,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不为大众接受和欣赏的分歧。但是莫言《檀香刑》敢于揭开历史伤疤的勇气、敢于反思历史的强大生命意志是可以冲破历史的局限,交给时间来审视的。
注释
徐兆武:极刑背后的空白——论《檀香刑》的主体和主题缺失,文艺争鸣,2011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文学自由谈,2001
余杰:在语言的乌托邦中迷失——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社会科学论坛,2004
莫言:《檀香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第143页
莫言:《檀香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第145页
赵云洁:酷虐刑难扶将倾之大厦——论莫言《檀香刑》的悲悯情怀,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
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译,三联书店,1988,第175页
王一芝,龚胜勇:《论“丑”的美学价值》,安康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约翰·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24页
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24页
宋春香: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
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83页
莫言:《檀香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第147页
巴赫金著:《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57页
参考文献
[1]李敬泽:伟大压不垮《檀香刑》[J],北京晨报,2001
[2]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J],文学自由谈,2001
[3]莫言:《檀香刑》[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4]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6卷本)[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宋春香: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08
[6]吴丽丹:论莫言小说《檀香刑》中的生存与人性[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7]王学谦:残酷的慈悲——莫言《檀香刑》的存在原罪与悲悯情怀[J],当代作家评论,2014
[8]徐兆武:极刑背后的空白——论《檀香刑》的主体和主题缺失[J],文艺争鸣,2011
[9]夏忠宪著:《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余杰:在语言的乌托邦中迷失——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J],社会科学论坛,2004
[11]赵云洁: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艺术特色研究[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
[12]王一芝,龚胜勇:《论“丑”的美学价值》[J],安康学院学报,2007
[13]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14] [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9
[15]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4
[16]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钰,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