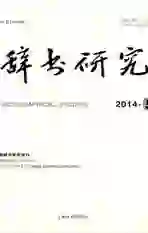《中国惯用语大辞典》的编纂特色
2015-05-11孟祥英
孟祥英
摘 要 《中国惯用语大辞典》于2011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文章认为,该辞典的主要特色有:从收语来看,收录了大量“非三字格”惯用语,所收惯用语均为描述性语言单位;从立目来看,以结构完整、表义明晰的形式立目,并恰当处理了异形惯用语的立目问题;从释义来看,坚持描述性原则,释义准确简明。
关键词 《中国惯用语大辞典》 收语 立目 释义
由温端政、吴建生主编的《中国惯用语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于2011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笔者对该辞典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与其他同类辞典进行了比较,如《汉语惯用语词典》(施宝义、姜林森、潘玉江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实用惯用语词典》(黎庶、艾英、伊介编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中国惯用语》(陈光磊编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惯用语小辞典》(陆元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常用惯用语词典》(王德春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现代汉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规范词典》(李行健主编,华语教学出版社,2011)等等。我们认为,《大辞典》在语汇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收语、立目、释义等方面都体现出较高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一、从收语来看,收录了大量“非三字格”的惯用语,所收惯用语均为描述性语言单位
正确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指导是辞书编纂的前提。21世纪以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温端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语词分立”的主张,建立了“汉语语汇学”这一与“汉语词汇学”并列的汉语分支学科。2005年出版的《汉语语汇学》是其语汇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明确揭示了语汇的性质和范围,对于语汇提出了合理的分类标准。
惯用语与成语、谚语、歇后语等并列,均属“语汇”范畴。因此,编纂一部“惯用语辞典”,首要的一点就是确立收录惯用语的标准。然而,关于什么是惯用语,近几十年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传统观点认为,惯用语“在语言结构上,音节(字数)都很短,多数是三个音节的动宾结构词组”(马国凡,高歌东 1982:3),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此后很多学者的著作及一些汉语类教材在编写惯用语部分时都采用此说。
80年代末,孙维张(1989:199)否定了“唯三字格”论,认为汉语惯用语“从音节构成上看,有多有少。少则三字,多则七字、八字不等,甚至有十个字的”。进入21世纪,温端政(2005:235)立足于汉语语汇系统这一整体,进一步把惯用语定义为“非‘二二相承的描述语”,这一表述言简意赅,准确到位,从形式和内容上对惯用语进行了规定,能够很好地把惯用语与其他的语汇单位区分开来。吴建生(2007)也对惯用语进行了专门探讨,并指出:“把惯用语纳入‘语的范畴, 在承认其词组性、相对固定性以及口语性的基础上, 重点强调其形式上的非‘二二相承和语义上的‘描述性,在实践上比较可行。”以上观点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于惯用语辞典的编写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大辞典》即在坚持以上理念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其对惯用语的界定清晰,收语合理。与其他惯用语辞典比较,《大辞典》在收语上有如下鲜明特色:
(一)从音节上来看,收录了大量“非三字格”的惯用语
以往的惯用语辞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所收惯用语多数为三字格,三字格以上的收得很少,如《中国惯用语》《常用惯用语词典》等。而《大辞典》突破了这一限制,不以音节数作为判定惯用语的标准,所收的“非三字格”的惯用语远远多于三字格的。如A部收三字格惯用语18个,非三字格38个;B部收三字格惯用语112个,非三字格522个,如“挨当头棒、鼻子翘上天、矮子里选将军、搬倒葫芦洒了油、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把别人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等等,字数不等。也就是说,判定一个语言单位是否为惯用语,关键不看其字数的多寡,而应看其意义特点和结构特点。
(二)从语义上看,所收惯用语均为描述性语言单位
有些惯用语辞典在收录惯用语时,不区分概念性语言单位和描述性语言单位,二者混收,如“鸿门宴、空城计、小报告、眼中钉、迷魂汤”等等就被某些惯用语辞典收释。实际上,它们均为概念性语言单位,《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是把它们作为名词来标注的,说明它们被视作词,与“惯用语”是不同级的语言单位,被收入“语典”是不合适的。《大辞典》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所收惯用语均为描述性语言单位。从结构上来说,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的短语多是对事物或现象进行形象地叙述或描写,语义上具有描述性特点;而定中结构的语言单位多用来指称具体的事物或现象,具有概念性。因此,像下面的语言单位,《大辞典》只收后者而不收前者。
攻坚战——打攻坚战 免战牌——挂免战牌 对台戏——唱对台戏
独木桥——过独木桥 夹生饭——做夹生饭 小动作——搞小动作
阳关道——走阳关道 烟幕弹——放烟幕弹 西洋景——看西洋景
高帽子——戴高帽子 冷板凳——坐冷板凳 十字架——背十字架
老虎屁股——老虎屁股摸不得 狐狸尾巴——狐狸尾巴露出来
硬骨头——骨头硬 软骨头——骨头软前四行中,破折号之前的都是定中结构的语言单位,应该把它们当成词来看待,《现汉》把它们标注为名词;而破折号之后的都是动宾结构的短语,以上短语中的“唱对台戏、戴高帽子、坐冷板凳”等为《现汉》所收,未标注词性,显然也是把它们当成惯用语来看待的。第五、六行中,破折号之前的是定中结构的语言单位,是概念性的词语;破折号之后的是主谓结构的短语,是描述性的。
二、从立目来看,以结构完整、表义明晰的形式立目,并恰当处理了异形惯用语的立目问题
在明确了惯用语的性质和范围,确定好要收录的对象以后, 以什么形式立目是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大辞典》以结构完整、表义明晰的形式立目,并很好地处理了异形惯用语的立目问题。
(一)以结构完整、表义明晰的形式立目。如:
A组:
闭门羹 (一)泛指拒绝客人进门,不与相见。多和“吃”字连用。(二)喻指拒绝别人的要求或意见。(施宝义等《汉语惯用语词典》)
闭门羹 羹:指带汁的肉。指主人闭门拒绝接待来访的人。(李行健《现代汉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规范词典》)
吃闭门羹 比喻被人拒之门外。(《大辞典》)
B组:
风马牛 《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不相及也。”风,放逸、走失。及,到。本指齐、楚相距很远,即使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一说兽类相诱叫“风”,马牛不同类,不致相诱。遂喻指事物之间彼此毫不相干。(陈光磊《中国惯用语》)
风马牛不相及 指马和牛不同种,雌雄不能相诱;一说两地相距甚远,马牛不会跑到对方的境内。比喻彼此毫不相干。语见《左传·僖公四年》……(《大辞典》)
A组是以“闭门羹”立目好呢,还是以“吃闭门羹”立目好?我们认为,以后者为佳。理由如下:首先,从结构上看,“闭门羹”是定中结构的词,是一个概念性的语言单位;“吃闭门羹”是动宾关系的短语,是一个描述性的语言单位,惯用语辞典理当收录描述性的语言单位。其次,《现汉》既收了“闭门羹”也收了“吃闭门羹”,将前者标为名词,作为副条;而后者未标注词性,显然是把“吃闭门羹”当成惯用语来看待的,且作为主条。最后,查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以下简称“CCL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输入“闭门羹”,在所得的123条语料中,“闭门羹”绝大多数都是与动词“吃”组配,常见的就是“吃闭门羹”这一基本形式,当然还有其他灵活的用法,如“吃了一个闭门羹”“遭到了闭门羹”等,但较少见,属于一种临时搭配。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采用“吃闭门羹”这一结构完整的形式,语义明晰,更易于读者理解和运用。
再看B组,在CCL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输入“风马牛”,得到215条语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风马牛不相及”这一六字格形式出现,可见它更具有使用上的普遍性,而且与三字格形式“风马牛”相比,六字格形式完整,语义表达也更充分,便于读者把握。《大辞典》取“风马牛不相及”作为主条来立目是合理的。
其他的如:迷魂汤—喝/灌迷魂汤、鸿门宴—摆/唱鸿门宴、小算盘—拨/打小算盘、小聪明—耍/玩弄小聪明、龙门阵—摆龙门阵、白日梦—做白日梦、长舌头—扯长舌头、掉馅饼—天上掉馅饼,《大辞典》均是以后者立目,显示出较高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广泛收录惯用语的异形形式,并做富有创意的处理
异形惯用语指的是意义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一类惯用语,如“爱面子、爱脸面、爱情面”,均有“怕损害自己的体面,被人瞧不起”的意思,但它们写法不同,这体现出惯用语结构上的相对灵活性特点。与其他惯用语辞典相比,《大辞典》在处理异形惯用语时是富有创新性和科学性的。该辞典收古今惯用语约1.1万条,其中主条约8700条,副条约2300条。在“凡例”部分就收条的具体方法做了说明:主条外加【 】;副条外加[ ],按下列不同类型放在主条下面:
(1)“早作”条。古今同义、异形的,以今语作为主条,古语作为副条,按“早作”处理。
(2)“也作”条。凡语形、语义与主条基本相同,只是某些结构成分略有区别的,按“也作”处理。
(3)“增作”条。凡在使用中增加了一个部分的,按“增作”处理。
(4)“减作”条。凡在使用中可以只出现一部分的,按“减作”处理。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大辞典》对异形惯用语的处理有两个主要标准:
第一,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即立足于现代汉语层面,以今语作为主条,古语作为副条。“早作”条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一惯用语在出现时的最初形式,了解其源头。如对“半斤对八两”这一惯用语进行释义后做说明:
早作[半斤逢八两]〔例〕公公前日不识人,山鸡怎逐凤凰群?又没家舍又身贫。却不如马力共牛筋,那些个半斤逢八两门,傍人恁般行径。(明·无名氏《白兔记》一〇出)
“半斤逢八两”出现在以上戏剧情境中,言辞文雅,文学味浓。而在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半斤对八两”通俗易懂,口语色彩突出。通过“早作”条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对读者全面深刻地把握这一惯用语大有裨益。
第二,以使用频率为标准。即以使用频率高的为主条, 使用频率低的为副条。“也作”条、“增作”条和“减作”条都是副条,相比主条来说,它们使用频率低一些,以副条的形式出现,其目的在于:让读者把握某一个惯用语的多种形式,方便查考和运用。如把“矮半截”立为主条,“矮二寸、矮一半、矮三分、矮几分、矮三辈儿、矮一头、矮几寸、矮一截”等八种形式按“也作”条处理。查考CCL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矮半截”出现26次,使用频率是最高的,而“矮一头”出现12次,“矮一截”10次,“矮三分”9次,“矮一半”2次,“矮几分”1次,“矮二寸、矮三辈儿、矮几寸”均为0次。显然,把“矮半截”立为主条是科学合理的。
三、从释义来看,坚持描述性原则,释义准确简明
释义是语典编纂的重点和难点。《大辞典》在释义时坚持描述性原则,释义准确简明,并且正确地选用了提示词。
(一)坚持描述性原则
语汇学理论认为,“根据语的叙述性特征,以叙述方式为标准,把语分为三种类型:表述语、描述语和引述语”(温端政 2005:60)。其中,谚语具有知识性,属于表述语;惯用语重在描述人或事物的形态和状态,描述行为动作的性状,属于描述语;歇后语由引子和注释性叙述组成,属于引述语。而成语既有表述性的,也有描述性的。《大辞典》对惯用语的释义坚持描述性原则。如:
抱粗腿 比喻攀附、依靠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例〕也还不止于牵扯丈夫,还要把那家中使数的人都说他欺心,胆大,抱粗腿,惯炎凉。(《醒世姻缘传》四四回)
开场锣鼓打炮戏 开场锣鼓:戏曲正式演出前演奏的打击乐。打炮戏:打头炮的第一场戏。比喻工作开始前营造气氛和做第一件事。〔例〕“唱野台子戏挑大梁,比在大戏院里跑龙套,更有用武之地。”郓兰渚笑问道,“匹夫,开场锣鼓打炮戏,你想怎么唱。”(刘绍棠《十步香草》三六)
“抱粗腿、开场锣鼓打炮戏”是惯用语,都是对人的行为、动作进行描述,其释义具有描述性特点。
(二)释义准确简明
《大辞典》坚持“从语料中来,到语料中去”的原则,对惯用语的释义既准确到位,又简洁明了。试比较:
A组:
不蒸馒头蒸口气 ①喻指条件再困难也要争气。褒义。〔例〕就这样干下去吧!不蒸馒头蒸口气,给咱们穷人,给咱们妇女争口气。(浩然《艳阳天》)②喻指死要面子。贬义。〔例〕曹师傅说,做人要学会“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不蒸馒头蒸口气”,使性斗气。(《青年时报》2005年10月12日)(王德春《常用惯用语词典》)
不蒸馒头争口气 “蒸”谐“争”。比喻要发愤图强,做出个样子让别人看。〔例〕跳嫂吵架似地喊嚷道,“你得不蒸馒头争口气,别叫人家骂你是狗肉上不了正席。”(刘绍棠《京门脸子》四章七)(《大辞典》)
B组:
挂头牌 原指戏院里名字写在广告最前面的重要演员。比喻头号的数得着的人。(陈光磊《中国惯用语》)
挂头牌 原指在戏剧演出时,名字写在广告最前面的主要演员。比喻头一号的,数得着的人。(施宝义等《汉语惯用语词典》)
挂头牌 头牌:旧时演戏时,演员的名字写在牌子上挂出来,挂在最前面的牌子叫头牌。比喻担当重任。(《大辞典》)
C组:
吃大户 穷人集结起来强迫有钱人供饭或拿出财物。引申为依靠富足人家或集体、国家过活。(黎庶等《实用惯用语词典》)
吃大户 是农民一种自发的斗争形式。在旧社会里,遇到荒年,农民团结在一起到地主富豪家去吃饭或夺取粮食。(施宝义等《汉语惯用语词典》)
吃大户 原指旧时灾荒年饥民们到有钱人家去夺取食物。现指到有钱的单位或人家去吃喝或索取财物。(《大辞典》)
A组“不蒸馒头蒸口气”和“不蒸馒头争口气”为异形惯用语,就使用频率来说,后者高于前者;就语义来说,“争气”是这个惯用语表达的核心,前面用“不蒸馒头”这一形象化、生活化的说法表达出后面要“争口气”的意思,表义生动诙谐,比用“蒸口气”表义更为显豁。所以,我们认为,以“不蒸馒头争口气”为主条是比较合理的。从释义上看,前一部辞典认为这一惯用语有两个义项,其中第二个义项为“喻指死要面子。贬义”,考察CCL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我们发现:这一义项并不常见,只在个别语言环境中出现,属于一种临时用法,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常用的义项来处理,显然不合适。
B组从形式上看,“挂头牌”是动宾结构的短语,对其释义应是描述性的。而前两部辞典对其释义则是概念性的,“原指戏院里名字写在广告最前面的重要演员。比喻头号的数得着的人”,这是“头牌”的意思,而不是“挂头牌”的意思。《大辞典》对“头牌”进行了重点解释后,指出“挂头牌”的整体义是“比喻担当重任”是比较合理的。
C组中,《大辞典》对“吃大户”的释义中使用了“原指”“现指”这样的提示语,展示出这一惯用语语义上的发展变化,符合实际情况,体现了释义的时代性。而《实用惯用语词典》的释义没有把其意义的发展变化体现出来,不够准确;《汉语惯用语词典》只指出了“吃大户”在旧时代的意义,而没有涉及其在新时代的引申义,释义不够全面,而且表述不够简练。
(三)正确选用了提示词
在《大辞典》中,正确选用了“指、形容、比喻”等提示词,提高了释义的准确性和严密性。“指”多表示引申义,指明词义的范围;“形容”重在描述人或事物的性质或状态,凸显人或事物的某些特点;“比喻”是用一种或几种本质不同而又有相似点的彼事物来比拟此事物。在对惯用语进行释义时,有些辞典存在着提示词使用混乱的现象, 比较普遍的倾向是滥用“比喻”或“喻指”。尽管比喻是产生惯用语的主要途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惯用语都来源于比喻。试比较:
A组:
骨头硬 喻指意志坚定。〔例〕我们一直因而不打不是因为她骨头硬而是怕你心眼窄,不信把她叫来你看着。(王朔《许爷》)(王德春《常用惯用语词典》)
骨头硬 比喻刚强有骨气。义同“硬骨头”。(陈光磊《中国惯用语》)
骨头硬 形容人意志坚强,经得住磨难。〔例〕王柬芝在鬼子面前做假,不光掩住了他的罪行,村上好多人还夸他骨头硬。(冯德英《苦菜花》一二章)(《大辞典》)
B组:
创牌子 喻指产品通过高品质、良好的服务等优势赢得好的声誉,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例〕“奥索卡”刚创牌子时,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在中国登山协会的协助下,现在已发展壮大为一个国内知名品牌企业。(《中国体育报》2004年1月6日)(王德春《常用惯用语词典》)
创牌子 指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或单位的信誉,增加其知名度。〔例〕赵刚透露,之所以如此匆忙地前来北京注册“刘老根”商标,实在是为了保护好赵本山自己创出的牌子。(张漪《赵本山批量注册“刘老根”》)(《大辞典》)
A组中,前两部辞典对“骨头硬”的释义使用了“喻指”“比喻”这样的提示词,相关研究表明,“比喻”或“喻指”是适用于指事物的,而“骨头硬”是用形象化的手法来描绘人的特点的,宜用“形容”。B组中,对“创牌子”的释义,前一部辞典用了“喻指”,细致分析,我们认为“创牌子”是没有比喻义而只有引申义的,用“指”合适。
参考文献
1.马国凡, 高歌东.惯用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
2.孙维张.汉语熟语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3.温端政.汉语语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温端政, 吴建生.中国惯用语大辞典.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5.吴建生.惯用语的界定及惯用语词典的收目.语文研究,2007(4).
(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 山东 250013)
(责任编辑 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