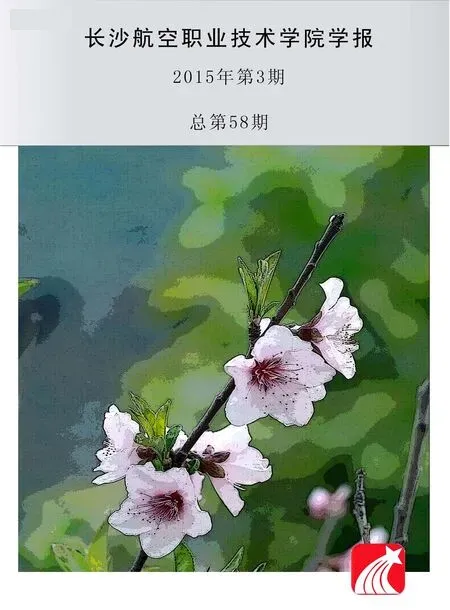从传统民俗看文化传承与文化记忆的建构问题
——以泉州元宵节庆为例
2015-05-06李双幼
李双幼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福建 泉州 362000)
从传统民俗看文化传承与文化记忆的建构问题
——以泉州元宵节庆为例
李双幼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福建 泉州 362000)
泉州元宵节庆历时久远、内容丰富,从时间维度和组织化情景两方面来考察,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特有的节日传统使其构成了一种公共文化空间,进而发挥了构建身份认同、传承文化传统、加固乃至重构文化记忆的功能。在这其中,元宵的节俗内容、节日意象和文化记忆的主导主体均发生了变迁。
元宵节庆;集体;沟通;文化记忆
在大脑和神经学领域的研究中,个人记忆并非原封不动地长期保存在人的大脑中,人的回忆是受主观经历、客观记录的事实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再现和建构过去的过程[1]。个人记忆尚且如此,具有广泛的时间维度和社会属性的文化记忆更体现出重塑的特征。德国学者夫妇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厘清了各种记忆形式的界定后,在文化社会学的框架下概括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的基本过程,并将文化记忆定义为“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御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2]。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参照过去并根据当下的需要来塑造文化本身,塑造的过程就存在着主体的问题,即文化记忆的过程受占主导地位的主体因素所左右。因此,描述历史、开展记忆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框架下进行,比如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就是通过学校教育、社会仪式、公共媒介等渠道进行强化的。泉州的元宵节庆因其特有的仪式性和集体的参与性,成为一种加深集体记忆、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有效实践。
一、元宵节庆的集体行为增加了记忆的沟通
不同的习俗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也寄托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愿景,承载的却是生活其中的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记忆的沟通和文化的传承有赖于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吸引群体成员在场并亲身参与某些重复性行为的元宵节庆,以其公共的时间、空间以及特有的节日意象,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记忆的场。置身于元宵节庆及其相关仪式氛围中的人们,超越了日常循环的生活秩序,找到了所谓的历史意识,完成了文化记忆。
本课题设置的调查问卷共分19个问题,分别对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对元宵节的认知、对元宵节庆活动的参与和评价等方面进行调查。在回答“以下哪些因素更能影响您是否参加元宵节活动”时,娱乐性和重温过节的记忆均占23%以上,而是否空闲和是否有伴分别以17.65%和16.93%位列第三、第四,集体的沟通和交流成为必不可少的行为,见图1。

图1 是否参加元宵节活动的影响因素调查
上元预示着新年接近尾声,新的循环即将开始,人们在此时节,通过展示美食、才艺和情感,展现民间的生活形态,使个人情感在传递、沟通和相互影响中引起集体的共鸣,使信仰需求和文化情怀得到正常的抒发,从而具有一定的心理和行为渗透性,既加深了记忆的沟通,又发挥了文化传承、情感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社会效益。
从巴尔金的狂欢理论看,节日与日常生活构成了批判的节律化关系,节日的狂欢式生活与日常生活相交替,构成了人在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节奏。节日狂欢将人从受限定的时空范围解放出来,使人暂时摆脱日常生活制度中秩序、教条、等级和禁忌等方面的约束,获得了释放本性感官生命力的机会,从而表现了人生的节律化,凸显了人的存在感。这也是世界各国不厌其烦地设立各种节日名目的原因之一。元宵节里,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聚在一起赏灯、游艺、看戏,往昔生活的艰辛、当下幸福的体验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在集体活动的沟通和交流中更加深刻,各种游艺展演也因为再现了丰富的民间生活场景而深受民众喜爱。火鼎公婆抬着火鼎三进三退,打诨笑谑,斗篮两侧贴着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的红联纸,体现了安平吉利的节日意味;骑驴子中的老夫牵着老太婆骑着的“驴”,假装因为彩礼的事带着女儿和“憨女婿”要到男方家评理,举手投足惟妙惟肖;装阁中“阁旦”经常扮演成“八仙”等民间传说人物,弄龙舞、台(刀旁)狮和宋江阵等综合了舞蹈和武艺,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而车鼓阵中的乐器都为闽南人所熟悉。热闹的表演、愉悦的场景气氛,冲散了日常生活的平淡感,使大众百姓获得了精神上的的欢欣和情感的交流,从而实现个人记忆与文化记忆的融合。
二、文化记忆的主导主体发生了变迁
向神明祈求农业生产丰收和子孙繁衍原本是元宵节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但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娱乐逐渐代替宗教占据了主体地位,民众为适应现代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情感需求、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自发地对节俗进行了调试。比如孝敬“代人”、祭祀“棕蓑娘”因为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脱节,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有些仪式的象征意义已从求子、多子多孙转换到期盼小孩健康、聪明,“拔拔灯”习俗也已从祈求河运平安、年丰丁旺转向共叙亲情、追求人生幸福。同样的,“妆人”游行是在迎神时为了娱神并向神明祈求一年的幸福和健康而进行的仪式性表演,这种仪式性表演也存在着一个从娱神到娱人的变迁过程,即转变为现今的群众性文娱表演,它的存在意义似乎也在于丰富群众生活、增添节日气氛。
如果说在古代传统社会,文化记忆的主导主体是民间的神明系统和乡绅阶层,现在的主导主体则转移到官方的行政机构了。从迎神巡游到文娱踩街的过程,集中体现了文化记忆主导主体的变迁。“巡游边界”不免各方力量暗中较量与妥协,实际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基层政权区位体系的组织运作格局。农村中,“迎灯”队伍在巡游前,由公众协议祖厝祭祀点的顺序以及整个巡游路线;府城内,迎神队伍的巡游路线,则由各铺份综合惯例和问卜情况而商定,有的“借道”有的“还道”,互相标明势力范围和亲善不和;现今的巡游则蜕化为文艺展演队伍的踩街,队伍成员由各街道组成,所走路线则是综合传统、主办方和负责安保工作的公安部门的意见而定。
泉州市区元宵灯会的举办经费动辄以百万计,如果没有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支撑,没有哪个机构敢承担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每年元宵前,均由市政府专门下文对时间安排、灯会地点、花灯数量等做出部署,并对有关协办单位提出具体工作要求,确保交通、消防、卫生等安全和医疗保障措施一一做足。而市政府每年大费周章地张罗元宵灯会,除了出于遵循传统做法和传播传承“非遗”文化的考虑外,更意在借机宣传各类城市建设主题,比如2002-2009年连续七届的海丝文化节、2010和2013的闽南文化节、2014年的东亚文化之都开幕式等,集中在正月十五前后几天举办文艺汇演、南音大会唱、摄影展览、泉商大会、学术论坛、闽南语歌赛、台湾特色庙会等各类特色活动,取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关注度,参与的群众有逐年增多之势。2015年的元宵灯会由于受上海跨年庆新踩踏事件的影响,市政府决定降低举办规格和规模,主办单位由地市级转为区级行政单位,举办地点分散在城区三个地方,举办经费也相对缩减。一位在文化部门常年参与组织元宵灯会的工作人员,直接将灯会定义为“政府组织的大型文化活动”,充分说明了行政机构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前几年(实际上)变成说我们包办,为什么说包办呢,你看选址我们就圈定在这个地方,(所以)选址是我们包办的,制作也是我们包办的。刚才说过,任务发下去,每个县(市、区)要三十盏你就要弄三十盏,每个企事业单位、市直单位,机关一盏、企业两盏,比如银行两盏,这都是用指令性的。连挂灯都是艺术馆组织的,请干部职工去挂,撤下来也是,变成高度组织性。只有参观(不是),其实参观也有点组织(的意味),比如有事先公布路线、交通管制,发信息(告诉)车子停在哪里,还有公交公司免费运送来观灯,体现了计划经济的(特色),说不清啦。其实现在我们不把它列入民俗的范畴,我们还是列入政府组织的大型文化活动这个范畴,如果用这个来理解就豁然开朗了。”(注:括号内容为笔者根据谈话内容补充)
而泉澎两地天后宫的“乞龟祈福”活动,脱离不了闽台深厚渊源和两岸融洽关系的考略,明显是在政府的允许下愈演愈烈,充分体现了行政机构在重塑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主导意志;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研究会等社团对民俗大舞台的支持、以“歌吹漫步”的名义坚守文娱踩街,则体现了社会组织在这一主导格局中日渐显出张力。
三、文化认同脱离不了地方性场景
文化记忆的内容是某一群特定文化主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对于集体文化认同来说,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一样,对其生存非常重要”[3]。仪式、实物和传统等形式提供了文化记忆的互动和空间两种媒介载体,泉州元宵节庆活动中的祭祖祀神、有关灯的活动、歌吹漫步等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延续了传统的内涵和形式,主办机构又在活动中着意充实、扩展在地文化元素,民众对此十分受用,并赖以自觉地树立一种自我形象和独特意识,从而形成群体和文化的认同。
据老人回忆,“文革”后至20世纪90年代元宵灯会都在开元寺举办,虽然展览的花灯不多,路边也没有什么小吃美食招徕客人,但大家每到元宵还是习惯性地前往西街“人看人”,偶有的火鼎公婆、踩高跷、骑驴子更是满足了人们看表演的兴致,如此热闹一番后大家才尽兴而归。元宵过节的气氛十分浓烈,乃至在“文革”期间小型的灯会仍然存在,只是民俗表演因为既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下的生产、生活需要,更与反封资修的革命政策相背离而取消,直到改革开放后,得以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复出。改革开放后的元宵灯展区经历了几次变迁,从开元寺,到文化宫,到府文庙、后城街、威远楼,到新门街。
在“如果在以下几个地方设元宵灯会,哪个展区您比较喜欢去”的选项中(见图2),文化宫、后城的响应占24.94%,开元寺、承天寺占22.80%,府文庙17.34%,新门街占12.83%,而侨乡体育馆仅占7.36%,威远楼6.41%,还有8.314%选择了其他。

图2 元宵灯会举办地点受欢迎程度调查
而在回答“您比较喜欢以上选择的展区灯会主要是考虑什么原因”时,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和花灯比较好看的响应分别以33.87%和22.27%成为最主要的两大原因,其次是交通便利17.40%、人多比较热闹16.01%。

图3 选择灯会展区的原因调查
综合分析以上两个问题的选择情况,文化宫、后城、开元寺、承天寺均举办过元宵灯会,但由于考虑到人流的安全,后来挪到府文庙举行,后来出于同样的考虑,从2012年起挪到相对开放的新门街举办。在主办单位看来,2014年新门街的元宵灯会无论从电力隐患、人群分流、场地容量、活动内容等方面来看,是历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内涵最丰、影响最大也最成功的一次,不出意外的话以后也将固定在这里举办。但显然民众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更喜欢到古色古香的闽南传统建筑空间里观赏花灯,在他们看来那里的传统文化氛围更加浓厚,观赏花灯更加应景。“重构过去的活动得以发生,道德感情必须具有柔韧性,易于变化”[4]。越是传统深厚的社会,文化的特质越稳定,越容易对重构产生抵制,建构记忆和文化只能在在地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认同离不开地方性场景。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文化记忆的理论视角来考察传承久远、盛演不衰的泉州元宵节庆活动,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特有的节日传统使其构成了一种公共文化空间,进而发挥了构建身份认同、传承文化传统、加固乃至重构文化记忆的作用。在这其中,文化记忆的主导主体从以往的神明系统和乡绅阶层过渡到现今的政府行政机构,而发挥传统节庆活动的文化记忆功能,离不开传统文化元素和地方性场景。
[1] 陈新,彭刚 编.历史与思想(第1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2]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 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 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英]安东尼·D·史密斯 著.龚维斌,良警宇 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 [美]马克·D·雅各布斯,南希·韦斯·汉拉思 著.刘佳林 译.文化社会学指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编校:龚添妙]
A Study 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Memory's Construction from Traditional Folklore
LI Shuangyou
QuanzhouPartySchool,QuanzhouFujian362000)
Quanzhou's Lantern Festival last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rich contents. It forms a public cultural space by the public timeliness and extensity, and the peculiar festival tradition. Therefore, it plays a part in building identity, inheriting cultural tradition, and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memory. In this course, the contents and imagery of the festival folklore, the dominant subject of cultural memory have changed.
the Lantern Festival;community;communication;cultural memory
2015-06-29
李双幼(1981- ),女,福建泉州人,讲师,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闽南历史与文化研究。
本文为2014年泉州市社科规划课题项目“文化记忆视域下的泉州元宵节庆”(编号:2014E14)阶段性研究成果。
G122
A
1671-9654(2015)03-07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