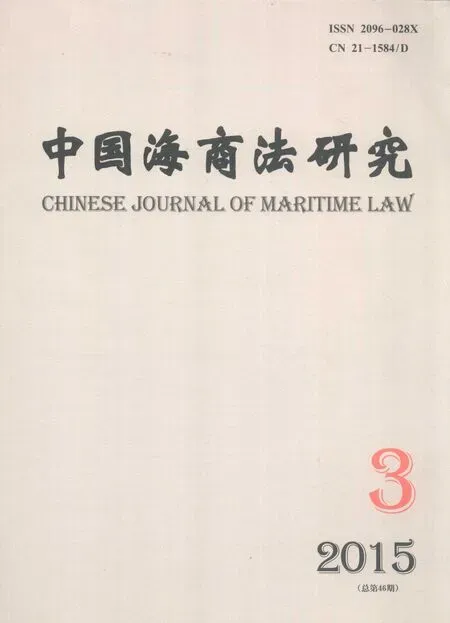新《东京公约》下的国际航空安全立法趋势
——兼论其对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与对策
2015-05-06俞世峰
俞世峰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620)
新《东京公约》下的国际航空安全立法趋势
——兼论其对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与对策
俞世峰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620)
2014年3月至4月间,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参加了修改1963年《东京公约》的外交会议,会后形成的立法成果就是该公约的议定书。其新增了管辖权种类、机上安保员等的具体法律制度,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航空安全立法的新“保护主义”趋势。航空作为自由贸易区航运建设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其自身的运营安全性一直处在首要位置。自由贸易区的航空安全立法需准确定位存在的法律问题,并找到有效的法律对策,则应结合负面清单制,分清机上人员的权限,妥善处理管辖权冲突,以此来应对自由贸易区法治建设的新要求。
机上安保员;机长;管辖权;自由贸易区
一、2014年《东京公约》(简称《公约》)①全称为《关于在航空器内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该公约于1963年9月14日在日本东京签署议定书的法律动因
2014年4月7日,国际民航组织(简称ICAO)在其官网上刊登了一则新闻通讯,[1]将修改1963年《公约》的最新成果,即修改议定书予以公布,并鼓励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对该文件进行签署与批准。
这标志着由100个ICAO成员国以及9个国际组织与机构派遣422名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初步共识,在会上签署了《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议定书》主要力图解决目前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中不断出现的新安全问题,即日益严重的航空器内暴力事件和不循规行为(unruly behavior),这些行为极大地影响了航空器内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出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议定书》着眼于两大内容进行了集中修订,其一是管辖国条款;其二是机上安保员(In-flight Security Officer,简称IFSO)的法律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9月至10月召开的ICAO第38届大会上所讨论的《议定书草案》(简称《草案》)对机上安保员问题提出了两种备选条文,第一备选条文是当出现航空器内犯罪时,赋予机上安保员和机长相同的权力;第二备选条文是依然保留了机长在出现航空器内犯罪或可能出现航空器内犯罪时的至高权力,其可以请求或者授权其他机组成员予以协助。最终《议定书》采用了后一种备选条文,也就是否决了第一种备选条文,反对赋予机上安保员以机长的广泛权力,该法律文件认为二者的法律地位显然是不同的。ICAO理事会的理事长,早在关于不循规旅客及执行《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法律工作的阶段性报告①参见A/38-WP/49,11/07/13,LE/1,Appendix。中,就曾指出“通过扩大对机上安保员的法律承认和保护,来提升全球航空安全条款,最大程度地增强ICAO成员国扩大其管辖相关犯罪的能力,将管辖权延伸至经营人所在国以及降落地国。”目前从ICAO的官方语境上来看,大会的最新成果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ICAO法律委员会指定的法律专家,在历经长时间的协商和研究后,向大会提交的最后《草案》中,出现了不少有待商榷的法律问题,不过在《议定书》的最后文件中,还是没有采纳《草案》中的某些瑕疵条款,避免了出现某些低级的“法律硬伤”,从而使得《议定书》在某些修订内容上的表达还是比较清晰合理的。
笔者将重新审视《议定书》与《草案》之间的联系,并且将对管辖权条款、机上安保员的法律地位以及外交大会上所普遍接受的处置方式做详尽的法律剖析,并对中国如何应对新的《议定书》给出自己的建议。
二、《草案》及《议定书》中的法律问题
(一)“修订”说还是“补充”说?
外交大会的一个重点就是将最优先、最重要的修订内容,以合理的法律措辞和法律观点,用议定书的形式固定下来。经过审慎考虑和激烈辩论,最终摒弃了《草案》对于第1条的建议。通过比较两个文件,可以发现《草案》采取的是对1963年《公约》进行“补充”的做法,而《议定书》采取的则是对1963年《公约》进行“修订”的做法。
分别在《公约》和《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一定会将这两个法律文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解读和阐释。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在互相发生法律关系并签署调整各自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文件时,其形式主要有条约、公约、协定、议定书、换文等。《公约》和《议定书》是“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②参见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1)(a)条。。在缔结国际文件时,必须满足四个要素,即国际法主体具备了与其他国际法主体在国际法下签署协议的资格;在缔约时,当事国存在适用国际法原则的意图;当事国之间存在着意思一致;当事国必须具有在其中间创设国家法义务的意图。[2]
《草案》中所用“补充”一词说明对《公约》的内容仅是进行了增加,而非“修订”。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2款的规定,修改《公约》的议定书被视作一个独立的条约,如果从“补充”的角度来看,这种独立性会受到很大的质疑。关键是,《议定书》中对很多法律条款的变动完全取代了原《公约》的规定,这从ICAO最后公布的综合案文可以得到印证。ICAO整合两个法律文件,从而方便了同时签署两份文件的当事国。
纵观目前的国际公约、条约体系,属于“补充性”条约的法律文件是非常少见的。例如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国际公约》与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后者对前者进行的就是“补充”,而非“修订”,议定书对公约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扩充,两份法律文件的实体条款间不存在互相冲突,[3]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并且该议定书的第1条第3款规定了“本议定书应由各缔约国执行,不受任何地理上的限制,已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亦应在本议定书下适用。”这一规定表明了即使没有国内批准或签署行为,缔约国将毫无例外地同时适用这两份文件。
相比之下,2014年《议定书》的签署行为直接决定了是否具有对缔约国的适用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1条第4款规定“修正条约之协定对已为条约当事国而未成为该协定当事国之国家无拘束力”,如果采用《草案》中“补充”说,则会直接违反了国际条约法的基本规则,而“修正”说则符合现今国际法基本准则,最后大会所接受的“修正”说也占据了主导地位,避免了犯下法律上的低级错误。
(二)“航空器内”涵义的忽略
《草案》第2条对机上安保员、经营人所在国以及登记国这三者总结出了定义,但在《议定书》中却没有再对其进行定义。《议定书》第2条取代了《公约》第1条第3款,该条这样规定:“一架航空器在完成登机后其所有外部舱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其任一此种舱门为下机目的开启时止,其间的任何时候均被视为在飞行中;在航空器迫降时,直至主管当局接管对该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和财产的责任时止,航空器应当被视为仍在飞行。”而原《公约》对此的规定则是“航空器从其开动马力起飞到着陆冲程完毕这一时间,都应被认为是在飞行中”。
比较这两条规定,不难发现《议定书》将“飞行中”的涵义做了扩大,这似乎符合现今航空技术的发展要求。但笔者也存有这样的疑问,《公约》的全称中有“航空器内”这一限定语,并且所指的犯罪也是发生在“航空器内”的,为何在《议定书》中忽略了对“航空器内”一词的界定呢?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呢?那么在“航空器内”犯罪是否等同于“飞行中”犯罪呢?这二者的外延是否是重合的呢?
《公约》第6条赋予了机长针对航空器内所发生的罪行行使权力,来维护机舱内的安全与秩序,《议定书》对第6条进行了增补,该条第3款、第4款加入了机上安保员的权力职责。几乎所有的会议文件都没有注意到“航空器内”这一涵义的界定,在他们看来在“飞行中”,所有的犯罪行为只会发生在“航空器内”,因为此时机舱门是封闭的环境。但是《议定书》对“飞行中”的解释还多出了“迫降时,当局接管飞机”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下,很有可能会出现在“航空器外”犯罪而可以适用“飞行中”期间的法律状况,那么《公约》的适用性就会从自己的名称上被否决,从而使得之后管辖权的行使陷入到混乱之中。
(三)管辖权的扩张
原《公约》的第3条是涉及管辖权条款的,现已被《议定书》的新管辖权条款所取代,这一变化是整个修订中比较重要的部分。通过对比新旧两份法律文件,可以发现新的《议定书》中的第3条增加了以下内容:其一,从整体结构上来看,增加了“一之二、二之二、二之三”条款;其二,从管辖权设置上来看,除了保留原有的登记国管辖权,还增加了经营人所在国管辖权以及降落地国管辖权;其三,“二之二”条款中,删除了“行为”,突出强调了“罪行”。
增加与补充的管辖权条款使得《议定书》更加符合现代航空运输的特点,也使得一直困扰许多国家无法行使管辖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摆脱了原本单一管辖的桎梏,丰富了国家管辖的实践经验。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保护主义”对国家管辖理论的影响在与日俱增,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以及普遍管辖的基础上,原先实践中机会较少的保护性管辖权,即“属人主义”逐渐兴起,其直接扩展了管辖权的基础——主权理论,使得航空“保护利益”的涵义得到了扩大解释的机会,从而间接地扩张了管辖权范围。在保护性管辖权理论中,着重以下几点:其一,主张管辖权的国家与罪行或行为有着利益上的关联;其二,在确定保护利益时,区分行为人具体行为的性质;其三,主张管辖权的国家之间注重互相协作与沟通。新的第3条可以参考表1。

表1 《议定书》第3条之管辖权条款
根据上述表格,笔者发现降落地国在行使管辖权时,对于罪行或行为的管辖,其满足条件要宽于只对罪行所进行的管辖,另外经营人所在国的管辖权在针对罪行和行为时几乎保持了一致。这些细微的差别表明了航空保护利益与管辖权主张国之间的密切程度。
例如条件1中,所规定的当飞机降落在一国领土内,且嫌犯仍旧在机上,其在航空器内犯罪,降落地国无论是否是《公约》或《议定书》的缔约国都可以“行使”管辖;而条件2中,所规定的具体满足条件既包含了条件1,也包括了其他条件,如前一起飞地点或下一预备降落地点,这说明罪行的发生很有可能不在缔约国的领土内,而只是后来飞机的降落地点在该缔约国境内。因此,航空保护利益在条件1和条件2中是不同的,显然条件1与保护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要强于条件2。这些差异性体现在管辖国的性质、行使管辖权的条件以及管辖权所指向的对象。而在《议定书》修订前,管辖对象全部固定为“罪行或行为”,这也说明“保护主义”的法理价值逐渐影响到了管辖权条款。
另外,《议定书》第5条规定了在第3条后加入一个条款,即“三之二”条,其规定了“如果根据第3条行使管辖权的缔约国被告知或获悉一个或多个其他缔约国正在对相同的犯罪或行为进行调查、起诉或司法程序,该缔约国应酌情与其他缔约国进行协商,以期协调其行动。”《议定书》在此处采纳了《草案》的修订意见,因为起草者早就预见了当“保护主义”的因素渗入至管辖权中时,势必会出现管辖权的竞合与冲突,从原先一种管辖权扩展至三种管辖权,在实践中不可能回避这种冲突,因此国家间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其实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简称IATA)是最早推动管辖权修订的国际组织,为此其还向大会递交了一份来信①参见DCTC Doc No.18,13/3/14。,在该信中提议将管辖权扩张至降落地国以及经营人所在国,并将这二者主张的管辖权视同为登记国管辖权那样的强制管辖权。
深究经营人所在国管辖的具体原因,就在于现今飞机租赁业务允许飞机在某一国境内登记,其具体的经营人却在另一国境内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实体存在,《芝加哥公约》第83条②该条规定:“允许航空器注册国的某些权利和义务在租赁、包机或互换航空器时转移给航空器运营国。”对此也予以了肯定③参见ICAO Doc 7300/8,2006。。IATA提出1963年制定《公约》时,飞机租赁并不普遍,而且第83条当时并没有被接受。经营人所在国管辖的出现,可以使管辖权与关系国之间的连接因素更为显著,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强制指定由登记国来管辖,这也从另一方面保护了关系国的主权权益。
IATA所倡议的增加经营人所在国管辖,遵循了第83条的规定,并与其扩大实践的趋势相一致。通过某些特殊的国家间协议,管辖权可以自登记国转移至经营人所在国,这在实际中也解决了对租赁飞机的规范和监管问题。在IATA看来,这样安排的优点是,可以对发生在航空器内的不循规旅客行为进行有效的管控,而这恰恰是经营人所擅长的。不过笔者认为,IATA所倡议的经营人所在国管辖在航空法领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法律概念,在处置刑事责任的航空法文件中也不具备创新性。诸如像1970年《海牙公约》、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2009年《非法干扰赔偿公约》以及2010年《北京公约》《北京议定书》这样的涉及航空运输的国际条约中,都能找到与其相同或类似的概念。所以说,这次《议定书》的修订,很大程度上依然借鉴了航空法其他领域立法的积极成果,其所解决的问题也一直是航空安全法发展过程中的陈年旧账,而非新涌现的问题。
(四)增加机上安保员
1.两种备选条文的选择
早在《公约》制定之后,由于需要迎合航空运输产业的发展,机上安保员制度的设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各大航空公司及旅客。《公约》中没有对安保员进行规定,更不用说进行定义了。那么在普通人眼中,机上安保员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媒体对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空警队所做的描述,让这个隐秘的重要机上人员展现在我们面前。
“他们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和其他上百名旅客相比较而言,他们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坐在大型的波音或空客飞机中,拿着报纸或杂志,手里还揣着黑莓手机。除了他们随身所携带的半自动手枪,这武器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他们学过如何在狭小的空间内进行身体格斗,也会在31 000英尺的高空,处理自杀性劫机者或炸弹袭击者,他们出手迅捷果断,起身与坐回等动作一气呵成。”[4]
在为修订《议定书》而召开的外交会议上,根据《草案》中所预留的两种备选条文,各成员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总体的倾向是选择备选条文二,即保持机长在处理飞行中且发生在航空器内的不循规行为时,拥有优先于机上其他人员的权力,而这也是其他成员国所持的态度。《议定书》在对《草案》进行比较和分析后,毅然选择了备选条文二。
其实备选条文二的法律基础在《芝加哥公约》附件六中,就已经得到了确认,附件六是关于航空器的运行规则,其第4.5.1条④这一条款并不要求成员国予以遵守,但如果不遵守该条,则成员国需遵循ICAO的建议措施。规定“机长要对航空器的运营和安全,以及在飞行中机上所有人员的安全负责。”机长的权力得到了法律的保证,考虑到当时并不存在的机上安保员制度,机长在机舱内的权力可谓是排他性的对世权。
不过ICAO法律委员会的起草专家们将备选条文一写入到《草案》中,看似令人难以理解,但这也说明了机上安保员的权力性质和范围界定,同样引起了航空法律实务界的重视。《公约》和《议定书》选择了机长作为管控整架飞机的人员,因此机上安保员根据备选条文二的规定,必须得到机长的授权,而且其自身也属于“其他机组人员”。ICAO空中航行局向ICAO理事会所提交的具体意见①参见DCTC No. 5,20/1/14。中认为,机长的权力是不可以被削弱和共享的,备选条文二是最合适机长行使权力并保障机上航行安全的立法。
2.与会各国的意见与争议
在外交会议上,日本提出机上安保员的首要目的就是,防止和处理诸如恐怖主义(包括劫机)这样的严重罪行,因此这些人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日本还建议,如果让机上安保员处理对航空安全影响较小的闹事行为,或者介入机上不循规人员的干扰行为,就会让他们的身份暴露给潜在的恐怖分子,从而使得安保员成为他们首要的攻击目标②参见DCTC Doc No. 10,31/1/14。。此外,日本的代表还指出,如果一名旅客因国际长途飞行而导致心情低落、烦躁甚至愤怒,并对一名空乘恶语相加,机上安保员出于维护飞行秩序而对该名旅客进行控制。这时,机上安保员会使其他乘客产生混淆,分不清到底是机长还是安保员在管控飞机。
如果多边国际条约接受了备选条文一的条款,则国家按照规定程序,对机上安保员如何使用枪支武器进行培训,卡塔尔对于此种做法提出了质疑。卡塔尔代表还对在民航客机的机舱内携带武器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更重要的是,在《草案》中依然没有解释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即相对于机长而言,如何安排机上安保员的座位,《草案》中没有准确的条款来规定。对于以上的观点,卡塔尔代表最后总结道,机上安保员的问题应该由国家间的双边协议来解决,而不是在《议定书》中解决③参见DCTC Doc No. 12,22/12/13。。
美国在提交至外交会议上的文件中指出,其并不赞同机上安保员权力要受制于机长权力的草案规定。因为如果要使机上安保员的行事更有效,更好地保护航空安全,其就不应该被归入其他机上人员的范畴,安保员应被赋予更符合他们角色和职能的地位。在某些情形下,安保员为了保护航空器、机上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为了维持机上的良好秩序和纪律,其经过授权可以采取合理措施。美国代表还认为,安保员和机长之间的权力不应重叠,后者的权威和职责要限制在保护飞机安全和整段航程的运营上,因此机上人员的安全将默示地由安保员来负责④参见DCTC Doc No. 7,23/1/14。。
美国代表在此处的意见存有两点模糊。其一是,如果机上安保员仅对机上人员和财产的安全负责,则该如何确定《公约》第1条的地位。机长采取措施,保护航空器安全或者机上人员、财产安全的权力以及机长维持机上良好秩序和纪律的权力,这两种权力是否是分别授予的呢?比较安保员的权力后,笔者发现《公约》第1条的适用范围,与美国代表对安保员所持意见是相矛盾的,因为安保员的权力适用范围受到了限制,那么第1条是否需要删减或修改呢?目前来看,《议定书》没有这方面的意图。其二是,除了维护机上良好秩序和纪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机上安保员的权力,美国代表对此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意见。如果美国的意见被接纳和吸收,则《芝加哥公约》附件六中有关机长绝对权力的规定就必须进行修改。重新启动《芝加哥公约》的修订工作,对ICAO来讲,为了规范机上安保员的权力,“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不值得的。
美国代表在会上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假设:一位旅客在机上一开始做出了扰乱机舱良好秩序和纪律的行为,但之后他的行为转变为危害飞机运营和航空器安全。那么此时如果依据备选条文二的规定,安保员在处理旅客扰乱行为时,为了能够及时处置,那他是不是在航班起飞前就去和机长做出个约定,即“机长负责驾驶舱,安保员负责客舱”呢?大会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正面回答。
另一种情况是,备选条文二中规定,机上安保员“有理由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保护航空器或所载人员的安全,防止非法干扰行为,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这种自发的行为是建立在一系列安保员主观判断之上的,美国代表对于“主观判断”的依据和标准实际上也给不出具体的阐明和论证。对“有理由认为”的认定,其是安保员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唯一条件。这是否会造成安保员拥有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他们对于自己所要执法的对象是否知晓,以及在维护良好秩序和纪律时,他们对自己角色的认知等。这些无论是《公约》《草案》或是《议定书》中都没有相应的规范。在某些时候,机上安保员的职责不仅会和机长重叠,甚至会和乘务人员也发生重叠。后者在大多数的航空公司培训上岗前,都会接受涉及安全管控方面课程的培训,他们的职责之一也是保障和维护好机舱内良好的秩序和纪律。那么,在突发事件中,何时以及何种程度下,安保员可以接管乘务人员的实际职责,二者间会不会发生互相干扰各自职能行使的情况,目前只能等待航空安全司法实践的检验。
印尼政府代表在提交给大会的文件中,对机上安保员的设置提出了自己的具体看法。印尼的态度是①参见DCTC Doc No.24,21/3/14。:“机上安保员受雇于航空器经营人所在国政府,并接受其培训和批准,搭乘该国航班,保护该架飞机和旅客,对抗不法行为。安保员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防止对民航客机的非法干扰行为。因不循规旅客所致危害航行安全时,如有必要,政府可以特别授权于机组人员以提供协助。换而言之,安保员在处置机上非法干扰行为时,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特别授权允许,则也可以处置危害航空器安全的不循规旅客行为。”
印尼对备选条文一提出了批评,其认为机长和机上安保员的角色绝不可以互相重叠,这会对管控整架飞机产生严重的争议和问题。印尼代表更倾向于备选条文二,因为机长对整架飞机的安全和机上良好秩序的掌控权力是完整的,不受限制的。机长可以命令或者要求任何人员予以协助,其中就包括安保员以及旅客,这种权力是不可能与其他人员的权力发生重合的,也就是备选条文一中的安保员的“权力等式”设计是错误。因为机长拥有完整的权力处置机上发生的罪行和非法干扰行为,所以备选条文二具备更多的法律确定性。
阿根廷观察到ICAO的成员国中至少已有40个国家,在各自的民航客机上安排了机上安保员。备选条文一将置机长于危险之中,机上安保员也可能独自作出有悖于机长意图的决定。阿根廷代表声明该国政府否决备选条文一的理由就是,机长的权力是最终的、不可分享的,否则会造成权力的减损,同样也会造成冲突与不确定性,而这些会对维护航空安全产生负面效应。
阿根廷的观点认为,机长对于航空安全的知识储备和危机处理经验要远比机上其他任何人员丰富得多,他所拥有的权力和责任中包括经营人所委托的保护航空安全的责任。而作为航空器经营人,是所有航空安全责任最终的承担者。与此相对的是,机上安保员拥有的权力和所需承担的责任委派于其他主体(通常是国家),而这些主体不直接为航空安全负责②参见DCTC Doc No.25,24/3/14。。
《草案》对机上安保员的定义中首次提到,通过国家间的双边、多边协议或安排,将安保员正式纳入到航空服务条款中,阿根廷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不过因双边协议只涉及两个国家,而无法充分为涉及第三国③这里指涉及第三国的案件,例如因为不循规旅客导致航空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时,飞机被迫降落在最近的机场,而该机场又位于第三国境内。的案件提供法律支持,因而其建议国家间应制定多边协议来覆盖涉及第三国的不循规旅客案件,但其也承认签署这样的多边协议难度极大。因而,阿根廷更倾向于通过《议定书》将机上安保员纳入到整个航空安全法体系中来。
3.争议的定论
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外交会议上,各国在对机上安保员备选条文的反复讨论后,备选条文二逐渐占据了上风。考虑到ICAO空中航行局的意见,ICAO似乎也采纳了这一内设机构的观点。但ICAO其他的内设机构,如法律事务和对外关系局、法律委员会等具备法学专业性质的部门对此次修订并没有发表各自的意见,两个备选条文的选择,以及争议的定论是直接在谈判桌上获得的。
著名航空法专家阿贝然特尼(Abeyrantne)教授对机上安保员问题有过一连串的提问④参见DOI 10.1007/s12198-014-0138-2。:“机上安保员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机上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其中也包括飞机本身的安全,如果其每次行动都要得到机长的授权,那么怎么才能发挥安保员最大的作用呢?虽然说机长接受过安全培训,但如果这名机长并不是一名安全专家,那么他要不要在极端情形下,给予安保员完全的行动自由呢?[5]由此而论,《议定书》是否需要增加一个附件,对机长与安保员之间的关系作出细节性的规定呢?”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答案就是,通过两个备选条文之间的让步与妥协来实现,最后通过的《议定书》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机长对整架飞机进行掌控,并且负责机上人员和财产的安全时,就应对机长和安保员之间有明确的理解,即在何时可以赋予安保员以自由裁量权,而无需寻求机长的同意。如果机长认为有必要的话,还应该指导安保员的具体工作。机上所存在的三种类型人员还应有明确清晰的行为准则,以此来适应其各自的职能,这三类人员主要是指:机务人员、乘务人员以及机上安保员。这些未完成的工作还需在ICAO的组织和各成员国的努力下才可能有所突破。
此外,由于各国对《议定书》中机上安保员定义的分歧实在过于巨大,最终《草案》中所拟定的安保员定义并没有被写入。不过《草案》中对安保员的定义有很大一部分是借鉴了欧洲空管局版本的定义。在这一版本中这样定义安保员:“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即通过经营人所在国政府和登记国政府的授权,被派遣至一架飞机上,其目的是保护飞机,处置非法的干扰行为。不过,排除了受雇于私人,为在机上一个或多个特定人员,提供完全私人性质的保护,诸如私人保镖。”[6]不仅如此,ICAO法律委员会也使用过这个定义,尤其是提及了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非法干扰行为,足以使安保员行使权力,这与“罪行”发生时行使的权利做出了区分。[7]《草案》第6条备选条文二中第2款规定被拆分为了两部分,分别是《议定书》第6条的第2款、第3款,看似做了细化的立法,但留下了基础性法律缺陷,因为《议定书》没有对第2款、第3款中所讲的“有理由认为”和“合理的预防措施”做任何的解释。笔者断定,未来这很有可能给适用《议定书》带来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下一次对《议定书》的修订依然不能回避这一缺陷。
三、新《决议》的法律预期
在外交会议上,除了通过《议定书》外,还协商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的全称是:关于更新288号通告——《〈关于不循规/扰乱性旅客法律方面的指导材料〉的决议》①该《决议》包括在ICAO主持下于2014年3月26日至4月4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审议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1963年,东京)的国际航空法会议外交会议的最后文件中。(简称《决议》)。该《决议》敦促ICAO理事会,并要求秘书长更新288号通告,列入更加详细的关于犯罪和其他行为的清单,并根据《议定书》对288号通告作出相应修改。《决议》还要求,ICAO将更新的通告散发给各国,并请所有成员国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将更新通告的内容纳入到其国内法律和规章。
ICAO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各成员国在国内立法中纳入更新的通告,这种做法在以往ICAO的立法活动中,并不常见。此处可能会产生如下疑问,即这种《决议》的做法是否具备了国际法合法性和基础;还有就是在《议定书》下,该《决议》类似于条约的附件,国内法纳入更新通告的要求是否具有强制性呢?当然外交会议协商通过此类决议,因其参考了理事会和法律委员会的具体报告,并预见到了未来《议定书》适用的前景。
一个已知的国际法事实是,在国际组织主持下的会议,其所通过的决议很有可能是无效的。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Brownlie)教授曾表达过他对国际会议、国际组织所形成决议的看法,他认为原则上这些决议只对那些接受国具有法律约束力。[8]换而言之,经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是没有合法性与可信度的,因为协商一致并不代表与会各国都接受了决议内容,只是同意将决议公布于众。另一名学者肖(Shaw)教授,在对联合国大会决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上,其认为:“我们必须引起注意,源自大会的任何成果可能会损害其对自身的法律评价。大会通过的决议通常是政治妥协和安排的产物,在这意义上,其是不会构成任何有约束力的规范的。我们必须从过度的实践中转移到法律规范的识别上来。”[9]
从《决议》内容上来看,还存在某些问题亟待回答,如国内法纳入更新通告的做法,ICAO的具体要求到底属于哪一种法律性质?成员国没有接受《决议》的具体内容,但接受了ICAO的倡议,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也许要等到“纳入国内法”的实践后才能寻找出答案。
尽管《议定书》中还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苦难和问题,例如在某些人员角色的法律定位上依然不十分清晰、机上安保员职能的重叠或权责不明、试图依赖共同决议来扩大适用等,虽然这些乐观和天真的修订内容可能潜藏着不稳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外交会议的召开及其成果理应受到称赞。《议定书》对《公约》的更新依然是具有法律前瞻性的。会议在修正《草案》中某些明显的法律硬伤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可能某些条款还需要斟酌,但是从目前的法律状况来看,《议定书》的通过对于缓解航空安全领域中的突出问题还是大有裨益的。
不过,判断《议定书》适用前景的最好方法就是看有多少国家对该文件进行了批准,以及《议定书》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予以实行。但似乎该《议定书》从通过那天起,其在ICAO法律体系中的未来就不被看好。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一部分是因为该文件本身存在的法律缺陷,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议定书》预留了大量空间给各成员国来积极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从而削弱了公约的统一性。
《议定书》在通过伊始,仅仅只有24个国家①这些国家是:安哥拉、巴西、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中国、刚果、科特迪瓦、多米尼加、斐济、印度、约旦、科威特、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里、墨西哥、尼泊尔、尼日尔、巴拉圭、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以及多哥。在该文件上签字,其中有14个国家是非洲国家。其余的国家中,两个来自南美,五个来自亚洲,一个来自加勒比地区,一个是太平洋岛国,另一个来自南美。北美的两大航空强国美国和加拿大没有签字。没有欧洲国家签署了该文件。虽然有100多个与会国参加了修订《议定书》的外交会议,但如此少的国家签署该文件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些问题。
国际航空法领域的每次变革都随着航空技术和产业的日益发展而深入下去,目前《议定书》所遭受的冷遇不能简单归因于ICAO本身对于统一全球性航空法没有热情。相反地,笔者认为ICAO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由其主导和组织国际航空法的立法和修订,对推动世界各国航空立法都是大有帮助的。但考虑到航空立法本身的复杂性,如航空安全与保安、航空环境保护、甚至航空运输经济学等,这些跨学科的立法因素都会使得航空法的关键区域成为各国角力的竞技场,从而使得航空立法和修订步履维艰,但ICAO致力于全球统一性立法的战略目标依然没有改变。
时至今日,成员国将其所签署36份条约和相关法律文件在ICAO处进行备案,其中很多是建立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此外,根据《芝加哥公约》第81条和第83条②这两条是关于现行协定和新协定的登记。的规定,ICAO还履行了条约登记的职能,成员国之间或者其与国际组织间的航空协定都会向理事会登记,并由后者向社会公布。但ICAO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进行国际立法,这一点已经被ICAO中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所意识到,笔者预计在未来,国际航空法律体系将会有更为频繁的立法和修订活动。
四、对自由贸易区的影响及对策
2013年8月22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核心体制是先行先试,并以贸易为发展的牵头动力,强调制度创新和法律创新。在航空法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即“自由贸易区建设,航空界准备好了吗?”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给航空界,乃至航空法学界都提供了新的社会试验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是经济、金融、贸易以及航运,其中上海浦东机场就是自贸试验区的一部分。谈及自由贸易区航运建设时,很多人会局限于海运、集装箱运输方面,其实航空运输也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内容。在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文件中,着重提及了要增加浦东机场中转集拼能力,提升飞机融资租赁的规模等涉及航空领域的内容。
笔者认为航空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航空安全的“保驾护航”。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势必带来人员、货物的密集流动,浦东机场满负荷的运转更需要注重航空安全的制度建设。无论是从航空旅客运输安全,还是从航空货物运输安全上看,皆是如此。
中国航空安全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及一整套的航空条例与规定上的,零散的体系、众多的立法空白,使得中国对于借鉴国际立法一直十分重视,此次ICAO召开外交会议,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中国也派出了代表出席。最终签署了新修订的《东京公约》议定书。
从中,我们可知政府对于航空安全立法亟待改善的渴望,经过上述对《东京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法律剖析,笔者认为中国在新时期,尤其是加大力度建设上海自由贸易区背景下的法律对策应着重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国际立法应持采取逐步推进、谨慎求证的法律人态度,防止因出现急躁立法而导致社会经济成本的上升。
第二,针对《议定书》所修订的主要内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扩大中国保护性管辖权适用范围,增加立法中的降落地国管辖权和经营人所在国管辖权。但同时须做好处理管辖权冲突的司法准备。二是对于增设机上安保员法律制度,应该明确其具体行使权力的范围,以及其与机长等其他人员间的法律关系,做到权责分明、处置有力。三是对于中国航空安全立法中的空白着力进行先期调研或课题研究,按照ICAO的指导性意见逐步进行补充。
第三,可以和某些国家开展双边或多边协议的谈判,为完善中国航空安全立法体系而进行准备,当ICAO所主持或支配的国际立法体系建立起来时,就应以国际立法为核心重新审视和构造国内立法。
第四,对于《决议》所提倡的列举罪行或行为清单,应考虑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所采用的“负面清单制”,以此保证自身权利,扩大适用范围。
第五,加强大陆地区与香港、澳门、台湾的交流,可以就航空安全立法组织研讨会、共同探讨合作研究新路径。
第六,积极主动地继续参与国际性立法活动,展开与航空大国与强国间的航空安全合作,吸收其立法中的优点,以此来作为参考借鉴的标准。
自由贸易区的航空安全立法体现了制度与法律创新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法律和制度建设应先行一步,而现有的国内立法制度和体系在面对最新的国际立法时,表现出某些不合时宜的不适性。《民用航空法》中对航空安全的法律规制较为单薄,而该法律自身的修订工作也持续了多年而毫无进展。借着自由贸易区大发展的契机,航空安全立法也应对接国际航空安全立法体系,准确而及时把握ICAO与IATA等国际航空组织的最新立法意图,加大自身立法修订及改革力度,以此来迎接自由贸易区背景下的“大航运”发展时代。
(References):
[1]ICAO.ICAO Diplomatic Conference delivers new protocol addressing disruptive passengers[EB/OL].(2014-04-07)[2015-05-20].http://www.icao.int/Newsroom/Pages/ICAO-Diplomatic-Conference-delivers-new-Protocol-addressing-disruptive-passengers.aspx.
[2]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 Report[R].Hague: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1951:15.
[3]AUST A.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221.
[4]Air marshals:Canada’s secret weapons in war on terror[EB/OL].(2010-04-04)[2015-05-22].http://www.thestar.com/news/canada/2010/04/04/air_marshals_canadas_secret_weapons_in_war_on_terror.html.
[5]ABEYRATNE R.Hijacking of Ethiopian Airlines Flight ET 720—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Security,2014(7):191-198.
[6]In-flight security officer[EB/OL].(2012-04-05)[2015-05-24].http://www.eurocontrol.int/lexicon/lexicon/en/index.php/In-flight_security_officer.
[7]ICAO.Report of the Special Sub Committee of the Legal Committe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TokyoConventionincluding the issue of unruly passengers[R].Montreal:ICAO,2012:Appendix 4,Appendix A at A4-33.
[8]BROWNLIE I.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691.
[9]SHAW M N.International law[M].5th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10.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ecurity law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TokyoConvention—the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free trade zone
YU Shi-feng
(Science Institute,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During March and April of 2014, the delegates of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to modify theTokyoConventionof 1963 in Montreal, Canada. The legislative result of this conference is to form a new protocol, in which it adds the jurisdiction, IFSOs, reflects the new trend of protectionism in the legislation of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ecurity law. Air transport,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shipping construction in the free trade zone, is always posed in the primary position due to its special trait of security or safety. The legislation of aviation security law in free trade zone should focus on the existing legal problem and find the way to solution. The measures of legal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 include such areas as how to deal with negative list, the powers of peoples in the aircraft and the conflicts of jurisdiction.
IFSOs; aircraft commander; jurisdiction; free trade zone
2015-08-23
司法部课题“飞机租赁合同的中国本土化研究”(14SFB30040)
俞世峰(1984-),男,江苏扬州人,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E-mail:yushifeng@ecupl.edu.cn。
DF961.9
A
2096-028X(2015)03-0090-09
俞世峰.新《东京公约》下的国际航空安全立法趋势——兼论其对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与对策[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5,26(3):9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