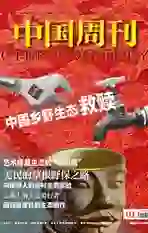昨日的布达佩斯大饭店
2015-04-29吴宜华
电影结束,当屏幕出现“受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启发”时,方才在一瞬间将《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荒诞滑稽好似卓别林默片的电影与昨日的欧洲一一对照起来。可以这样说,不看茨威格,恐怕很难读懂那些夸张虚构的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叹息和喜剧的悲悯。
曾经辉煌无比的布达佩斯大饭店,毫无疑问指向茨威格用尽溢美之词来描绘来缅怀的欧洲黄金时代。它们相似地日渐衰落,一边是门童Zero在萧条中维持;一边是作家茨威格带着一代欧洲人的怀旧伤感书写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前半部如初恋的信笺,后半部满是痛惜和决绝。两年后茨威格在对理想破灭的绝望中自尽。
这位发誓“永远也不写一句赞美战争或贬低别的民族的话”的犹太作家,一生追求和平、自由、艺术。他大学时曾为反对拆除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请愿抗议,他写道:“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子的拆除,就像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不得不说,茨威格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无论何时都保持着传统贵族的尊严和修养,视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比生命更神圣。
在影片中,饭店管家古斯塔夫身上高度浓缩了欧洲老牌的高雅,而这失落文明的演绎如今只是让人感到滑稽,比如好不容易越狱后最需要的却是香水,即将掉落悬崖时也不忘吟诗,逃命前要先为死者默哀一分钟……昨日的欧洲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古斯塔夫代表了茨威格的前半生,门童Zero便是他后半生的投射。希特勒上台后,茨威格的书籍被公开禁止和焚烧,他遭纳粹驱逐,流离失所。他最终成为一个孤独的远离祖国的没有身份的难民,一个被歧视和剥夺自由的流亡者,一个叫“零”的人。
茨威格一生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的践踏,影片中古斯塔夫也有两次在火车上遭受纳粹质询的经历,为挺身而出捍卫Zero的自由和权利,他高贵的信仰被法西斯粗暴的铁靴踩在脚下。
进驻大饭店的军队在大堂挂满双Z字样的军旗,暗合了纳粹的标志。古斯塔夫看着这一切悲伤地说:“布达佩斯大饭店变成了军队的营房,这辈子我都不要进门了。”而茨威格在书中恰好回忆了奥地利的家被秘密警察搜查的情形,他说自从警察来过之后他便不再喜欢他的家了。这些细节不难看出导演韦斯·安德森对茨威格作品的喜爱和敬意。把对严肃作品的字斟句酌转化为一部幽默的喜剧性电影,而含泪的微笑正是对荒谬时代的嘲讽。
此外,电影中的大饭店,与布达佩斯并无关联,请允许我理解为导演也曾被书中一个小小的片断震憾。那是茨威格从前线乘坐伤员列车回到布达佩斯时,发现城市惬意得就像在做梦,人们穿着好衣裳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尽情享受太阳的光辉。战争让人变得脆弱无比,“他们大概正是感受到一切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享受”。
战时的欧洲,除了瑞士仍是和平与自由的驻地,布达佩斯的那个明媚的上午想必是茨威格记忆里最梦幻的一帧画面,好像乱世里的世外桃源。而这种太过美妙的不真实,被移情到了甜美得如同门德尔蛋糕的粉红色大饭店,它因此被称作布“达佩斯大饭店”。
精神故乡阴霾重重,优雅自由的欧洲一去不复返,一生反战的茨威格临终前对昨日世界的沉沦毁灭感到绝望无力。他在书籍的扉页上引用莎士比亚的“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几乎可以想像他每一下落笔的动作都伴随着多么痛苦泣血的回顾,以及对堕落的时代再也无能为力的垂死挣扎。
如今,距离一战爆发整整一百年,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中东战争仍硝烟未灭,巴以军事冲突在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不时上演。当时的茨威格并不能预见明日的世界,生存空间的悲剧依旧存在。至少他曾看过昨日世界里真正的光明,而今日世界中的许多人,却从未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