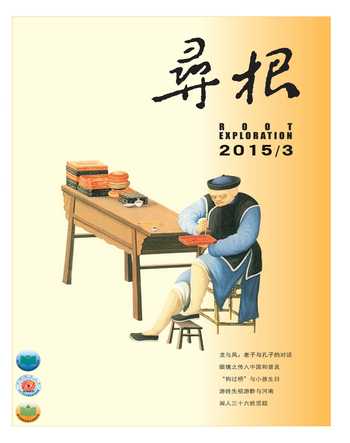闽人三十六姓觅踪
2015-04-29周朝晖
周朝晖
在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历史上,曾经活跃过一个中国移民群体——“闽人三十六姓”。据载,明洪武、永乐年间曾有一批来自福建沿海的特种技术团体“奉旨往琉球”。有关这一历史,在东亚海域诸国各种文献颇有涉及却又语焉不详。而在东亚海洋史上,这支族裔的身影时隐时现,随历史的疾风怒涛聚合零落,跌宕无常,历程颇为悲壮。
笔者曾经几度前往冲绳。为了了却多年的夙愿,利用差旅之余的闲暇,多方打探求索有关这支神秘族裔的前世今生。
扑朔迷离的传说
琉球国自1372年正式与大明王朝建立官方往来关系,迄至1875年被日本并吞的500年间,一直是明清两代册封朝贡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双方往来十分频繁。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福建被指定为中琉之间往来的出入境口岸。自此琉球国与福建、闽人与琉球国之间的渊源有如水乳交融般密不可分,“闽人三十六姓赴琉”就是其中一段广为传颂的民间交往史。
闽人何时开始赴琉已无从稽考,有确切文字记载见诸“明实录”洪、永年间的“赐闽人三十六姓赴琉球”一说。明清王朝在对外战略上实行封贡体制,规范华夷秩序,宣示天朝威仪,怀柔周边小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四海安宁。这种对外体制,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向心力为依托,经济上则以“薄来厚往”的朝贡交易形式予属国类似最惠国待遇的提携,包括技术上的援助。东亚海域的朝鲜、安南、占城、暹罗、苏禄、南掌、佛大尼等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孤悬汪洋的琉球,技术、文化十分落后,不便往来朝贡。明朝不但赐舟琉球,还从闽地派遣技术、文化精英团队前往援助“令其往来朝贡”,正是在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闽人技能集团陆续前往琉球并就地归化。
有关“闽人奉旨赴琉”一说,东亚海域诸国各有不同侧面的文献记载。中国明清两代历任册封使撰写的见闻录,朝鲜出使琉球的通信使日记,琉球国史《球阳》和《历代宝案》,更有琉球闽人历代相传的家系族谱,都留下类似记载。但由于《明史》等中国正史文献中并无相关的文字,使得此类记载亦幻亦真,甚而有人怀疑其可靠性。尤其在赴琉的人数上和姓氏上更是异见迭出:究竟是三十六人、三十六姓,还是三十六户?甚至所谓的三十六姓究竟是笼统虚数还是实指,又具体到由哪些姓氏构成,也是众说纷纭。
我曾多次走访福州琉球馆,里面展示的“三十六姓”(实为三十五姓)如下:蔡、郑、金、林、陈、毛、王、梁、阮、孙、曾、魏、程、红、周、李、高、吴、沈、田、马、钱、宗、叶、范、杨、郭、翁、于、韩、贾、俞、陶、伍、江。但我求教过闽台研究所所长、中琉交流史专家谢必震教授,据他的研究:上述姓氏中只有前26个是靠谱的,余者真伪待考。
琉球国地处汪洋一隅,地狭人稀生产落后,是“东瀛十数岛中最贫者”,直到明初,其造船能力还停留在“缚竹为筏,不驾舟楫”的原始阶段,而且驾船航海、识海路、晓天象的技术人才更为匮乏。中琉之间的往来唯赖海路,朱元璋曾多次赐舟,后直接从闽海地区派遣专业造船航海技术团队前往协助。
这支专业技术团体加入琉球国后,对振兴琉球国力,传播先进的中国文化,促进琉球和中国的密切往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短短一个世纪,原本“不谙舟楫”的蕞尔岛国一跃而成以航海行商为业,“以舟楫为万国津梁”的东亚海洋贸易中转站,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往来密切,光是有明一代记录于正史的就有171次。琉球商船穿梭于中国福州以及泰国、越南、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等地港口,就像后来的荷兰,在东亚扮演了海上马车夫的角色,创造了“物华天宝充满十方刹”的繁荣盛世。
琉球国的中国文化烙印
闽人族裔对于琉球国的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支代表着东亚乃至世界上最优秀最先进的技术、知识的文化精英团队,他们在融入琉球国社会的过程中,也把所在国的诸多领域打上深深的中国烙印,其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婚冠丧庆等礼仪规范也渐渐为琉球贵胄与庶民所仿效。
在文化艺术方面,闽人对琉球传统音乐的启蒙点化之功也是有口皆碑的。琉球王国的国乐——宫廷音乐,乐谱和演奏冲绳音乐的代表性乐器三弦、太鼓,直接源于闽人或册封使团中的随行乐师。琉球宫廷雅乐叫“御座乐”,乐手列队跪坐在室内席上表演的一种歌乐,由乐器演奏的“乐部”和演唱的“歌部”组成,阵容华丽,旋律典雅,是琉球国在举办重大国典,或重要外事接待活动中才得一见的琉球艺术。据中日专家合作研究考证,琉球国的御座乐,乐队的编排不仅与明代宫廷乐队的编制,甚至和福建鼓吹乐的编制十分相像,而“唱部”的编制与泉州南音和莆田十音也存在着相承关系。笔者十年前有幸亲睹第37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世界年会在福州举办的盛况,来自冲绳县“御座乐复原研究会”成员15人现场为300多名中外传统音乐界专家学者演奏了多首琉球宫廷雅乐,几百年前搭乘万里惊涛骇浪从福建传到琉球的汉唐雅韵又回响在榕城的世纪乐坛,引起如浪潮般的反响,至今难以忘怀。
而在日常生活习俗上,闽人留下的印迹无处不在。至今走在冲绳县的老街古镇,沿途的石墙红色炼瓦掩映在三角梅和扶桑花丛中,屋顶装饰着辟邪物的石狮、丁字路口的石敢当等,令人油然想起闽南、金门渔村的独特景观。由于和福建省的特殊渊源,源于闽海的保生大帝、妈祖信仰至今在冲绳有着广泛的影响。
琉球国的衣冠士族
“闽人三十六姓”这一来自先进大国的技术精英群体,在琉球王国也备受礼遇和优待,他们大都被委以重任参与国家重要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活动,成为琉球王国里举足轻重的特殊阶层。其中的“善操舟”“习海者”,到琉球后“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知书者”也就是知识、文化精英被授予大夫、长使之职,担任朝贡使、谢恩使等对明朝贡册封往来的外事要职并世代袭职。
琉球国赐予闽人宅邸和土地,让其安居乐业。王府将久米村指定为“闽人三十六姓”独立的聚居地。久米村原是那霸港边上的一个名叫“苦念搭”的浮岛,闽人来居后,被称为“唐营”,即唐人聚落,后更名为“久米村”。据史家考据,“久米”一词意喻“永久享有俸禄”的恩遇。
闽人士族子弟都受到良好教育。学校就设在孔庙之堂北。“久米士之秀者,皆肄业其中,择文理精通者为之师,岁有廪给。”学校教育以汉语为基础,以儒家教义为旨趣,旁及典章规范外交文书的制作。十岁时称“若秀才”,国王赐给大米一石;到十五岁剃发,先拜谒孔子,再晋见国王。国王把他的名字登录在籍,称为“秀才”,赐给禄米,并着重培养,佼佼者还可与王族子弟一起进入北京国子监留学,学成归国另加重用。
依照琉球官制,居住在王都首里的尚、向等王族七姓,世代为王国高官,法司、紫金大夫这种等级的官员,均不出七姓。但这一惯例很快被闽人杰出后裔打破:福州长乐郑氏后裔郑迥,品学兼优,能力超群,官拜法司官,迁往国都居住;而琉球人至今老少皆知的蔡温、程则顺等闽人后裔,更是琉球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名相。闽人族裔成了琉球国中最负盛名的族群,连大清册封使李鼎元也不禁慨叹道:“琉球国重久米人,有以也!”
沉浮在历史风涛中
然而,这支曾经在琉球王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族群,百年之后却突然黯然失色甚至支零破碎。就像他们神秘的身世由来充满神秘感一样,他们的衰微也在东亚中琉史上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明朝册封使前往琉球册封尚宁王时,发现三十六姓中“仅余蔡、郑、林、程、金、梁六家,而族不甚蕃”,路过久米村,“强半丘墟”的颓败景象令大明使者惆怅不已。崇祯十三年,大明王朝谢幕前的最后一次册封时,久米村老弱者仅存30人。到了清顺治七年,朝廷遣使册封琉球新王。据使节的调查记录,六姓中又少了程姓,只剩五家。
究竟何种原因,致使这支神秘的族群在历史长河中衰微零落呢?
有关这一族群神速崛起又悄然凋落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定论,这也让这个原本就神秘不已的传说更显得云缭雾绕不为世人所知。
闽人三十六姓今何在?
梁氏吴江会龟岛裕文会长告诉我:在冲绳县,目前能找到的闽人姓氏只有22个,总人口约4万。但在人口只有130万的冲绳县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一则他们作为琉球国历史上的精英群体,影响深远;二则在经济上也是不容小觑的力量。历史上琉球王赐予闽人土地宅邸并世代承袭,其后裔至今仍然是冲绳广大土地的拥有者,政府建设征地乃至涉及美军基地用地的纠纷绕不开他们;闽人后裔拥有遍及各个领域的人才精英。深厚的人文传统,使其后裔勤奋上进,锐意进取,在冲绳县人口当中,闽人后裔出身的卓有成就的学者、教授、科学家、作家不胜枚举,深孚众望者开始步入政坛,为生民请命、为冲绳未来命运奔走呼号,活跃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
往事如烟沧桑如幻,今天这些闽人的后裔,在姓名、语言、习俗、价值观甚至归属感上,与他们几百年前“奉旨赴琉”的先人相比虽已大相径庭,但他们还相当顽强地维持着门宗组织,以“门中会”的形式凝聚宗族力量,顺应时事的变迁顽强生存发展,并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散发着独特的人文气息。今天在冲绳县的那霸市中心原久米村一带仍活跃着好几个闽人门中会。我特别拜访请益的“梁氏吴江会”是冲绳最具影响力的闽人后裔宗族机构,历史悠久。据载其始祖是福州府长乐县江田村人梁嵩,于永乐年间奉命前往琉球,“广敷文教”,如今冲绳后裔有308户,1429人。冲绳“阮氏我华会”是漳州龙溪(今厦门)阮氏后裔在冲绳的宗族组织。据《那霸市史》及《阮氏家谱》载:始祖阮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渡琉,居于久米村。今冲绳的阮氏后裔有3500人,宗族会员317户;“王氏槐王会”先祖是明朝万历十九年从福建漳州龙溪前来琉球的王立思。王氏一族的祖庙“世德堂”至今还在龙海角美镇石美埭头村(今属厦门)。
梁氏吴江会机构名取自宗族祖籍福州长乐吴航镇江田村。关于梁氏的远祖,据《梁氏家谱》和《吴江梁氏总世系图》记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时代,末子庸受封于夏阳的梁山,称为梁伯,其后世子孙冠名梁姓,并分散各地。福建福州一支,始自晋朝安帝年间迁来福州长乐并定居下来。明朝永乐年间,江田村梁嵩受明政府派遣前往琉球国“广敷文教”,是为琉球梁氏始祖,其后人世代居住久米村,代有显达之辈。
冲绳梁氏有祖墓在那霸市牧志一带,但墓主是琉球梁氏第四代梁显,此前者均不见记录,据说梁显的父祖辈老后归国不知所终。也就是说到梁显这代始定居琉球。从墓碑文的内容看,墓主是久米村总役,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最高行政长官。而到第九代时梁氏后裔就官拜正议大夫,成为国中重臣,梁氏望族声名自此而始。
第九代时开始分家。长子梁邦基为家族继承人,是为大宗家。次男一支为“古谢家”;三男为“当问家”和“上江洲家”;四男为“崎山家”“濑名波”“国吉家”“吉滨家”;六男为“安仁屋家”。大宗家到第十代,被委任胜连间切龟岛地头(地方最高长官)一职,大宗家就以龟岛名之。因大宗家不在冲绳居住,供养祖先一责就由其宗族组织“梁氏吴江会”承担。“梁氏吴江会”总部设在那霸繁华街区的久米町壶屋一带,琉球王朝时代即是梁氏一族的封地。
作为闽人后裔的宗族机构,如上所说的“阮氏我华会”“毛氏久米国鼎会”“梁氏吴江会”都是正式注册的社团法人或中间法人团体,颇有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流风余绪,又有鲜明的日本特色。这些宗族组织在当今冲绳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民俗学和社会学意义呢?
通过比较,我发现梁氏这一宗族组织在发挥社会职能方面基本与其他宗族机构类似,在冲绳的诸多闽人后裔“门中会”里是个颇具典型性的民间社团。机构都由若干理事组成,下设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宗族活动中六项内容:学务、财务、土地、广告、祭祀和制定落实各种宗族规章。
会费主要来源是宗族祖产中的土地租赁使用收益及每户缴纳的1000日元。
梁氏吴江会的运作内容主要有三项:管理宗族土地财产;宗族助学奖学计划和实施;组织筹划宗族庆祀和其他传统活动。
促进文化教育也是宗族机构一大功能,梁氏吴江会设立“学事奖励会”支持鼓励族内的文化教育事业。
此外作为梁氏一族的宗族机构,还要担负组织祭祖及其他宗族重要传统节庆活动,增强家族凝聚力,开拓新的社会资源网络之类的使命,而一年一度清明节回乡寻根祭祖则成了近年宗族机构的一大职能工作内容。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0世纪80年代末起,冲绳人开始踏上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旅途,大量闽人后裔前来福建寻根认祖,一时成为潮流。冲绳县闽人的宗族机构的活动也出现了新的内容,就是定期组织族内成员前往中国福建认祖归宗,修订族谱,合作兴办企业,为宗族寻求新的社会资源网络。
冲绳闽人后裔前来福建寻根,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据谢必震教授介绍,1987年由冲绳县政府有关部门牵头,陆续安排学者、专家携带闽人三十六姓家谱来闽寻根。当时的福建省政府调动一切资源全力配合,几年之内基本完成在福州蔡、林、金、梁等姓,莆田陈姓,泉州蔡姓,漳州毛、阮、王、陈等姓氏宗祖地的查证。在此基础上冲绳的闽人后裔各团体纷纷踏上了前往福建的寻根之旅。
冲绳闽人族群后裔,这支散发着历史人文气息的族群,经历了历史风雨的洗礼和时世变迁的激荡,至今焕发着强韧的生命力,其宗族组织在21世纪的今天,在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开放社会,继续发挥着整合族群,建立族群共同生活,扩大社会联系网络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