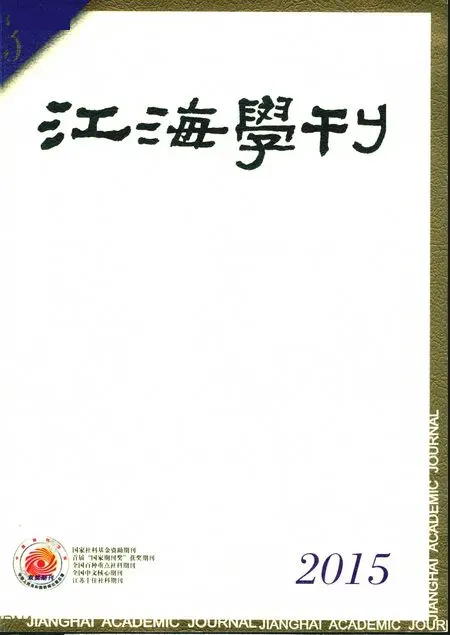19世纪80年代日本民间对于汉字汉文的态度*
2015-04-18曹雯
曹 雯
前 言
在欧洲现代化模式获得世界性推广的历史背景下,近代日本对于语言的改良无疑是其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后必将要采取的措施。日本语言的改良起自明治维新前后,但实质性行动,迟至80年代以后才逐步有所展开。日本语言改良,首先面对的便是如何对待自己语言中的汉文抑或汉字这一命题,即语言要简化,首当其冲是如何设法减轻因汉字难学难记所造成的学习负担。于此,民间舆论早有分化:是全部废除汉文字,还是对汉字的数量进行适当删减。前者的主张显然过于偏激,既不能得到政府的回应,亦很少能获得民间舆论的同情;而后者的观念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逐渐成为关注现代化运动的有识之士认真考虑的改革目标。近代日本语言的改良,其过程漫长而复杂,虽起始于幕末,然至19世纪90年代,改良之雏形亦不过初步确立,而其间的80年代是语言改良最终得以实现的铺垫、积累时期,本文之写作目的即在于揭示上述80年代日本语言的改良过程。今日,我们知道,日本语言虽然经历了现代化的发展,但日本并没有完全抛弃汉字,甚至可以说在其语言中仍保留了大量汉字,这在汉字文化圈内是个特殊现象,即与中国直属版舆相邻的越南,甚至朝鲜在殖民主义的吞噬下均废弃了汉字,而不乏废弃汉字呼声的日本却在自己的现代语中最终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汉字。更为引人注意的是,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汉字在日本明治时期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大放异彩,由其构造出的种种现代新词汇不仅为日本社会大众所接受,甚至回流到中国,影响并促进了中国现代语的发展。那么,日本最终没有放弃汉字的理由是什么?而展示其演化过程就是本文写作的动机。
本文所引用的文献均来自明治时期的出版物。自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国会图书馆不断建立以及完善自己的电子书库,竭力将馆藏明治时期的出版物全部实现数码化,以飨读者。通过对明治时期出版物的原书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并复原出一个更加符合历史客观的明治日本,以及那些与明治日本发生众多历史关系的国家或地域的面貌。欧洲现代化进程在推及至东亚时,首先意欲突破的是中国大陆,不料被欧洲称为顺手牵羊而为之的日本,却先中国克服本土文化与近代外来文化之冲突,接受并开启欧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日本究竟如何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期间亦颇为曲折艰辛,论其原因,曾尊崇汉学之日本知识界面临着汉学、西学宜舍此取彼的艰难选择,即明治日本对于汉学的态度其实直接决定了它的西方近代化发展的成功与否,而这样的抉择必然受着各种情绪的干扰或牵扯,绝非一蹴而就。受资料限制,以往中国对于近代日本的研究,常常有失于简单化或公式化,会不自觉地将某种为后来者所认可的观点归结为日本那一时代的意识主流,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日本在最终确立西学地位之前,曾经也经历过观念多元化甚至不同观念之间混打哄争的纷扰时期。得益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公开,我们可以通过那些直接参与社会变革的经历者们所留下的种种笔迹,观察并整理出上述演化的过程。
日本新闻、杂志的发展
如何能改变社会风气?近代之前,书籍是主要传播理念的工具;近代以后,报纸、杂志因可以迅速开启民智而成为启蒙者激赏的重要传播手段。效仿欧美国家,明治以后的日本亦不例外地积极推进报纸、杂志事业的发展。
早期的明治政府并非无所顾忌地开放言论自由。明治元年(1868)5月,政府向全国发布命令,规定新刊本、翻译书、重刊本均须获得官许之后才能出版,至明治四年(1871)7月,又进一步改由新成立的文部省负责审查。除书籍出版权被重新规范外,明治二年(1869)3月,政府颁布新闻纸印行条例,规定东京府内发行的报纸、杂志必须接受政府监查,若有违背条例者,将给予处分。①在如此监管下,报纸、杂志的创办数量仍保持持续增长。据统计,明治二年(1869)新增报纸、杂志10家,其中《中外新闻》和《远近新闻》乃上年被禁办者,经重组获得许可后复刊;明治三年(1870),新增报纸、杂志4家,其中,日本最初的日报《横滨每日新闻》于当年7月创刊;明治四年,新增报纸、杂志6家;明治五年(1872),新增报纸、杂志9家,著名日报《东京日日新闻》于是年创刊,在《太政官日志》于明治十年(1877)停刊后,成为政府的代言人;明治六年(1873),新增报纸、杂志12家;明治7年,新增报纸、杂志7家,现今仍傲然驰骋日本报业界的《读卖新闻》于是年正式发行,而明治初期重要的启蒙杂志——《明六杂志》亦于是年登上舞台;明治八年,新增报纸、杂志17家。②至此,日本全国共计有70家在营运的报纸、杂志,它们大都分布在东京、横滨、京都、大阪、名古屋、长崎、函馆等都会城市或贸易开放城市,而三分之二的刊物又集中在东京,新都东京成为情报或信息最为流通的城市。明治四年1月,东京在籍人口为671748人,而到了明治六年年末,已猛增至813488人。③
虽然,明治政府压制不利于政府或国家的言论公诸于世,但另一面却又鼓励全国上下积极推广报纸、杂志等信息的传播方式,以争取民众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振兴国家的事业中去。明治三年12月,日本开始启用具有近代意义的邮政制度。明治四年12月,邮政省即发布公告,称报纸杂志的发行人可委托邮政发送报纸、杂志。据统计,明治五年2月至10月间,申请上述服务的报纸、杂志共有16家。④
根据对几家主要的日刊报纸发售状况的调查,我们可以粗略估算出报纸杂志的利用人数。《读卖新闻》,明治八、九、十、十一(1875、1876、1877、1878)的年发行量分别为 3340736、5457000、6189674、6544679 份;《东京日日新闻》,明治八、九、十、十一的年发行量分别为2826191、3285000、3422792、2125292 份;《邮便报知新闻》,明治八、九、十、十一的年发行量分别为699720、2393000、2070509、2119061份。⑤以一年 365 天计算,《读卖新闻》,明治八、九、十、十一的日发行量分别为 9152、14950、16958、17930 份;《东京日日新闻》,明治八、九、十、十一的日发行量分别为7742、9000、9377、5822 份;《邮便报知新闻》,明治八、九、十、十一的日发行量分别为1917、6556、5672、5805份。以一份刊物有四个人在使用计算,《读卖新闻》,明治八、九、十、十一的读者分别为36608、59800、67832、71720 人;《东京日日新闻》,明治八、九、十、十一的读者分别为30968、36000、37508、23288 人;《邮便报知新闻》,明治八、九、十、十一的读者分别为 7668、26224、22688、23220人。三者汇总,明治八、九、十、十一的报刊读者分别有75244、122024、128028、118228人。这个数据虽然不精确,但可以初步推算出,明治八年(1875),日本全国各种刊物的使用者应在10万人左右;明治九年(1876)起,刊物发行量有了飞跃发展,各种刊物的使用者应在15万人左右,之后的发展又处于维持状态。据统计,明治九年1月,日本全国人口34338404人,其中,男17419785人,女16918619人。⑥如此,明治八年,使用者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率应接近0.3%,如果以男性读者远多于女性读者为前提,男性刊物使用者在全国男性总人口中所占比率或许接近0.5%;明治九年起,使用者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率应接近0.4%,男性刊物使用者在全国男性总人口中所占比率或许接近0.7%,而且,我们可以猜测,在大都会,尤其像东京这样的城市,男性读者的比率应该更高。尽管真实情况或许低于上述推测,但有一个结论是可以得出的,即日本已初步拥有一批利用出版物,尤其是通过报纸、杂志来迅速吸收社会信息的人群。这为改良者制造舆论提供了生存空间。
舆论造势的时代与汉字、汉文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一个舆论造势的时代。随着初期启蒙期的渡过,不同的主张蜂拥而出,接受社会民众的洗礼,大浪淘沙,最后的胜出者将会成为政府执政的新目标。因此,考察这一时期文字文章改良者的动态,对厘清汉字、汉文在日本的生存状况尤为必要。
明治初期,国字改良者们确实有过大声疾呼,但收效甚微。明治十二年(1979)10月,当学士会院会员福羽美静提出的一道建议——《学士会院应制定日本文法书之建议》,在获得该学士会院的认可后,国字改良者的举动又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当年10月,在学士会院刚刚通过福羽美静提案后,主张洋字国字论的西周即建议该院成立日本文学社,以便调查国语学之诸事项。明治十三年(1880)2月,学士会院向文部省申请文法书的编纂权,获得许可。加藤弘之为培养博言学研究的人才,建议文部省应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却招致西周的反对。自此,关于国字国语改良之论争再起硝烟。
1.假名文字论者
明治十四年(1881)12月,伊藤圭介以《这是必须被强调的,这也是必须被实行的》为题发文,期待日本废除汉字,采用假名,并竭力宣扬这一做法的益处。假名文字书写虽然不能为政府所控制的各类机构所采用,但早在明治八年所新增的报纸、杂志中,就已经出现了利用假名文字编发的报刊,如《平假名绘入新闻》、《假名读新闻》等。而伊藤圭介撰文的背景是,是年秋天,吉原重俊、高崎正风等人发起假名使用运动,随后加入的有物集高见、大槻文彦等人。至明治十五年(1882)夏,池原香稺、那珂通世、南部义筹、内田嘉一、大槻文彦、丸山作乐、福羽美静、清水卯三郎、物集高见等17人组织成立“かなのとも(假名之友)”学会,于翌年明治十六年(1883)3月,将其办会宗旨公之于世。5月,假名之友发行《かなのみちびき(假名之路)》第一卷。据说,该会成立之初就拥有200名会员,而到了第二年,会员人数增至2000名。⑦
同样于明治十六年夏,与该会相呼应,另外三个假名文字学会即“いろは会”、“いろは文会”和“いつらの友”三会合一,组成“かなのくわい”学会,会员有三宅米吉、小西信八、辻敬之等师范学校出身的教育学者。9月,“かなのくわい”发行《かなのまなび(假名的学习)》第1号。三宅米吉发文称现行文字在发音上存在许多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⑧
在上列众人中,大槻文彦是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1875年,他接受文部省的委托,开始编纂国语辞书,这部被最后命名为《言海》的辞书,定稿于1886年,因文部省无力筹措经费,最终由大槻文彦在1891年自费出版。也就是说,大槻文彦参加假名文字运动的背景是他本人正在从事国语辞书编纂活动。我们从“かなのくわい”学会的会规中可一窥其办会宗旨。其大意为:为减少追求日本学问之阻碍,不宜再使用古今、和汉有别的语言,而应选择简明易懂的假名作为表记文章的文字,故当务之急为尽早确立一套可行的表记方法。虽然,假名文字论者纷纷以为,除假名外不应再使用其他形式的文字,但上举学会的会员则却依然采用的是汉文直译体。不过,假名文字学会的活动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10月至12月,针对社会各界对“かなのくわい”的批判,大槻文彦连续发表十余篇文章,一一给予批驳。12月28日,《かなのくわい大戦争》第一册问世发行。⑨
这一时期,假名文字论者通过各种尝试来树立假名在日本社会的影响。比如,明治十七年(1884)1月25日,大槻文彦、渡边洪基、丸山作乐、物集高见、殖田直太郎、清水卯三郎、平田东雄等7人在东京组织语学会,从事假名文字的研究,创会当天即召开第一次会议,此后连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但持续到第六次会议后便草草结束了。4月,金田丰太郎发表题为《假名文字的写作以及大概规则》的文章,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文章应以俗语或人们熟悉的雅言来书写,一是应以意思明了的和语来改写或翻译文中或会出现的汉语。5月,铃木辰海以《谨与假名会员相谋》为题发文称,虽赞同废除汉字,却主张专用片假名而非平假名。7月1日,语学社同“かなのくわい”合并,改会名为“かなのくわいとりしらべがかり”。7月30日,杂志《かなのみちびき(假名之路)》改称为《かなのしるべし》,于该月发行第1期,该杂志于第二年的7月1日,又改称为《かなしんぶん》,至明治十九年(1886)7月15日,再次改称为《かなのてかがみ》。这样频繁更换杂志名称,可以看出办刊人不停摸索、调整其办刊宗旨的意图。明治十七年8月30日,三宅米吉在题为《关于各国之讹言》的文章中,论说应专用假名,期待日本未来之文章语应是言文一致的状态。他建议说,若要言文一致,首先应调查各地方言以为制定标准语而做好准备,并提出调查方言的具体方法。⑩
这并不是假名文字论者首次提到文字改革的目标是要达成言文一致,明治十七年2月20日,在题为《关于文章的写作》的一篇文章中,其作者即“かなのくわい”某位会员就提出言文一致的主张,并期待日本今后能够采用横排书写方式。此后的明治十八年10月15日,又有神田孝平站出来,在学士会院以《读文章(西村茂树)论》为题发表演讲,反对西村茂树所提出的改良法,赞同言文一致论。假名文字论者的观念并不是统一的,对于大部分持假名文字论的人来说,将现行文体中的汉字部分翻译转化成假名文字是他们努力的目标,而言文一致论则要求更加简明易懂的表述语言,如果能将口语直接转换成文章,就可使得更多的民众去阅读并撰写文章,而现行的文字文体状态则令他们强烈感受到日本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不过这一时期,普通国民教育结构尚未完全确立,知识分子中仍以接受传统汉字汉学教育者居多,这部分人对于要求更加简化的文字文体的主张——言文一致保持着谨慎态度,上述西村茂树的观点就是一个例证。但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无法用纯粹的日本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所不得不面临的苦恼,即他们必须用掺杂着外国语(比如大量的汉字词)的汉和、甚至汉和洋语言才能精确完成自己的观念表述,结果寻求、确立本国独立的语言表述成为他们的诉求。
明治十八年(1885)1月2日,平岩愃保在《六合杂志》上发表题为《日本文字论》的文章,主张将现有假名文字精简至19字,若以此为国语,则较现今之平假、片假名更为简洁易用,并称此举将带来国家文运之昌盛。对于这样的主张,3月16日,同为假名文字论者的高桥五郎在同一杂志上撰文驳斥平岩愃保的假名节减说。于此,平岩愃保在4月30日出刊的《六和杂志》上又回应了高桥五郎。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假名文字论者之间亦存在争议。这是个争议的时代,在没有统一标准的状态下,他们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宣扬观念。明治十八年1月20日,岛野发文提出,“日用文”应用东京语来统一记述,这是笔者看到的首次提出日本应确立标准发音的文章。2月,片山淳吉以《かなのけういく(假名之展望)》为题,历数汉字之危害,倡导使用假名文字,并提出假名文字的教育方案。7月10日,铃木唯一以《信的写作方法》为题发文称,写信时尽量避免使用僻字、僻语。8月9日,外籍人E.fusiroda在教育会常集会上以《日本国语论》为题发表演讲,力排汉语,鼓励日本采用洋语来丰富日语词汇,并建议日本应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在一篇发表于11月20日、以《俗语をいやしむな》为题的文章中,作者非常鲜明地提出应使用俗语来书写文章。
因为有学会刊物,假名文字论者发出的舆论在后来的几年仍不时引起人们关注。比如,明治十九年8月15日,高桥新吉在题为《文字改正的问题》的文章中,由文字之起源,论及和字与汉字同和字与洋字之优劣,提出就记录日本语而言日本固有文字当为最合适之文字,并专门论及其书写方法以及文法。10月15日,松危ながゆき在其题为《鉴于中国人亦苦于汉字之多而应使用假名》的文章中,列举实例证明汉字难习,藉此断定汉字迟早当废除。12月15日,岐阜学艺同好会杂志刊载文章称,以国语书写的文章之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在于不用假名,所以应全面使用假名。
明治二十年(1887)的上半年,假名文字论者似乎进入一个短暂的休眠期,至6月15日,村尾恺太郎发表《使用假名是教育经济》一文后,又开始恢复其活力。8月15日,在《かなのてかがみ》上,物集高见载文,列举文章必须如说话一般进行记述的理由。9月15日,物集高见再次发文称,如果以口语书写文章,并在全国得到推广,那么就可以实现文章雅俗共赏之目的。至年底,有假名文字会组织发出创建假名学校的倡议书。12月1日,假名学校在东京九段坂下玉章堂开设。明治二十一年(1888)1月15日,平井正俊在其题为《文字之论》的文章中,由文字的职能谈起,赞成排斥汉字的假名说,并论及言文一致。2月15日,かなのくわい学会发表《假名书写法》。4月,在かなのくわい学会的大会上,末松谦澄列举以汉字记录人名、地名所造成的危害,主张应创造属于日本的词语,确立言文一致式的国文学,期待将文字确实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呼应,大槻文彦发表题为《信的书写方式》的文章。6月1日,かなのくわいみらぐみ的会刊《あまがさひづり》第 1 号发行。
如上述,假名文字论者的呼声虽然很高,但因缺乏实践性,其大多主张的可行性受到社会广泛质疑,调查、研究、确立一套可行方案成为下一阶段假名文字论者的必选之路。12月20日,由宫地岩夫、福西四郎左衙门、墨田太久马等筹划的语言调查所正式成立。日本语言的调查工程由此开启,而在未作好进一步的准备之前,假名文字论者在完成最初的造势阶段后,暂时退出社会舆论的中心。
2.罗马字论者
明治初期,游学归来的森有礼即提出过以英语为日本国语的建议。这样过激的提案鲜少能得到呼应。然而,随着西洋风潮的卷入,倡导罗马字的文字改良论者开始涌现。相较假名文字,罗马字在日本受到冷遇,宣说者转而主张假名文字论者间或有之。到80年代,随着文字简化运动的蜂起,不仅假名文字论者粉墨登场,鼓噪社会,罗马字论者亦看准时机,举帜而出。明治十五年4月25日,矢田部良吉在《东洋学艺》杂志上发表题为《以罗马字表述日本语说》的文章,阐述现行文字严重阻碍了日本文运的昌盛,明确指出应采用罗马字,并提出实施方法。就笔者在明治十五年的记录里只找到在日英人对矢田部良吉有所回应一事表明,日本社会对以洋字取代现行用文字的提议不以为然。
如前所述,假名文字论者之间的意见并不统一,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字改良者并非人人对于文字的改良方向都抱有清晰不变的目标。既然有罗马字论者转为假名文字论者的现象发生,也就能观察到假名文字论者转为罗马字论者现象的存在。外山正一是位汉字废除论者,在选择何种文字为国语的当初,他站在了假名文字论者的队伍里,在明治十七年(1884)2月,公开发表题为《废除汉字》的演说,并将其演说笔记向假名之会公开。6月,外山正一以《废除汉字勃兴英语乃今日当务之急》为题,发文称应驱逐汉字,破除知识壅蔽,方能与西洋诸国相竞争。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罗马字是国字的最佳选择,但因赞成者居少数,所以可暂时屈从假名文字说。明治十七年12月2日,罗马字会成立,外山正一在创会演讲上,宣读罗马字会发起之因和办会宗旨,正式加入罗马字论者的行列。当月,外山正一撰写的《新体汉字破》出版问世。
自明治十八年(1885)起,罗马字论进入其第一个活跃期。是年3月,罗马字会议定以罗马字转写日本语之书写法。4月,罗马字会发表以罗马字转写日本语的方法。5月25日,矢田部良吉在其题为《罗马字会书写法之理由》的文章中,列举使用罗马字应遵循以下几点:第一,不根据假名用法,而依据发音;第二,以东京普通受教育者间流行的发音为标准;第三,就罗马字使用,其子字采用英语中的通常发音,其母字采用意大利语(即德语或拉丁语)的发音。6月10日,罗马字会发行会刊《罗马字杂志》第1号,上载岛田三郎题为《罗马字之便利》的文章,其旨意乃宣扬罗马字在排版方面所凸显的便捷特性。7月10日,《罗马字杂志》第2号发行,三宅雄二郎在其中题为《文字之争》的文章中称,英语在欧洲普遍为人们使用,很多文豪的作品因被翻译成英语而广为流传,若要使得罗马字为日本人所熟知,应以罗马字创作一些大诗文,人们只要以这些大诗文为摹本,即可进行罗马字的写作练习。三宅雄二郎的提议是建立在必须有一批日本文豪愿献身日本罗马字推广的基础上,其可行性显然低下,当即遭到外山正一的反弹。10月10日,松井直吉以《文字的历史》为题,在回顾文字历史的基础上,排斥汉字,主张改用罗马字。到当年底,《罗马字杂志》共计发行7期。
在早期罗马字论的推广者中,矢田部良吉显得较为活跃。明治十九年(1886)1月10日,矢田部良吉的文章又出现在第8号《罗马字杂志》上,该文重申文字不过是获得知识的工具,与其花费工夫学习困难的文字,不如尽早驱逐汉字。2月25日,矢田部良吉继续利用《罗马字杂志》这一宣传工具,发表《烦劳教育家一读》一文,论述既然日本决定输入西洋文化,就应着手使用罗马字。社会读者对于矢田部良吉的提议也提出猛烈的反对意见。5月25日,氏家鹿三郎即针对矢田部良吉撰写的《烦劳教育家一读》进行反击,称其表面看似忠心,实乃卖国之人。反对声中的最强音是指责罗马字的书写方法破坏了日本语本身的诸多法则。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一些显要人物也开始关注这一文字的改良方向。明治十九年1月23日,在罗马字会第一次总集会上,华族井上磬发表演讲,谈到文字后缀的方法,并指出应编纂相应的文法书。当天,出席会议的驻日英国公使在其演讲中也阐述了罗马字的便利性,并提出施行的具体方法。就采用罗马字一事,在日外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有能力者会利用各种场合向日本当局宣扬使用罗马字的好处。
5月10日,又一家宣扬罗马字的杂志即罗马字新志社社刊《罗马字新志》第1号发行,在这期杂志上,发表了罗马字用法。就罗马字的使用问题,罗马字论者各陈己见,期待一套成熟的使用法能获得确立并被推广。比如,6月10日,北川乙次郎在其题为《针对这些挑选出的文字我们应给出怎样的名称呢?》的文章中,就26字的读法提出意见。8月10日,外国人R.Allain向罗马字杂志寄去关于罗马字使用法的意见。9月10日,青木セイジロー就罗马字略号提出自己的意见。12月10日,草野纹平在其题为《罗马字行于世之意见》的文章中,论述其方法。
总之,罗马字论者以为,以罗马字来进行书写,可以帮助日本人学习“洋学”,而且便于西洋人阅读日本书籍,可谓一举两得,内外均受其益。另外,兴“罗马字会”者称,罗马字书写方便,用书写假名文字一字的时间可书写两字以上;而且,罗马字的发音更精确,比如用日本语标注西洋诸国的人名地名是万万比不上罗马字的。归纳之:一,由于日本文辞所具有的不规则以及不确定性,不适于同西来文明并驾齐驱,故若将其改良为罗马字,日本文明发展可获得锐意进步;二,日本文辞不易习学,若将其改正为罗马字,可开启知己知彼之途。
然而,罗马字论者的鼓动似乎并不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比如,很多人以为,即便日本人记住了罗马字的连缀法,但在阅读西洋书籍时仍不能理解其意;同时,西洋人也会遇到相同问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现行的罗马字使用法尚未融通日本语,若长此以往,则前途堪忧。也就是说,罗马字会与假名文字会有相同的境遇,如果不实施严格系统的语言调查,将无法确立能为日本民众所接受的罗马字使用法。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5日,田中义重等在茨城县古田部町创立罗马字研究会。
这一时期,无论是假名文字论者,还是罗马字论者,消除人们对汉字的依赖是他们行为中的共同点。比如,明治二十年(1887)1月10日,外国人SumiKatsusaburo在其题为《期待罗马字应实施汉字限用法》的文章中,指称如果不废除汉字,罗马字终将难以变为日本的国字。2月10日,外国人ShirakiKinzo在其题为《期待罗马字之扩张》的文章中,又以外国人所持立场对罗马字与假名进行比较,并指出汉字的危害,阐述当今进步社会应使用音符文字,尤其罗马字。上述事例表明,在日外国人对罗马字在日本的推广可谓充满期待。
在如此氛围下,罗马字会第二次总会于明治二十年3月19日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榎本武扬大力宣扬罗马字的便利性,并提出普及罗马字的方案;出席会议的美国公使则畅言文字改良是新知识顺利输入并能获得发达的关键,并就改良方法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渡边洪基历数汉字之危害,主张应废除汉字,改用横写书体;外国人B.H.Chmmberlain指出罗马字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依然在使用难解的汉文体这一奇怪现象,宣称如果要采用罗马字,当首先改革文体,只有言文达到一致,罗马字才能成为人们的首选书写文字。
外国人似乎觉得在罗马字的使用方面,他们能给日本提供很多有益的建议,也希望日本能找到罗马字在日本通行的真正途径。5月2日,I.T在其题为《应明确语尾的变化》的文章中,告诫日本人在使用罗马字书写法时应注意历史中假名的用法。6月25日,TiriuoyaKurunn在其题为《会话与书写物间之距离》的文章中,指出无论在何国,都存在着口语与文章语之间有差异的现象,而正是因为这些差异才导致开化即启蒙活动的产生,因此日本无须为现存口语与文章语间的差异感到惶恐,只要在启蒙活动中将口语与文章语结合起来即可,而原有的文章语仍应保留,就像口语适用于俗事,学问之表达则依赖文章语。由此,我们看到一些外国人的主张反倒比某些日本人显得理性。
上述理念又回转到近代教育问题上来。10月10日,外国人O.S.Eby在当日举行的大日本教育会上发表题为《日本教育进步与否在于日本语发达之程度》的演讲,指出一国之发达在于普通教育隆盛与否,而普通教育之起点在于日本是否拥有成熟的本国语言,而日本语能否发达之关键在于是否采用罗马字。这一说法把罗马字的地位提升到“国是”的高度。不论日本国民是否普遍赞同这一说法,与上述言论保持一致的文字改良者却不乏其人。比如,4月23日,涉谷信次郎在茨城县古田部町罗马字会总会上发表题为《假名与罗马字的比较》的演讲,声称较假名,以罗马字记写日语发音更加精细。12月10日,手岛精一在其题为《罗马字在教育上之得失》的文章中,以西洋儿童为例,指出若欲使得儿童迅速获取知识,当采用罗马字。
在罗马字的推广中,外国人以及洋学者积极参与其事成为显著特点。比如,于明治二十一年4月14日召开的罗马字会第三次总集会上,作为外国方的出席者,英国人O.S.Eby发表演讲,就汉字、假名、罗马字进行评述,鼓励日本采用罗马字。6月22日,罗马字会又召集第四次总集会,出席大会的法国公使指出,日本如果想与欧洲诸国保持亲善关系,即便有种种困难,亦应尽可能采用罗马字。外国驻日大使出席罗马字会总集会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参加同次集会的外交官末松谦澄则鼓励人们多练习罗马字,劝导人们即便在最初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只要习惯了就会一切变得自然可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主张假名文字论的前岛密也参加了这次集会,但在他的发言中,只谈到应把汉字从普通文中驱除出去。前岛密的行为再一次证明,当时持不同主张的文字改良者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明确,而为了争取社会对文字改良舆论的同情,他们甚至可以互相利用各自的鼓动力量;同样,他们内部,对改良的方向,也依然会保持不同的观点。比如,在发行于5月25日的《六合杂志》上,即有题为《以罗马字书写日本人名的方法》的刊文,该文作者就目前日本社会存在的世人万般崇拜西洋的现象,提出严厉批评,指称无论如何,在姓名的书写顺序上应保留日本风格。此后倡导罗马字的舆论开始趋于平淡,这大概是其不能获得社会回应的结果。零零落落间,明治二十四年(1891)1月10日,井上哲次郎发文列举日本必须采用罗马字的理由;翌年明治二十五年(1892)8月10日,天国浪人在其题为《关于罗马字的意见》的文章中,对汉字、假名罗马字进行了比较,赞同罗马字采用说,并提出普及方法,与高峰时期的状况相比,正可谓昙花一现。
与此相对应,反罗马字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辰巳小次郎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8月25日发表题为《驳言文一致论》的文章,对罗马字杂志所刊载的言文一致论进行了大力讨伐。其实,文字文体的改良是日本发展现代化过程中的必走之步。只是,由于过激且不合实际的改革目标,导致一般世论对假名文字论抑或罗马字论保持着鄙视抑或警惕的态度,而温和改良论即精简汉字论则附和了大众心声。
3.精简汉字论者
明治十七年(1884)4月,三宅雄二郎在其题为《做假名军之猛将,让世人惊诧》的文章中,首列汉字易学之例,鄙视专用假名之说,阐释罗马字说不可行之理由,附和汉字假名合并说。其实,幕末、明治初期的政府文书所使用的书写文体——汉文直译体即由汉字与片假名组成。这里所提到的汉字假名合并说,其中心意旨在于汉字、假名各占多少比率,以及表述方式是采取汉文书写顺序还是日本语本身所具有的顺序,简言之,是否要将口语的表达方式引入到文章书写中来。
这一时期,对于文字文体改良方向提出研究性建议的有矢野文雄。明治十九年(1886)3月,其所著《日本文体文字新论》出版,这是他主张精简汉字的研究性结果。为将精简汉字理论联系到实践中去,他力行编纂《三千字字引》,于当年发表在《邮便报知新闻》上。矢野文雄的主张在温和改良论者中极具代表,因其提案富有可行性,其著书不仅在出版当初即引起人们关注,甚至到了文字文体改良已成为一种社会趋势的90年代也是重要的参考书目。因此,通过解析《日本文体文字新论》,我们可以基本获知80年代温和改良者的主张。
根据佐藤宽的分析,矢野文雄将日本现用文体划分为汉文体、汉文变体、杂文体、两文体、假名体等五大类。在这些文体中,矢野非常欣赏两文体,意外给使用者带来诸多便利。就像今日大量使用该文体的报纸,这些报纸日发行几十万份,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如果没有这些报纸,可能一天接触一个汉字的机会都没有。但是近来因为有了这样的读物,甚至妇女或孩子,只要是每日读报的人,都可以跟随文中汉字旁加注的假名文字来接触汉字。如此,一天一份报纸,可接触到上千的汉字,如果每日坚持读报,5、6个月下来,那些常见汉字便能以这种自然的方式记住,而起始不过是仅仅知道四十余字假名文字的人,通过这些假名,却意外地很快记住了一些汉字,即由最开始须通过假名来理解汉字,逐渐发展至可以直接阅读汉字。两文体其实是汉文体与假名体的结合。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可以是一种假名体;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可以是一种杂文体;而对某些人来说,它开始可能是一种假名体,其后又发展成为一种杂文体。对于那些不识汉字的妇女或蒙童来说,通过阅读这样文体的文章,他们获得了逐渐习学汉字的机会。此种文体大放异彩。据此,我们看到,不论国民教育中使用的教科书是否使用这种两文体,为获取最大读者群的报纸、杂志却喜欢使用这种便捷的两文体,而社会的改革力量由此得到壮大。
在汉字教育方面,矢野如是说:在常用汉字里,名词之数,从人体到天地、山川、舟车、器具、禽兽、鱼介、草木,凡八百有余,再加上一些珍稀之草木、禽兽、鱼介,其数约在一千五百内外。动词、形容词、副词、前置词、代名词、间投词、接续词等,约为八百八十有余,前者八百加之后者八百八十,两者相加不过一千六百八十有余。其中,尚有或以一字对应一语,或以两字对应该词语的情况存在。如此,其数或又可略减三五。于是,在矢野所提出的精简汉字方案里,日常汉字的数量被设定在二至三千字。佐藤宽在其出版于90年代的著述中非常赞成矢野的意见,认为以二三千汉字,加之于日本五十音字即假名文字而形成的文体,无论于阅读抑或书写,均十分便利,非他国文字可比。
矢野文雄在其著《日本文体文字新论》中,将当时的日本语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日本土语有而中国语无的语词,可被称为“長持类”语词;第二类为中国语有而日本土语无的语词,可被称为“簞笥类”语词;第三类为日本土语、中国语皆有的语词,被称为“(ツルギ)、(ケン)类”语词(它们分别是“剑”字的训读和音读)。这三类词中,第一类以及第二类词只有一种语体,而第三类词就会有两种语体(土语与中国语各一)。接着,他具体分析道,因中国文明悠久,第一类语词较少,而第二类语词则较多,比如“仁、义、孝、悌”等类语词在传入日本时,均找不到可以对应的日本土语。结果导致在日语中,有相对的土语,就在汉字旁加注训义;没有相对应的土语,就直接借用汉字的原字原意。日本土语不仅数量小,发音亦少。随着中国汉字、字音的输入,日本土语的发音开始丰富起来。这种现象与日本后来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时的情景很相似。
据此他认为,假设现在抛弃汉字,只用日本假名,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只用日本土语将给人们带来生活不便,原本想读两册书的人大概读了一本也就够了,原本想读20页书的人在读完10页后就会显得疲倦,这样可能会大大妨碍人民拓展知识的前进步伐。简言之,人们只有在阅读用自己喜爱的文字所创作的书籍时才会不自觉增加阅读时间。他说,日本不能放弃汉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语的发音仅有330余个,而中国语的发音在1300个以上,这导致日语中同声同义词众多,不及中国语,即日本语需用中国语之形字来弥补日语发音少易产生歧义的缺陷。他总结道,在本邦事物中,仅有中国语、无日本土语者,固然要用中国语,然中国语、土语二者皆有者,在必要之场合亦须采用中国语,这其中的奥妙乃在于利用平声音词可以大大精炼抑或缩短由短声词、急促声词构成的冗长语句。今天,我们提倡用假名书写文章,并不是旨在废除汉字,中国语弥补了日本土语多由短声词、急促声词构成的缺陷,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没有了汉字的日语将会呈现出怎样糟糕的状态。于此,矢野文雄清楚给出了汉字不可废、只能精简的充足理由。
矢野文雄的改革提案代表了温和文字文体改良者的改革方向。明治十九年4月10日,大森惟中在教育会总集会上发表题为《文章的变迁》的演讲。他从教育与语言文字间之关系说起,略述和汉文章的变迁,随着外国语的输入,固有的语言文章不免衰退,当今文章之晦涩难读实有害于教育。9月,帝国大学设置博言学科。明治二十年,在罗马字论者不断掀起股股社会浪潮的背景下,5月8日,中村正直在学士会院发表题为《汉学不可废论》的讲演。明治二十一年3月11日,西村茂树在学士会院发表题为《日本的文学》的讲演,指出不可废弃汉字的理由。明治二十二年(1889)1月,有贺长雄在其题为《汉字在日本教育里的地位》的文章中,从事实上、法式上、艺能上等三方面阐述汉字不可废弃的理由。
余 论
这一时期,文字文体改良呼声虽然不断,但于官方而言,文字以及文体到底以何种状态给予固定仍需时日洗练。笔者列举一本发行于明治20年(1887)的小学生用普通读本字引即可反映出明治日本政府的态度。这部字引显然是为小学用精读读本而编纂的,其所载字、词基本来自读本。据笔者统计,该部字引共收纳单个汉字即单字词847个,双字或双字以上汉字词1509个,若按照双字词计算,汉字在3000个左右,两项相加,并清理重复汉字,该部字引收纳汉字当在3000以上。若此,这一标准与明治初期发行的小学用普通读本字引所收纳的汉字数量差距不大。也就是说,尽管社会上要求精简汉字的呼声不断,但在实际的基础教育阶段,汉字基础掌握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欧洲现代化对世界各地域所造成的影响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将19世纪以来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择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们除了要将其放入本土的历史环境中去进行观察外,尚须观察欧洲现代化对该研究对象所造成的影响,即无论承认与否,我们的研究对象如果在这个被我们称之为特殊时期的历史场景里发生了某种变化,其变化均与欧洲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性。具体到本文,就是要透过对汉字汉文在近代日本之演变状态的观察,来细节性地解读日本欧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读那些明治时期的出版物,犹如面对一个又一个活跃于明治时期的人物,他们或激昂或平静地讲述着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以及他周边人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一个栩栩如生的明治日本社会,这符合历史研究者努力要回到历史中去观察历史事件的诉求。我们会愕然发现,在那个时代的社会里,日本读书人对于汉学的态度,并不像日后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嗤之以鼻,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憧憬;而对于西学的态度,亦不像日后人们所揭示的那样欣然敞开怀抱,迟疑中的前进是他们真实的情怀。而19世纪80年代,汉字精简论在众说纷纭中占据着日本文字文体改良舆论中的主导地位即是上述状态存在的明证。这一主张最后成为明治政府着手推进日本文字文体改良的重要参考与依据。
①④⑤⑥朝仓治彦、稻村彻元编:《明治世相编年词典》,第26、59、645、131 页。
②朝仓治彦、稻村彻元编:《明治世相编年词典》,第32、44、62、86、104、117、129 页。
③朝仓治彦、稻村彻元编:《明治世相编年词典》,第47、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