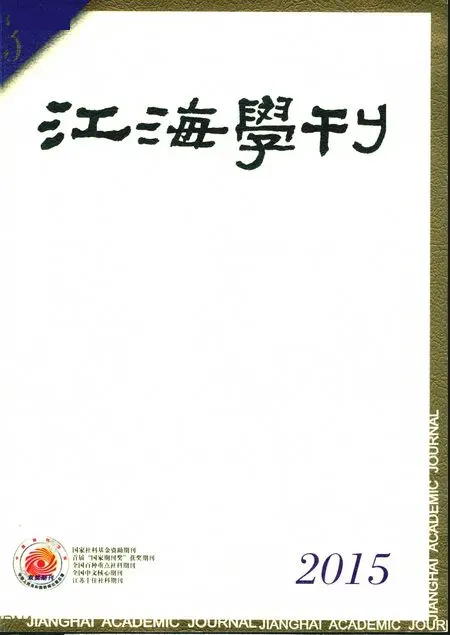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2015-04-18魏志江魏楚雄
魏志江 魏楚雄
十到十四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也是东亚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欧洲海洋交涉网络正式形成的时期。所谓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略称海丝路或MSR),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内涵迄今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本文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其内涵应该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并沿半岛西海岸南下,经日本博多湾、九州和西南诸岛以及琉球群岛一带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向西南延伸,经中南半岛南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红海乃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基本特征:(一)必须是以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为输出或枢纽港,并形成常态的海上航线;(二)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土特产品为主要输出品,并承载相关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人文的交流;(三)海上丝绸之路并非单一的航线,而是沿相关航线区域形成的呈交叉形态的海上交通网络。因此,十至十四世纪,中国宋元王朝与朝鲜半岛高丽王朝之间的海上航线和海洋经济文化交流,无疑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高丽时代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主要代表是中国学者方豪、宋晞、陈炎、陈高华、吴泰、王文楚等①;国外代表性学者,无疑应首推韩国东亚大学金庠基以及高丽大学史学科李镇汉教授等,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高丽时代中韩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②。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高丽时代中韩海上航线的演变、中韩海上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东亚海洋交涉网络的形成等问题加以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高丽时代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
十至十四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韩海上丝绸之路演变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中韩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此一时期,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和发展:
第一阶段(918~1071)。此一阶段,中韩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918年,高丽王朝建立,与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主要是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交往。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也是利用此航线,《宋史》载:淳化四年(993)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陈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高丽王遣使白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③。考宋之登州,郡名东牟,今山东蓬莱县;八角海口,即今山东福山县西北八角镇;芝冈岛即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而高丽翁津即今朝鲜海州西南翁津;阎州,今朝鲜延安;白州,今朝鲜白川。④《宋史》谓:“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⑤故登州一直是五代、宋初以来与高丽往返的海上航线,《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谓: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⑥。宋仁宗时亦谓:“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⑦故自高丽建立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宋丽海上交通主要利用此段航线,这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中韩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及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进行往来的主要航线。此外,作为此航线的网络支线尚有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至高丽翁津口登陆,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第二阶段(1072~1270)。此一阶段,中韩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由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其具体航线,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至三九《海道》有明确的记载,学者王文楚教授也做了深入的考证。⑧简言之,从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虎蹲山),东至昌国县(今定海县)沈家门、补陀洛迦山(即今普陀山),自此出海,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今浙江沿海、长江以北至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亦称黑水沟,今马里亚纳海沟洋面,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洋面;经夹界山,亦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今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为中国、朝鲜领海分界处,即为中国与高丽海上分界线;过白山,今大黑山岛东南之荞麦岛;经黑山,今韩国大黑山岛,为中韩海上丝路南路之枢纽,船舶往来停歇地;过黑山岛后,沿群山列岛海岸北上,抵紫燕岛,今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位于首尔东南,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今仁川西之永宗岛⑨;至急水门水道,进至礼成港,于碧澜亭上陆,再由陆路抵达高丽都城开城。碧澜亭,今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由此舍舟登陆,去开城。自北宋神宗熙宁后至南宋,宋丽之间海上航路盖经由此路。如趁季风便利,五六日即可抵达。此外,南路航线还有泉州港,亦为与高丽贸易之重要港口⑩,如苏轼谓:“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南宋时,海外贸易发达,有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商舶常往来泉州,并成为泉州遂北上连接明州与高丽,以西连接粤东、广州通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不过,其与明州港相比,主要还是南洋、印度洋以西的船舶往来的港口,并不能取代明州在对高丽海上往来中的地位。
第三阶段(1270~1357)。此一阶段,中韩明州海上航线衰落,元朝海运兴起,其主要以太仓(今江苏太仓)为起点,沿海岸线北上,经山东半岛到沙门岛,入莱州洋,再由渤海湾北上,经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西海岸。元丽运粮以及海上贸易往来,多由此条海运航线北上,并由山东莱州湾至辽东半岛到高丽西海岸。而元丽官方朝贡贸易往来,则主要是从辽东陆路往返,即由大都(今北京)沿陆路经山海关抵辽东半岛,渡鸭绿江南下,抵达高丽都城开城。此外,元代海运虽然逐步取代了明州对高丽贸易的地位,但是,泉州港却仍然是与高丽往来的重要港口,如元代时来华的马八国王子孛哈里“居泉州”,娶高丽女子蔡氏为妻,高丽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曾遣使向高丽王献礼物。据陈高华先生考证,其即是由泉州从海路到高丽。
第四阶段(1357~1392)。此一阶段,由于元末中国战乱,南北交通隔绝,海运无法继续,所以,以庆元(今宁波,即宋代的明州)、泉州和太仓为中心的江南航线成为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南方割据势力张士诚占据以苏州为中心的浙西地区,方国珍占据以杭州为中心的浙东地区,这些割据政权继续与高丽进行海上贸易往来。张士诚政权与高丽的贸易以及明初高丽使者往返两国,主要通过苏州太仓作为两国的港口;而浙东方国珍政权则主要通过庆元港(今宁波)与高丽往来。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刻有“庆元路”字样的秤砣,一般认为该沉船即是由方国珍割据浙东时从庆元路起航的。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韩海洋经济、文化交流
高丽时代,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承载着物质文化的交流,也承载着精神文化的交流。
首先,中韩之间的海洋物质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两国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个方面。朝贡贸易是高丽时代中韩两国最传统也是最基本的贸易形态,两国都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朝贡贸易的机构,如宋元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以及密州板桥镇设置市舶司,此外,还在澉浦、华亭、温州等地创置了市舶场或市舶务。市舶机构掌“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其中,广州和泉州市舶司,主要掌往来南海诸国的海上贸易品,而明州和杭州市舶司,则主要掌往来高丽、日本等东北亚海上的船只物货,所以,中韩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贸易往来,主要是由明州和杭州市舶司管理。市舶司主要负责对高丽朝贡物品的检验、解运、收纳、交易和处理等贸易事务。但是,元朝统一中国后,随着海运的兴起和陆路贸易的开拓,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贸易由海上贸易转为陆路贸易为主,即从元大都出发,经辽东半岛,渡鸭绿江,趋平壤南下,抵开京。不过,民间贸易仍有沿袭海上丝路者,如《朴通事彦解》记载高丽来的商人赵舍就是从海路上来到元朝进行贸易的。只是元成宗七年(1303)实行海禁政策后,元丽的民间海上贸易被迫中断。迄元末战乱,方国珍割据浙东,才开始重新启动宋朝明州(元改称庆元,即宁波)至高丽的海上航路。此外,高丽王朝不仅对中国海商设置有专门的驿馆,而且,也相应地制定了有关管理王室朝贡贸易的制度,主要是掌管中国皇帝颁授的诏书和领受皇帝的恩赐,而高丽大、小府寺则负责收纳、处理中国皇帝赐予的物品以及向中国王朝进方物等事务。中国从海上输往高丽的贸易品主要是各种绫罗绢纱等丝织品和赐予高丽国王的衣带等服饰、鞋靴之类物品以及瓷器、茶叶、药材、沉香、玉器、金银器、乐器、鞍马、笔墨纸砚等,而高丽对中国的输出品则主要是衣褥、银器、铜器、人参、麝香、松子、药材、苎布、香油、草席、折扇、松烟墨、狼尾笔、螺钿漆器等。显然,双方交易以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当然也有部分物品如香料等为少数从南洋转运而来的交易品,反映了十至十四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
其次是中韩民间海商经营的贸易活动。新罗时代,在东亚海上航行的最大的贸易集团是崛起于朝鲜半岛东南端莞岛海上的张保皋贸易集团,其一度垄断了东亚的海上贸易。十至十四世纪,活跃在东亚海域的海商主要是宋朝和元朝海商,他们从东南沿海横渡东海,组成中、小型船队前往高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抵达高丽之后,宋商在礼宾省的安排下,住于高丽清州、忠州、四店、利宾等馆驿中。这四座馆驿为高丽专门接待宋商的客馆,宋商在高丽的贸易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与高丽王室进行的所谓“朝贡”贸易,在《高丽史》中多被记载为“献方物”等,高丽国王再以“方物数倍偿之”;另一类是民间进行的自由贸易。对于宋商进行的民间贸易,由于高丽并无统一固定的市场,“唯以日中为虚,男女老幼、官吏工技、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而且,高丽也无抽解和征税的制度,只是宋商回航时,高丽监察御史要对商船进行检视,以防止违禁物品出境。除了宋商来高丽贸易外,高丽商人以王室为首也经营对中国的海上贸易,丽商主要依附于高丽使团和搭载宋商船进行贸易,其贸易品主要是银器、铜器、螺钿器、苎布、绸缎、人参、麝香、松子、药材以及香油、草席、折扇、松烟墨、狼尾笔、高丽纸、漆器等,以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织品和药物、香料、书籍、佛教用具、玉器、木器、文具等各种物品,而明州则是丽商在华进行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最后是中韩海上的精神文化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交流,也是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在人文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主要体现在:
第一,两国人才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这是高丽时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中韩人文交流最重要的成果。十至十四世纪,中国宋元王朝都有大量士人移居高丽,并出任高丽的官职,而高丽也派出大量留学生进入宋朝国子监求学,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有的还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并一举及第。高丽光宗七年(956),后周进士双冀入居高丽,并于光宗九年(958),正式将中国的科举制度引进高丽,效法中国,以进士、明经科为主,开科取士,从此,科举制度成为高丽教育培养人才的主要制度,极大地促进了高丽文教事业的发展。
第二,使臣交往的诗词唱和。如高丽使朴寅亮《使宋过泗洲龟山寺》云:“门前客棹洪涛急,竹下僧棋白日闲”,深受宋人赏识,宋人将其与金觐的诗文合刊为《小华集》,而宋人苏东坡词更为高丽文士所喜爱。高丽忠宣王留居元朝大都,筑万卷堂,高丽文士李齐贤等与元朝名士阎复、姚燧、赵孟頫、虞集等文人多有诗词唱和与交流。此外,元代赵孟頫的书法——松雪体风格亦颇受高丽文士喜爱,并流行于高丽。
第三,音乐、舞蹈的交流。主要是《高丽史·乐志》保留有宋雅乐,而雅乐在中国已失传矣,宋神宗时,有高丽乐人随使节来东京献艺舞蹈,宋丽音乐交流主要在宋徽宗时期。
第四,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来华,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版《大藏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以及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方国珍主政浙东时,还专门向高丽赠送《玉海》《通志》等典籍。而高丽由于“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因此,也有大量书籍输往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此外,宋本已不全的《说苑》,赖高丽所献方得以补全;而已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由高丽重新输入宋朝。高丽忠肃王元年(1314),高丽博士柳衍奉高丽国王之命赴中国江南购买书籍10800卷,同年,元仁宗赠送给高丽宋秘阁所藏善本书4371册,达一万七千余卷。
第五,宗教文化的交流。因高丽举国信佛,故宋元与高丽的宗教文化交流主要是佛教的交流。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大藏经》的互赠和交流;高丽僧人谛观、义通和高丽王子义天来宋朝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尤其是天台宗有关典籍的回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丽僧义通也被尊为天台宗第十六祖嫡传祖师。而高丽王子义天,宋哲宗时来中国,遍访名山古刹,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其带来华严宗大量的典籍足可以补中国华严宗典籍之缺,其从杭州慧因院净源法师学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义天还向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请教天台教观之道,义天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余卷,并主持高丽国清寺,在高丽弘扬天台、华严二宗,提倡教观兼修,还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而元朝高僧绍琼应高丽僧人邀请去高丽弘法,高丽僧冲鉴拜其为师,以《百丈清规》为高丽禅宗寺院的法规,而绍琼被尊为“瑝明国师”;高丽僧宝鉴国师混丘与中国僧人也多有交往,元禅师“尝作《无极说》,附海舶以寄之,师默领其义,自号无极老人”。可见,高丽时代,两国高僧经常通过海上航路进行文化交流。
第六,陶瓷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唐末五代以来,浙江越州(绍兴)龙泉窑烧制的青瓷,薄如纸、声如謦,为瓷器中之珍品,深受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喜爱。新罗末,张保皋的贸易船曾经从越州带回陶工,开始了朝鲜半岛烧制青瓷的过程,故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谓:韩国烧制瓷器是“通过掠越州窑工来实现的”。故高丽时代,浙东烧制青瓷技术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韩国的康津成为青瓷的烧制基地。在学习宋人技法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高丽陶瓷工匠进一步进行改良,将青瓷颜色由真绿色变为影青瓷釉,烧制出蜚声中外的高丽翡色青瓷,其器形、纹饰也多有变化,纹样有细阴刻草花纹、刻菊唐草纹、阴阳刻莲瓣纹等,被宋人徐兢赞誉为“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唯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㉔。由于高丽烧制青瓷技术的提高,高丽时代成为韩国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型时期,高丽也由瓷器的输入国一跃成为对日本乃至东南亚瓷器的输出国。
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十至十四世纪高丽时代的中韩海上丝绸之路,是东亚海域交涉网络形成的关键时期,以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初步形成了连接东亚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的海上航路,主要体现在:
第一,十至十四世纪,东亚海域形成了一系列港口群,除中国的登州、杭州、明州(庆元)、泉州和广州港外,韩国翁津、开城、仁川、群山列岛、黑山岛、济州、合浦等和日本博多、平户、琉球等都成为东亚重要的对外交涉港口。高丽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泉州港崛起,并与广州港相连接,成为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海域交流的枢纽港口,泉州港以东、以南,有广州为集散地,主要是与东南亚诸国海上进行交易;泉州港以北,主要是与明州港对接,连接高丽、日本,进行海上贸易和人文往来。随着印度、阿拉伯商人从东南亚、印度洋海路来华,并渡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泉州遂成为连接东、西部海上航路的枢纽港,并以明州、泉州、广州为中心形成东亚海域的贸易网络和区域集散地,如中韩海上贸易的沉香等香料和象牙、玳瑁、犀角、珍珠等海产品以及部分药材等,均产自西亚或东南亚诸国,而非中国与高丽本土所产,其中,泉州市舶司就经常收入大量从西亚、东南亚进口的乳香、西洋药材以及犀角、玳瑁等海产品,而大部分香料都会运到京城香药库,通过中韩海上转、赐贸易等形式进行交易。东亚大量港口群的出现,标志着东亚海上区域交流网络的初步形成。
第二,十到十四世纪,不仅形成了连接中日韩三国的海洋航路,而且,也形成了东亚海洋区域交涉的网络。新罗后期,东亚海域的交涉,基本上被张保皋海上贸易集团所垄断,但是,即使是张保皋经营的东亚海洋贸易,仍然是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过渤海湾,抵达山东半岛的航线,其时,中韩之间的南路航线,即明州航线并没有成为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路。但是,高丽中、后期,明州至仁川的东海航路已经成为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值得注意的是高丽忠烈王时期,随着元丽联军海上对日本的征伐,初步开辟了由高丽西南海岸沿群山列岛南下,经济州岛、釜山,并抵达日本对马岛、壹岐岛、博多湾和九州的航线,而元江南军从庆元港出发,直接开辟了由庆元抵达平户岛与元丽联军会师的航线,从而形成了以平户岛为枢纽的东亚海上交涉网络。因此,元日之间的贸易航线,“在元朝是庆元(宁波),在日本是博多。因此,所有的商船都往来于这两港之间,从而航路一般也是横渡东中国海,航海日数似乎只是十天左右”㉕。此外,高丽三别抄抗蒙和琉球王国的建立,也促进了中日韩三国东亚海域网络的形成,㉖琉球成为东亚海域交涉网络中的重要环节。
因此,十至十四世纪的高丽时代,东亚中日韩三国的海域交涉航线基本上形成,即(一)大洋路:由日本九州北部经五岛列岛,到达浙江、江苏沿海;(二)北路:由九州北部经对马岛,抵达朝鲜半岛,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渡过黄海,到达山东半岛,遣隋使、遣唐使均沿用此航路;(三)南岛路:由九州南部南下,经西南群岛、琉球群岛,抵达福建沿岸。大体上,十到十三世纪以前,日本与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海洋交涉,基本上是采用北路和大洋路,而琉球群岛成为东亚海域的枢纽,并作为日本直航福建沿海的所谓南岛路,至迟应该在十四世纪已经形成。
第三,十至十四世纪,随着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西亚等国贸易联系的加强,东亚海域交涉网络得以正式形成。此一时期,出现了东亚海上跨区域贸易的明显特征,尤其是从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大食等东南亚、中东诸国转运来的香料、象牙、玳瑁等物品,通过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等形式运到中国,除部分留在当地的市舶司以外,大量运到京城的香药库,如宋太平兴国初年“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并成为中国转赐高丽的重要奢侈品,表明东亚海域贸易网络已经在逐步形成。此外,泉州商人孙天富、陈宝生二人“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阇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显然,元代的泉州,已经成为连接东亚海域贸易网络的枢纽。此外,高丽末昌王时期,琉球国遣使向高丽献方物,其中包括胡椒三百斤,表明以琉球为中介的东亚转口贸易已经形成。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亚洲最大的古代沉船后,从1976年至1984年,从新安沉船打捞出2万多件中国元朝陶瓷器,28吨达800多万枚中国铜钱,1000多件紫檀木等众多水下文物,其中发现有高丽青瓷,故可以判断新安沉船的瓷器应是输往日本。如此说成立,那么也佐证了东亚中日韩三国已经形成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到高丽群山列岛西海岸,并南下经济州海峡到日本对马岛、博多湾沿岸的海洋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
结束语
高丽时代的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洋区域交涉网络的形成,于东、西方海洋交涉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随着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十到十四世纪,东亚海洋世界真正形成。由于海洋世界的边缘性特征,大陆中央王朝的权力往往难以控制海上世界。海上居民的自由流动和海洋的物质文化交流使得东亚海域形成由山东半岛经黄海,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济州岛、九州和博多湾以及琉球群岛到中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等的海洋交涉网络。海上世界具有完整的地域关联性和共同的海上信仰、宗教、民俗等文化生态特征。但是,随着近代民族和主权国家的构建,阻碍了东亚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海洋地域文化的主导地位。”因此,东亚海域相互关联的海上世界,随着各主权国家海洋权力的扩张,海上世界的完整性被打破。由主权国家制定的领海、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法将海上世界分割隶属于各自主权、民族国家的范畴,并导致了海域世界的纷争。海上世界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相对完整的区域,如何打破岛屿和有关海域权力的纷争,恢复海洋世界本身的相对完整性,并实现海洋沿岸国居民在海上的自由流动和物质、文化的交流,无疑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性基础。
①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②[韩]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景仁文化社2011年版;金庠基:《东方文化交流史论丛》,乙酉文化社1948年版。
③⑤《宋史》卷四六六《高丽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④光绪《山东通志》卷二七《登州府·山川》,参见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载《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3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六年(年)五月,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⑧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载《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页。
⑨参见[日]津田左右吉《朝鲜历史地理》卷二《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
⑩《宋史》卷三三一《罗拯传》:“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
㉔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二之二,“知不足斋”本。
㉕[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1页。
㉖参见《日本と朝鲜半岛2000年下》,日本NHK2010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