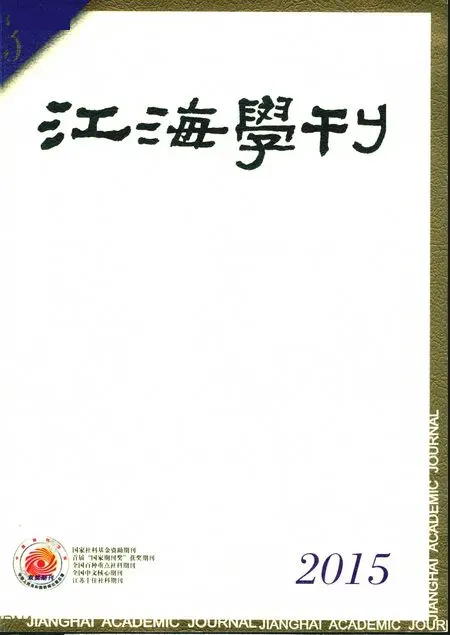社会动荡发生概率降低趋势的分析*
2015-04-18吴忠民
吴忠民
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是一个不争的常识。不过,社会矛盾的一些具体样式却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一个社会由传统社会逐渐走向现代社会(社会转型)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历史大趋势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动荡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但是,如果不是从不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如国家利益矛盾与冲突)的角度着眼,而只是就同一社会共同体当中的社会矛盾相关方(社会矛盾相关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言,社会动荡尤其是激烈的社会动荡发生的概率在逐渐降低。正是类似的一些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多个重要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社会动荡发生概率的降低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与社会骚乱等社会矛盾冲突现象明显不同,社会动荡一般是指“重度”或“极度”的社会不稳定、不安全的现象。①从强度等级角度看,同一般的局部性、区域性的社会矛盾冲突不同,社会动荡是最为严重、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动荡的基本特征在于:一是目标的颠覆性。从抗争目标角度看,社会矛盾相关方的关系已经是“誓不两立”、不可调和,抗争方往往以颠覆现有的基本制度、摧毁现有的政权为主要和直接的目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②。二是后果的严重性。从抗争后果角度看,社会动荡所引发的后果往往十分严重,甚至具有严重毁坏性,且涉及面广泛,往往会造成如是情形:经济发展出现停顿甚至倒退,整个社会失去控制,各种社会抗争力量蜂起,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迅速攀升,致使民众生活陷入苦难状态。社会动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伤筋动骨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三是有时冲突方式的激烈性。从冲突方式角度看,社会动荡有时伴随着激烈、流血甚至惨烈的暴力冲突方式,导致生灵遭受涂炭。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社会转型)来看,一个明显的历史大趋势是,就同一社会共同体内部而言,社会动荡特别是激烈的社会动荡的发生概率在降低。尤其是从现代化由低到高的发展进程来看,更是如此。
在传统社会,一般来说,社会动荡发生的概率相对较高,而且社会动荡有时会以一种十分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使整个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当一个社会文明程度不高,生产力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时,其基本生活资源一般而言是比较匮乏的,极端精神因素的影响比较大,社会成员的包容意识相对不够,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工合作、相互依赖程度也比较低,社会同质性较强、异质性较弱,民众从众心理较强,制度也缺乏足够的容纳与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一旦出现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围绕着最为基本的生存资源而争斗的严重问题,则容易出现颠覆性的、激烈的社会动荡,并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在文明程度较低的传统社会当中,颠覆性的、激烈的社会动荡往往呈现出一种十分惨烈的场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末年和明朝末年所发生的社会动荡就是如此。据《旧唐书》记载,黄巢再次攻陷京师后,“怒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俘人而食,日杀数千”。③《明史》有记载,张献忠“入黄州,黄民尽逃,乃驱妇女铲城,寻杀之以填堑”,“又西陷汉阳,全军从鸭蛋洲渡,陷武昌,执楚王华奎,笼而沈诸江,尽杀楚宗室。录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为兵,余皆杀之。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胔蔽江,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将渡,风大作,献忠怒,连巨舟千艘,载妇女焚之,水光夜如昼”④。
社会动荡往往会引发巨大的社会灾难。社会动荡必然意味着经济运行的停滞和半停滞,民众日常生活陷入苦难状态,意味着社会战乱、社会暴乱持续不断,严重者,甚至会使广大生灵遭受涂炭。特别是在传统社会,更是如此。有学者通过统计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每次社会大动乱通常都有兵燹、饥馑、瘟疫接连发生,所以才造成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历史上共有7次人口数量的大振荡,其中古代6次,分别发生在秦末、西汉末、东汉末、隋末、唐末五代、元末明初。其振荡的幅度,有的接近50%,有的则超过50%。中国古代人口数量大幅振荡的时期,一般也是古代社会发生大动乱和统治者‘改朝换代’的时期。或者说,每次人口数量的大幅振荡在社会层面对应着一次‘天下大乱’”⑤。
在现代社会,社会动荡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小。自“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历史跨入21世纪以后,社会矛盾相关方利益诉求的表达及抗争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抗争活动虽然仍然存在,并且在有些局部地区,社会骚乱十分激烈,如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等。这些社会骚乱有时甚至会造成一些流血冲突事件,如美国1967年的底特律种族骚乱以及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事件等。但是,具有颠覆性的、涉及全国范围的、具有伤筋动骨破坏性的并且伴随着激烈流血方式的社会动荡已经大幅度减少,已经很少出现。雷蒙指出,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趋向是,“逐渐摆脱消极状态,加紧展开请愿活动;革命运动的势头和运用暴力的癖好逐渐减弱”⑥。
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表明了它们所要追求的是更人道的、更纯洁的、更有文化的社会,一种更为自由的私人生活,以及追求政治活动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种向往正好与工业社会的传统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相矛盾,后者关心的是物质要求的满足,即生存与安全需要。”⑦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社会抗争活动,即便规模很大,也鲜有以颠覆现有的基本制度、基本社会秩序为主要目标,以激烈流血冲突为主要抗争方式,并且造成严重社会灾难的社会动荡现象出现。比如,2009年1月29日法国发生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活动。这场罢工活动由法国总工会、民主总工会、公务员联合会、全国自治公团联合会等团体发起,提出的利益诉求是就业保障、提高工资、减少不平等、改善劳动条件等。当天法国各地有近200场示威游行活动,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参与了这次大罢工活动,造成了数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这场罢工活动尽管规模巨大,但并没有提出颠覆基本制度的目标,没有出现激烈流血的对抗,也没有引发巨大的社会灾难。再如,2011年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活动,提出的利益诉求是反对权钱交易、反对社会不公。这场活动也是规模巨大,波及100个城市以上,虽然如此,但这场活动同样并没有以颠覆现有的基本制度为目标,也没有出现激烈对抗流血的局面,没有造成社会混乱无序的局面,更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呈现出一种相对复杂的情状。这大致可以以“二战”为界限。“二战”之前,转型期的社会动荡有时会出现,而且有时还带有激烈冲突的色彩;之后,社会动荡有时还会出现,但大规模、激烈、流血性的社会动荡已经难以出现。
在19世纪的早期工业化的国家,惨烈的社会动荡时有出现。以巴黎公社为例,可以看到矛盾双方惨烈冲突的情景。“在通向巴黎各要冲的战斗中,公社社员牺牲了不下1万5千人,在5月21日至5月28日的街垒战中,阵亡的总人数约达2万5千人之多。”⑧“在‘五月流血周’中,整个巴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在战火熄灭后,梯也尔仍然在巴黎大开杀戒。有两万人未经法庭审判被杀害或枪决,此外,1万3千人被判处流放阿尔及利亚或新喀里多尼亚。”⑨
“二战”后,一些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在转型期间仍然会出现某些社会动荡的局面。不过,这些国家社会动荡的激烈、惨烈程度或许会有所降低。虽然如此,但是这些国家社会动荡所引发的巨大社会灾难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仍然在所难免,并且经济结构的重建十分艰难,为以后的现代化建设留下巨大的隐患。
就“二战”后转型期国家的社会动荡状况而言,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动荡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社会动荡的局面。俄罗斯也曾在短暂的时间,在局部的区域出现较为激烈的、流血的社会冲突现象,如曾出现炮击“白宫”(议会大厦)的现象,但持续的时间不长,影响的范围有限。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社会动荡主要表现在社会失去了正常的运行秩序,经济遭受重创,特别是俄罗斯民众的基本生活陷入了一种十分苦难的状态。经此社会动荡,“布热津斯基直言俄罗斯已经跌落到‘第三世界的水平’。普京称之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和民族灾难’”⑩。这些,十分明显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上:其一,经济严重滑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连续7年平均以每年6.77%的速度衰退,1992年GDP下降幅度高达14.5%。1998年 GDP只有1991年的60.6%。”其二,通货膨胀严重,居民收入严重缩水。“消费价格指数1992年达到26.1倍,1993年达到9.4倍,到2000年为1991年的73.15倍。”“居民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2000年不足1991年的一半,劳动者实际工资1999年只有1991年的36%。1992~1995年平均工资增长了392倍,而物价却上升了1608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在1992年和1998年分别达到53%以上。人口平均以每年75.9万人的速度减少,1991~2000 年共减少 672.6 万人。”其三,失业率大幅度增高。“根据俄罗斯科学院就业问题研究所统计,俄罗斯的失业率1992年为4.76%,1993 年 5.6%,1994 年 7.43%,1995 年 8.21%,1996年9.05%。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奥西波夫认为再加上大量的隐性失业者,实际失业人数已达有劳动能力总人数的13%。”其四,人的预期寿命大幅度降低。“俄罗斯男子的预期寿命1987年时为65.1岁,1989年为64.2岁,1991年降到 63.5岁,1992年为 62岁,1993年降到了59岁,1994年又降到57.5岁,1995 年为58.2 岁,1996 年为 59.6 岁。”
由上可见,作为一个历史趋势而言,随着历史进程特别是现代化过程的推进,社会动荡发生的概率在明显降低,强度也在降低。
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为何减小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动荡之所以会出现大幅度减少,其主要原因如下所述:
第一,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已经不成问题。
伴随着大工业的兴起,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二战”以来,高科技获得了突飞猛进,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技术获得了急速的发展。在高科技和互联网的推动下,人类创造潜能得到了巨大的、倍增的开发。凡此种种,使得人们生活资料总量以及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得到了大幅度增加,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基本生存的需求。
除了物质文明获得了长足发展之外,在现代社会,以人为本、自由、平等等现代理念被人们普遍认同,制度文明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些又具体体现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度化和体系化。比如,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北欧国家已经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社会福利制度,几乎全面覆盖了社会成员人生各个阶段以及职业生涯主要方面的需求。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注重对贫困者的援助。以失业救济为例,英国现行制度规定,如果失业者是单身,每周可以领取45.45英镑的失业救济金;如果他的妻子或伴侣没有经济来源,则升至每周73.5英镑。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凡是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一般都不高,甚至偏低。2000年前后,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28,法国为0.33,挪威为 0.26,丹麦为 0.25,瑞典为 0.25,英国为 0.36;美国最高,也不过0.41。在这样的条件下,基于民众基本生存问题而产生的大规模的、颠覆性的、暴力流血的社会动荡现象已经几乎不可能出现。
第二,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极端精神因素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小。
现代化过程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世俗化生活世界的形成。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只能满足于简单的生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多数社会成员亦即农民的固定生活方式,多年一贯不变,人们对生活甚至都缺乏想象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乎就是最高目标。人们即便有什么理想目标,也大多由于缺乏相应的能力而无法实现,只好将之作为一种乌托邦目标放到彼岸世界或者是遥远的未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必然缺乏“人”的自我意识,而只能是匍匐在神灵脚下,乞求神灵的保佑。这是一些极端宗教力量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基础。而伴随现代化过程的推进,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以人为本的意识在觉醒并被广泛认同,人们已经摆脱了以往简单的生存与再生存的生活观念,越来越重视现实的世俗化生活问题,越来越重视社会质量的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极端宗教意识逐渐淡漠。极端宗教意识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很难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日益减退,宗教信仰越来越成为个人的私事。”
现代化过程还意味着社会成员独立意识和理性意识的普遍形成。在传统社会,民众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和蒙昧性的特征。当时,人们在经济领域当中的严重人身依附性也延伸至社会领域和精神文化领域,表现为社会成员缺乏自主性,个人的行为和观念容易为群体或强势人物所左右。再者,当时人们文化程度低,缺少理性意识和独立的判断能力。依附性和蒙昧性,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时难以进行理性的把握,因而容易形成一种从众心理。这种情形一旦在某个情境当中,与自身基本生存利益诉求结合在一起,加之如果再有人领头前行的话,就容易形成比较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现代社会则不然。市场经济使得每位社会成员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然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依赖自我独立的选择;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认同科学精神,越来越重视理性的判断;而法治社会的形成,则要求每位社会成员都必须按照规则行事。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更倾向于以理性博弈取代激烈对抗。这一切,必然会使得社会成员以往的附属意识、从众心理以及盲从心理大幅度、大面积减弱。同时,极端的意识形态、极端的种族主义以及极端的宗教意识的影响力必然也会相应地大幅度、大面积减弱。凡此种种,进而使得社会动荡的概率明显降低。
另外,现代化过程还带来了一个后果,这就是人们宽容精神、包容意识的普遍化。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离不开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资源互换和文化交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有宽容和包容的意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生存发展的合理位置和空间。这也是现代社会能够充分开发社会潜能,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原因所在。现代社会的这种普遍的宽容精神和包容意识,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唯我独尊、排斥其他群体和社会成员的极端精神因素的基础。
第三,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流动渠道的增多以及社会流动本身趋于平等,使得社会成员的希望增多,可能的不满会减少。
在社会转型或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职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动,伴随着社会成员自由、平等意识的普遍形成,社会流动的速率必然会相应增大,社会流动特别是上行社会流动的机会也在增多并趋于平等,进而给民众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相应地,人们不满的可能空间在减小。“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相比:(1)社会流动的绝对比例通常是高的,并且向上流动——例如从低级职位流向更高级职位——明显多于向下流动;(2)流动的相对比例——或者说流动机会——是更平等的……(3)流动的绝对比例水平和在相对比例上的平等程度是随着时间而增加的。”
一方面,社会成员流动机会的总量在增多。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人口增加,专业性职业的绝对数量也增加了,经济发展使专业性职业在全部职业中的百分比提高。人口发展和经济增长为下一代提供越来越多的晋升机会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特权阶层出生率较低有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促使人们对服务行业的需求量迅速增大,进而导致大量职业种类特别是服务行业当中职业种类的大幅度增加,职业结构日益复杂化。现代社会当中的非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开始超过体力劳动者。比如,英国体力劳动人员人数比例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缓慢下降,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下降速度加快。英国的体力劳动人员在主要职业团体中的百分比从1911年的74.6%下降到1981年的47.7%,而非体力劳动人员的比例则由1911年的18.7%上升至 1981年的 52.3%。美国白领人员所占的百分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赶上并超过了蓝领人员,其比例由20世纪40年代初的31%上升到1979年的50.9%。社会流动渠道的增多,意味着大量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增多,进而更倾向于认同社会。相应地,社会动荡的概率自然会降低。
另一方面,社会流动的机会也在趋于平等。市场经济对于资源充分流动的现实要求以及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理念的价值追求,使得现代社会极为重视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所强调的是,凡是具有相同能力、相似意愿并有着同样努力付出的社会成员,应当有着相似的前景。“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逐渐消除各种人为障碍、各种特权,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发展的过程。“一是阻碍某些人发展的任何人为障碍,都应当被清除;二是个人所拥有的任何特权,都应当被取消;三是国家为改进人们之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财富、权力以及声望往往是分离的,而不像传统社会当中三者往往是一体化的。在现代社会,对于社会各个群体来说,各有各的平等上升通道,而不会出现一家独大、赢家通吃的局面。这种情形,会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增加对未来的希望。“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亦即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希望的增加,意味着社会怨恨的减少,进一步看,实际上这就减小了社会动荡发生的可能性。
第四,现代社会中异质性的增强,减弱了抗争力量的直接对抗性。
麦迪逊有一个观点十分重要。他指出,“如果多数人由一种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必须找到有效方法,“使社会中包括那么许多各种不同的公民,使全体中多数人的不合理联合即使不是办不到,也是极不可能”。这个有效方法就是,“它所有的权力将来自社会和从属于社会,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以致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很少遭到由于多数人的利益联合而形成的威胁”。㉔虽然麦迪逊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政治结构而言,而且提出的时间也比较早,但是,这一观点对于从现代社会当中异质性增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动荡趋势减弱这一重要问题,有着不小的启发意义。
与传统社会不同,在现代社会,异质性成分越来越多,从一定意义上讲,整个社会越来越从一个同质性的社会走向一个异质性的社会。“社会机体中的子单元如各种行业、各种职业日益增多,社会机体中各种性质不同的成分也日益增多”,而且,“分化后的各种子单元的相对自主性逐渐形成”。㉕在现代社会异质性不仅越来越多,并且众多的异质性相互之间是重合叠加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实际的社会结构的特点则体现在复合异质性上,复合异质性是由几个有时是许多相交叉的类别参数来表示的。性别、种族、国籍、宗教和职业上的差异都不尽相同,尽管其中某些差异之间有相关关系。复合异质性指的就是由这些差异引起的各交叠群体及为数众多的亚群体”㉖。
显然,社会异质性的增多,对于社会矛盾冲突有着重要的缓冲作用。其一,各个群体利益诉求及观念的多样化,有助于直接减弱抗争群体的对抗力度。一个社会,如果同质性过强,则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结构相对单一,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及观念也相对简单。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旦某个主要群体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基础性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那么,这种相对单一的利益诉求便会集中在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如基本生存问题),并不断积累进而逐渐酿成巨大的社会冲突势能,形成巨大的对抗力度。相反,在一个异质性成分占据主要位置的相对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从以往的“单向度”的情形演变为“多向度”亦即多维度、多层面的情形,社会成员的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而且在现代社会当中,基本生存的利益诉求相对民众来说已经不是头等大事,所以,抗争群体利益诉求的目标往往容易出现分散化的情形,难以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并持续积累,相应地,社会动荡所必需的大量社会冲突势能便难以形成,社会冲突的力度便会明显减弱,社会矛盾冲突很难在一个节点上集中爆发。其二,复杂多样的社会组织同样也有助于减弱抗争方的对抗力度。社会异质性的增强还表现为大量社会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利益群体机构等的出现。社会组织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社会组织存在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以及不同的层面,不但多种多样,也十分复杂。这些复杂多样的社会组织往往代表并维护着不同行业内、不同领域内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重要的是,这些存在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已经不可能具有某种令行禁止的权威和跨行业、跨领域的“大一统”管辖力。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方面,从微观上看,每一个社会组织对本行业、本领域的群体有着不可缺少的整合意义;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看,复杂多样的社会组织相互间具有一定掣肘、制约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个群体包括抗争群体,其规模都难以独自做大到明显左右整个社会的地步,其意志难以达到高度统一以至于能够使其成员舍弃自家性命的地步。总之,在现代社会异质性成分大面积存在的情形下,社会各个群体利益诉求及观念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多样,极大地减弱了社会矛盾冲突势能的积累,减弱了社会矛盾冲突的力度。
第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重。
现代化过程的推进,使得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即职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的各种复杂成分越来越多。这种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化所带来的一项重要后果,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各种构成要素之间呈现出一种高度关联性。这种高度关联性已经不是以往传统社会那种简单的社会分工所产生的社会整合程度所能比拟的。“现代社会所有部分的相互依赖使现代秩序比更为简单的经济组织形式敏感得多。实际上,庞大机制的各个部分愈是精密地相互适应,以及各个要素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干扰的反应就愈重,即使是最轻的干扰。”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经济及社会合作程度的提高。从社会成员及社会群体的各种经济及社会活动哪怕是细微的经济及社会活动来看,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各种活动,越来越离不开其他人及其他群体的协作和帮助。虽然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个体人意识在增强,个人的自由选择余地在增大,但是,即便是单个的社会成员要想实现一些差异化的追求,也离不开其他群体及其他社会成员所提供的平台和其他种种必要条件。
社会风险的大量出现,促使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群体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性增强。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扩散,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使得现代社会面临着空前的不确定性及风险。“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而且,这种社会风险涉及面十分广泛,扩散速度很快。“它们包含着一种打破了阶级和民族社会模式的‘飞去来器效应’。生态灾难和核泄露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即使是富裕和权势的人也在所难免。它们不仅是对健康的威胁,而且是对合法性、财产和利益的威胁。”吉登斯将风险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外部风险”,也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另一种则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大多数环境风险,例如那些与全球变暖有关的环境问题就属于这一类”。社会风险一旦控制不当,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对共同的社会风险,不同的社会成员及社会群体必须共同应对、相互合作。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群体共同应对风险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不同成员,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依赖性空前增强,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损害了对方,就等于损害了自身。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别人的存在、发展及帮助。
总之,社会成员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使得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互惠互利的社会交往对于各方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利的,因而合作共赢逐渐成为某种共识。“对于社会合作,我们别无选择,否则,要么是互不情愿直至仇视抱怨,要么出现互相抵制直至内战。”哪怕对于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来说,利益的获得对自身的益处并非无止境的,利益对自身的益处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给对方一定的发展余地,让渡某种利益对自身是有利的,可以换取诸如安全、尊敬一类的益处。“在经济十分富足的社会中,精英中的许多成员可能倾向于做出一些经济上的让步,以便尽可能增大其他方面的报偿,如安全、尊敬和闲暇等……精英们具有多重目标,并非只关注物质报酬的增大,所以,在一个高度富足和不断扩大的经济中他们可能愿意做出一定的经济让步。”而占据优势位置利益群体的一定程度的利益让渡,有利于社会矛盾抗争方抗争力度的减弱,有利于社会动荡概率的降低。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既然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已经不成问题,人们为基本生存而意欲通过激烈流血的方式来毁灭对方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既然极端精神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越来越世俗化、理性化;既然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多、社会流动本身越来越平等,社会成员的希望在相对增多,怨恨在相对减少;既然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逐渐增强,社会群体之间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在增大,合作共赢逐渐成为某种共识,那么,激烈、颠覆性的社会动荡发生概率自然会大幅度降低。
余 论
从以上对社会动荡发生概率逐渐降低趋势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形成这样两点看法:
第一,社会动荡发生概率的大幅度降低,能够有效减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进步的成本。
应当承认,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重要的社会进步需要有时甚至是必须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包括剧烈的社会动荡才能摧毁妨碍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不宜过大,如果过大,则其积极意义便会减弱。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时期之一。在秦王朝统治下,赋税极为繁重,民众不但要按照田地的多少交纳“田租”,还要按照人口的多少交纳“户赋”,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而且徭役之负担,达到了极点。一般民众“年十五始服役,六十岁老免。一生中须为正率一年,屯戍一年,每年还要为更卒一个月”,“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额外徭役,有的甚至不计役期”。秦始皇挥霍无度,修建大量的奢华宫殿,“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其中的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另外,秦朝还实施极为残暴的严刑酷法。凡此种种,严重损害了各个主要群体的基本利益甚至是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民众长期难以忍受,引发了激烈的民众暴动,进而又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经此动荡,秦王朝被推翻,以往严重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被破除。但秦末社会动荡的代价巨大。有记载,到了西汉初年,社会一片残破景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经过西汉初年“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社会开始恢复了元气。
同时还应看到,并非每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都必然会带来社会进步。有的社会动荡并不具有“进步增值”的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卢旺达,发生了灭绝式的种族仇杀,数十万人惨遭杀害,十几万女子被暴力侵犯。从社会动荡的角度看,其程度已达到极致。但这场罕见的社会动荡显然没有带来社会进步。像中东一些国家当中原教旨主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也并没有带来这些国家的社会进步。如是,意味着社会“白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代价。
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经不起社会动荡的打击。现代社会的分工十分复杂且专业化,需要各个职业群体的合作。任何一个群体都无法离开别的群体而独自生存。现代社会的经济总量十分庞大,而且,现代经济是由极为复杂的各种经济实体及构成要素组合而成的,相互间是高度依赖的,其中一个要素发生了变化或者消失了,对于别的构成要素进而对整个经济体都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旦出现了社会动荡现象,这种动荡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传递、放大、叠加的种种连锁性的负面效应。“大众在行动上野蛮的、冲动的和情感的爆发,对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都意味着大灾大难,因为现代社会有机体的相互依赖日益猛烈地传播着每一个失调的结果。”再者,由于现代社会体量庞大、环节复杂,一旦崩盘,不仅会遭受财富的巨大损失,而且其重建的难度也相对更大。另外,相比传统社会来说,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所以,在现代社会,从心理层面看,民众也更经不起社会动荡的打击。
显然,社会动荡发生概率的大幅度降低,不仅大幅度减小了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成本,而且使得现代化发展具有了可持续性及可预期性。这种情形,既是人类社会自我调整的结果,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第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应当积极缓解社会矛盾冲突,防范激烈社会矛盾冲突情形的出现。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当中;巨大社会能量的激活与规则体系的阙失这样两种情形同时并存;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出现;社会风险空前增多。而且,社会焦虑现象弥漫于整个社会。凡此种种,成为诱发和加重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现阶段,如何才能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冲突,防止激烈社会矛盾冲突的出现,尽可能减小发展的代价?就此而言,涉及方方面面。择其大要,要特别注意这几件事情:
其一,保证民众的基本生存底线。在社会转型初期,民众对基本生存的需求十分迫切。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乎社会基本安全的问题。进一步看,如果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使得民生问题与民主化问题两者结合在一起,那就必然会对社会的安全状况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具体到中国来看,尤其如此。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而且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几乎都已出现。别的国家和地区有的社会矛盾,在中国大都已经出现,别的国家和地区没有的社会矛盾,在中国现阶段也出现了不少。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种“并发症”的情状。不过,如果从社会矛盾产生的基本根源来看,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基本民生或者说是同民众的切身物质利益直接相关的部位。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现阶段,有必要大力改善民生,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如是,则能够从源头的意义上减小激烈社会矛盾冲突发生的概率,至少可以减弱社会矛盾冲突的强度,以确保中国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安全局面。
其二,为民众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上行流动空间。民众是否拥有上行流动的空间,不仅事关民众生活的改善问题,而且事关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的自致性努力有无平台的问题,事关民众对未来是否拥有希望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不给民众提供自致性努力的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众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不满乃至绝望心理。希望的减少或消失,绝望的增多,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积怨,进而促成大量社会矛盾冲突的出现。反观如今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冲突,就是由于利益结构固化,使得民众自致性努力的空间和发展的机会受到严重挤压,进而催生民众大量的不满及积怨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而拓展民众上行流动渠道的关键在于,从横向的角度看,必须消除种种歧视现象,如财富歧视、身份歧视(包括体制内外身份不平等、户籍制度身份歧视等)等;从纵向角度看,必须破除不公正现象的代际传递,如“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现象。唯有如此,方能使民众对未来抱有希望,方能进而使民众减少积怨并积极认同社会。
其三,为社会安全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保障是解决或缓解社会矛盾的必要前提。现代社会是一个依靠公正合理的制度体系来运行的社会。现代型的制度具有公正性、广泛性、包容性等特征。通过制度或者在制度内解决社会矛盾,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从总体角度看,通过制度化解社会矛盾,意味着社会共同体对社会各个利益群体意愿及利益诉求接受的广泛性、包容性和诚意;意味着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并非单方面决定,而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化解相互间的纠纷;意味着有章可循,通过法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随意性。从利益诉求方的角度看,通过制度化解社会矛盾,意味着由于利益诉求渠道的增多,大量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解决,即便暂时得不到解决的也有渠道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凡此种种,以往的那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叠加的情形便可得以有效缓解,进而减少社会矛盾特别是严重的社会矛盾冲突发生的概率。有学者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把社会运动纳入体制的能力很强,该国家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反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就有可能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可谓明智之论。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或社会运动,而是指国家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轨道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这也应当是目前所说的‘提高执政能力’的宏观要旨。”既然现代型的制度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如此之重要,所以,中国应当积极进行制度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以此为社会安全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①吴忠民:《中国中近期社会动荡可能性的研判》,《东岳论丛》2013年第1期。
②孙立平:《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瞭望》2009年第36期。
③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下·朱泚 黄巢 秦宗权》。
④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九·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李自成张献忠》。
⑤王鸿生:《中国历史治乱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⑦[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279页。
⑧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872年巴黎公社史》(下册),马龙闪等译,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593页。
⑨吕一民:《法国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⑩关雪凌、刘可佳:《俄罗斯经济现代化:背景、布局与困境》,《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1期。
㉔[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6页。
㉕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㉖[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