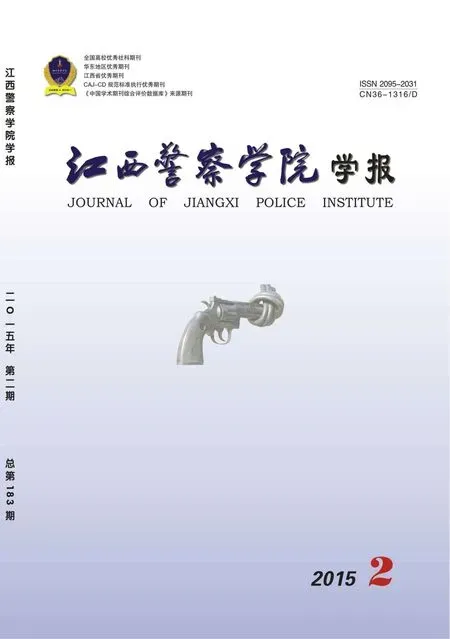论“花钱买刑”和解困境的消解
2015-04-18李建东
李建东
(河南警察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刑事和解制度发端于西方社会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人类社会对报应型刑罚思想和监禁刑罚失败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犯罪人在监狱内交叉感染使和刑满释放后的无法复归正常社会生活,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致使在犯罪率居高不下,使刑罚失去了犯罪改造的基本功能。的反思之下所结出的刑事司法文明硕果。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与恢复性司法理念高度契合,是近十多年我国司法实践不断探索和理论研究共同作用下内生性的一条适合于我国当下社会的刑事司法制度。和解制度有着无可替代的功能,在实践中也能缓解涉诉涉法信访上访等现实问题,然而,“花钱买刑”的质疑始终是困扰和解制度的运行,更是阻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深入、良性发展的难题。
一、“花钱买刑”和解的质疑
毋庸讳言,实践中多数案件之所以能达成和解,绝大多数案件是由于加害人向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尤其是足额之后方能获得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和解一旦达成,加害人在检察阶段可以根据情形被“不起诉”处理,在审判阶段被“从宽处罚”。人民法院“从宽处罚”,实践中通常会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刑罚,主要是适用缓刑,个别情形下可能适用管制,或者进行“可汤泡馍”②即指被告人在审前程序中被羁押了多长时间,法院就会按其被羁押的时间来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法院通常的做法是,对在于审前程序中一直处于被羁押状态的被告人,即便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仍会判处其有期徒刑,不过这个有期徒刑是极有讲究的,用法院内部通俗的说法,就是要做尽可能做到“可汤泡馍”的量刑。即指被告人在审前程序中被羁押了多长时间,法院就会按其被羁押的时间来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这样的判决能够起到当庭释放的效果。式的处罚。虽然立法者和各级司法机构不断对“花钱买刑”的质疑进行反驳,但始终无法平息舆论对其的质疑。最高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高贵君曾经于2013年2月27日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某些时候会按照被告人积极赔偿的情况予以从宽量刑,但并不意味着“赔钱减刑”或者“花钱买刑”。[1]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也坚决否认“花钱买刑”,并且认为和解从宽处罚恰恰是刑法 “罪刑相当”原则的体现。[2]可以说,刑事和解制度自其产生便与“花钱买刑”的质疑相伴,和解制度因“花钱买刑”导致富人与穷人在适用上的差异而与法律适用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理念相悖而为人诟病,两者冲突的背后体现着现代法治与后现代法治理念之争。不能否认的是和解赔偿的确解决了当前社会所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因而,如何平衡经济赔偿和解下的从宽量刑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冲突自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何消减公众对“花钱买刑”的质疑是当下刑事和解制度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花钱买刑”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性指导
(一)被害人接受加害人经济赔偿而达成和解权利的理论分析
被害人①2013年10月16日日下午3时许,何某锋与朋友在广东增城市百花林水库划水俱乐部游玩。何某锋看见正在水库浮台边游玩的陌生年轻女子李某,何某锋便从后面抱着李某的腰一起跳入水库中。当发现其很长时间都没有浮上来,就与他人一同下水寻找,然而受害人已没有呼吸,法医鉴定其为溺水死亡。何某锋向公安机关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良好。何某锋的亲属积极与被害人父母协商赔偿事宜,在支付了500万澳门币(约合386万人民币)后,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父母的谅解,法院审理认被告人何某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2013年8月13日增城市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何某锋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两年,判决已经发生效力。究竟是否有权利在接受加害的赔偿而与加害人在达成和解后要求“从宽处罚”加害人,这是首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被害人的谅解不能成为酌定量刑的情节,[3]据此观点,加害人自然没有权利以此获得从宽处罚的权利 ,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在存有被害人的公诉案件中,加害人主要侵害了三方主体的权益。首先,加害人直接侵害了被害人权益;其次,侵害了正常社会秩序下法律所保护的犯罪客体,即侵害或挑战了国家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继而侵害了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管理权力;最后,也侵害了潜在的受害人权利。显然犯罪如果得不到制裁,每个社会中的个体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人,因为社会秩序因犯罪行为受到破坏,秩序已不再安全。因而,事实上公诉案件对加害人制裁的权力(权利)涉及被害人、国家与社会大众的三类主体,具体而言在刑事诉讼中分别涉及三方力量:被害人、侦查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舆论力量。因此,由于是直接的犯罪行为受害者,在刑事和解中都应有权利分享一定的对加害人的处罚权。被害人既然享有对加害人一定的处罚权,在其享有权利的范围内,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其他主体自然不应当进行干涉。因此,被害人自是有权利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接受加害人金钱赔偿而谅解对方。
国家公权力机关为了迅速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基于效率和以人为本的后现代司法理念,在和解案件中将其对加害人处罚权的向被害人进行了部分让渡。从和解案件的轻质上来看,属于准自诉案件。公诉和解案件属于轻罪类型的案件,在我国理论通常认为,法定最低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为划分标准较为适当,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都属于较重罪,反之,则属于较轻罪。[4]我国现行刑诉法所规定的和解案件范围中,和解案件均属于轻罪类型的案件,加害人人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均较小,主观恶性不大。因此,这类案件属于“准自诉案件”。既然属于与自诉案件极为类似的 “准自诉案件”,那么在对加害人进行处罚的过程中,自然也应当采取与自诉案件相近的立场,即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体现“以人为本”的后现代司法理念。国家公权力机关事实上放弃了其大部分对加害人的处罚权,并将放弃的这部分权力交由被害人行使,称之为被害人和解的权利。
根据上述分析,社会公众同样也享有部分的对加害人处罚发言权,只不过主要体现为社会舆论的监督。众所周知,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两大类的自诉案件中,加害人通过积极的经济赔偿,获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而从宽处罚,甚至免于处罚的情况实践中并未少见,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属于 “花钱买刑”,然而这两类自诉案件的和解实践并无遭受公众质疑。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公众认为被害人有权利与加害人达成和解,另一方面自诉案件通常属于轻罪类型的案件,社会危害不大。社会大众所以发出“花钱买刑”的质疑,主要是对刑罚不公的担忧,更担心富人借助和解程序逃避应有的制裁,使富人与穷人在适用法律上的差异。公众的担忧不无根据,因此,社会大众公众理应享有部分对加害人的处罚的发言权,具体就体现为舆论对和解的监督权。显然,较前两个主体而言,社会舆论监督力量对的发言权明显较为弱化,毕竟从与犯罪行为的距离来看,普通公众并不是犯罪直接的受害者,也不是直接的社会秩序管理者,而仅是潜在的可能受害者,因而,社会公众事实上是以舆论监督的方式间接的分割一小部分对加害人处罚的发言权,体现为社会公众对和解案件被害人处罚权的监督权。在实行和解的案件中,被害人接受加害人的经济赔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因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所造成的身心伤害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每一个社会个体也都是不确定的潜在受害人。因此,只要和解不违背社会公众的接受底线和情感底线,通常不会被舆论质疑。
(二)公众对“花钱买刑”和解案件质疑的实践指向
那么实践中社会公众为何还会发出“花钱买刑”的质疑具体指向是什么?这是必须考察清楚的问题。近期饱受舆论质疑的何某锋“过失”致人死亡案①的判罚对于了解公众对“花钱买刑”质疑指向而言具有样本式的意义。
该案判决后,立即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和质疑,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加害人的巨额赔款、当地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如此 “从宽的判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再次引发民众对和解“花钱买刑”的强烈质疑。不少网友怀疑真相并未如加害人所言,“是出于开玩笑搂抱受害人入水致死”,认为本案的定性发生错误,应当是猥亵妇女罪且致受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属于重罪案件,不能适用和解程序,但由于其巨额赔偿而改变案件性质,使加害人逃脱严厉的制裁,象征性的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而且缓刑两年,属于明显的歪曲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这才引发公众“花钱买刑”的强烈质疑。[5]显然,从本案而言,表面上看是舆论对“花钱买刑”的质疑,其实质恰恰不在于金钱赔偿,而在于对案件事实和定性是否正确,加害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应否适用和解程序,继而逃避应有的刑事制裁。因此,公众对于本案“花钱买刑”的质疑,主要质疑的是公安司法机关将重罪性质的案件“转化”为适用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中的加害人,从而通过高额赔款逃避惩罚。
笔者认为,无论加害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若所犯罪行为本身真的属于轻罪案件,加害人主观恶性不大,只要能让被害人能接受其悔过自新的诚意,相信绝大部分公众也会接受双方的和解。反之,如果案件性质本身属于重罪案件,加害人主观恶性较大,只是因为“花钱”而使本不应适用和解程序的重罪案件变为可以适用和解程序轻罪案件,通过歪曲案件性质和错误适用法律的方式,借助高额的经济赔偿迫使被害人或其家属和解,从而致使和解制度异化和滥用,自然会引发公众最强烈的质疑,从而也使正当的经济赔偿异化为“花钱买刑”。必须承认,加害人足量的经济赔偿当然有助于获得被害人的谅解,然而公众更关心的依然是加害人是否应当被谅解,案件性质是否恶劣,案件定性是否准确,能否适用和解程序。
因此,通过上述个案分析,可以实践中与其说是民众对“花钱买刑”进行质疑,毋宁说是对和解异化与滥用的质疑,而非质疑“花钱”行为本身。通过歪曲事实和扭曲法律,将原本不属于和解案件范围的重罪案件适用和解程序,使和解制度变为富人逃避制裁的特权,完全违背了和解制度的初衷,更根本动摇了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三、“花钱买刑”式和解的制度防范
为了避免和解制度在实践中的滥用,必须设置相应的制度机制来防范和制约“花钱买刑”式的和解异化现象,使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因正当的经济赔偿而达成的和解在规范程序中适用。具体说来,应当建立争议案件和解监督体系从、完善量刑规范化建设、和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一)建立争议案件的和解适用监督制度
实践中,适用和解程序产生争议的案件多数并非单纯的轻罪案件,越是“花钱买刑”争议较大的和解案件,其案件事实和定性越是容易引起纷争的案件。如前文所述何某锋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公众争议的核心则是案件事实认定是否故意人为的定性错误。不少人认为本案应定性为猥亵妇女罪,并且有致受害人死亡的从中情节,属典型的重罪案件,根本不能适用和解对加害人以此“从宽”。近年来出现的将原本的强奸幼女的案件定性为如此嫖宿幼女、将肇事后二次碾压的故意杀人行为定性为交通肇事行为、将故意犯罪定性为过失犯罪等等一些引发社会广泛质疑的案件,都存在将重罪案件错误定性为轻罪案件,高额赔款后适用和解程序,最后被免于监禁刑处罚。这些本不应适用和解的案件,由于不当适用和解程序,而使案件性质发生变化,致使加害人逃避应有的刑事制裁而引发民众对和解案件的质疑,因此,对和解争议案件应当有着严格的监督制度。
监督制度设置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完备的和解争议案件听证程序,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实践中,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在得到足额的经济赔偿后,不再关注加害人悔罪和赔礼道歉是否真诚,这也是不少民众质疑“花钱买刑”的一个因素。因此,一旦出现和解争议案件,应当启动听证程序,不应当仅仅将和解权交由被害人,因为此时争议的案件极有可能不属于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此时受潜在危害的是不特定社会公众,被害方个人不能代表全体公众的态度,不能消除罪犯对他人的威胁和危害,因此,不能仅仅以被害方的谅解作为对这类犯罪从宽处罚的理由”。[6]二是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允许普通公众旁听。和解案件的定性必须准确,事实必须查明,这也是适用和解程序的基本前提。在此过程中允许公众旁听增加和解案件的透明度,避免公众对“花钱买刑”的暗箱操作质疑。三是严格贯彻判决书说理制度或不起诉说理制度,即时公开案件的判决书或不起诉决定书。通过判决书和不起诉书说理制度,使社会公众对和解案件的判罚和和解方式之间 “花钱买刑”的联系淡化。四是一旦发现属于定性错误的案件,尤其是出现将重罪错误定性为轻罪案件的情形时,案件即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并且加害人已经向被害人支付的经济赔偿不得索回。
(二)对和解案件进行量刑规范化的制度建设
和解案件不一定对加害人就免除刑罚或免除监禁刑罚,公众对此问题有一定的误区,认为“只要拿钱就可免除牢狱之灾”。不过,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刑事和解制度的量刑存在较大的不规范性,随意性较大,全凭办案人员的主观意愿判罚。和解制度的量刑,需要有理有据,加害人的犯罪性质、情节和后果、悔罪程度、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谅解程度等因素都是影响对加害人判罚的依据。为了避免过于随意性对案件判罚的影响,在进行和解量刑规范化的制度建设同时,可以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电脑量刑模式已经在我国个别地区的法院进行实验。电脑量刑虽然伴有不少争议,但其在量化规范化建设上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三)多元化和解形式消减“花钱买刑”质疑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和解案件就是通过加害人支付经济赔偿的方式达成和解,这正是公众对和解异化为“花钱买刑”质疑的现实依据。为此,应当冲破单一的经济赔偿和解的模式,实现多元化的和解形式,以消减舆论质疑和误解。
1.赔礼道歉形式
对于一些给受害人没有带来直接或明显的间接经济损失的案件,如果加害人真心悔过,积极主动的赔礼道歉,应当鼓励被害人与加害人进行和解。事实上,不少邻里亲友之间的纠纷和其他一些突发性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和加害人往往只是出于“争一口气”的心理而使矛盾升级为刑事犯罪,双方并不在乎经济赔偿的多寡或有无。这种情形应当教育加害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及公众公开道歉,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应被害人要求,通过现代媒体技术手段进行公开道歉,通过这种真诚、公开的赔礼道歉形式能够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当然,涉及隐私的情况除外。这种赔礼道歉形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让公众产生“和解只认钱”的误解心理,同时能够强化对加害人的道德及心理约束。
2.劳务补偿的和解形式
对于经济能力较弱的加害人,若能真诚悔罪,真心赔礼道歉,愿意悔过自新,可以鼓励加害人通过劳务补偿的方式进行和解。劳务补偿的和解形式较为适合 农村地区发生的和解案件。例如,被害人如果家庭劳动力不足,可以由加害人向被害人或被害人的亲友提供劳务的方式,当然前提是被害人和其亲友同意。不但能够解决被害人的实际困难,在此过程中,通过被害人加害人的直接接触交流,增进双方的融合,可以有效地化解双方之间因争斗和诉讼产生的怨恨,有利于双方及时的修复关系,增进社会和谐。这种形式的和解不仅能够有效地避免直接的钱财补偿引发的“花钱买刑”误解,更重要的是为经济条件较差的加害人和解找到了出路,使和解不再是富人的“专利”。
3.完善的社区矫正形式
作为非监禁刑处罚,社区矫正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在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试验探索阶段,尚未能将该项制度与和解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社区矫正制度应当规范化、制度化,使其发挥应有的矫正功能。应当是社区矫正制度与缓刑制度进行相应的衔接。[7]社区矫正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可以使缓刑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可以成为承载缓刑制度的有效路径。社区司法作为社区主导下的新型司法范式,因为其融法律与道德、实体与程序、惩罚与矫正、恢复与救助、协商与调解等复合功能,在完善基层民主治理方式和凝结社区核心价值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8]
[1] 袁定波.最高法回应“花钱买刑”质疑[N].法制日报,2013-2-28(35).
[2] 陈宝成.最高法副院长称‘花钱买刑’有望被规范”[J].法制与经济,2009,(11):3-4.
[3] 王瑞君.刑事被害人谅解不应成为酌定量刑情节[J].法学,2012,(7):128-136.
[4] 高铭暄,王作富.中国刑法词典[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9:410-411.
[5] 刘昌松.政协委员猥亵美女致其死亡凭啥获轻判[EBOL].(2014-08-13)[2014-10-17]http://liuchangsong1.blog.sohu.com/304921657.html.
[6] 张军.死刑政策的司法运用 [C].中韩死刑制度比较研究——第五届中韩刑法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2.
[7] 李涛,唐振刚.问题与路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J].河北法学,2013,(12):176-181.
[8] 李本森.社区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双系耦合[J].法律科学,2014,(1):166-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