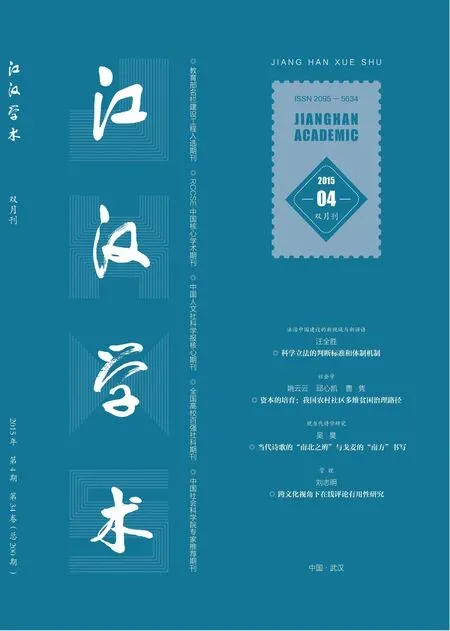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2015-04-18赖彧煌
赖彧煌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赖彧煌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
摘要: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
关键词:诗歌体式;言说方式;晚清诗歌;五四新诗;诗歌史;美学机制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4-0067-09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 jhun. edu. cn/jhx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诗观念史上的谱系研究”(11CZW059)
一、被体式和经验割裂的诗之“内外”
诗歌史叙述中,体式的转换似乎是晚清至“五四”诗歌演变的基本特征,这在胡适的《谈新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文中亦有不厌其烦的申说。在形式规范层面,体式一般具有可计量、易辨别的特点,经常用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诗歌的区分,诸如古典诗歌被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等,新诗被分为自由诗、格律诗、半格律诗等。然而,体式作为凝定形态的诗文类标识,只能起到笼统、抽象的聚合作用,它是难以涵纳诗所遭遇的经验冲击以及它的书写策略、美学特质的分类。正如一种体式的探索、萌生和形成无法一蹴而就,另一种体式的动摇、瓦解和崩溃也有一个漫长的、藕断丝连的过程,无论旧体式的调适、变形还是新体式的实验、新建,体式本身既不具备使诗持守不易的自足性,也不具备使诗聚合转变的原动力。毋宁说,体式不过是诗的变奏过程中部分形式要素的成型与征显。
以诗歌体式的变动为标志,至多表明了某种既定的、外在的诗歌形态特征,它无法标记诗歌写作在具体历史语境下遭遇压力和形变的过程,也很难指示体式本身的活力或惰性,更遑论分疏出业已深刻介入到文类内部的经验等问题,以及诸多要素之间长期的冲撞、分裂与暂时的平衡、媾和。这意味着,尚需引入其他维度才能更好地彰显该时段诗歌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降的诗歌较之过往的任何时代,都更深刻地受制于外部的挤压与牵引,它经由文化与社会系统得到展现,这是诗歌书写的语境和现场。但是,源于现实情势和语言策略之间的非决定论关系,如何处置诗的外部和内部,在该时段的诗歌研究中将更费思量。
在成熟的、有活力的体式中,外部冲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形式结构吸纳,成为内心情致和语言节律的交响,并生动隐现于语言的坡度、拐弯和褶皱中,最终呈现为已然被形式化的体制与外观。有鉴于此,必须强调,密集的诸多事件无论裹挟多少或
峻急或迂缓的声浪,因其被物化成语言的现实,对它们的谛听从来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语言秘纹中的声响,也只有在这里,声响才不是它自身的空洞回声。一如折射定律唯有在光线、物质和观看之间才能成立。这就是为什么,在深刻书写家国情怀的屈原和杜甫那里,几乎难以将他们的遭际从文本剥离出来,相反,只有深入到内部,才能更好地听到和看见。倘若企图以切割和分离的方法还原、捕捉“外部”,以为它是可以从诗中轻易度量、轻松揭取的“外部”,必将误入歧途。
有人或许会说,楚辞与唐诗作为诗的类型在其时已高度成熟,是为可依傍的体式,再假以天才自是辉煌的创造,水乳交融后的形质当然再难以也没有必要分离。而转到不成熟甚至备受质疑的体式时,“外部”与“内部”的扞格如此扎眼,在技术层面,自可以将它们分离出来。然而,在某种体式中调适自我的诗,无论有多少权宜性、短暂性的特点,无论时势与语境中的世界之表象多么难以呈现,“外部”从来难以自外于“内部”,“内部”也从来不能独善其身,而是一同隐没在诗的编织物之中。内与外之间的缠绕使得人们不能轻忽如下事实:诗必得从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双重挑战予以考量,而该时段诗歌较之以往(譬如盛唐时期在既有体制上加富增华的诗歌),益发深刻体现为矛盾重重的探求、质询乃至重建——如何既不自外于美学自律性的准则,又不自闭于对经验的开放。
理解晚清至“五四”的诗歌,自然也要面向如下目标,即诗最终必以内部反应的方式面对“外部”。但是,作为对内外关系的分辨而不是分离,叙述策略上却必须以“外部”作为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突出“外部”的双重性:它既是强大的势能,又是有待确认的后果。换言之,“外部”是一个绝对的、但又有待在语言中彰显和检验的“前见”,它成了人们打量该阶段诗歌的入口。值得注意的是,有论者已将早期新诗的探讨置于外部与内部的会通之中,他认为,诸如诗集的出版、评论等方面的外部力量之调度,实际上汇合成了内外交织层面的制度与美学的创生,于此才能真正展露新诗“发生”的理路。[1]
当然,外部世界在具体的诗人那里的亲疏关系或大相径庭,有人拥抱现实急切于诗歌之力的挥发,又有人背对时势幻想于纯粹的吟哦,但即使如后一种类型,他们的语言态度也不过是以拒绝的姿态重叙外部,并显现出伦理态度的折光和反映。这是因为,无论拒绝还是沉溺,在语言的维面必将反映相应的曲径,实际是作为承受者的语言被改写的写照。另一方面,“外部”也被语言改写,哪怕前一种类型亦然,源于“外部”进入诗中时,绝不可能无抵抗地长驱直入,这和语言特质相关。
毋庸讳言,势能指的是现代性在经验层面的运动,作为动力或压力展现于伦理的维面,体现为普遍性,后果指的是经验介入和语言策略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它沉积在语言的维面,体现为特殊性。就前一种情形而言,现代性作为“问题”在近年来晚清文学的重评以及清季民初思想史的研究中,被不断“意识”到且得到了有力呈现。王德威对晚清小说被“五四”遮蔽予以了颠覆性的反拨,振聋发聩地追问:“究竟是什么使得晚清小说堪称现代,并以之与‘五四’传统所构造的现代话语相对应?又是什么阻止我们谈论晚清时期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2]将“现代”的标杆予以前置的做法,对于拆除“五四”新文学强硬的权力话语樊篱,的确功不可没,把“五四”老套视野中充满歧见与压抑的“他者”眼光转到了晚清对“自我”的呈现,生机勃勃的晚清和“五四”之间不是差价关系,而是“共谋”关系。重新张扬被“压抑”的晚清不仅表现在文学上,史学上亦然。王汎森梳理晚清“新史学”的问题时发现,自梁启超《新史学》的出场,一种足以“从头写史”的格局被奠定了。[3]从晚清的“新史学”中,人们既能感到强烈的政治意味,也能体会现代时间试图展开新规划的冲动,后者意味着强大的现代性诉求。
以渗透和流动为特征的现代性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语言作为一种介质却要以相应的方式对现代性作出反应,正是在这里,无界别的绝对主义被收缩、黏着在时空落差、语言特性所盘踞的部落之中,被多重差异纽结而成的特殊性再次标定。因此,尽管王德威重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富于启迪,但是,诗文类与小说之间存在差异,它在承受、吸纳或者拒斥现代性时可能和小说不同。比如晚清诗歌的评价问题,它的命运是否像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断言,有着“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倘若更多注意到诗文类成规的制约,是否将挖掘出另一种景观?事实上,晚清诗歌深陷古典型的美学机制难以自拔,这是一幅古典与现代性
相互缠绕的图景,进而言之,未得张扬的现代性的压抑很可能来自古典本身。
显而易见,没有必要对诗歌遭遇的现代性之强弱表示犹疑,它相当深刻地载入到了其时中国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被迫承受还是主动追摹。然而,面对诗中的现代性问题时,一方面,不能把文化与社会系统凌驾于诗之上,企图以此判定诗的高下,如此极易滑入浅陋的机械决定论中难以自拔;另一方面,又不能将诗仅仅视为纯粹的语词符号的组合,陷入某种康德式的抽象,后者惯于与外部掩面相对。因此,该时段诗歌必须理解为自外部策动的历史语境与从内部持守的文类规范之间,即经验与体式之间不断角力、相斥和包容的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体察出它如何在异动中走向变奏。
二、“言说方式”与现代性的纹路
有鉴于此,必须就语言的维度中对现代性的特定反应作进一步梳理。但明眼人必已看出,我们不仅绕过了现代性从西方进入中国的文化差异性,甚至忽略了对现代性在西方的源起与发展的辨认,径直奔向现代性在语言特殊性中的表征问题。在承认现代性作为“前见”的同时,有意抹去了有待分辨的现代性的多义且充满歧议的“内容”,是为置语境的限定于不顾的对现代性的理念化使用。从严格的逻辑关系看,实为一种僭越。的确,从“内容”层面,现代性有丰富且复杂的面相。
在与文化身份、政治意识密切相关的一类研究中,譬如思想史的研究,没有具体时空的限定和差异性的社会人类学方向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的逻辑起点即是破除文化统一性的幻觉,这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和解释现代性。显然,作为来自西方且歧义纷争的概念,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有尺度与范围的争议。本杰明·史华兹就严复遭遇的中西文化冲突困境指出:“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量,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4]在史华兹看来,西方和中国均非不言自明的“已知量”,应谨慎地深入各自文化差异的内部把握研究对象的特征。就中国而言,封建帝国崩溃过程中伸展的现代性诉求,它的品格不能以西方(欧洲)的理性和启蒙动力为绝对的评判标准,无论发展阶段还是远景目标均和西方有相当的差别。
不唯如此,从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看,也没有某种口径统一的理论能轻便征用。有马克思、韦伯的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原则上的现代性,也有哈贝马斯的试图弥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现代性,等等。哈贝马斯把现代性工程更深地扎入到发达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经验现象中,既作为对马克思、韦伯的现代性的修正与拓展,又作为对后现代理论冲击下的这项“未竞事业”的辩护。①但无论哈贝马斯伸延到“现在”(尤其是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多么雄辩,不可轻忽的是,很大程度上,他的雄心与梦想源于应对时代语境的压力——改进(装)过的马克思等人的原则如何与当下的资本主义现实展开周旋和抗争。②
实际上,现代性在中国和西方的争议均围绕它在相应的文化语境中的量值之多少展开,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这种分辨意义深远,某种程度上,只有推定现代性的量值,才能推定与此紧密关联的文化与政治,反之亦然。但是,对于已经进入到诗中的现代性,应予以关注的重心与其说是它的量值,毋宁说它成了一个关系项进入到诗中时引致的语言策略的反应问题。比如分属两个世代的梁启超和刘大白,他们表达的现代性体验,“内容”上虽有鲜明的差异,但进行精细辨认的任务应该交给思想史,因为它对于把握晚清至“五四”时期诗歌更内在的特性,几乎毫无助益。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写道:
……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其时人静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龙睡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士兀然坐,澄心摄虑游窅茫。正住华严法界第三观,帝网深处无数镜影涵其旁。漠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5]
将“新世纪”这种现代时间作为主体确立自我的标竿,所谓“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时间和自我认同于此合流了,因而,现代性是有待主体拥抱的崭新事物,它向未来无限伸延。但
是,在刘大白的《淘汰来了》[6]中情形已变得截然不同,现代性既是动力也是焦虑:“回头一瞧,淘汰来了!/那是吞灭我的利害东西哪!/不向前跑,怎的避掉!/待向前跑,也许跌倒!/唔!就是跌倒,/挣扎起来,还得飞跑!/要是给他追上,/怎禁得他的爪儿一抓,牙儿一咬!”在“向前跑”和“淘汰”之间划出了截然的界线,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人们甚至可以从“就是跌倒,/挣扎起来,还得飞跑”中体会到现代性特有的英雄主义意味。
在晚清至“五四”的时段,可以找出许多类似的诗歌文本,它们承载的现代性体验,正如福柯对此问题的论说:
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7]
然而,无论该时段诗歌中的现代性体验多么强烈,作为“思想和感觉的方式”、“行为和举止的方式”的“态度”多么丰富,唯有交织进诗歌文本,藉着相应的语言和体式征显自身。现代性的介入既已成了物化的后果,对它的考量也唯有深入到诗的美学机制中,才能把握它在形式媒层的运作和反弹(在这一点上,毋宁说,社会学或思想史的深入需要形式和结构的分析,海登·怀特等人走向后现代的历史诗学实为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才能探析到不再纯洁的语言和体式走向形式重组的路径。这也再次说明,承认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现代性作为该时段诗歌的“前见”只是第一步,应该更深入地分辨,语言策略以何种方式因应现代性的介入。前引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从中可以看到强大的现代性诉求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诗歌旧有体制的因袭(梁启超采用大盛于唐诗的歌行体,李白用此种体式写出了大量气势磅礴的诗篇),因而它并没有指向固有美学范式的变更。刘大白也仅仅着眼于“内容”的表现,全部嘱意只是为了表达“进步”意识。但无论哪一种现代性(包括伪现代性、反现代性),因其需要表达,就无法悬浮于最终将吸纳和改装它们的语言的形式与结构之上。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宣称,“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8]。固然从语体和语用、书面语和口头语、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关联与差别等层面,有必要对他不无简单、粗糙的逻辑予以反思,但是,就晚清以降的诗在“说话”、表达上的困境而言,胡适实质上深刻触及了“内容”的介入与形式的承载之间的矛盾。的确,该时段诗歌面对的是:“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后者无疑更为突出,因为“怎么说”不仅是其时尖锐的诗的现实,更是诗的紧迫的使命。为此,更值得注意的是“说”的“方式”而非“内容”,“言说方式”当然是诗的核心命题。
现代性的介入成了诗歌调适自我的压力与动力,是诗走向变奏时既是外部的又是普遍的推动,但现代性的运作既是发挥,也是挥发,并化合进诗的形制之中。在此意义上,引入“言说方式”的框架,是为了将经验冲击内化到美学的反应中。需要强调的是,至此虽然完成了方法论的申说,却不能仅仅把“言说方式”目为诗学层面③的一个概念。尽管它标示了由外而内、以内应外的路径,从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双重考验来把握诗的实际运作,也为克服诗歌(文学)研究内外分治的局面指示了方向,但是,对于有一定长度且诗的体式形态前后迥然有别的区间,“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架构,不仅要应答诗学层面的要求,而且要容纳诗歌史的眼光。质言之,只有统一于诗学与诗歌史的双重目标,它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才能得到彰显。
三、克服时间性难题:一个美学的梳理
粗看起来这几乎是悖论性的。一方面,“说”的问题作为诗学命题,“说什么”被涵纳在“怎么说”中,现代性介入的普遍性得以和它申说自身时的特定反应驳接起来,反应最终被视为是语言策略的。“言说方式”成为共同的使命贯穿于、回旋在晚清至“五四”的区间,展现为同质的、共时的结构。另一方面,诗歌史的要求是,“言说方式”不能碍于对差异、分裂和转折的辨认,藉此才能确定方向,体现出异质的、历时的运动。但是,诗学的形式化是内指的,以定型为目标,而诗歌史的演进是外指的,以不定型为动力,两者似乎不可弥合地分裂着。
文学理论史上,这通常被视为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因为它的不可逾越性,总是顽强地出现在理论家的视域中。但即使像韦勒克这样举足轻重的理论家,解决上述问题时也极不成功。在其重要论文《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里,他意识到它们之间互为支援的必要性,然而,源于他过度信
奉文学应采取内部研究的方法,归于“外部”的历史研究即使不被明目张胆地放逐,也是作为内部研究的附属物被偏置在决定论的关系中的。韦勒克更欣赏的是法国思想家马尔罗在《无墙的博物馆》中践行的理念,必须清除历时性的栅栏、围墙和壁垒,艺术作品的美学特质只能展现于共时性的结构中:“同造型艺术一样,同马尔罗的沉默的声音一样,文学最后也是一种声音的合唱——贯通各个时代的声音,这种合唱说出人类对时间和命运的蔑视,说出人类对克服暂时性、相对性和历史的胜利。”[9]显而易见,韦勒克争辩的是,诗学体现的共时性优于文学史追求的历时性,历时性的问题实质上被共时性消解了。在此必须强调,这篇文章中的“文学理论”指采用内部研究的方法,更多着眼于作品的形式、结构特点的诗学分析,是一个可以和诗学相互置换的指称,而非他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所指向的、范围更广的作为概念和实践系统的“文学理论”。因而,前者是后者提供、划分和规定的几个单元之一。
事实上,作为概念和实践系统的文学理论,面对诗学与诗歌(文学)史、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时,难以摆脱其间的主从设置,因为系统的运作乃至重组均离不开系统内部各单元之间的偏侧与抑扬,哪怕重新选择研究路径亦然。譬如德国理论家姚斯,他采取彻底历史化的策略,所谓“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他认为,形式和结构的“共时性”体现为美学的特性,但只要诉诸审美感知,就不可能自我封闭和长存:“因为每一共时系统必然包括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作为不可分割的结构因素,在时间中历史某一点的文学生产,其共时性横断面必然暗示着进一步的历时性以前或以后的横断面。”[10]47在极端的情况,共时性最终被历时性的黑洞所吞噬。
韦勒克和姚斯的处理,从逻辑上说,印证的是时间性问题的二律背反——侧重可凝定的、共时性的维面,必须跳脱于时间的约束之外,侧重不定型的、历时性的维面,则必须开放到时间的运动中,解决它的不二之途无疑是摆脱诗学与诗歌史、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互为对峙的困局。然而,时间性问题首先是巨大的哲学疑难,为此有必要从20世纪哲学和美学的进展提取有益的参照。
时间性的难题曾在海德格尔探讨实存哲学时被异常尖锐地突显出来。他的《存在与时间》试图回答的是,存在问题必须引渡到时间性的地平线中才能追问和推定。众所周知,哲学史上这部著作几乎颠覆性地重置了探讨本体论和形而上学问题的方法与立场,内中纠集了极为复杂的、盘根错节的运思,却并未有相对显明、直接的对诗(艺术)之时间性问题的探讨。尽管后来有将艺术命意到哲学论述中的另一重要著作《艺术作品的本源》,但即使在这里,海德格尔也没有以简洁、清晰的话语勾勒出时间性问题在艺术中的实际运作,而是延续和深化了此前他对存在这个元命题的关注。在此,不妨从另一个哲学家关于艺术作品的时间性命题的一篇论述集中的论文谈起。这就是伽达默尔的《审美的时间性问题》。从伽达默尔整体的哲学追求看,固然他与海德格尔之间差异大于相似,但是,时间性作为哲学疑难,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有相当一致的致思步骤,背后是共同的形而上学悬设和处置方案。伽达默尔的策略则从美学问题中提取证明,这与本文的目标更贴切。因而,我们的方法是,先缕述伽达默尔解决时间性疑难的方案,再回到他与海德格尔一致的哲学立场。
伽达默尔这篇文章的中心命意是,“同时性”(共时性)将投掷在“现时性”(历时性)中,而“现时性”折射和确认“同时性”。“同时性”作为绝对的时间,它寄身于艺术作品的结构,与作品的表现相关,而时间性则体现在审美感知中,“现时性”的审美意识印证艺术作品的“同时性”。客体的维面即作品的表现作为共时性的表征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主体的意识即审美感知以其每一个特定的时刻表现历时性的特点。在他看来,倘若没有“亲历其中”的意识置入,对象也仍旧是空洞的对象,但“亲历其中”不是对对象的据有,而是以此时此地的意识为开端,确认同时性。他如此道说现时性与同时性的关系:
无论如何艺术作品的存在总是与同时性相关。这同时性构成“亲历其中”的本质。同时性不是指审美意识的共生性,因为这种共生性指的是在一种意识中各种审美对象的同时存在和同时有效。与此相反,“同时性”在这里是要说一种独一无二的东西自行诉诸我们,哪怕它的来源是那么遥远,但在其指述中它便获得了完满的现时性。同时性也不是指意识中的一种给定性的方式,而是向意识提出的一项使命,一种根据自己所要求行使的作为。同时性还在于,它把握住事情本身,
从而这种“同时性”得以显示,而且这也意味着,在整个现时性中所有中介都被扬弃了。[10]123-124
在伽达默尔看来,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矛盾不仅可以实质性地克服,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矛盾甚至有望解决。同样,具体到晚清至“五四”期间的诗歌问题,循着伽达默尔的致思路径则是,诗学关注的即为他所言的艺术作品的表现问题,它牵连着本体的维度,诗歌史关注的则是艺术作品的感知问题,它关涉着认识的维度。借鉴伽达默尔意义重大,这不仅事关为“言说方式”所确立的诗学与诗歌史的双重目标提供依据,也为在更大的背景下——即诗学研究说到底是一种与美学活动有关的运思方式——提供启示。可以说,伽达默尔重新校正了理解艺术作品的美学路径。
显而易见,上文所引的“本源性的东西”、“自行诉诸”以典型的海德格尔式的话语显露了后者作为一种资源和方法的重要性,为此,必须回到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作进一步的论述。他在其中反复追问的是,譬如凡·高的油画《农鞋》,它的意义是否在于它对于某一双鞋的质地、外观以及这双鞋的所有者一时一地的精神状貌的直观性涂抹,以表象的方式对物的摹仿或是对某个柏拉图式的理念的分有?是否在于它体现了形式与质料的统一,成为感觉物和体验的对象?他认为这幅画得以成立有更深刻的根源,即“真理的自行置入”——艺术作品表征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真理本身,是存在的敞开和显现,与此同时,真理又保证了表征的展示。[11]这表面有些循环论的思路和海德格尔的独特运思有关,不如征引伽达默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导言》中的解释更直接:“海德格尔所密切注视的这一特有的存在是被遗忘了的人的存在,它并不处在固定的现存状态中,而是在操心的动荡状态中为自己的存在担忧,忧虑着它自己的将来。人的‘此在’是这样突现出来,即从他自己的存在出发去领悟自己的‘此在’自身。由于人的‘此在’不得安息地要追问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因而,就人来讲,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是受着时间的地平线的规定的。”[12]在这里,存在的“同时性”和此在的“现时性”之间不是单向的决定论关系,而处于互为关涉的“保证”与“显现”的双向抱持格局之中。在此,还可以略加回顾,诗学的方法出现在作为源头的亚里士多德那里时原本即有的丰富性,它在路径上和伽达默尔如出一辙。
如果说诗(纯文学观念兴起后,诗成了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类,亚里士多德的诗则指整个艺术门类)的核心命题是“言说”的问题,而戏剧的核心命题则是“观看”的问题(现有《诗学》的存本主要探讨悲剧,悲剧观即为亚氏的诗学观)。尽管古希腊时期用于表演的戏剧和今日主要用于阅读、聆听的诗截然不同,但是,亚里士多德阐述悲剧观的理路,实际上可以成功地支持上文所设定的,即“言说方式”应和诗学(结构的、本体的)与诗歌史(运动的、感知的)的双重目标。亚里士多德从两个维面设置他的悲剧观念。第一,悲剧作为客体即观看对象的规定性,它在技术层面如悲剧长度、剧情转折、性格特征等方面被约定为一种自足的、绝对的结构,在此结构中,悲剧的本质体现为普遍性和绝对性,所谓“偶然的事件又符合因果关系”,悲剧的进展“按可然或必然的原则”结构而成。第二,悲剧自足和绝对的结构必须在具体的感知(观看)中实现,因而关联到观众实际的审美反应,正是在观看中,绝对性的悲剧每一次得以重临。[13]本质上看,亚里士多德将诗学处理为结构与运动、客体和主体的辩证法。
四、面向诗学和诗歌史的双重目标
颇费周章地为“言说方式”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之统一陈说依据,无非为了强调,它是有充分依据的考量,其结构性的特征绝不静止、封闭,而包含有结构与运动的辩证法。换言之,诗学以它的共时性结构展望着历时性的“感知”,诗歌史的确认本质上是对诗学特性的感知,且为“结构”中的感知。这几乎可以视为研究中国新诗的重要途径,而不只为晚清至“五四”时段的诗歌所独有。因为诗歌演进的辩证法无外乎是,诗的特性之维护如果不是封闭静止化的,必得在历史的川流中不断检视,以保证何为诗的追问。反之,诗歌史的脉络如果不织进诗之特性中,则名之为社会史亦可,名之为文化史亦无不可(从破除学科壁垒的角度,我们并不反对诗的阅读、理解和研究有多种途径,对于在复杂时势与语言媒介几乎转折性改变中演进的诗歌,对它进行政治阅读无疑具有特别隆重的意味,但是,如果试图从作为美学活动的诗之变化来把握诗,则有难以跨越的路径需要穿透)。的确,这是诗歌(文学)研究特别的疑难。
“言说方式”面向诗学和诗歌史的双重目标,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的双向关联诚如上文所展望的,既类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此在,也相近于伽达默尔的结构与感知,同样,也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约定与观看之间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作为绝对的同时又有待检验的悬设那样,古希腊的典范悲剧也在形式规范层面首先被约定为结构性的,但它不能自我征显,只能在观看中被感知。这意味着,诗学和诗歌史、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也应确立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悬设。毫无疑问,应该选择共时性的结构作为绝对和待检验的一极,据此,对于一个时段的诗的把握,既不致过于决断地将它理念化,仿佛它是某一体式自设的结果,也不致过于仓促地将它放到线性伸展的链条中,仿佛它只是某些诗人个体和群落的流水作业。
将经验冲击内化为语言问题的诗歌,因而必将深刻地体现如下特点:形形色色的诗人们无论在实践上成功或失败、在观念上进步或保守,均不可能在经验与体式互为摩擦之外重置他们的语言和世界。作为一套显现语言策略的机制,“言说方式”超越代际、身份和诉求而成为共同的使命。与此同时,经验与体式摩擦之下的具体作为却丰富多样甚至相互对峙,“言说方式”也就成了梁启超、黄遵宪、胡适、郭沫若们位置的生动标定,醒目勾连在诗歌史历时性的辨认和感知中。
正是这种既是结构性的考量,又是差异性的凸显中,曾被简单化的体式问题在诗歌研究中的位置、功能和局限就可以得到进一步彰显。体式的凝定或破格说到底均不是诗的自足性的显示,哪怕在予以微调的梁启超或予以持守的王闿运那里亦然。比它更重要的问题恰恰是,古典性作为经验与体式之关系的表征所显现出来的闭抑与分裂的特点,尖锐地突显了诗辨识和建构它的“言说方式”的困境。再如同是以新诗象喻求解放的精神状态的康白情和郭沫若,他们的差异在自由诗这种笼统的体式中难以有效辨认,更内在的命题是,经验的冲击如何催逼出新的观物方式,使得立足于物象的康白情,在主体性的建构上落后于立足于心象的郭沫若:后者把平面、粘滞的物象的临摹变而成为心象的发明。实际上,“发明”作为一种崭新的美学有力地突显了康、郭在“言说方式”上的差异。
的确,只有紧扣“言说方式”的共时性结构,视之为诗的基本机制,才能重新评估闻一多、梁实秋与俞平伯、康白情的分野,他们的分歧在于对经验与形式、素材与技巧的不同侧重;与此相似,正是激赏汪静之《惠的风》在情感的直接性、经验的贴近方面等方面的新鲜、大胆,鲁迅诸子才会不遗余力地鞭挞并无视胡梦华关于伦理维度的诉求,在新诗张扬自我和个性的途中,他们才会宁要其“显”而不要其“隐”的表情方式,尽管他们的知识学养对古老的“温柔敦厚”之诗教并不陌生。
有人或许仍旧不免疑惑,为何不直接依仗诗歌史的尺规,将诗人们的作为放置到有深刻目的的叙事线索中,以此让彼此之间的合作、分歧、疏离以及彻底的分道扬镳显现出来呢?的确,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表层图像似乎是,有一条从“旧”走向“新”的明晰线索,但很大程度上却是借助传统/现代的模式想像出来的。这并不是说,从文学代际和文学先锋的意义上,该时段的诗歌没有守成与开新的区别,而是强调,“言说方式”作为一种从诗学到诗歌史的指示,必须以诗学层面的结构性的特点来征显诗歌史的变动性的特点,这意味着,要“锁定”诗人个体或群落在具体的诗的写作和观念上的展现,即在“言说方式”的系统中,他们的美学反应是什么。只有这样,“言说方式”作为一个涵纳经验的冲击于语言策略中的系统既体现为结构性的,在相应的语言策略中又体现了变动性。例如就晚清诗歌而言,要避免用“五四”“发明”晚清的陷阱,就必须把对象还原到它的自我纠缠。一般的诗歌史纵然摆脱了线性伸展的递进逻辑,然而值得警惕的仍然是研究视角的预设,例如黄遵宪通常被认为不如胡适“革命”,然后轻松抵达“不够进步—进步”的结论。但在线性的脉络中,显然掩蔽了如下更可行的路径:应该以黄遵宪等人的写作纠集的问题本身作为考察基点,通过他们身上的“古典性”质询古典本身。至于胡适们可能的“革命”意义,也不能按照新/旧、白话/文言、新诗/旧诗的逻辑来肯定,而应从语言策略的因应上显现的作为,即在超脱古典的层面上予以评价。一俟不同的“言说方式”之建构的差异性得以辨明,诗歌史的叙述才能合法地征显。
如果说,诗学分析中的共时性结构,为诗歌史的描述提供坚实的、可辨识的依据,那么,当转向诗歌史的历史性问题时,共时性结构则是作为目标得到凸显。只有这样,“五四”时期的诗的观念上的新
旧纠缠,就不仅应该看到人们祭起诗歌传统的背后,诗歌史尺度所具有的建构力量,更重要的是,内中作为机制的“言说方式”的考量才是诗歌史叙事的根本驱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新诗反对派的梅光迪诸人那里,他们采取理念化的诗歌观念否弃新诗,新诗人的诗歌(文学)史焦虑——胡适是最突出的代表,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文学史的结撰,为自身的写作确认一个能够自我决断的、与古典无关的共时性的系统,如此新诗人即可以在其中生动地、有合法性地展开他们的实践与建构,确立诗歌写作的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整理国故背景下的重新解释诗经、旧诗今译表面上是新的历史观的推动,实质上是“言说方式”作为一种共时性的系统造成的压力——他们要通过建构自身的历史评判确立现时性——相对于古史辨派和新诗人共时性的系统。因而,历时性的评判不仅是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历时性的叙述实际上是对共时性系统的确认和争夺。为此,面对反对派的美学理念,他们对新诗的攻击必须放在“古典型”和“现代型”的诗学对峙中予以审视;而颇有声势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改写“旧诗”的背后,“新”历史的冲动契合的则是“现代型”美学的创制要求。
五、结语
将形式维面的体式和内容层面的经验予以分离的做法,是曾经广泛影响文学理论的形式/内容二分法的体现,这种割裂带来的损害实质上是双重的,秉持此种陈旧框架的既有康德式的审美主义者,也有社会学式的经验主义者,但无论采取单边主义还是主从关系的做法,均难以全面审视诗(文学)在多重关系中的运作和变动。提出“言说方式”作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核心命题,是为了克服上述两种误区(两者择一和一主一从),试图融通体式与经验之间互为形塑的关系,进而将现代性的介入内化到诗在语言策略的反应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言说方式”并非静止的、惰性的结构,它的诗学诉求及表现始终被时间性——任何写作均是一定时段中的写作的命题所烛照,因而,“言说方式”是面向诗学和诗歌史的双重目标,在结构与运动、共时和历时中体现其辩证法的自觉。此点亦体现为对变动时代的诗之美学新变的关切:一方面,新诗在美学特质的认定、文学史的评价等方面都遭遇着特殊的困难。作为从正典的古典诗歌脱臼而出的诗歌,它要获得自主性的身份、标识,则必须和古典诗歌构成差异性的关系,因之是一种较之古典诗歌走向变奏的诗歌。另一方面,诗文类作为美学的沉积,它在破坏与承袭中始终无从割断既是背景也是框架的诗的理念,这使得新诗的研究必须在差异性与关联性之间建立张力。因而,即使现代性的诸种体验突兀地矗立于梁启超、黄遵宪、胡适、郭沫若们面前,也必须把它们内化到诗的考量之中,这既是诗学层面,也是诗歌史的要求。
注释:
①尼格尔·多德出色地梳理了哈贝马斯在修正、拓展马克思、韦伯的现代性构想方面的努力。(《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26-154页)
②帕特里克·贝尔特云:“哈贝马斯的事业无疑是勇敢无畏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案已被大多数人抛弃的时候,哈贝马斯旨在为批判理论找到新的哲学基础。”(《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190页)。
③“诗学”是充满争议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使用中时有变动。在这里,当指涉对一部作品(无论叙事性还是抒情性的)的形式、结构进行分解和辨认时,称为诗学分析,与此相应,下文将提到的“言说方式”,当它指涉诗在语言特质的维面中的运作时,也称为诗学层面的命题。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诗学则是与后来的文学理论互换的两个指称,但本质上看,诗学侧重的是和语言特质密切相关的可在技术层面分解的理论与方法。
参考文献:
[1]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3]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M]//罗志田. 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1-2.
[5]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M]//饮冰室合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6]刘大白.淘汰来了[M]//许德邻.分类白话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52.
[7]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M]//汪晖,译.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430.
[8]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M]//顾阳哲.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M]//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18.
[10]H·R·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M]//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1]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M]//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2]伽达默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导言[M]//美的现实性.张志扬,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
[13]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 126. com)
“Speaking Way”of Poetry from Late Qing to“May Fourth Movement”——Also on the Debates of Poetics and History of Poetry
LAI Yu-hu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Poetry changes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to“May Fourth Movement”,came from both the language style construction and also the press of modern experience. But how to understand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of the genre,and to avoid dispersing them,or unreasonable combination,this is just the key and difficulty to study the poetry of this period . Thus “speaking way”may be explained as that modernity would become a mix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t language “perception”,it lies in the lines interwoven with form and experience,changing the poem,while being changed by the poem. So,the“speaking way”must get rid of static,inert structure,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timing and get legitimacy from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It comes to be concern of poetry history from poetic appeal,and in the two mutually demonstration,finally,as a concept with dual aims of poetics and history of poetry,it reflects the dialectic character of structure and movement,synchronic and historic. On this basis,the poetry of this period kept fighting between style and experience,it can properly be understood as a process of mov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Keywords:poetry style;way of speaking;the late Qing Dynasty poetry;new poetry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poetry history;aesthetics mechanism
作者简介:赖彧煌,男,福建上杭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收稿日期:2015 - 03 -2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