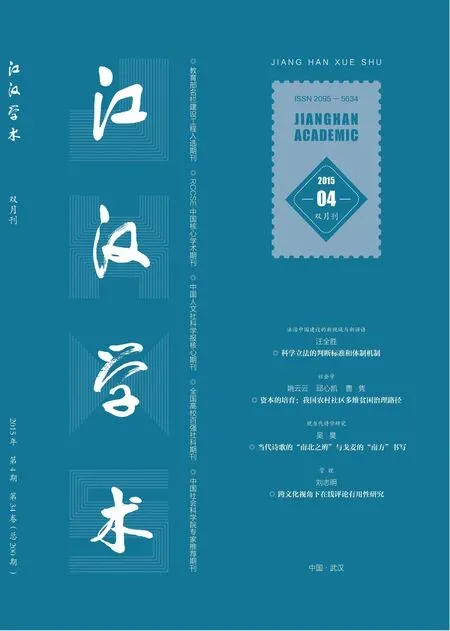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扩权现象研究
2015-04-18马岭
马 岭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北京10008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扩权现象研究
马岭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自改革开放30年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平稳过渡的时代需求。但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面对委员长会议的扩权现状——对常委会有明显的领导性,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不时超越权限代替常委会作出决定——有必要分析原因,限制委员长会议权力,改进人大制度。出现委员长会议不断扩权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没有厘清委员长会议制度建立的初衷,另一方面是由于行政集权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据此可知,要将委员长会议的权力“还权于会”(常委会),需要很多配套工作,如加强常委会能力,延长常委会的开会时间,真正落实自下而上的民主选择等。
关键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监督
中图分类号:D920. 0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4-0010-05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 jhun. edu. cn/jhxs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对人大制度的改进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等等①。笔者认为,这些任务的落实都与人大制度本身的健全完善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只有人大自身的权力运作模式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才能真正发挥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而我国目前人大系统内部的一些制度其合理性、民主性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最高权力机关中的委员长会议制度、在地方各级权力机关中的主任会议制度都存在一些弊端,其中有些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些是立法中就存在的问题。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在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1982年宪法设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以下简称“委员长会议”)制度是必要的,合理的。改革开放30年来,委员长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推动作用。据部分委员长会议的统计情况来看,其会议讨论和决定的内容,有些是属于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如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2010年6 月11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6月22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并对十五次会议的议程进行了建议与日程安排;2009年12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12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2009年6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6月22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2009年4月1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4月20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等等。有学者指出,“今天中国能够走上一条稳定、良性、独特的民主化道路,委员长会议合理审慎地行使议程设置权的功劳不容否定”[1]。笔者虽认为委员长会议行使议程设置权是否“合理审慎”尚需要再讨论,但中国的人大制度能够走到今天,能有今天的成就,委员长会议的功劳确实不容否定。只是这种功劳
可能主要表现在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平稳过渡的时代需求,满足了一种其他操作不可能立即实现民主化因而对“行政领导”的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对行政领导的需求应该逐渐淡化,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不是这样,而是与此恰恰相反,人大的行政痕迹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浓,甚至对宪法设计的原有轨道有所偏离,这就令人不能不为我国人大制度的发展前景担忧了。
二、委员长会议的扩权现状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委员长会议是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机构②,而“非实体权力机构,也不具有行政领导职能,无权代替常委会行使任何职权,只能为常委会行使职权服务”[1]。它不是决策机关,不是权力机关,而是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关。这种日常工作的处理权应具有服务性、辅助性的特点,具有某种处理议会内部行政事务的性质。《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将委员长会议的职权细化为四个方面是合宪合理的③,其中前三个方面是合宪的,第四项(处理“其他重要日常工作”)也是基本合理的[2],但在实践(包括立法实践)中被滥用了,多少偏离了宪法为之规定的方向。而《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监督法》等法律对委员长会议的有关规定则大幅度地超出了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范围,与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渐行渐远[3-4]。尤其是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及各地人大的主任会议更是极大地突破了法律的规定而拥有绝对实权。它名义上是常委会的日常工作机构,实际上重权在握,对常委会有明显的领导性,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并不时超越权限代替常委会作出决定,这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委员长会议应多长时间开一次,每次会议的时间是几天,会议召开的理由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有关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1993年委员长会议通过的《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第7条规定:“委员长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由于该规则是由委员长会议(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因此不应具有法律效力,它只是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这种“自我授权”很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在实践中,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开会的次数不尽相同,如第十届全国人大期间(2003—2008年),截至2008年2月28日共举行了75次委员长会议,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2008—2012年),到2011年4月21日共举行了62次委员长会议,其中2008年委员长会议开了15次,2009、2010年均各开了20次④。全国人大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⑤,委员长会议开会的次数却越来越多,“不定期召开”演变成“经常召开”,在人大这样一个应该体现民主的机构里,权力似乎被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了。
三、委员长会议不断扩权的原因分析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有些机构宪法或法律赋予其很大的权力,在实践中却发挥不出来,权力总是难以兑现或萎靡不振;而另一些机构,宪法或法律没有赋予其多少权力,却能够通过“实践”不断扩充自己的地盘,抢滩争权,委员长会议显然属于后者。从委员长会议30年的运作历史来看,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常委会工作机构的工作,起着核心领导作用。所有提交代表大会和常委会的议案实质上都由它决定。它还通过发布委员长会议纪要等方式,决定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发布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意见,常委会的人事任免办法等。可以说,委员长会议才是常委会真正的核心,而这个核心中的核心人物则是委员长和秘书长”⑥。
委员长会议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不能不令人担忧:我们的人大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是在向民主化还是向集权化方向前进?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人大曾被寄予厚望,宪法赋予它的崇高地位和巨大权力,虽然没有完全落实,但毕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如果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正在日益集中到十几个人组成的委员长会议手中,其民主性将受到挑战。议会的工作方式如果不能体现民主性,即使有效率,即使能实现实质正义,也有违民主议事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委员长会议有可能演变成“二政府”。如果人大本身的民主性不是在逐渐加强而是在日益削弱,甚至在演变成一个新的行政集权机构,那么笔者担心,这样的人大越强势,对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可能越不利。
何以至此?原因何在?
首先,委员长会议建立的初衷值得我们反省。1982年宪法的制定背景是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全
面铺开的初期,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人治”大泛滥之后,民主法制建设受到空前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设置委员长会议制度应该也是完善人大制度的一个重要措施。但委员长会议的作用与人大会议制度的性质是否会发生矛盾,二者应怎样衔接,才能有利于(而不是妨害于)人大制度的民主建设,这些问题当时可能在认识上尚不十分清晰。参与了1982年宪法修改工作的老一代宪法学者认为,委员长会议这种形式“对于发挥集体智慧,加强领导核心的作用,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5]。这是当时的普遍认识。问题是,为什么要在合议制的集体领导中“加强领导核心的作用”,谁是“领导核心”,委员长会议是人大的领导核心吗?议会这种实行合议制的民主机构是否需要一个核心领导,如果需要,合议制与首长制还有什么区别?宪法为什么要把人大设计成合议制而不是首长制?合议制的功能就是“发挥集体智慧”,如果不“加强领导核心的作用”,“集体智慧”是否就发挥不出来?我国中青年一代的议会专家也基本认同委员长会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机构”,虽然同时强调这“丝毫不意味着它有行政领导的职能”,其“行政化的倾向是应予防止和克服的”[6]。但笔者认为,如果承认委员长会议对常委会有“领导”作用就很难排除其“行政性”,从根本上说,委员长会议不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机构”,宪法没有赋予它这种地位。可能正是由于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不甚明了,我们才将委员长会议制度作为一种领导核心的因素嵌入到人大制度之中,一开始就寄希望于它发挥一种非民主的“领导”作用。
其次,行政集权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委员长会议在实践中的职权扩充是迅速的,又是无声无息的,正因为如此,才尤其令人担忧。由于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在人大中既要发挥集体智慧,又要加强领导核心的作用,因此在随后的实践中,包括在有关立法中,也就自然地沿着一种使人大集权化的方向行进,将委员长会议的地位一再提高,职权一再扩大。这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对民主的认识不够,偏爱集中,喜欢集中,习惯于集中,这样必然地与议会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驰。在实践中,常委会越来越依赖委员长会议,委员长会议越来越操控常委会会议,这种趋势已经得到立法的肯定,被制度化、法律化,且在实践中有愈演愈烈之势。难怪有年轻人在初步研究了委员长会议制度之后很自然地认为,“委员长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发挥着‘主管、管家’的作用”,委员长会议作为人大制度的“‘核心’指挥性作用表现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之间,委员长会议处于承上启下的交接地带”,委员长会议的存在,“弥补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各专门委员会直接领导、监督的不足和不便,提高了处理紧急事务的效率,在全国人大机构中承担了重要的职责,在整个全国人大架构框架中也凸显出了其中坚性地位”④。这样的认识很准确,很符合实际情况,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但不符合宪法肯定的议会民主之本质,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权力集中模式不仅表现在我们的体制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空气里,在上上下下所有人(包括老中青三代人)的思维中,使我们接受起来毫无困难。正是这种“软实力”可以将制度变形,可以将民主制演变为集中制,可以把人大逐步行政化。这一切都发生得悄无声息,即使专门从事宪法学、立法学研究的学者们,对此也少有警觉和批评⑦,仿佛是一场静悄悄的演变。
可能有人认为,人大内部的民主性可以到下一步再解决,现在先解决人大无相应权力的问题,只要人大(不管是人大还是其常委会或委员长会议)的地位提高了,能起关键作用(能决策、能监督),能形成权力制约(如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就是好的。但笔者担心,人大在提高自己地位的同时,如果自己也在日益行政化,这种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没有民主性做基础,将使我们的政治体制中缺少民主议事、民主监督的民主“主”渠道,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代表民意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就可能演变成官僚机构之间的摩擦和倾轧,而且也可能使政府分裂——行政权宜集中而不宜分散。如果委员长会议成为“二政府”,就可能出现多头行政,不仅降低效率,而且可能会有灾难性后果——在紧急关头互相扯皮、当断不断亦会误大事。同时,当人大内部已经形成权力集中模式且这一模式已经十分坚固后,再去克服它是否为时已晚,或许会在人大内部引发“革命”性的动荡。因此,不如在人大建设的过程中,边提高自己的地位边逐步实践其内部的民主,如果内部是民主决策,其对外行使的职权也将更有分量——其监督体现的是“民主”监督(14人组成的委员长会议即使有监督权也很难说是民主监
督)。坚守民主程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大当下落实自己的宪法权力(如由于内部实行民主程序而争执不下,一时难以形成统一的决定),进而影响到对外的监督效果,但从长远来看,从民主法治的“制度”建设(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效果)来看,是值得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解决当前的某个或某些实际问题,而是要建立起一个制度,要完善一个体制,设计一套权力程序,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抑制委员长会议扩权的对策
在分析了委员长会议不断扩权的原因之后,人们不难发现对其进行改进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要将委员长会议的权力“还权于会”(常委会),涉及到许多配套工作。如常委会能力的加强需要委员的专职化、专业化,需要为其配备大量助手,使委员们有时间、有能力从事有关立法和监督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同时需要延长常委会的开会时间,目前每两个月开一次会,一次会七天左右,一年不足六十天的会议体制,与国外议会一年四五个月甚至八九个月的会期相比,显然是过短的。如果说全国人大因代表人数多不便经常开会的理由尚能成立的话,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百五十多人比许多国家的议会人数还少,是完全可以延长开会时间的,因此常委会不能经常开会在理论上很难说得通。此外,常委会大权旁落和产生它的全国人大不是直接选举也有密切关系。间接选举与选民的距离相对较远,尤其全国人大代表是经过两层间接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由省级人大代表产生,省级人大代表由县级人大代表产生,县级人大代表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隔阂”就更加突出,因此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对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是明显有利的。当然这应该有一个过程,可以先实现省级和较大市级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之后再逐步过渡到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措施涉及到国家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如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如果能真正落实,代表们真正由民众选举而非上级指定或变相指定,他们就能转变意识——不再是“举手代表”、不再“唯上是从”,在他们积极行使代表权力、努力维护选民利益时(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再当选),很自然地不会再容忍自己的被动地位,对委员长会议的种种越权行为自然会积极提出批评和抵制,要求其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职权。当这种呼声不限于个别人而是具有普遍性时,制度的变革就可能发生。当然许多人寄希望于出现开明的领导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近代史上不乏当权者主动进行改革的事例,如自上而下地要求各国家机关严格依宪办事,依法办事,真正落实宪法对人大制度的种种规范,包括委员长会议仅仅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人大的权力真正取决于大会或常委会的讨论决定,取决于每一个代表或委员的投票,投票前允许竞争性辩论,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保障,等等。这期间,民众的法治意识、学界的思想成熟度、媒体的监督力度,都可能对人大及其代表产生极大的影响,毕竟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各种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注释:
①参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②我国1982年《宪法》第68条第2款规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③《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规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一)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二)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三)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四)处理常务委员会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④参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2008级本科生陈寿杰同学的学年论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制度研究》及其附件(未发表)。
⑤如八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时间分别为17天(1993年)、13天(1994年)、14天(1995年)、13天(1996年)、15天(1997年);九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时间分别为15天(1998年)、12天(1999年)、11天(2000年)、11天(2001年)、11天(2002年);十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时间分别为14天(2003年)、10天(2004年)、10天(2005年)、10天(2006年)、12天(2007年)。
⑥见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236页。蔡定剑教授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关于“核心中的核心”,《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第5条的规定可从一个侧面予以佐证:“委员长会议的议题由秘书长提出,委员长确定。”众所周知,会议议题
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权力。
⑦如我国有立法法学者这样介绍我国法案审议权的归属和审议程序:“审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法律案的权力,由委员长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常委会会议以及专门委员会行使。”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303页。
参考文献:
[1]冀业.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组织与权力运作研究[EB/ OL].(2009-06-05). http://m. 110. com/flzs/135358. html.
[2]马岭.《全国人大组织法》对委员长会议职权的规定[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3]马岭.中国《立法法》对委员长会议职权的规定[J].学习与探索,2013(8).
[4]马岭.我国非基本法律对委员长会议职权的规定[C]//周永坤.东吴法学:春季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512.
[6]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35,237.
责任编辑:刘伊念
(Email:lynsy@ jhun. edu. cn)
Phenomenon of Expanding the Right of the Leadership Council of NPC Standing
Ma Ling
(School of Law,China Youth Political College,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Leadership Council of NPC Standing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a certain extent,to meet the times needs of smooth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ety. B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to uphold and improve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when facing the reality of that the Leadership Council of NPC Standing expanding its right,such as leading NPC Standing obviously,from time to time exceeding its authority to make decision instead of NPC Standing,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causes,to limit the powers of the Leadership Council of NPC Standing,to improve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Keywords:NPC Standing;the Leadership Council of NPC Standing;People’s Congress system;democratic supervision
作者简介:马岭,女,河北邢台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4 - 12 - 23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