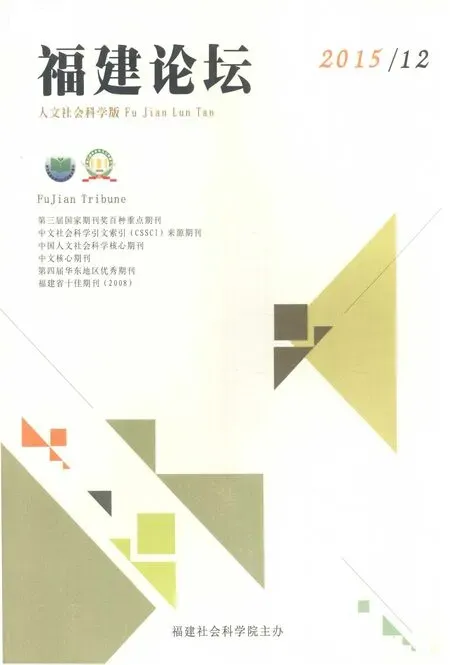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视域下的公平、效率和产权
2015-04-17吴闽川奉茂春
□ 吴闽川 奉茂春
马克思唯物史观将人类社会发展演绎出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源,以基本制度的变革为标志社会形态由低向高的变迁过程。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显然,马克思的制度变革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作用。其中,产权、效率和公平的价值观构成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强调的基本要素。
一、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的基本价值观
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的基本价值观强调社会公平,集中体现为阶级之间的平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伴随着资产阶级平等要求而提出来的。恩格斯指出,自从资产阶级的废除封建阶级特权的要求提出之时起,与之相应地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废除阶级本身的要求。无产阶级的平等不是表面的,它应当是实现于社会和经济的领域中的。
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的公平、平等价值观与新自由主义倒退的价值观截然对立。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倒退的价值观,不仅是因为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相对立,也因为其完全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在价值观上对自由、平等、公平三个基本价值观统一起来的进步观念。众所周知,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是把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建立在平等的假设前提之上的。他认为一个哲学家与一个挑夫的差别要远远小于一个牧羊犬与一个猎犬的差别。②斯密在这里指出了人与人之间天赋的差别与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是极不相称的。显然,他的矛头所指是封建等级特权对资本主义自由的限制和阻碍。这种限制和阻碍是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挑战,当然必将要被历史前进的步伐扫除。古典自由主义在价值观上对自由、平等、公平的观念是三位一体的。他们的平等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等级特权、要求自由经营的进步观念。
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对平等价值观的强调是建立在强调工人阶段利益和警示社会矛盾问题之上的。马克思1857年在分析英国工厂工人状况时指出:“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正在迅速接近爆发真正的社会战争的地步”。③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的平等价值观不但不是反映时代进步的“新”的理念,而且是历史倒退的落后观念。“分析旧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纲领之间的区别,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是看它们如何理解平等问题。”④这是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米瑟斯在平等价值观问题上的自我总结。他认为早期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的出发点是人人生而平等,这种忽视人与人之间巨大差异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甚至认为:“要想把人变得真正平等起来,这是靠人的一切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还将继续不平等下去。”⑤在这里,新自由主义部分代表人物的极端保守思想跃然纸上。 因此,人们又把新自由主义称为“新保守主义”,看来是不无道理的。
米瑟斯的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直白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奴隶时代。亚里士多德说:“非常明显,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⑥它使弱者把强者贬低到他们的水平上。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对平等的理想既十分同情,又十分警惕。当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时候,它只能是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即所有的人享受法定的或者名义上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平等就是不剥夺人们追求平等的权利,尽管这种追求的结果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可以让一个平民上升到权贵不敢轻视的地位,但整个社会是不可能到达终极平等的,当到达平等彼岸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就停止了进步。
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辩护将平等的主观理念与平等的客观条件混为一谈,完全掩盖不了其极端保守的右翼理念。弗里德曼就提出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有着本质的不同。“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格或任何其他无关的特性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才能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⑦这种说法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反对等级特权的革命思想,明显表现出为资本主义人与人结果不平等理念的辩护性质。事实上,从来也没有一位思想家要求彻底的事实上的终极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是现实世界可以而且应当追求的目标。但是,平等这种进步的理念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追求,在思想观念上把平等与社会进步对立起来,如何能够保证机会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怎么能够将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而加以对立?相对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把平等、公平、正义从自由的理念中割裂开来的错误认识,温和的新自由主义在价值观上是有可取之点的。例如,罗尔斯认为,可以把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观念与正义原则联系起来,自由相应于第一个原则,平等相应于与公平的机会平行的原则, 博爱相应于差别原则。⑧尽管罗尔斯没有把平等放在与自由、正义等同的地位,而是认为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但是相对于极端的自由主义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比古典自由主义前进了一步,他在肯定自由价值的同时,不仅设法解决平等问题,而且还试图将传统政治哲学所忽视的博爱问题纳入社会基本结构之中。”⑨这种温和的自由主义是对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用机会平等的概念把平等与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完全割裂的回归。当然,否定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的倒退的平等价值观并不是要求达到人与人之间终极的平等。同样一个孩子,如果出生在非洲战乱的国家里和出生在美国上流社会里,其人生道路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价值观认为对公平和效率是统一起来的,如果社会的普遍的不公正则会导致“人的完全丧失”和“社会解体”的结果。⑩所以,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在倒退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极度不稳定。这种模式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欠发达国家越来越频繁地爆发金融危机。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都突出地反映了“华盛顿共识”倒退的平等价值观建立的新的剥削模式。二是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绝对贫困和饥荒越来越严重。在1996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在落后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灾害能与饥荒相比,后者在近两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⑪
二、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破除了私有产权高效率的崇拜
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强调所有制的基础作用,并且认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要彻底解决这一矛盾,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把公有制与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并且在苏联解体后,成功地掀起了私有产权崇拜的高潮。在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核心就是私有化,甚至改革的目的就是私有化。这种极端的观点之所以能够推行,是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影响密不可分的。该理论认为,私有制消灭后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推行公有制将会面临严重的极权主义问题。1944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⑫这是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独裁主义混为一谈的一贯做法。当然,作出这种论断,也是看到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公有制实践中的失误。例如1939年,在苏联国民中11%-12%的上层当时的收入大约占国民收入的50%,这个差别比美国的还要大些,因为在美国当时10%的上层人的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35%。⑬
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产权崇拜的理论核心就是“华盛顿共识”理论基础之一的科斯产权理论。其所用的手段就是用模糊概念和逻辑错误的方法来神化私有产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斯的产权清晰论的实质是什么?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科斯的产权清晰就是私有产权。”⑭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成功地神化了所谓“科斯定理”。⑮“科斯定理”的中心概念是交易费用和产权清晰。而交易费用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西方现代产权学派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争议是不可解决的,如果他们达成了一个统一而明确的概念内涵,这一学派的基础和内核将面临分裂和崩溃。他们用一个模糊的概念推导出只有私有产权才是产权清晰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和实践错误。
首先,私有产权--产权清晰--资源利用的高效率,这样的推理具有逻辑上的错误。产权是财产权利的简称。产权的形式有个人私有产权、共有产权、股份制产权、集体产权、国有产权等等多种形式,并不是只有私有产权才是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也不必然导致资源利用的高效率。由于资源的稀缺和人类欲望的排他性,产权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私有制的产生就是在人类有一定的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基础之后发生的。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进一步促使了社会分工和财富的增长。这种增长建立在对人的激励和竞争的基础之上。因为“只要我们生活在稀缺性的世界之中,我们就无法减少或者消除竞争。”⑯
然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财富的增长却加剧了贫富分化,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商品。”⑰私有制虽然能够产生激励和动力,但它隐含着提倡人的占有欲望。马克思认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以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为中介而取得的。”⑱所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强调分配正义。只有解决人与人之间这种占有欲望的矛盾,私有财产才能充分发挥出激励作用。也就是说,需要解决财产的分配问题,私有产权才能有高效率。然而,私有产权的分配问题正是导致竞争失败和社会冲突的根源。所以,私有产权-产权清晰-资源利用的高效率,这样的逻辑忽略了分配问题这一重要环节, 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甚至是错误的。
其次,私有产权-产权清晰-资源利用的高效率,这个推理也违反实践经验。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常常会提出只有私有产权才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的观点。因为私有制产权明确,资本的所有者(股东)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监督到位,效益就高。这种道理似乎简明透彻,无懈可击。然而,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典型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美国资本主义, 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公司丑闻” 暴露出私有产权仍然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上的同样困境。2001年美国能源业巨头安然公司被揭露虚报近6亿美元的盈利和掩盖10亿多美元巨额债务而宣告破产,2010年美国高盛集团涉嫌欺诈投资者10亿美元被指控,2013年美国银行被法院判决出售欺诈性抵押贷款,大量的私人垄断集团的典型欺诈事件说明,西方产权理论“主张只有私有制才是产权明晰和高效率的观点,违背了分析逻辑和实践经验。”⑲
由此可见,私有产权崇拜并不是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私有产权崇拜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垄断资本向全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国际垄断资本在向全球自由扩张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国有制为基础的金融机构。因而他们试图推行其并不流行的私人垄断银行,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命脉控制在私人手中,以便排除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权力对国际垄断资本的阻碍。事实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对本国的主要金融机构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 例如,据统计,在所调查的全世界92个国家中,没有国有银行的国家只有7个,分别是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南非、新西兰、塞普路斯。⑳单就国家数量来说,我们可以说国有银行才是常态,私人银行反而是特例。与此相对应,英国、美国的前十大银行都是控制在私人或家族手中。这些金融垄断资本一方面要求维持现有的垄断秩序,一方面又要求能够凭其强者地位在自由竞争中获利,反对国家干预,反对福利国家,这就需要向其他国家推行私人垄断银行这一模式。这也是为什么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又被人们称为保守主义者的原因,也反映了“华盛顿共识”理论上的右翼性质。
三、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揭示了国际垄断资本利益集团的剥削模式
马克思制度变革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从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看,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日益社会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权的集中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极少数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从国家垄断进一步走向国际垄断。以上两个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矛盾和危机。马克思指出:“尽管有过去的种种警示,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新出现,所以,我们不能把个别人的冒险行为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㉑。“华盛顿共识”是在20世纪末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国际大趋势下形成的。与19世纪马克思时代的全球化运动一样,目前的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国际资本流动。所不同的是,这一轮全球化运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一次以信息革命为主要技术特征,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力量的全球化运动。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制度变革的必然现象,特别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下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现象。这种模式既要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利益,又要能够被广大欠发达国家接受。从“华盛顿共识”推行的过程看,国际垄断资本正是利用了欠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模式。从“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看,许多国家相继发生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后台的美国却再次强化了世界霸权。虽然作为本次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技术特征的信息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技术上的特征掩盖不了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性质。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对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现象作出了科学的本质分析和回答。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列宁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资本输出。”㉒资本输出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㉓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这种剥削性质不但没有改变,而且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兴起,“华盛顿共识”模式向发展中国家和原苏联和东欧的推行,这种国际剥削还有加剧的趋势, 并且逐渐建立起新的剥削模式。这是一种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为基础,以美国武力保护为核心,以新自由主义全球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国际剥削秩序,表现为“华盛顿共识”推行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结构。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正是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需要极力维护的剥削性质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垄断资本一方面极力主张资本的国际自由,一方面又极力维护技术和劳动力的管制,这就必然导致在国际交换中的两种不平等:“一种是由于各国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引起的不平等;另一种是由于各国的工资率不同引起的不平等”。㉔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不平等从表面上看只有后者才具有不平等交换的性质,然而,前者的不平等即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造成的不平等更隐蔽地反映了不平等国际交换的性质。㉕因为正是资本有机构成和国际分工决定了工资率,而不是相反由工资率的差别决定资本有机构成和国际分工。从本质上说,这两种不平等是互相统一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所造成的不平等国际分工导致的国际剥削更具有基础性和隐蔽性。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加速扩大,国际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促使资本流动的形式也相应变化。在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力量的条件下,资本流动从银行借贷为主转变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借贷三足鼎立,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不平等国际分工全球化模式。
注释:
①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2012年9月第3版。
②参见(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原文为:“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 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就天赋资质来说,哲学家与街上的挑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 比长耳狗与牲畜家犬的差异, 少得多。”
③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
④(奥地利)米瑟斯著,韩光明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奥地利)米瑟斯著,韩光明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第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弗里德曼著,胡骑译:《自由选择》,第13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⑧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第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⑨罗文东:《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正义》,载《自由与秩序》,第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2012年9月第3版。
⑪参见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季海宏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15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⑫⑬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第1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⑭吴易风:《不能让西方产权理论误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载何秉孟主编《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第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⑮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叫做“产权神化”。 他研究了几种神话,他说:“经济学中也许没有一种神话像我要说的产权神话那样影响深远。这种神话认为,人们必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恰当地界定产权,这样经济效率就能得到保证。产权如何界定无关紧要。”参见吴易风:《不能让西方产权理论误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第22页,载何秉孟主编《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⑯[南]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著,蒋琳琦译:《产权经济学》,第3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⑰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7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⑱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03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
⑲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前言第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⑳李扬主编:《中国金融理论前沿Ш》,第78页,社会科学方面出版社,2003年版。
㉑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01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
㉒《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㉓《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㉔参见杨玉生、杨戈著:《价值·资本·增长》,第26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㉕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曼纽尔(ArghiriEmanuel)1969年出版的《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认为,仅仅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平等对于外贸来说并不是特例,一国不能因其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别国而抱怨在同其他国家交换中失去剩余价值。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做了一些基本的假定:1、各国间的劳动是不流动的,而资本是流动的;2、 资本的流动性引起各国间的利润平均化;3、由于各国间的劳动不流动,工资是一个独立变量,在不同的国家形成不同的工资水平;4进入国际交换的某些商品对某些国家是不同的;5、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欠发达国家)的工资差别大于其生产力的差别。参见杨玉生、杨戈著:《价值·资本·增长》,第26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