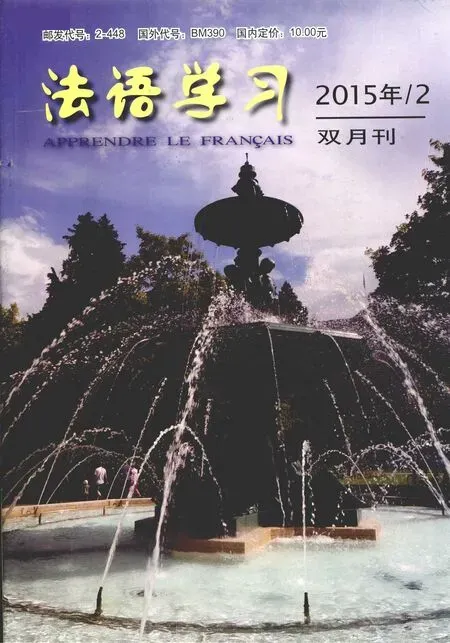加缪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形象
2015-04-17南京理工大学胡园园
●南京理工大学 胡园园
加缪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形象
●南京理工大学 胡园园
在《知识分子论》中,赛义德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来定位知识分子的角色。他的知识分子观,为解读法国作家加缪的知识分子形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从《局外人》到《正义者》、《反抗者》,从“荒诞”到“反抗、自由、激情”,加缪的知识分子形象贯穿他的一生并反映在他的众多作品中。从严格意义上说,加缪不是一个后殖民知识分子,没有参与解构主义观照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但以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身份话语来看,他具有这一群体普遍的认同特征:流亡、介入、世俗批评、捍卫普适价值。本文将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结合《知识分子论》的相关理论,还原一个具有“后殖民知识分子”形象的加缪。
加缪,知识分子论,局外人,反抗者,正义者
一、引言
在传统观念中,加缪与“后殖民知识分子”的称呼相去甚远。即使是曾介入过殖民主义讨论的萨特都没有被称作是“后殖民知识分子”,尽管他曾为弗兰茨·法侬的后殖民主义著作《地球上不幸的人们》做过序言。就连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本人也把萨特而不是加缪看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萨特那种“甘冒重大的风险,以全然的努力、冒险、意志来讨论殖民主义、献身、社会冲突”(赛义德,2013:18)的介入态度打动了赛义德。当然加缪也是个介入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一位站在后现代主义土壤上的文化英雄”(王洪琛,2011:5)。但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没有反对法国干预阿尔及利亚的态度使之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擦肩而过。事实上,通过对加缪生活、思想和作品的深入挖掘,我们发现这位被福克纳视为“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一直以来从未屈从于任何势力、任何团体,在任何时刻都以一个醒世作家的身份去针砭时弊。他的身份、他的态度、他的行动与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不谋而合。
1993年,赛义德在莱思演讲中表达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观,他的演讲集结成《知识分子论》这本著作。这是对后殖民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一次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赛义德看来,知识分子,无论其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是什么,都要坚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为了担起这份责任,必须不偏不倚,打破思想的壁垒,成为“局外人”、“业余者”,以语言表述立场,以介入呈现态度。当然,后殖民知识分子们不同于雨果、左拉所开创的知识分子阵营。他们不仅有醒世、介入、反抗的表征,更有自身的身份印记。而这些印记将他们与传统意义上、技术层面上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后殖民知识分子有着真实和隐喻的流亡身份,世俗批评和捍卫普适价值的践行身份。“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后殖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罗如春,2012:91)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样一种知识分子形象与在1960年就已谢世的加缪有着非常相似的吻合。接下来,我们将从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出发,依托加缪的生平、思想和作品,给这位在任何时刻都具有时代性的作家做出另一番文化身份定位。
二、真实和隐喻的流亡身份
加缪于1913年出生在法国殖民时期的阿尔及利亚。二战前,由于与阿尔及利亚当局政见不合,加缪曾经有过一段流亡法国的岁月。虽然与其他流亡作家不同,加缪来到的是他的血缘母国,但是由于从小在殖民地长大,深受地中海多元文化影响,加缪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尽管之后的加缪在法国文坛上大放异彩,成为“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但是1951年《反抗者》的发表所引发的加缪与萨特之间的论战,让他在巴黎知识分子中受到了排挤,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使之一度放弃政治,只投身于艺术创作中。50年代后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更是让加缪处在两难的境况中。在这场政治军事斗争里,加缪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不会选择站在任何一方。因此他遭到了来自双方的责难,一时间成了孤独的局外人,两个祖国的流亡者。作为真实的流亡,地理迁徙与政治文化冲突给加缪贴上了流亡者的身份标签,也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中得到了反映。存在于理想中的王国必定要经过现实中的流放才能到达。这部作品通过六个故事展示了不同形式的流放。“在颠簸困顿的旅途上,在异教徒酷热灼人的盐城里,在狭小简陋的工厂中,在荒凉不毛的高原上,在巴黎古老破旧的街区里,在巴西偏远蔽塞的小镇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空虚、冷漠、隔阂、误解、孤独和愚昧的气氛,令人感到窒息、恐惧、压抑、悲哀、惶惑和愤懑。”(郭宏安,2011:107)但人也只有在如此艰难的真实流放中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洞悉到各种利益、集团、主义之外的普遍价值。这部发表于加缪晚期的作品凝集了加缪的人生感悟,勾勒出一个冷峻而坚定的流亡知识分子形象。
流亡从现代意义上看,不仅是真实的流亡,更是隐喻的流亡。它指的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赛义德,2013:48)。这些独立于主流,坚守自我价值观和判断力的知识分子,甘做任何体系的局外人,处在一个时刻警觉的批判立场。荒诞一直是加缪的经典小说《局外人》的意识色彩。面对一个荒诞的社会,主人公莫尔索所表现出来的漠然是其最终从这个社会上出局的关键原因。但面对道德和司法的评判,莫尔索表现得却是光明磊落、拒绝撒谎。这是“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格勒尼埃,1997:68)”,一个以身试法去超越荒诞的人。“‘荒诞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为‘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郭宏安,2011:59)作为一个局外人,莫尔索身上有着流亡知识分子的影子。他在精神上的偏离、疏远和独立,帮助他打破思想壁垒,颠覆社会权威。莫尔索身上也有加缪的影子。从青年时代开始,加缪就是一个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早年在阿尔及利亚,他反抗过殖民当局的压迫政策;二战时期,他加入抵抗运动,参加反法西斯战斗;战后,他不参与任何政治派别,超越左右派对立,跨越边界,独树一帜地只为正义而言。回顾过往,隐喻的流亡身份的确让加缪更靠近真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萨特屈从了意识形态,那个管猫叫作猫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加缪。
三、世俗批评家和普适价值捍卫者的身份
在赛义德看来,真正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世俗批评家。“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赛义德,2013:13)这里的世俗批评指的是以语言表述立场,介入现实的行动。作为一个世俗批评家,后殖民知识分子表现出无比可贵的勇气。加缪也说过知识分子是“敢于抵制一时风气的人”。(Daniel,2010:146)他本人与殖民当局对抗过,与法西斯周旋过,与民族主义谈判过;他坚定不移地反对死刑,反对一切的专制、集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冲突。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期间,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回到那里,做哪怕是最后一线的和平努力。不可否认,加缪是一个不安分的人,热衷于反抗的人,这也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世俗批评家。作为加缪后期的思想作品,《反抗者》是其超越荒诞之后的一个思想大集合。它的时代背景为它带来更多的批判意味。在当时以左派思潮占优势的法国文化界,加缪是为数不多的清醒明智并敢于表达的人。他既反对美式帝国主义,也反对苏式社会主义。“加缪的思想超越于左右两种思想的对立,唯以揭露当代的虚无、极端和失度为务……”(郭宏安,2011:176)这一点与赛义德对待中东问题的立场如出一辙。赛义德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反对西方干涉的同时,也指责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的不对之处。身处流亡状态的后殖民知识分子,以一种中性的视角来干预社会,以反抗的形式进行世俗批评。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在进行一种身份的建构。“我反抗,故我们在。”(加缪,2010b:185)像其他后殖民知识分子一样,加缪的自我身份认同表现在这种积极践行世俗批评的行动中。
赛义德认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应该是普适价值的捍卫者,他们应从整个人类的范畴来看待问题,而不是去维护某个集团的价值。虽然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特性,但是赛义德要求后殖民知识分子们能摆脱民族内部共有的特色、偏见和固定的思维模式,逃脱民族和社群在我们周围设定的边界和藩篱,以人类的普遍正义作为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反抗是为了维护正义,维护独立于虚无主义和革命之外的人性价值。在取自于历史题材的剧作《正义者》中,加缪给我们描绘了两个饱满的当代英雄形象——卡利亚耶夫和多拉。他们具有为理想、为解放全人类的献身精神,但同时他们却没有丧失人性中固有的良心。因为同情、友爱和尊严,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暗杀之路。他们是加缪心中所深深敬佩的人,“因为他们在最残酷的任务中,未能消除良心的不安”(加缪,2010a:196),因为他们“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加缪,2010a:218)。《纽约时报》曾称加缪为“局指可数的具有健全和朴素的人道主义外表的文学大师”。长期以来,加缪都遵循着以人为本的简朴道德观。在《反抗者》一书中,加缪并非破而不立。在中允地进行反抗的同时,他遵循着普适的人性价值,倡导一种平衡适度的“地中海思想”。“在思想的中午,反抗拒绝神化,以便共同斗争,承担共同的命运。我们选择了伊塔克岛,忠诚的大地,大胆而朴素的思想,明智的行动,通达的人的慷慨大度。世界在光明中成为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我们的兄弟们与我们在同一个天空下呼吸,正义在发挥作用。于是欢乐涌现世间,有助于人们生存与死亡。”(加缪,2010b:405)这种“地中海思想”具有一定的理想高度。但站在人类普遍正义的角度,它与后殖民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普适价值是相吻合的。珍视生命、追求幸福、崇尚均衡、讲求正义,这些最简单不过的字眼在面对民族、种族、地域,甚至是性别冲突时,都会变得难以实现。而此时就需要我们的后殖民知识分子,以局外人的立场、反抗者的批评、正义者的道德来维护和捍卫它们。
四、结语
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活动离不开后殖民主义话语。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从后殖民批判的角度出发,定位在以他为代表的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上。但是他的知识分子观超越了后殖民的理论范畴,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偶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赛义德,2013:65)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是沿着人类进步的车轮而来的。他们独立,向权威挑战,为弱者说话,坚持正义。他们的身份特征虽然产生于特殊的后殖民语境,具备一定的理论渊源,但这些特征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并非只局限于后殖民主义一隅。加缪身上所具备的知识分子特征恰好与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身份表征具有共通重叠之处,这为我们对他的文化身份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文化身份具有多重性,它伴随着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的经历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生前的,也可以是生后的。一向与“主义”保持距离的加缪,想必不希望我们把他与任何“主义”挂钩。在这里,我们不能妄下定论,给加缪贴上“后殖民主义”的标签,我们只是客观地还原他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形象。这是我们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结合当代理论,对加缪的文化身份所尝试的另一番解读,所提供的另一种思考。
☉
阿尔贝·加缪(柳鸣九 等译),加缪全集(戏剧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a.
阿尔贝·加缪(柳鸣九 等译),加缪全集(散文卷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b.
爱德华·W·赛义德(单德兴 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郭宏安,阳光与阴影的交织[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罗如春,论后殖民知识分子——重读赛义德《知识分子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87-91.
罗歇·格勒尼埃(顾嘉琛 译),阳光与阴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王洪琛,加缪的思想世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Daniel Jean,Avec Camus—Comment résister à l'air du temps,Paris:Editions Gallimard,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