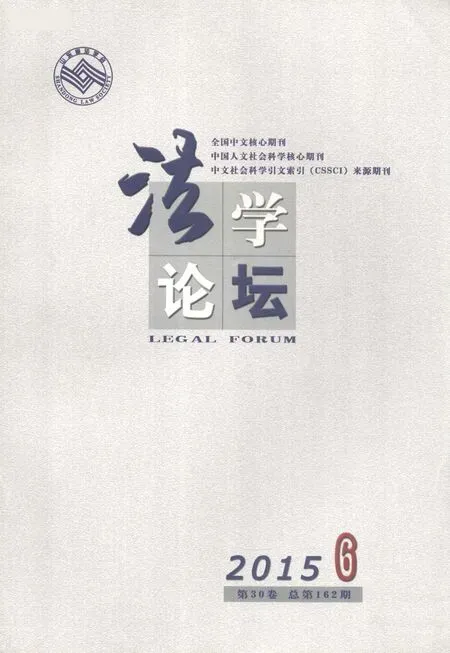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新发展:表现、效果及应对
2015-04-17陈正健
陈正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29)
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新发展:表现、效果及应对
陈正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29)
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自诞生以来就始终与国民待遇交织在一起,并以限制国民待遇为目的。进入21世纪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出现了新发展,除了继续限制国民待遇外,其开始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发挥限制高水平投资保护标准的作用。然而这一新发展并没有得到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肯定,从而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限制效果。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在投资仲裁实践中主张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并没有向前演进,而是冻结在尼尔案确定的标准上;同时在对外签订的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或指向。
国际最低待遇标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公平与公正待遇;保护与安全标准;尼尔案
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最早可追溯至14世纪关于外国人的待遇规则。*参见Martins Paparinskis, The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 an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1.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中的最低待遇标准一直都是 “文明国家”与落后国家、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文明国家”(或殖民国家或发达国家)始终赞同和支持使用国际法中最低待遇标准对国民待遇进行限定;而与之相反,落后国家(或殖民地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极力对此进行反对。*参见[意]卡塞斯:《国际法》,蔡从燕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4页;[英] 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白桂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20世纪以来,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论从国际公法领域逐渐延伸到国际经济法领域,尤其是国际投资法领域,一直都未停息过。基于对本国文明程度(经济、政治、文化尤其是法律制度)的自信,以及对其他国家文明程度的不信任,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国际最低标准是习惯国际法规则,旨在为外国人提供基本的待遇,而不管东道国的国内法规则。换言之,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与国民待遇标准是相对应的概念。*参见Roland Kläger,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9.国民待遇标准规定外国人仅能获得与东道国国民相同的待遇,而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则通过国际法为外国人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东道国必须赋予外国人的,同时其也不受东道国给予其国民的待遇的限制,违反了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可能导致国家承担国际责任。*参见Alexandra Diehl, The Core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145.
然而,进入21世纪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即除了继续对国民待遇进行限制外,其在国际投资法中开始扮演限制高水平投资保护标准的角色。不管原因如何,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这一新发展都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两类国家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问题上首次达成了“共识”。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这一新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出现的一些投资仲裁案件频繁涉及到对此的认定。无疑,认定的实际效果将直接决定这种转变是否有效和成功。正基于此,本文拟结合相关国际投资条约和投资仲裁实践对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这一新发展及其实际效果进行探讨,并针对其中的相关问题提出中国可采取的应对之策。
一、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新发展的表现
“在2000年以前,公平与公正待遇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原则性的宣言,一个东道国保护外国投资的目的的宣言,而绝不是一个有着实体内容的适当的法律保护。当国际仲裁庭开始对公平与公正待遇进行解释时一切都改变了。如今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与违反不得征收的条款一道,不遵守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成为了投资者最频繁指控政府违法的理由。”*Sebastián López Escarcena,The Elements of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http://ghum.kuleuven.be/ggs/publications/policy_briefs/pb14.pdf, p.2, 2015-05-19.与公平与公正待遇相比,虽然保护与安全标准一开始更不被人们所注意,但是由于其自身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近些年来,以此为依凭主张投资保护的案件逐渐增多,且其确定的投资保护水平也不亚于公平与公正待遇。*参见陈正健:《投资条约保护和安全标准的适用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5期。可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并没有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因为其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然而,这一情况在近年来明显改变了。公平与公正待遇几乎成为了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每案必涉的核心问题,保护与安全标准的“出场率”也大大提高,两者甚至被经常滥用,从而导致国家与外国投资者之间利益失衡情形的频繁出现。对此,国际社会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对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宽泛的范围进行限定,其中引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它们进行限制是一种主要方式。经过总结,笔者发现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进行限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NAFTA的解释对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纳入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一个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缔结的区域性贸易协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其第11章“投资”中第1105(1)条“最低待遇标准”规定:每一缔约国得依据国际法赋予缔约他国投资者以待遇,包括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的保护与安全。从文本来看,该条款仅提到依据国际法,而并没有提及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字眼。由于“国际法”渊源的多样性,致使外国投资者不断依据该条款所规定的高水平保护标准提起投资仲裁。面对这一条款,投资仲裁机构也以一种相当宽泛的标准对其进行解释,即认为公平与公正待遇是“添加”在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之上的投资保护标准。仲裁庭的这种解释方法远远超过了三缔约国设计该条款的初衷,因此,三个国家都对此种发展深感忧虑。于是,2001年NAFTA自由贸易委员会发布了解释说明(Notes of Interpretation),对“最低待遇标准”进行了解释:1.第1105(1)条规定将习惯国际法上的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作为赋予缔约他国的投资者投资的最低待遇;2.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概念不要求超过习惯国际法上的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3.对NAFTA其他条款或其他条约的违反并不构成对第1105(1)条的违反。该解释说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高水平投资保护标准(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进行限定,其明确否定了之前的投资仲裁庭采用的“添加”解释路径,而规定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严格地限定在习惯国际法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上,不允许有任何扩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还存在即使国际投资条约中没有提及“习惯国际法”,国际投资仲裁机构依然援引习惯国际法对某些有争议的条款进行限定(解释)的现象。参见陈正健:《国际投资条约中不排除措施条款的解释》,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从文本上来看,这种方式有效地限定了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范围的扩展。
NAFTA自由贸易委员会的解释说明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进行限定的做法很快被很多其他国际投资条约(范本)所采用。
(二)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对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纳入
作为NAFTA缔约国的美国和加拿大发布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中非常一致地采用了上述路径。2004年和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5条“最低待遇标准”规定:1.每一缔约方应该根据习惯国际法赋予条约所涵盖投资以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2.为进一步明确,第一款中规定的是根据习惯国际法上的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赋予条约所涵盖投资以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概念不要求添加或超越该标准,也不创设额外的实体权利。 2004年《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5条“最低待遇标准”也采用习惯国际法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来限制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的路径:1.每一缔约方应该依据国际法赋予所涵盖投资以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2.第一款中的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概念并不要求添加或超越由一般国家实践接受为法律的外国人待遇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要求。3.对本条约或其他国际条约的另一条款的违反不能认定为对本条的违反。
NAFTA缔约国除了在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中采用这一路径,还在对外缔结的国际投资条约中使用这一路径,如2005年《美国和乌拉圭投资条约》第5条“最低待遇标准”采用了与美国2004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完全相同的规定;又如2012年缔结的《中国和加拿大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4条“最低待遇标准”规定。
除了NAFTA缔约国发布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和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用习惯国际法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来限定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外,其他一些国家也采用这一方式,如我国在近些年来也开始采用这一路径对它们进行限定。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哥伦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双边协定》第2条规定:3.每一缔约方都应根据习惯国际法赋予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以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的保护与安全。4.为进一步明确,(1)“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的保护与安全”的概念并不要求赋予超出根据习惯国际法标准赋予外国人的最低待遇标准所要求之外的待遇。
(三)双边经济贸易协定对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纳入
引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进行限定的路径很快被一些含有投资章节(条款)的经济贸易协定所借鉴。
首先,这一路径表现在NAFTA缔约国对外缔结的一系列贸易协定中,如2006年《美国—阿曼自由贸易协定》第10章“投资”的第10.5条“最低待遇标准”规定:1.每一缔约方应该根据习惯国际法赋予所涵盖投资以相应待遇,包括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2.为进一步明确,第1 款规定的赋予所涵盖投资的最低待遇标准是习惯国际法上的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其中,“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的概念并不要求添加或超越该最低待遇标准,也不创设额外的实体权利。第1款规定的义务:(a)“公平与公正待遇”包括根据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在刑事、民事或行政裁决程序中不得拒绝司法;(b)“全面保护与安全”要求每一缔约方规定依据习惯国际法所要求的治安保护水平。3.对本条约或其他国际条约中任何其他条款的违反并不构成对本条的违反。除此之外,2006年《美国—秘鲁贸易促进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以及2007年《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巴拿马贸易促进协定》等都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措辞。
其次,近些年来,很多NAFTA缔约国以外的国家缔结的贸易协定也采用了这一路径。如2009年的《印度—韩国综合经济伙伴条约》第10.4条规定:1.每一缔约方在其境内应该赋予另一缔约方投资者的投资以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的保护与安全。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概念不要求添加或超出习惯国际法上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所要求的待遇。又如2012年9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第6条“最低待遇标准”规定:1.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国际法赋予所涵盖投资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2.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保护与安全概念并不要求添加或超出最低待遇标准的要求(为进一步明确,本条中规定的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应为依据被普遍实践所公认并接受为法律的国际习惯中赋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最低标准待遇)。3.对本条约其他条款或其他条约条款的违反并不构成对本条的违反。
采用这一路径的经济贸易协定还有2006年《日本—菲律宾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9年《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马来西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等。
二、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新发展的效果
21世纪以来国际投资条约中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新发展到底有什么实际效果呢?显然,具体效果需要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来进行判定。因此,下文将对近10多年来涉及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新发展的一些投资仲裁实践(主要集中于NAFTA背景下的仲裁案件中)进行梳理,以此来说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新发展是否发挥了实际效果。
(一)力主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演进
实际上,投资仲裁实践中关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争论较多地集中于尼尔案所确定的标准上。更为具体地讲,到底外国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是停留或固定在尼尔案所确定的标准上;还是相对于尼尔案标准已经向前演进,即其违反门槛已经明显降低。在NAFTA自由贸易委员会发布关于国际法的待遇即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解释说明后,关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认定问题出现了许多仲裁案件。下面将其中一些较为有代表性的裁决进行梳理。
波普与塔波特诉加拿大(关于损害赔偿)案(Pope v. Canada)*参见Pope v. Canada, UNCITRAL Arbitration, Award in Respect of Damages, May 31, 2002, paras.57-66.。早在2001年NAFTA自由贸易委员会发布解释说明之前,波普与塔波特诉加拿大案就已经作出裁决。而该案的损害赔偿裁决却是在解释说明发布后的2002年作出的。尽管加拿大指出习惯国际法原则被冻结在尼尔案裁决作出的那一刻,仲裁庭只有在其行为是“过分的”或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时才应该作出赔偿,即将尼尔案裁决作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门槛。但是在裁决中,仲裁庭却拒绝了加拿大提出的关于习惯国际法静止的观点,依据的理由有两方面。一方面,作为NAFTA缔约国之一的墨西哥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习惯国际法概念已经演进了。从国际法角度看,习惯国际法是通过国家实践演进的。国际条约构成国家的实践并成为促进习惯国际法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尼尔案所确定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范围已经出现了明显扩展。仲裁庭还进一步指出1989年的艾利托尼加·斯库拉案(Concerning Elettronica Sicula S.P.A.简称“ELSI”)关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表达比尼尔案中的表达要更有说服力,因为其要求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不再是需要暴行的,而仅需要对政府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就可以了。而且,通过援引“适当程序”概念(而不是“政府行为”), ELSI案对评价政府对人们或公司行为的一种动态和负责的标准更加适用于外国投资保护的当代背景。仲裁庭拒绝了加拿大关于习惯国际法内容的争辩,因为它认为这些标准自1926年以来已经演进了。
蒙代夫国际有限公司诉美国案(Mondev International v. United States)*参见Mondev International LT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ward, Case No. ARB(AF)/99/2, October 11, 2002, paras.94-125.。蒙代夫国际有限公司诉美国案的仲裁庭在回答“规定了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的习惯国际法的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其首先否定了加拿大所指出的习惯国际法的内容是由尼尔案裁决确定的观点。仲裁庭认为尼尔案以及其他相类似的案件针对的并不是外国投资待遇,而是外国人的实体安全(physical security)。而且,尼尔案中的特别问题是墨西哥没有对杀死美国市民的武装人员采取有效调查。总之,国家不必为私人的行为本身负责,只有在缺失随后的调查行为时的特定环境下才有可能负国际责任。这样,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将NAFTA中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条款限定在尼尔案所确定的粗暴待遇标准上。第二,上世纪20年代的尼尔案和其他裁决作出时,正值国际法中个人的地位和外国投资的国际保护还远没有得到什么发展的时期。然而,后来国际法上个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经历了相当大的发展。根据这些发展,将外国投资的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全面的保护与安全定义在20世纪20年代适用于外国人实体安全时的含义上是不足为信的。用当代的眼光看,不公平和不公正并不需要满足暴行或过分的要求。更进一步说,一个国家不以恶意为目的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的措施也有可能会是不公平与不公正的。第三,绝大多数双边和区域性投资条约都规定了外国投资的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在仲裁庭看来,这种一致的实践必然会影响到当前国际法中的外国投资待遇规则的内容。仅仅通过尼尔案确定的标准对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是不可思议的。经过分析,仲裁庭最终认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不能限定在1920年代的仲裁裁决所认定的习惯国际法内容上。
ADF 国际公司诉美国案(ADF Group INC.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参见ADF Group INC.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se No. ARB(AF)/00/1, Award, January 9, 2003, paras.46-179.。1998年9月弗吉尼亚交通部发出斯普林菲尔德立体交叉道第2、3期项目建设和交付的投标邀请函。最终雪莉承包公司(Shirley Contracting Corporation)提交了最低的报价,并签订该项目的合同(主合同)。1999年5月19日加拿大一家公司的子公司——ADF国际公司与雪莉承包公司签订了分包合同,约定由ADF国际公司向雪莉公司承建的9(9)桥提供和交付所有结构组件。在随后的生产过程中,ADF国际公司发现美国本地没有充足的设备来生产产品,而请求在加拿大利用ADF国际公司的母公司设备对美国生产的钢材进行特定的加工。弗吉尼亚交通部告知雪莉承包公司ADF国际公司的上述运营方案不符合主合同第102.05节特别条款(“使用国内材料”)的约定和美国《联邦公路管理规章》(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中“购买美国产品”的要求。双方协商无果后,ADF 国际公司向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提出仲裁请求,主张美国的一些要求(如“购买美国产品”)侵犯了其依据NAFTA第11章所享有的权利。其中第1105(1)条的内涵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经过分析,仲裁庭指出美国关于第1105(1)条所指的习惯国际法并没有冻结在过去,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是不断演进的态度非常重要。即在美国看来,自由贸易委员会的解释说明指的是现在存在的习惯国际法。同样重要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接受了美国的这一观点,尽管它们同时都强调了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门槛依然很高。换言之,习惯国际法并不是停留在尼尔案裁决所确定的外国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上,因为习惯国际法和外国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都在不断地发展中。
美林及环林唱片诉加拿大案(Merrill & Ring Forestry v. Canada)*参见Merrill & Ring Forestry L.P. v. Canada, NAFTA/UNCITRAL, (ICSID Administered Case) Award, Mar.31, 2010, paras.204-213.。在美林及环林唱片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认为:国家实践已经越来越少地支持尼尔案所确定的标准,而且,因为缺乏广泛且一致的国家实践以及缺少法律确信来支持习惯国际法规则,所以除了严格限制的个人安全、拒绝司法和正当程序外,在尼尔标准中并没有发现可适用的一般习惯国际法规则。仲裁庭指出习惯国际法不能成为一个裁缝,以不同的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原告,因为如果这样做将会支持一个不被接受的双重标准。最后,仲裁庭得出结论:除了安全原因和正当程序外,现在投资者的习惯国际法最低标准变得比尼尔案及其后继者要宽泛很多。
除了上述案件外,2004年的废物管理公司诉墨西哥案(Waste Management Inc. v. Mexico)*参见Waste Management, Inc.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Number 2”), ICSID Case No.?ARB(AF)/00/3, April 30, 2004, para.92.、加米投资公司诉墨西哥案(GAMI Investments v. Mexico)*参见GAMI Investments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In proceedings pursuant to NAFTA Chapter 11 and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Final Award, November 15, 2004, para.95.、2006年的雷鸟国际博彩公司诉墨西哥案(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v. Mexico)*参见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Corporation v.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in the matter of a NAFTA arbitration under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rbitral Award, January 26, 2006, para.194.等案件的裁决中都主张外国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较于以前已经向前演进了。
(二)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转向的实际效果
关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新发展的实际效果问题,即最低标准是否能有效或成功地限制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问题,有的学者通过对没有约束力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和受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限制的公平与公正待遇在实践中的效果进行分析,指出因为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已经向前演进了,即以前违反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高门槛现在已经演变为不需要那么高了,所以,作为独立条约标准的公平与公正待遇和作为等同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公平与公正待遇实际上是一回事,它们只是名义上的不同罢了。*参见Matthew C. Porterfield,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by Investment Tribunals, http://www.iisd.org/itn/2013/03/22/a-distinction-without-a-difference-the-interpretation-of-fair-and-equitable-treatment-under-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by-investment-tribunals/, 2015-5-19.这样,演进后的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与独立自主的高标准公平与公正待遇形成了重叠。
其实,学者们的上述观点在投资仲裁实践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在安然案(Enron)中,仲裁庭就指出: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是否是添加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之上的问题实质就是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实体内容的问题,无论主张哪一种观点,这一问题的答案实质上可能都是一致的。*参见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 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1/03, Award, May 22, 2007, para. 364.显然,该仲裁庭认为无论在公平与公正待遇和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关系问题上持哪种观点,最终的结果都没有什么不同。又如2006年萨鲁卡案(Saluka)中,仲裁庭关于该问题的观点是:无论成员方关于此问题的争议是什么,在适用具体案件的事实时,条约标准(指的是作为独立自主条约标准的公平与公正待遇)和习惯最低标准之间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表面上的。*参见Saluka Investments BV (The Netherlands) v. Czech Republic,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under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1976, Partial Award, Mar. 17, 2006, para.291.再如CMS案仲裁庭也对公平与公正待遇和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之间的不同做出过分析,仲裁庭认为:这种不同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已经演进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也要求商业环境的稳定性、可预见性以及一致性。*参见CMS Gas Transmission Co.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May 12, 2005, paras. 81-85.
除了上述对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限制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外,有学者经过梳理和总结,指出将保护与安全标准视为高于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独立条约标准和主张保护与安全标准等同于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后者随着近些年来的演进,使得它已经和独立的条约标准具有了相同的效果。*参见Roland Kläger,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arie-Claire Cordonier Segger Markus W Gehring, Andrew Newcombe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orld Investment Law 241,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0, pp. 245-246.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引进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进行限制的做法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以公平与公正待遇为例,首先,“从理论上看,将公平与公正待遇和习惯国际法相连的保护标准比欧盟的独立自主的标准更加尊重政府的权威。”*Matthew C. Porterfield,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by Investment Tribunals, http://www.iisd.org/itn/2013/03/22/a-distinction-without-a-difference-the-interpretation-of-fair-and-equitable-treatment-under-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by-investment-tribunals/, 2015-5-19.其次,有学者也提出这种认为作为独立条约标准的公平与公正待遇和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等同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没有什么区别的观点和做法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做法。“公平与公正待遇和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所包含的要素有重叠部分,这一点已经得到共识。但是,是否公平与公正待遇所包含的要素独立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所包含的要素这一点是不确定的,而这是导致人们对于公平与公正待遇和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之间关系进行争论的重要原因。”*Thomas J. Westcott, Recent Practice on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J.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07, pp. 411-412.而且,尽管有共享的内容,但是外国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仍然被理解和解释为一个与不受限制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相比在责任的门槛上要求更高的标准。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所统计的那样,原告依据这两个不同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类型的成功率有明显的不同。“统计数据显示,原告主张违反NAFTA项下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比违反双边投资条约项下的公平与公正待遇要难很多。在NAFTA项下,公平与公正待遇和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相连,原告的成功率要远低于依据传统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提出主张的成功率。因为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笔者注)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经常被认为是与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不相连的独立自主的标准。”*UNCTA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 Sequel,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http://unctad.org/en/Docs/unctaddiaeia2011d5_en.pdf, pp.61-62, 2015-5-19.
总之,随着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演进,用其对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进行限制与没有限制的而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条约标准的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即从总体上来看,21世纪以来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纳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高水平投资保护标准进行限定的新发展(变化)实质上并不成功。
三、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新发展问题的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飞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从国际投资关系来看,一方面,我国作为投资东道国面临着被诉至仲裁机构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的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也面临受到其他国家的侵害风险。事实上,我国作为被告被诉至ICSID(如2014年韩国中坚建设公司安城住宅产业公司将中国诉至ICSID)以及我国投资者的权益受到其他国家侵害的案件(如2014年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共和国案)已经出现,因此,如何平衡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实际上是我国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参见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具体来讲,现阶段所谓的利益平衡实际上就是要对外国投资者的高水平投资保护进行限制,因为从现行的国际投资法来看,对于投资者的保护不是过低,而是太高了。已经有学者提出我国应该摒弃之前对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片面批判态度,在对外缔结的国际投资条约中适时地引进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来对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进行限制,*参见刘笋:《论投资条约中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6期,第106页。而且我国实际上在近些年来的国际投资条约中的确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在笔者看来,我国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引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高水平投资保护标准进行限制的方法无疑是可取的,是适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但是,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近些年来有关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来看,这一引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新做法并不成功。本文认为,要想真正发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限制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的作用,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仲裁实践中的应对
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上述“困境”与美国遇到的情形极为相似,因此,美国近些年来在投资仲裁中采取的应对措施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上文提到,NAFTA第1105条在仲裁实践中被认定为独立自主的范围宽泛的标准使三缔约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深感担忧。为了限制这种扩大化解释,三缔约国组成的自由贸易委员会于2001年发布了解释说明对NAFTA第1105条进行了严格限制——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等同于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然而三国的这种努力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随后的投资仲裁庭虽然表面上全部遵循了“等同”路径,但是几乎所有的仲裁庭却都通过主张国际最低待遇标准随着时间的发展演进了,从而最终与独立自主的条约标准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美国试图通过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高水平投资保护标准进行限制的计划落空了。针对这种情况,美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通过坚持主张习惯国际法尚停留在尼尔案所确定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上来限制外国投资者的高水平保护标准,从而获得胜诉。
美国坚持主张尼尔标准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件是2009年格拉密斯黄金有限公司诉美国案(Glamis Gold v. America)。*参见Glamis Gold, Lt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ward, June 8, 2009, paras.545-627.在该案中,加拿大的格拉密斯黄金有限公司主张美国违反了NAFTA第1105条的规定,并认为美国试图将第1105条要求限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解释要求上,而不承认国际最低标准的演进性质的主张是不正确的。格拉密斯黄金有限公司指出公平与公正待遇是一个动态的标准,将公平与公正待遇冻结的观点已经被当代的很多仲裁庭所否定。格拉密斯黄金有限公司认为NAFTA中的习惯国际法已经被很多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双边投资条约所影响,双边投资条约的法理证明了习惯国际法的两个根本要素——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并最终形成了习惯国际法上的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
作为抗辩,美国首先指出根据2001年三个缔约国组成的自由贸易委员会所作出关于该条的解释,第1105条规定的依据国际法的公平与公正待遇仅仅指的是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因此,关于该条的争论实际上就变为美国是否违反了习惯国际法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问题。而要确定该问题,就必须对何为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进行界定。接着,美国指出作为习惯国际法的最低待遇标准,其演进当然应该受到习惯国际法变化发展的要件限制。美国认为只有原告举证证明了习惯国际法演进所具备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才能确定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已经演进了或者更具体地说演进到何种程度了。换言之,原告负有证明习惯国际法存在以及美国违反了相关规定的举证责任。显然,格拉密斯黄金有限公司并没有完成这种举证。美国指出国际仲裁庭的裁决并不能构成国家实践,因此当然也就不能证明习惯国际法的出现或发展。美国特别强调了形成习惯国际法的两个构成要素(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其坚持认为一个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最终成为习惯国际法,只能通过国家一致的实践,而且这种实践还得在法律确信的支配下。
仲裁庭经过分析认为原告有义务证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已经演进到要求超过尼尔案中所主张的“令人震惊的”(egregious)标准。尽管原告指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粗暴”的要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尼尔标准适用于当下情形时可能会出现发生在当代令人震惊或异乎寻常的做法并没有达到过去所要求的标准的情形。但是,仲裁庭还是认为这些理由并不能使习惯国际法超出尼尔标准成为必需。其指出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仅仅是一个最低标准。它的作用如同一个“地平线”(floor)或一个绝对的底部,在它之下的行为将不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最终,仲裁庭认为原告并没有完成证明尼尔标准不适用于现在的举证责任,并认为违反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国家行为需要达到“令人震惊的”标准。
显然 ,仲裁庭采纳了作为被告的美国的观点,指出原告要证明习惯国际法演进了,就必须证明习惯国际法形成的两个要素——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而要证明这两个本身就有分歧的要素(尤其是后者)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难度极大,原告败诉命运不可避免。
(二)明确条约中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
除了借鉴美国在投资仲裁实践中的上述经验外,中国也可以通过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来达到限制高水平投资保护标准的作用。具体来讲,可以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或指向,例如可以采用注释的方式对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赋予其明确、可操作的内容,如可以规定:违反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应该达到暴行、恶意、完全的忽略义务,或者政府行为不当且远未达到国际标准,以至于每一个理性的和不偏不倚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种不适当;也可以在条约中直接指出:本条约规定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专指1926年尼尔案所确定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当然,除了采用注释的方式以外,还可以直接在最低待遇条款中明确规定上述内容。
前述两个途径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达到利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限制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的目的,但是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借鉴美国在投资仲裁实践中经验的做法只能作为中国现阶段应对投资仲裁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根本之策,因为该做法毕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过分依赖投资仲裁机构或仲裁员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会使投资仲裁最终的裁决非常不确定。此外,如果仔细分析美国的上述主张以及格拉密斯黄金有限公司案仲裁庭的裁决会发现一些问题:首先,既然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要符合一致的国家实践和基于法律确信而采取的一致行为,而不能通过仲裁裁决来判断习惯国际法的形成,那么很难说尼尔标准是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因为尼尔标准本身就是通过一个裁决确定的;其次,假设尼尔标准在当时被文明国家接受为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那也并不表示世界各国都接受该标准,特别是对处于被殖民或落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第三,再退一步,假设20世纪20年代的尼尔案标准在当时取得了国际共识而被确定为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这也并不能否认后来尤其是二战后广大的新独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该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一致抵制甚至反对。如果说尼尔案标准以前是习惯国际法标准,那么近代以来的国际实践已经表明其形成所要满足的两个要素已经被“抽离”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自20世纪至今,国际关系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变化,这样,习惯国际法必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二战期间以及之后出现的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运动,拥有独立主权的新的发展中国家大量涌现,国家主权理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西方社会文明国家的概念逐渐被主权国家所取代。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对之前所谓的习惯国际法,尤其是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予以强烈地抵制,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的出台,以及以南美洲为代表的卡尔沃主义的盛行,都对之前的所谓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进行了挑战。因此,如果非要说之前存在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话,那也是少数西方国家的“特殊习惯国际法”,而经过二战后的国际实践,这种“特殊习惯国际法”明显受到挑战,而必然出现新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存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尚不明朗。”*Olatokunbo Lad-Ojomo, Wha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Standard and the Minimum Standard of Treatment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http://www.dundee.ac.uk/cepmlp/gateway/files.php?file=cepmlp_car13_79_167622186.pdf, p.14, 2015-5-19.现在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这一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是一个比作为独立自主条约标准的公平与公正待遇门槛要高的标准,即作为独立自主条约标准的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内容要比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宽泛得多。然而,到底宽泛多少,程度如何,具体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等问题尚无明确答案。*参见余劲松:《外资的公平与公正待遇问题研究——由NAFTA的实践产生的几点思考》,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答,那么美国的上述主张以及格拉密斯黄金有限公司案仲裁庭裁决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受到质疑,其对之后类似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先例指导和借鉴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要想真正发挥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限制高水平投资保护标准的作用,或者说要想真正实现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新转变,较为稳妥的方法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或指向。
四、结语
人类进入21世纪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除了“一如既往”地对国民待遇进行限制外,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变化,即其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对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进行限制。这一新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等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国家利益的变化,具体而言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同时具有了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双重身份。过去单方面地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做法已经不适应当代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潮流。而引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高水平投资保护代表性条款——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保护与安全标准条款进行限制是平衡国家与外国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举措。经过上文分析,我们看到引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进行限制的做法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面对这一困境,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在投资仲裁实践中主张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并没有向前演进,而是冻结在尼尔案确定的标准上;同时在对外签订的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或指向。
[责任编辑:许庆坤 吴岩]
Subject:The New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 of Treatment:Expression,Effect and Response
Author & unit:CHEN Zhengjian(Law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China )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 of Treatment (“MS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ational Treatment since its emerg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treatment is to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Apart from continuously limi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the MST has experienced new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began to limit the high level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standar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However, such kind of development was not affirmed b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because of this, the MST did not have good effects in limitation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practically as it should be. Concerning this issue, China can take America’ experience as lessons, and advocate that the MST has not evolved in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t all. That is to say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frozen in the Neer Standard. And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make a clear statement about the cont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MST, when sign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 of treatment; NAFTA;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standard; Neer case
2015-09-16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科研课题《国际投资法制的新发展及中国缔结投资条约的对策研究》(14QD06)的部分成果。
陈正健(1983-),男,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D996
A
1009-8003(2015)06-005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