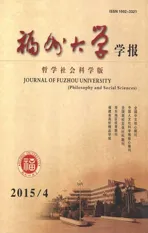基于创新驱动理论的区域发展评价研究
2015-04-16赵静薛强
赵 静 薛 强
(1.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北京 100045;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1)
基于创新驱动理论的区域发展评价研究
赵 静1薛 强2
(1.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北京 100045;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1)
经济发展依靠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其空间载体必然是特定区域。创新驱动的客观表现与特定区域的发展规模、经济质量和持续动力密切相关。而这一实现过程,需要通过量化的指标来衡量,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价。现阶段,评估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特征仍然处在探索阶段,主要采用已有评价经济或者产业发展的方法,突出科技创新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及其实现路径,评价内容集中在创新能力、竞争力和发展绩效。
创新驱动;区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基础
实现对创新驱动的量化评价,需要从其基础理论的角度进一步解读,分析评价指标的统计学特征及其现实意义。现阶段,国际上评价科技创新活动和绩效的方法和体系很多,如全球竞争力报告(GCR)、欧盟创新计分牌(IUS)、全球创新指数(GII)、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STI)、知识经济指数(KEI)、创新能力指数(ICI)等,相对系统地建立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度量方法并开展了具体实践。与此相联系,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基于创新驱动发展判别评价的研究。由于创新驱动的理论表述和实践探索时间较短,对其内涵和实践性的理解仍然存在一定分歧。在研究评价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构建创新驱动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不同角度的分析。一是借鉴相似的评价理念形成评价基本准则,包括卓越绩效模式(Performance Excellence Model)[1]、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特征模型[2]、知识竞争力指数[3],凝练基本的导向理念,进而提出评价标准的设计框架和创新驱动各要素影响值的判别原则。二是针对特定区域的创新驱动评价,基本原则是立足区域的特殊性,突出知识创造、投入产出、创新环境、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特点,采取分层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式,并围绕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三是针对区域内的特定主体进行评价,研究重点是创新型区域内部的某一类资源禀赋和要素主体,由于评价对象相对孤立,因此较为容易确定评价目标和实现途径,比较典型的有科技资源配置、创新型企业等方面的研究。
在创新驱动的区域评价中,产业集群始终是评价热点和主要方向。集群供应链的研究发现在协作博弈的条件下企业可能处于不均衡状态,而对称的协作博弈模型、拒绝博弈理论、演化博弈理论三种方法可能作为打破不均衡状态的路径依赖,为集群供应链的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预测和帕累托优化方法。[4]创意集群通常被视作产业集群的子集,与其他产业使用相同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响应。但是文化领域因其自身的精神因素,本质上又与波特和马歇尔提出的产业集群存在差别,因此文化创意集群的评价要体现文化领域的独特性。[5]关于IT产业集群方面,有学者描述了在IT产业集群的创建、持续发展和成功背后的特征,以定义一个IT产业集群并能够区分它与其他类型产业集群的独特特征。[6]还有学者将产业集群的概念应用于其它领域,如主张在全球或本地采购时增加产业集群分析,进而通过整合概念提出一个新的、差异化的全球采购的方法。[7]
二、评价内容
(一)创新能力评价
区域创新以经济、科技等为外化指标,以各类产业和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为内涵。从评价指标维度上看,狭义范畴是与创新能力直接关联的科技类指标,广义范畴可包括产业类、社会类相关性指标。从评价主体上看,既有对单个主体或要素(如企业、科研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的评价,又拓展至其相互作用机制的创新集聚效应评价。国际上比较经典的模型是库克的二系统模型和拉多塞维克的四要素模型,前者从经济、学习、治理、资本、互动等角度分析了欧洲部分区域创新,提出了知识开发应用和产生扩散的二系统;后者则基于区域创新的不同层次视角,在国家、部门、区域和微观维度,建立了四种要素对区域创新系统相互作用的模型。
创新能力的评价属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问题,按照确权方式,基本分为主观确权和客观确权。前者强调通过主观判断和定性分析为主的方式进行权重赋值,常见的有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等;后者侧重通过客观数据研判形成权重的具体赋值,主要有因子分析法、BP神经网络模型、灰色关联分析法、密切值法、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此外,还包括补偿模糊神经网络算法、BP神经网络和DE算法综合运用、熵值法和TOPSIS法综合使用等。
在评价指标选择和构建的方式上,核心问题是科学、合理圈定评价指标范围,即如何选取、选取哪些指标作为评价的基础。主观方法可以基于不同角度构建多层次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网络视角(创新主体网络、创新支撑网络和创新环境网络)、集群视角(核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集群整体企业技术水平、集群网络创新能力、集群创新环境)、绩效视角(投入产出、经济绩效)等;客观方法可以采用数学降维等。
(二)竞争力评价
关于区域竞争力的解释,目前尚无基本共识性的定义。一方面,可以用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概念来凸显区域竞争中产业要素的作用,而且,集群竞争力也包含科技创新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按照经济外部性的特征,竞争力反映在区域内部各类主体要素通过单独或者共同作用,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力或者影响力,以此形成对外的竞争优势。虽然基本定义上缺乏统一,但是公认比较经典的评价模型是波特的钻石模型,以及Tim Padmore、Harvey Gibson提出的GEM(Groundings Enterprises Markets)模型。[8]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区域的竞争力更多体现在科技创新要素对特定地理空间经济规模和质量的影响与作用上。与传统评价区域竞争力的关注点不同,经典模型强调科技要素的功能和贡献。
在钻石模型应用于区域竞争力评价的过程中,基于企业、生产、需求、相关产业的四要素和政府、机会的两变量,更加注重从评价指标遴选范围上体现科技创新的驱动效应。企业要素中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初创企业,生产要素中增加智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需求要素出现了反映城市化水平、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等指标,相关产业则强调了服务业包括现代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对现有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些新的指标,主要原因是科技创新从原有的潜在、间接驱动竞争力逐渐向明确、直接驱动方向转变,进而显著体现相关新的评价指标上。此外,政府和机会的两变量因素也与财政科技投入、颠覆性技术的潜在变革影响等因素相呼应,从而拓宽了竞争力评价的范畴。
GEM模型。该模型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总结为6个,并根据这6个因素的属性分成了3对。在3对6因素指标体系中,供给因素吸纳了创新要素和基础设施,包括科技型人力资源、金融资源、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结构要素则体现了新技术领域由于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而形成的新企业、新产业特征;需求要素受到市场交易模式和交易空间虚拟化的影响,延展了各类主体需求的范围和表现形式。有许多学者对原有方法进行了改进,主要是在GEM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因素,包括体现资源动员的嵌入性和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竞争关系的GEMN模型、增加产业链要素的C-GEM模型、增加创意因素的GEMC模型、将政府政策和社会环境二因素作为“因素对Ⅳ”——环境加入的GEMS模型等。
(三)发展绩效评价
区域发展绩效的评价主要从竞争力的定性评价发展而来,侧重综合性评价。其理论基础与前述钻石模型、GEM模型相衔接,并拓展至新产业区理论、集群理论等范畴。在创新驱动的视阈下,特定区域基于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绩效,客观表现为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围绕绩效评价的主题,基于投入产出、系统视角等方面,在上述理论基础上,运用DEA、AHP、阈值法等方法,筛选评价指标。实证分析过程中,从规模和效益维度、回归和预测维度、外部和内部维度等,构建了具有创新型特征的评价指标体系。总的来看,区域创新的绩效体现了不同的类别表现特征,如产业的集聚、竞合、投入、产出绩效,集群内部的结构、需求、学习、创新,区域经济的内部实力、外部竞争力,创新驱动的路径、目标、演进、生态系统等,这些都成为不同指标体系建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判断。
在评价方法的优化和改进过程中,平衡记分卡、BP神经网络、绩效棱柱法等成为关注重点。平衡计分卡的基本要素为维度、战略目标、指标、行动计划,关注财务、顾客、内部经营、学习创新等方面,强调区域绩效的预先设定、绩效激励、细化设计指标、反馈和改进完善,突出了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绩效实现过程中的内在激励作用。BP神经网络是在人工神经网络基础上形成的神经元模型,其最大的优势是模拟主观评价过程,获得与评价专家较为接近的评价结果,由于创新型区域绩效评价的研究历史较短,而BP神经网络具有不需要提前获得内在映射关系的特点,因而在样本量能够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模型学习算法反复刺激神经网络,由此实现评价指标的赋权。绩效棱柱法针对利益相关方建立评价体系,计量的起点是创新型区域的利益相关者及其愿景、执行战略,确保在区域范畴内能更好地将价值传递给利益相关者。
三、区域评价研究
此类研究的主要目标比较明确,重点针对特定区域(如省份、城市)进行分析,研究方法上基本是客观条件梳理、问题比较分析、定性设计框架与路径,其优势是研究的针对性很强、实证特征明显、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和实施可行性,但是在定量分析、制度设计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少见。从我国的地区差异角度来看,分别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先发地区或者发达省份。[9][10][11]这类地区的共同特征是经济发展迅速且仍然处在上升期、科技创新的资源禀赋的配置能力较强,特别是江苏苏南、广东珠三角以及部分中心城市基本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后,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且由于内外部条件的约束,只能依赖创新驱动路径来实现;从主要驱动力的选择上看,其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的核心作用,突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式部署,在发展理念、创新环境、舆论氛围、基础要素配置等方面形成了新的思路;从区划范围上看,不仅局限在省份的概念,细化到片区、城市,甚至广东的研究提到了专业镇的实践经验和探索意义。
二是后发地区。[12][13]这类地区在我国的地域面积较大,总体上看是相对东部发达省份比较而言的,其内部各省份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别,相似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其中资源能源的一次产品直接外销相对普遍,即便自身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陕西等少数省份,其科研成果、人才资源也都呈现向外流动的特征,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十分有限。从路径选择上看,其基于后发的特征因而放弃模仿跟踪先发省份原有的发展路径,转为选择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并针对区域内的各自优势如文化优势、政策试点、资源利用等,在新的维度上设计创新驱动路径框架。
三是高新区。这类地区在经济基础相对较弱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实践中,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高新区“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一定意义上说,高新区20多年的实践兼具了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双重特征,因此在新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大环境下,更具有典型代表性。对国家高新区的评价研究,指标选择上主要是基于科技部建立的统计数据体系,评价方式运用了多种有效方法,总体上看是突出高新技术和科技进步的双重属性,特别是如何客观反映科技创新对高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作用。在时间序列上,2001年高新区实施“二次创业”战略,评价主要针对“四位一体”的发展定位,指标体系选择上相对突出这四方面的特征指标,评价结论和对策上也顺应了发展趋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高新区表现出应对危机的独有特点。创新对高新区增长的贡献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拉动效应减退情况下,技术进步对劳动、人才等全要素生产率的带动作用更加凸显。目前,在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下,国家高新区面临着发展战略地位、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层次、资源整合和辐射带动等方面的新困境,需要通过创新评价方式形成新的引导和对策建议。
注释:
[1]崔有祥、胡兴华、廖娟、谢富纪:《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测量评估体系研究》,《科研管理》2013年专刊。
[2]尹德志:《基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13年第3期。
[3]吴宇军、胡树华、代晓晶:《创新型城市创新驱动要素的差异化比较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11年第10期。
[4]Zhou Min,Deng Feiqi,Wu Sai,“Coordination game model of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on cluster supply chains”,Journal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vol.19,no.3(2008),pp.499-506.
[5]Lily Kong,“Beyond Networks and Relations:Towards Rethinking Creative Cluster Theory”,Springer Netherlands,vol.98 (2009),pp.61-75.
[6]Catalin Boja,“IT Clusters as a Special Type of Industrial Clusters”,Informatica Economica,vol.15,no.2(2011).
[7]Claus Steinle,Holger Schiele,“Limits to global sourcing?: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dependency on international suppliers: Cluster theory,resource-based view and case studies”,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vol.14,no.1 (2008),pp.3-14.
[8]Tim Padmore,Hervey Gibson,“Modelling systems of innovation::II.A framework for industrial cluster analysis in regions”,Research Policy,vol.26,no.6(1998),pp.625-641.
[9]洪银兴:《现代化的创新驱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
[10]陈勇星、屠文娟、季萍、杨晶照:《江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对策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2年第20期。
[11]朱桂龙、钟自然:《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广东专业镇发展及其政策取向》,《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2]苏源泉、陈寒凝、孙晓娜:《基于十八大精神的陕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路径研究》,《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3]梁爱文:《基于创新驱动的云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艳林]
F124
A
1002-3321(2015)04-0021-04
2015-01-18
赵 静,女,陕西宝鸡人,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研究员,硕士;
薛 强,男,辽宁沈阳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科技部高新司综合与计划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