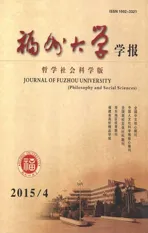朱熹及其弟子的孝道理论与实践
2015-04-16方彦寿
方彦寿
(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福建连江 350506)
朱熹及其弟子的孝道理论与实践
方彦寿
(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福建连江 350506)
在朱熹的影响下,他的弟子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朱子的孝道伦理进行各种不同的研究、解读、充实和传播。其中,着重在孝道实践运用的有陈文蔚和度正,而黄榦、陈淳和真德秀则既重理论研究,也重视孝道在民间的推广;继承朱熹编写童蒙读物的传统来推广孝道,最有成效的应数陈淳。他开启了以近乎童谣式的文学作品来宣传儒学孝道的先河,对涵养儿童的品德和塑造人格有一定作用;他所使用的五言绝句的方式,对晚宋林同、元代郭居敬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孝道伦理;教化实践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精髓的,应推儒家的仁义思想和忠孝理念。历代统治者在提倡忠君的同时,必先褒扬孝道,宣扬“以孝治天下”,从而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
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的孝道理论,及其推行孝道的社会教化与教学实践,对以黄榦、陈淳为代表的一批弟子,和以林同、郭居敬为代表的宋元后学,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朱熹推行孝道的实践与理论
朱熹在尤溪,其父朱松从小就对他进行孝道教育。朱松《五言杂兴七首》之二:
黄香卧讲肆,日芜五亩园;
儿诵声尤雏,未厌咽耳喧。……[1]
就是用东汉孝子“黄香温席”的故事作为教材,尽管年幼的朱熹“诵声尤雏”,却让朱松“未厌咽耳喧”,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朱熹的童蒙塾师史志缺载,已佚其名。他传授给朱熹的教材中就有《孝经》。黄榦《朱文公行状》载:“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通之。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2]李方子《紫阳年谱》也载:“先生幼有异秉,五岁入小学,始诵《孝经》,即了其大意,书八字于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3]朱熹少年时期的启蒙老师刘子翚,字彦冲,其父刘韐死于靖康之难。他“痛愤,哭坟三年。事继母及兄子羽尽孝友。”[4]
(一)朱熹推行孝道的社会实践
受其父辈的影响,朱熹后来无论是在各地讲学,还是作地方官,宣扬孝道,传播孝道之学,既是他推行社会教化的举措,也是其传授给学生的重要必修课。
比如,在江西南康,为把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的思想广泛播向民间,特撰《示俗》并广为公示。文末总评为:
庶人,谓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顺。虽是父母不存,亦须如此,方能保守父母产业,不至破坏,乃为孝顺。若父母生存不能奉养,父母亡殁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载,幽为鬼神所责,明为官法所诛,不可不深戒也。
最后几句尤为精彩:
以上《孝经·庶人章》正文五句,系先圣至圣文宣王所说。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5]
朱熹在此以《孝经》来取代佛经,要求百姓广泛诵读,这就使儒家经典不再仅仅局限于书院、官学的课堂之内,而是广泛迅速地以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向民间传播,这在儒学传播史上,可谓一个创举!
淳熙十年(1183)四月,朱熹在武夷山五曲建成武夷精舍,开始了他长约八年时间的武夷精舍教学和研究的活动。在教学实践中,朱熹感到尚缺小学阶段启蒙教育所需的教材,于是和他的弟子刘清之一起开始编纂《小学》一书。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小学教材。全书六卷,分为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内篇述虞夏商周圣贤之言行,外篇皆述汉以来圣贤之言行。此书刊行之后,数百年来,一直是儒家实行启蒙教育的重要教材。
在此书中,孝道教育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后来被林同采入《孝诗》的舜、闵损、老莱子、伯俞(瑜)、黄香、陆绩、王祥、王裒、庾黔娄、王延、子路、江革等,被郭居敬采入“二十四孝”的虞舜、闵损、老莱子、伯俞、黄香、陆绩、王祥、王裒、唐夫人、庾黔娄、朱寿昌等孝子故事,已先后出现在本书中。其中,收入《小学》内篇“明伦”一章的有虞舜、闵子骞、老莱子和伯俞;收入外篇“嘉言”的有黄香、陆绩和子路;收入外篇“善行”的则有江革、王祥、王裒、唐夫人、庾黔娄和朱寿昌等。
由此可以推断,林同、郭居敬以及其后的“二十四孝”改编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朱熹编纂的《小学》的影响。晚宋时期,此书已被誉为“小学之工程,大学之门户”[6],作为启蒙读物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其中所选的孝子很自然地成了后学编选孝子类图籍的重要参考。
(二)朱熹的孝道理论
1.行仁之本与仁之本:仁与孝的体用关系
孔门弟子有子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有子此问,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孝弟为仁之本”的讨论空间。
朱熹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为仁,犹曰行仁。”[7]认为有子所说的“为仁”,应理解为“行仁”,其本意指的是孝是推行仁道的起始。他引用程颐的话说“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也就是说,“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8]对程颐的“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朱熹认为“此言最切,须仔细看,方知得是解经密察处”[9]。将此“密察处”解读正确,则无本末倒置、体用混淆之虞。朱熹后来在给他的学生解说此段时,反复强调“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发出来底。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论行仁,则孝弟为仁之本。”[10]
2.亲亲、仁民、爱物:行仁自孝弟始
有弟子问,孝弟为仁之本的“仁”是何意?朱熹一再强调说:“这个仁,是爱底意思。行爱自孝弟始。”[11]“论仁,则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则当自孝弟始。”[12]又说:“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亲亲是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时序上,亲亲、仁民、爱物表现为前后三段式,朱熹将其形象地描述为:“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爱物则三坎也。”[13]
在与“四德”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孝弟是行仁之本,义礼智之本皆在此:使其事亲从兄得宜者,行义之本也;事亲从兄有节文者,行礼之本也;知事亲从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14]
因此,朱子重视孝道,认为仁义礼智等德性都是从孝悌之道开始的。孝悌之道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如果不能做到,那么一切的道德原则都是空谈。朱熹在各地讲学,提倡忠孝之道一直是其讲学的重要内容。他在湖南岳麓书院题写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成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人生座右铭,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学子勇猛奋发!
3.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
作为一个教育家,朱熹认为儿童与成人的教育有所不同,应该遵循人的认识规律和教学规律,分阶段有层次地进行。他认为人生八岁,皆入小学,十五岁以后,则是实施大学教育的时期。小学阶段的教育,以“教之以事”为主。他说:
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15]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16]
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古人于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17]
以上几段引文,可以看出,所谓在小学阶段“教之以事”,最主要的就是如何事君、事亲、事父、事长等有关乎孝弟忠信的“事”。朱熹将此总结为“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18]。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19]朱子后来还将此写入他的《家训》之中,仁君忠臣,父慈子孝,构成了朱子对其晚辈居家处世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所谓“孝”,是指子女要对父母要发自内心的爱与尊敬,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父母在世,要侍养,死后要按照礼仪下葬和祭祀。
在朱熹忠孝思想的影响下,他的弟子如黄榦、陈淳、陈文蔚、度正、真德秀等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朱子的孝道伦理进行各种不同的研究和解读,对儒学的孝道伦理进行了充实、推广和传播。
二、朱门弟子的孝道思想
(一)黄榦:入孝出悌,为万善之根本
弟子黄榦,有《孝经本旨》一卷,系受朱熹之意而纂。朱熹编《孝经刊误》之后,本欲再编纂前人所著,可以阐发《孝经》之旨者作为外传,因无暇顾及而委之黄榦。黄榦“辑六经、论、孟于言孝者为一书,厘为二十四篇,名《孝经本旨》”[20]。书成于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由门人陈宓刊行于延平书院。[21]遗憾的是,此书今已不存。
黄榦认为,从道德层面来说,“入孝出悌,为万善之根本”[22],“人之百行,非孝孰先?”[23]一个人从安顿自我的心身,到齐家,到走向社会,实际上往往表现为移孝为忠的过程。所以“处心以忠实,持身以端谨,居家以孝友,施之政者真知体国爱民”[24],既是黄榦对其友人的赞美,其实也是他对学者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从教育实践的层面来说,黄榦早年在受学于朱子之时,就强烈感受到,朱子“其所教人,以孝弟为人道之大端”[25]。什么是道?什么是为人之道?他认为:“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与人交之信,根于吾心之本然,而形见于事,为之当然者皆是也。”[26]也就是说,人子之孝,与君仁、臣敬、父慈和与人交往所必须坚持的诚信一样,都是要植根于每一人的内心之中的本然之德,落实在每一件行动之中当然之理。
为此,他在各地任地方官,奉劝子民行善行孝,“士农工贾,各务本业,起居出入,常存道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亲戚乡党,交相和睦。”[27]
在任地方官断案时,孝道伦理往往也是黄榦断案的重要依据。他在知新淦县时,有兄弟为争母随嫁田的诉讼案件。县民刘下班有三子,长子刘拱辰,系正房郭氏所生;次子刘拱礼、刘拱武系续妾所生。刘家原有户税钱六贯文,又有郭氏随嫁田税钱六贯文。刘下班及郭氏去世后,刘拱辰与其弟分产,只将户税钱六贯文均分,而独占其母之钱。刘拱辰去世后,二弟将其子刘仁谦先后讼于县衙、宪台和帅司。先后六次定断,出现了三种结果:一是不当均分,合全给与拱辰;二是兄弟三人合与均分;三是“合以郭氏六贯文税钱析为两分,拱辰得其一,拱武、拱礼共得其一”。黄榦接到此案后,认为:“以法论之,……自随之产不得别立女户,当随其夫户头,是为夫之产矣。为夫之产则凡为夫之子者皆得均受,岂亲生之子所得独占?以理论之,郭氏之嫁刘下班也,虽有嫡庶之子,自当视为一体,庶生之子既以郭氏为母,生则孝养,死则哀送。与母无异。则郭氏庶生之子犹已子也,岂有郭氏既死之后,拱辰乃得自占其母随嫁之田?”这是黄榦从孝道伦理角度对此案得出结论。通过此案的审理,黄榦认为:“官司理对公事,所以美教化移风俗也,岂有导人以不孝不友,而自以为是哉?”[28]
黄榦的孝道,还表现在他对《西铭》的独特解读上。
北宋理学家张载撰写的《西铭》,可谓千古名篇。众所周知,朱熹是从“理一分殊”的角度来解读。按说黄榦只要固守师说就可以了。但黄榦却说:“《西铭》今看了,三十年来,血脉文理终不能得通贯。”[29]经过长期思考,(开禧)丁卯(1207)夏天,他在三衢舟中思之,豁然有得。他认为:
“乾父坤母,予混然中处”此四句是纲领。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帅、塞,为吾之体、性,言吾所以为天地之子之实。“民吾同胞”至“颠连无告”,言民、物并生天地之间,则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党与,特有差等之殊。吾既为天地之子,则必当全吾之体、养吾之性,爱敬吾之兄弟党与,然后可以为孝,不然则谓之背逆之子。“于时保之”以下,即言人子尽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体、养吾性,爱敬吾兄弟党与之道,尽于此矣。[30]
孝亲是儒学的伦理规范,朱子的《西铭解》强调“理一分殊”和“天人一体”,而罕言孝道。黄榦的解读则于此是一个补正。他认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这四句是纲。讲天地为人之父母,人,则是天地之子。“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阐述的是人之所以为天地之子的理由。从“民吾同胞”至“颠连无告”,讲人、物并生天地之间,同样都是天地之子,但在具体表现上,有差等之殊,即爱有差等。最后,从“于时保之”以下,讲的是人子应尽的孝道,即把人子的孝行扩大为人类的“事天之道”即对天地父母行孝,从而为“孝”注入了神圣性,使“孝”成为信仰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陈淳:孝之“根原”在乎“天理”
陈淳《闲居杂咏》三十二首,以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父子、君臣、夫妇、兄弟等为题,各咏五言绝句一首。其《孝》诗云:
孝以事其亲,斯须不离身;
始终惟爱敬,二者在书绅。[31]
绅,古时士大夫束腰的大带子。书绅,把警句、格言书写在绅带上,时时能看到,从而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言行。《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32]是说子张问怎样才能到处行得通。孔子说:“说话忠诚守信,做事厚道谨慎,即使到了野蛮落后之域也会畅通无阻。如果说话不忠诚实信,做事不厚道谨慎,即使在本乡本土,也很难行得通。站立时,要像这些话就在面前。坐车时,要像这些话就刻在车辕横木上,一言一行,时时不离于忠信、笃敬,这样就处处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自己腰间的大带上。
陈淳这首以《孝》为题的五言诗是说,作为子女,孝敬自己的父母,和自始至终地爱亲敬亲,是时刻不能忘的两件大事,要把它书写在绅带之上,牢记在心,时刻不要忘记。就好像孔子告诫他的弟子要把忠信、笃敬牢记在心,时刻不忘,并落实在行动上一样,陈淳则将此引申到孝道上,强调以孝事亲,要“斯须不离”。
《训儿童八首》是陈淳专为少年儿童撰写的童蒙读物。其中以《曾子》为题,讲的是曾子与《孝经》:“敬谨曾参氏,临深履薄如。平生传圣训,要具《孝经》书。”在《人子》一诗中告诫“人子勤于孝,无时志不存。夜来安寝息,早起问寒暄”[33]。孝亲要落实在每一天,每时每刻,夜息早起嘘寒问暖,和洒扫、应对以及进退起居之中。
陈淳认为,孝的“根原之所自来,皆天之所以命于人,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其道当然,诚自有不容已处”。天下之人,都不可能是“天降而地出,木孕而石产”,都必然是由父母之胞胎而生,这是不可移易的“天理”,所有的人都是不可能“出乎”这个“天理之外”。所以,为人之子,“决然在所当孝,而决不容于不孝。”这是由孝所产生的这个根原即“天理”所决定的。所以,“为人子,止于孝”是“为人道大本,确然终其身,而不可易者”![34]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陈淳认为,“孝弟便是箇仁之实”,是“仁”在父子、在兄弟关系层面的具体道德表现。他说:
大抵性中只有箇仁、义、礼、智四位,万善皆从此而生,此四位实为万善之总括,如忠信、如孝弟等类,皆在万善之中。孝弟便是个仁之实,但到那事亲从兄处,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35]
通过这段描述,陈淳把“孝之根原在乎天理”,这个天理落实到“仁”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孝是仁的一个实在性的表现。
(三)陈文蔚、度正:忠孝为立身之本
陈文蔚和度正,分别是在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从学于朱熹的门人。陈文蔚(1154-1239年),字才卿,号克斋,信州上饶人氏。度正,字周卿,号性善,合州(今属重庆)人。之所以把这两位朱门弟子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孝道观具有某种共性。或者说,从理论上来说,这两位朱门弟子在孝道理论上均无多大建树,其重点在于孝道的实践运用上。
陈文蔚、度正都认为,忠孝乃儒者的立身之本,舍此则难以自立于天地之间。陈文蔚说:“文蔚自幼读书,已知忠孝为立身之本,居家则以事亲,立朝则以事君,舍此二者,无以自立于天地之间。”[36]度正则坚持“入则孝与悌,出则信与忠”[37]。在著名的《克斋揭示》中,陈文蔚解说了忠孝为立身之本的具体表现。他说:
入则孝,出则弟,人之立身莫先于孝弟。盖孝弟为人之本,人之所以戴天履地,而异于物者,以其亲亲长长而有是良心故也。茍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则无以为人矣。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父子君臣,人伦之首,故为人臣子者,事父必以孝,事君必以忠,然不孝则不能忠,忠孝虽二事,事君之忠,实自事父之孝移之耳。为僚而顺其长,居官而治其事,又非自外得,即事兄居家者而推之也。盖长官者,君命之,使长我者也,官事者,君付之,使我任其责者也。为僚而不顺其长,居官而不理其事,皆事君不忠也;事君不忠,皆原于事父不孝也。忠孝立身之大节,于此二者,一有缺焉,则不足以立身。[38]
众所周知,“移孝为忠”是传统孝道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克斋揭示》的意义在于,他把如何移孝为忠,从父子与君臣、兄弟与长上、居家与居官的层面做了一个很具体的阐述。
(四)真德秀:仁孝同源,忠孝与穷理尽性
真德秀是朱子的私淑弟子。他的孝道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学衍义》《西山先生读书记》等书中,内容较为系统。他的孝道思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仁孝同源”“孝弟为仁之本”
真德秀认为:“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39]他在《西山读书记》卷六中,把程朱以来对仁与孝关系的阐述作了一番梳理,强调了仁是性是体,孝是情是用,是仁之一事这一理论成果。
他在阐述曾子的“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和孔子“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40]这一观点时,将人类社会的孝道伦理推广至自然界。实际上就是传统儒学所谓“亲亲、仁民、爱物”,亦即朱熹所说的“仁之三坎”的第三坎的具体阐述。他说:“木不妄伐,兽不妄杀,此仁也,亦孝也。若断之、杀之不以其时,则是无复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耶?武王数纣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无节,是则所谓‘暴殄’也,是则所谓不孝也。物犹如此,况于骨肉之亲、民生之类,其亲之仁之又当何若邪?”[41]
2.知孝行孝与穷理尽性的关系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出处是《易经·说卦》。朱熹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是说《易》,不是说人。诸家皆是借来就人上说,亦通。”[42]又说:“穷理是见,尽性是行,觉得程子是说得快了。如为子知所以孝,为臣知所以忠,此穷理也;为子能孝,为臣能忠,此尽性也。能穷此理,充其性之所有,方谓之‘尽’。”[43]
真德秀借此表述知孝与行孝的关系,提出:“为子知所以孝,为臣知所以忠,此穷理也;为子能孝,为子能忠,此尽性也。能充其性之所有,方是尽性。”其来源还可以追溯到二程“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一说。程颐在《明道行状》说:“不识孝弟何以能尽性至命也?”还说:“后人便将性命别作一般事说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如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44]
3.孝乃爱敬,“心至于是而不迁”
真德秀认为,“孝之为孝,不出爱敬”二字。除了“为人子,止于孝”即孝亲之外,还要“推爱亲之心以爱人,而无所疾恶,推敬亲之心以敬人,而无所慢易”,如此“则天下之人皆在吾爱中矣”。[45]
孟子曾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46]。真德秀据此解释说:“世之言尧舜者,往往失之过高,故孟子直以一言以断之曰:孝弟而已矣。谓之止于是也。夫幼而爱亲、长而敬兄,人性所同,为尧舜者能尽此性而已。”[47]对《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止”字的解读,真德秀解读为“止云者,心至于是而不迁之谓也”[48]。具体落实在孝道上,就是要达到“爱亲敬亲”而坚定不移。
三、结语
在朱熹忠孝思想和推行孝道的社会教化与实践的影响下,他的弟子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朱子的孝道伦理进行各种不同的研究和解读,对儒学的孝道伦理进行了充实、推广和传播。其中,着重在孝道实践运用的有陈文蔚和度正,而黄榦、陈淳和真德秀则既重理论研究,也重视孝道在民间的推广。其中,黄榦和真德秀由于有各地担任地方官的实践,故其孝道实践往往贯彻到他们的政事中;而继承朱熹编写童蒙读物(如《小学》)的传统,来推广孝道最有成效的应数陈淳。他的以《孝》为题的五言诗和《训儿童八首》,开启了以近乎童谣式的文学作品来宣传儒学孝道思想的先河,对涵养儿童的品德、塑造其人格有一定作用;而他所使用的五言绝句的方式,对晚宋福建林同创作《孝诗》,元代郭居敬编纂《二十四孝诗》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1](宋)朱松:《韦斋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2](宋)黄榦:《朱文公行状》,《朱子全书》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34页。
[3][44](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6册,卷三十一,第120页;第705册,卷二,第49页。
[4](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一,《节义考·孝子三》,明万历三十年刻本,第27页。
[5](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5页。
[6](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卷五下,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年,第1072页。
[7][8](宋)朱熹:《论语集注·学而》,《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9][10][11][12][13][14][15][16][17][18][42][4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二十第471、471-472、461、463、463、461页,卷七第124、125、125页,卷十四第252页,卷七十五第1922页,卷七十七第1969页。
[19](宋)朱熹:《朱子遗集》卷四,《朱子全书》第26册,第703页。
[2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十二引《中兴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86页。
[21][22][23][24][25][26][27][28][29][30](宋)黄榦:《勉斋黄文肃公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年谱第845页,卷十七《郑次山怡阁记》第484页,卷三十六《祭朱文之》第736页,卷二十《书赵华文行状》第516页,卷二十《跋陈履道先坟庵额大字》第514页,卷二十四《隆兴府东湖书院讲义》第551页,卷三十七《临川劝谕文》第750页,卷四十《郭氏刘拱礼诉刘仁谦等冒占田产》第785页,卷三《与李敬子司直书》一第339页,卷三十七《西铭说》第747-748页。
[31][33][34](宋)陈淳:《北溪大全集》1168册,卷一第508页、卷三第522-523页、卷五《孝根原》第537-538页。
[32][4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2页、第339页。
[35](宋)陈淳:《忠信》,《北溪字义》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页。
[36](宋)陈文尉:《辞免恩命札子》,《克斋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1册,第45页
[37](宋)度正:《送张伯修省干归省重庆府一首》,《性善堂稿》卷一,第1170册,第154页。
[38](宋)《克斋集》卷七,第1171册,第50页。
[39][41][45][47][48](宋)真德秀撰,朱人求点校:《大学衍义》,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卷六第109页、第109页、第93页、卷五第85页、卷六第89页。
[40]《礼记·祭义》,《礼记注疏》卷四十八,明嘉靖福建刊本《十三经注疏》本。
[责任编辑:余 言]
G129
A
1002-3321(2015)04-0005-06
2014-12-02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5B069)
方彦寿,男,福建福州人,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