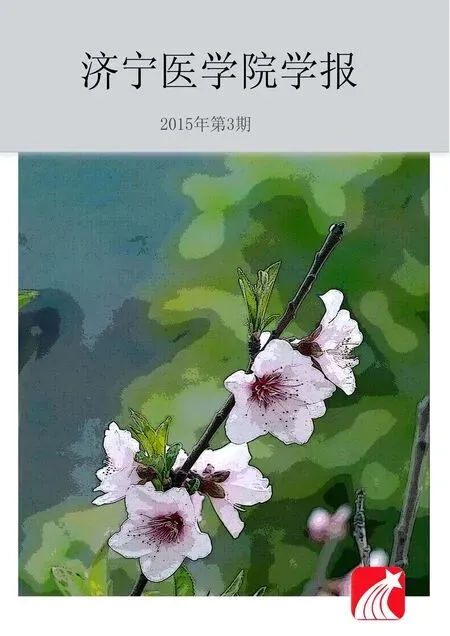电休克抗抑郁机制研究进展
2015-04-15曹龙飞综述李功迎审校
曹龙飞 综述 李功迎 审校
(济宁医学院2012级研究生,山东 济宁272067)
抑郁障碍的发病率、复发率、自杀发生率非常高,是目前全球所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预计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世界最大负担疾病。我国目前抑郁症患病率3%~5%,占疾病总负担的第2位,患者与家属遭受极大的精神痛苦及经济负担。在抑郁症患者中,有15%~20%的患者对药物治疗表现出抵抗性,经历多种抗抑郁药治疗而收效甚微,也称之为难治性抑郁患者[1]。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以下简称ECT)是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首选办法。电休克抗抑郁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多数学者认为电休克抗抑郁疗效机制与脑损害、遗忘、脑神经递质及神经发生有关。本文就近几年有关电休克抗抑郁机制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脑损害机制
ECT问世没多久,关于其疗效机制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一开始有很多学者提出ECT是通过对患者的大脑造成损害而发挥疗效[2-3]。1941年,将ECT从欧洲引入美国的Walter Freeman在他的一篇名为《大脑损害疗法》的文章中就写到“大脑损害的越厉害,精神症状就越可能消失……也许精神病患者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切除部分脑组织来使其思维更清晰”,这个观点在当时被很多学者接受,并且当时从接受ECT治疗后死亡病人的尸检报告中找到了大脑损害的证据,包括神经元细胞的坏死。Allen认为在电休克治疗过程中对大脑的损害有时是可逆的,但大多数是不可逆的。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种观点无论是在接受ECT治疗的患者的脑成像上,还是在多次经过ECT治疗患者死亡后的尸检报告中都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Devanand在脑结构成像、ECT治疗过的病人的尸检、动物电休克癫痫发作(ECS)实验以及血脑屏障破坏实验等方面,详细研究了ECT对大脑的影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ECT不会对大脑结构造成损害[4]。Scalia对一个92岁高龄,在22a的时间里接受过91次ECT治疗的抑郁症患者进行详细研究,包括她的服药历史并采取尸检方式检查了海马体的总形态、海马细胞结构和神经病理学的改变,发现没有病理性的改变可以归因于ECT[5]。最后得出结论:ECT治疗是安全的。Lippman在他个案报道里也提到:一个89岁的女性病人在她26a的双相障碍疾病史中,共接受了超过1250次有记录的ECT治疗,还有800次未经证实的ECT治疗,在她死亡后的脑解剖中发现,她的脑结构的改变无论从宏观结构上,还是从显微镜下,ECT还没有年龄因素对她的大脑所造成的影响大[6]。
因此,ECT对大脑造成的损害,不是ECT产生疗效的主要机制。
2 安慰剂效应
不论是在临床实践中还是在临床试验中,安慰剂效应的存在是一种事实,例如同样的药物,由专家、名医开出的效果会更好,这就是一种安慰剂效应。安慰剂通过心理暗示作用影响病人的心理状态,进而影响机体的生理功能,从而起到积极的治疗作用。在ECT治疗中,安慰剂效应也应该是存在的,但是Hrobjartsson在对130例安慰剂实验(安慰剂包括药物性的,例如一个药片;物理性的,例如一种操作;心理性的,例如谈话)的系统回顾性研究后,得出结论:安慰剂的作用非常有限,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没有必要将其作为一种治疗方式[7]。
因此,安慰剂效应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能完全解释ECT的强大疗效,例如没有求治欲望的不合作的病人,或是丧失希望的重度抑郁的病人,安慰剂效应几乎是不存在的,但ECT对这种病人确实有疗效。
3 心理学机制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抑郁症是内向性的愤怒(inward-turned anger)导致的,而 ECT 对身体造成了惩罚,消缓了这一愤怒,从而发挥了疗效。但是,改良ECT使用了麻醉药物,机体没有受到惩罚,没有满足潜意识对身体惩罚的需要,但同样发挥了疗效,和其观点背道而驰。另一种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认为,被过分压抑的性冲动和“超我”间充满了冲突,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抽搐治疗释放了这一冲突[8],从而达到治疗效果,但是这个理论被肌松剂在ECT中的使用否定了。使用了肌松剂的ECT治疗仍有疗效。
4 “遗忘”机制
在ECT流行的早期,有很多学者认为:ECT治疗所造成的短暂的记忆丧失有可能是ECT疗效的机制,而不把这种认知障碍当作是ECT的副作用。他们认为ECT使患者“忘记了他们的麻烦”。然而,双侧正弦波ECT(bilateral sine wave ECT)所造成的短暂的近记忆丧失更为严重,但是疗效却不理想(现已被淘汰)。相反,在采用简易脉冲式ECT(brief pulse ECT)、右单侧ECT(right unilateral ECT)、超简易脉冲式ECT(ultrabrief pulse ECT)治疗研究中,没有发现严重的认知不良[9-10](cognitive adverse),并且没有发现ECT治愈率和认知不良(短暂的记忆缺失发生率)之间有统计学相关性。
目前国内外统一的意见是这种ECT后记忆的缺失是其副作用,且多在1个月内恢复,而非其机制。糖皮质激素、脂质信号、谷氨酸之间的协同作用可能是造成ECT治疗后认知不良反应(例如短暂的近记忆缺失)的原因[11-14]。
5 生物化学机制
ECT对难治性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完善、有效的方式,在过去的30年里,对啮齿类动物、灵长类动物以及人类自身进行的大量电休克实验都表明:ECT对抑郁症患者的神经内分泌的影响,可能是其发挥疗效的机制。
5.1 五羟色胺(5-HT)
国外有文献报道ECT同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5-HT去甲肾上腺素(NE)再摄取抑制剂(SNRI)一样能增强5-HT和NE的生理作用[15],国内学者对病人电休克治疗前15min及治疗后5、15、30、45、60、90min后的病人采血送检,发现5-HT浓度迅速升高,5min时达到峰值,然后逐渐消减,60min后基本恢复正常[16]。动物实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对大鼠给予ECS后的短时间内,多动反应增强(5-HT引起)。
这似乎说明ECT是通过增加5-HT的生理作用而发挥疗效,反过来又支持了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单胺假说”。这个假说认为:由于某些未知的致病过程,如应激或某些药物,导致5-HT或(和)NE的耗竭,因此导致抑郁症的发病。
5.2 NE
Sehildkraut发现ECT可增加NE的含量,从而减轻了植物神经症状,其疗效与NE的血浓度是一致的。另一些研究者发现对用利血平治疗的大白鼠做ECT后,NE合成增加。他们认为如果抑郁症是由于NE缺乏,ECT的作用可能是使突触后肾上腺素能受体敏感性增加。这一研究同样支持“单胺假说”。
5.3 催乳素(PRL)
ECT后PRL的变化是目前最公认的发现之一。许多研究者在实验中都观察到ECT后血清PRL水平显著增高。Baperia在对33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ECT治疗中发现在治疗后15min时PRL最大量为正常水平的3倍,并且其高峰浓度随ECT次数的增加而下降,与疗效呈负相关。而接受感觉丧失控制试验的患者血清PRL没有明显改变。研究者认为ECT发作引起PRL增高,可能反映了下丘脑刺激程度。PRL是一种垂体前叶分泌的激素,它的分泌活动受到丘脑下部多巴胺(DA)神经元的控制,丘脑下部DA含量增多,则PRL的分泌减少。反之,DA减少时,PRL分泌却增多。因此,末次ECT后PRL释放显著减少是由于ECT引起突触后DA受体敏感性增加导致了PRL的抑制。
Swartz等对比双侧ECT与单侧ECT后催乳素的水平。结果发现,双侧ECT发作后PRL水平显著高于单侧ECT。他们认为这提示双侧ECT对下丘脑的刺激作用大于单侧ECT,也解释了双侧ECT对抑郁症患者治疗效果更优于单侧ECT的原因。
关于抑郁症和PRL分泌失调的研究很多,但结论不一。例如,有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对芬氟拉明、氯米帕明和L-色氨酸刺激的PRL分泌反应迟钝,但对5-HT的反应则增强。患者ECT后引起的PRL水平增高在抗抑郁治疗中应该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5.4 DA
由于血浆中DA的含量甚微,难以测定ECT后DA的水平,故研究者多采用间接性观察。因而一些结果相互冲突。
一些研究者发现ECT能提高DA增效剂阿朴吗啡的效应,并且ECT也可以改善对左旋多巴无效的帕金森氏病人的锥体外系症状。他们认为ECT可能引起突触后多巴胺受体的敏感性增加。Reches等在对鼠大脑的研究中发现多次ECT治疗,使阿朴吗啡效应增加,引起多巴胺合成受抑制,从而使黑质纹状体和中脑边缘DA通路中的自我受体产生超敏感性变化,故认为ECT引起DA释放过程中突触前自我抑制的敏感性增加。国外有研究报道ECT能增强多巴胺的效应[1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应在SSRIs和SNRI里几乎是没有的,这是否是ECT相比抗抑郁药物疗效更显著、快捷的原因呢?目前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5 促甲状腺素(TSH)
Baperia等在研究中观察到ECT治疗后30min时TSH达最高水平,明显超出正常值,其最高水平比PRL晚15min,并且随ECT次数的增加,TSH水平逐渐减少。他解释为DA能够抑制TSH分泌,ECT可引起突触后DA受体功能增加,导致TSH释放受抑制。如只采用感觉缺失,则TSH水平无改变。其表明了ECT的特殊作用。
另一些研究者在实验中观察到ECT治疗后TSH虽有增加但不显著,大多在正常范围内。Whallcy等认为TSH根本没有增加。
我们知道在典型的抑郁患者中,尽管甲状腺激素的值没有受到影响,但静脉注射TRH导致的TSH反应变得迟钝。另外,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甲状腺功能状态能够影响其对治疗的反应,甲状腺素浓度的升高能够增加抗抑郁药的疗效,我们有理由相信,ECT对TRH的影响应该是其抗抑郁机制的一个方面。
5.6 其它神经内分泌
研究者发现ECT后皮质醇水平也有增加,并随ECT次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其所测得语言学习结果与最大量皮质醇水平呈负相关,提示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中枢单胺氧化酶受体的功能变化。Misiaszek等在研究中发现ECT后有76%抑郁症患者血清各β-内啡肽免疫反应增加,这种增加是短暂的,20min内平均下降9pg/ml,48h后转为正常。其意义尚不清楚。Saekeim等观察到ECT有显著的抗抽搐作用,故认为这一作用是ECT引起γ-氨基丁酸(GABA)介质的增加有关。
此外,国内外还有很多文献报道ECT后其它神经递质或内分泌的改变,例如ACTH、白细胞介素、环氧化酶、谷氨酸等。总之,ECT对大脑神经内分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哪种影响起决定性作用,现在仍未可知。
6 神经可塑性机制
最近几年,对抑郁症病人进行的研究可以看出,抗抑郁药能提高海马的神经可塑性[18-19]。在大样本的动物实验中已经证实,ECT是海马神经可塑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诱因[20-21]。最近的研究显示ECT,在海马神经元形成以及神经元树突分支形成上有剂量相关效应[22-23],也就是说ECT所使用的电量越大,有利的神经组织改变就越大。这部分解释了病人在可耐受的范围内,为什么电量越大,治疗效果越好的原因。
当然ECT对神经可塑性的影响研究最多的还是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在灵长类和啮齿类动物中,ECT的刺激会使大脑结构性发生改变,改变主要集中于齿状回亚粒状区域不成熟的前体细胞,通过ECT刺激,这些区域不断形成新的神经元,并且新形成的神经元迁移到颗粒细胞层并使得突触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此外,Shors等发现,ECT对啮齿类动物神经再生及海马依赖性记忆也有重要作用,这表明ECT可能对神经再生有关的区域细胞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随后的研究表明,ECT可以增加海马中新形成的神经元增殖,并且这些增殖的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再生密切相关。此外,重复的ECT刺激还可以进一步增加CA1区锥休神经元和海马颗粒细胞中树突密度的重新分布[24]。ECT的抗抑郁作用与树突的重塑和突触功能的影响之间有密切的关联。
许多研究发现在海马和前额皮质中会出现神经元结构性的变化,包括神经元的缺失和皮质中胶质细胞的减少[2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大体结构上某种改变被发现,还可能会出现许多微小的结构的变化,而这些微小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突触效应的相应改变。研究发现,尤其是长期的,重复的ECT刺激会使突触可塑性发生改变,从而使ECT对突触可塑性产生一定的影响。ECT可以诱导CA3区海马锥体神经元尖端树突萎缩[26],伴随的是空间学习记忆方面出现特定的认知损害。ECT剌激可以使苔藓纤维与CA3细胞紧密接触,使得突触小泡出现重新分布,伴随的是堆积密度的增加和总的突触小泡数量下降大约40%。这种突触传递变化的功能性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因为有关突触传递的情况在动物实验中没有记录。然而,这些发现表明ECT诱导的突触变化局限在突触前和突触后结构中,表明长时间的突触结构的变化或许与观察到的突触强度的改变有关。
目前,关于ECT对突触超微结构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很少。通常人们认为,仅有一次的ECT刺激可以使海马中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的表达出现短暂的下调,而长期的、重复的ECT刺激可以使得BDNF的表达上调。Pozzo-Miller等发现,敲除BDNF的杂合子大鼠在CA1区海马中,用高频刺激后突触之间的传递更容易疲劳,而这表明神经递质的释放出现了损害。这可能与突触之间传递的突触小泡数量减少密切相关,也分别与小突触泡蛋白和突触素之间的突触表达下调有关。因此,BDNF似乎直接与突触前末梢蛋白的调控有关,这与突触传递的长期和短期调控相一致。研究发现ECT可以增加CA1区突触小泡的数量和突触结合蛋白、突触素和小突触泡蛋白的表达[27]。
苔藓纤维的萌芽与ECT密切相关,ECT后海马齿状回细胞中,苔藓纤维轴突的萌芽与ECT刺激某一区域神经元功能的长期适应有关[28]。在BDNF基因敲出的杂合子大鼠中,ECT诱导的萌芽是逐步衰减的。这一结果表明神经营养因子在苔藓纤维的萌芽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然而,在分析这些数据时,发现混合注入BDNF的大鼠体内不会影响苔藓纤维的萌芽[29-30]。在大脑中苔藓纤维的萌芽,BDNF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由于BDNF可以迅速影响树突的萌芽和皮质锥体神经元的形态学改变,就像可以增强海马神经元的轴突萌芽一样,BDNF对苔藓纤维萌芽的影响是重要的[31]。
在动物实验中,更引人注目的是ECT抑制了杏仁核的兴奋性神经突触以及减少了树突分支[32-33]。考虑到杏仁核在产生负性情绪方面所起的重要性(尤其是焦虑和恐惧),这个发现直接在神经生物学上为ECT在改善情绪方面的作用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持。也就是说,ECT凭借着减少杏仁核的异常反应,从而达到治疗抑郁症的目的。
7 小结
目前,关于ECT抗抑郁疗效的具体治疗机制尚未阐明。正是因为ECT对大脑的影响过于复杂,ECT抗抑郁疗效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由多种机制共同参与。单一的研究一种疗效机制可能是错误的。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很有可能是2个或2个以上的机制同时在起作用。当然,电休克动物模型还是我们研究ECT治疗机制时首选的方法,最根本的治疗机制研究还是使用电休克动物模型进行,如可以通过基因敲除小鼠或是通过化学药剂干预使一种疗效机制不起作用,逐个机制的进行研究。
对于ECT治疗机制的研究是必要的。首先,探明ECT治疗机制会改进ECT治疗技术,或许幸运的话,还可以研发新的药物。其次,探明ECT疗效机制也能使那些对ECT治疗持怀疑态度的病人宽心。最后,我们对ECT治疗机制的研究也是一个对抑郁症再认识的过程。进一步的认识抑郁症,消除人们对抑郁症的偏见也是一个精神科大夫应尽的义务。
[1] Little A.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J].Am Fam Physician,2009,80(2):167-172.
[2] Read J,Bentall R.The effectiveness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a literature review[J].Epidemiol Psychiatr Soc,2014,19(3):333-347.
[3] Fosse R,Read J.Electroconvulsive treatment:hypotheses about mechanisms of action[J].Frontiers in Psychiatry,2013,4:94-95.
[4] Devanand D P,Dwork A J,Hutchinson E R,et al.Does ECT alter brain structure[J].Am J Psychiatry,1994,151:957-970.
[5] Scalia J,Lisanby S H,Dwork A J,et al.Neuropathologic examination after 91ECT treatments in a 92-year-old woman with late-onset depression[J].J ECT,2007,23:96-98.
[6] Lippman S,Manshadi M,Wehry M,et al.1,250electroconvulsive treatments without evidence of brain injury[J].Br J Psychiatry,1985,147:203-204.
[7] Hrobjartsson A,Gotzsche P C.Is the placebo powerless?An analysis of clinical trials comparing placebo with no treatment[J].N Engl J Med,2013,344:1594-1602.
[8] Sackeim H A.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do not throw out the baby[J].J ECT,2014,30(3):177-186.
[9] Sackeim H A,Prudic J,Devanand D P,et al.Effects of stimulus intensity and electrode placement on the ef cacy and cognitive effects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J].N Engl J Med,2013,328:839-846.
[10]Sienaert P,Vansteelandt K,Demyttenaere K,et al.Randomized comparison of ultra-brief bifrontal and unilateral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major depression:cognitive side-effects[J].J Affect Disord,2014,122:60-67.
[11]Nagaraja N,Andrade C,Sudha S,et al.Glucocorticoid mechanisms may contribute to ECT-induced retrograde amnesia[J].Psychopharmacology(Berl),2014,190:73-80.
[12]Andrade C,Singh N M,Thyagarajan S,et al.Possible glutamatergic and lipid signalling mechanisms in ECT-induced retrograde amnesia: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involvement of COX-2,and review of literature[J].J Psychiatr Res,2014,42:837-850.
[13]Andrade C,Thyagarajan S,Singh N M,et al.Celecoxib as an in vivo probe of cyclooxygenase-2mechanisms underlying retrograde amnesia in an animal model of ECT[J].J Neural Transm,2013,115:1063-1070.
[14]Andrade C,Shaikh S A,Narayan L,et al.Administration of a selective glucocorticoid antagonist attenuates electroconvulsive shock-induced retrograde amnesia[J].J Neural Transm,2013,119:337-344.
[15]Lanzenberger R.Neurotransmitters and ECT[J].J ECT,2014,30:116-121.
[16]赵学鼎,李恒芬,张志华,等 电抽搐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5-HT及 MAO的影响[J].中原精神医学杂志,1995,1(1):15-16.
[17]Kellner C H.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in Parkinson’s disease:ECS and dopamine enhancement[J].J ECT,2014,30:122-124.
[18]Pittenger C,Duman R S.Stress,depression,and neuroplasticity:a convergence of mechanisms[J].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13,33:88-109.
[19]Andrade C,Rao N S.How antidepressant drugs act:aprimer on neuroplasticity as the eventual mediator of antidepressant ef cacy[J].Indian J Psychiatry,2014,52:378-386.
[20]Bouckaert F,Sienaert P,Obbels J,et al.ECT:its brain enabling effects.A review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induced structural brain plasticity[J].J ECT,2014,30:143-151.
[21]Chen F,Madsen T M,Wegener G,et al.Repeated electrocon-vulsive seizures increase the total number of synapses in adult male rat hippocampus[J].Eur Neuropsychopharmacol,2013,19:329-338.
[22]Smitha JSM,Roopa R,Khaleel N,et al.Images in ECT:ECS dose-dependently increases dendritic arborization in the CA1 region of the rat hippocampus[J].J ECT,2013,29:156-157.
[23]Smitha JSM,Roopa R,Sagar BKC,et al.Images in ECT:ECS dose-dependently increases cell proliferation in the subgranular region of the rat hippocampus[J].J ECT In Press,2014,76(9):25-27.
[24]Nobler M S,Sackeim H A.Neurobiological correlates of the cognitive side effects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J].J Ect,2013,24:40-45.
[25]Lorena Rami-Gonzalez,Miquel Bernardo,Teresa Boget,et al.Subtypes of memory dysfunction associated with ECTxharacteristics and neurobiological bases[J].The Jouranal of ECT,2014,17:129-135.
[26]Bouckaert F,Sienaert P,Obbels J,et al ECT:its brain enabling effects:a review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induced structural brain plasticity[J].J ECT,2014,30(2):143-151.
[27]Schmidt H D,Duman R S.The role of neurotrophic factors in adult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antidepressant treatments and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ve-like behavior[J].Behav Pharmacol,2013,18:391-418.
[28]Zheng X,Zhang X,Wang G.Treat the brain and treat the periphery:Toward a holistic approach to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Drug Discov Today,2014,68:512-517.
[29]Juergen Dukart,Francesca Regen,Ferath Kherif.Electroconvulsive therpy-induced brain plasticity determines therapeutic outcome in mood disorders[J].PNAS,2014,21(1):1156-1161.
[30]Fabbri C,Crisafulli C,Gurwitz D,et al.Neuronal cell adhesion genes and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in three independent samples[J].Pharmacogenomics J,2015,4(4):149-150.
[31]Viswanath B,Harihara SN,Nahar A,et al.Battery for ECT Related Cognitive Deficits (B4ECT-ReCoDe):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Asian J Psychiatr,2013,6(3):243-248.
[32]Khaleel N,Roopa R,Sagar BKC,et al.Images in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pilot impressions suggesting that ECT reduces excitatory synapses in the basolateral amygdala[J].Indian J Psychiatry,2013,55:204-205.
[33]Khaleel N,Roopa R,Smitha JSM,et al.Images in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 attenuates dendritic arborisation in the basolateral amygdala[J].J ECT,2013,29:156-157.